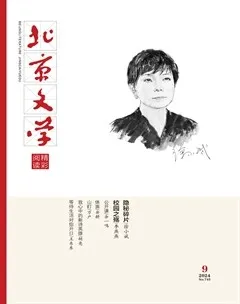蜀道苍茫
我想,古蜀道看似只是莽莽蜀山中一条瘦削的线,但这条线却是苍茫而幽邃的,有时光的显性与隐秘。显隐之间,那些于其上走过的身影,清晰如昨,又缥缈如烟……
——题记
1
蜀道苍茫,一路向北。
出成都市区,至广汉,我与一条名为“鸭子河”的河流相遇。鸭子河,古称马脚河、雁江或金雁河,发源于龙门山脉太子峰南麓,是长江之重要支流沱江的支流。
“鸭子河”从五千年的时光深处流出,流到广汉三星堆遗址,穿越古蜀国的城垣,又被远古蜀人唤作“洛水”,古蜀人傍洛水而居,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蜀中秋晚。洛水两岸,蒲草还保持着盛夏时的碧绿,夹杂其间的芦花已开始迎风飘洒,摇荡着亘古旷远的苍茫之气。几只白鹤在“鸭子河”上空抖开白亮亮的翅膀。叶发千年,花飞花散。河上戏水的鸭子、岸边汲水的古人杳不可寻,蒲草、芦花、白鹤是否依然是它们祖先的模样?
在三星堆遗址,游客散空的博物馆一片沉默。这里,曾经矗立过一座占地面积达十二平方公里的古城。这里,曾有七万古蜀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流过三星堆遗址的洛水,曾流出婚姻,流出子孙,流出稼穑,流出水稻,流出梦与花朵。洛水,润泽过古蜀人的肌肤,支撑过他们的骨头。五千年后的初秋,洛水之滨,三星堆在我的眼睛里复活了。
洛水上游不远处的高架桥上,两列银白色的动车呼啸着驶来,又呼啸着远去。它们在洛水上交错,带来秦巴山脉那边中原的气息,也带去三星堆、洛水、几只白鹤和一河芦花的传说。
更远处,广汉市区高楼接云摩天。新时代的蜀人与古蜀先民相傍而居。历史与新生,开掘与传承。洛水畔,古邑边,芳草碧云天,故事绚烂了这片厚土,也必将继续绚烂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蜀道上,三星堆博物馆内已发掘及深藏地下的文物是静止的,静止的背后,涌动穿越千年的生命气息。三星堆博物馆外广袤的平原上,一切鲜活,千年以后,它们又将静止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
2
公元263年,蜀道在阴平(今甘肃文县)裂开一道分支。这条分支,就是“阴平道”。
江油,“阴平道”之终点,背倚龙门山。翻过摩天岭,就是阴平道的北端起点——阴平。说来如此简单,其间的艰辛,大概只有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国大将邓艾才知道。可以说,魏蜀两国长达三十五年的对峙、拉锯至江油而终结,历史的拐点就出现在蜀道上的“旁门左道”——阴平小道。蜀汉两代军事领导人诸葛亮、姜维苦心经营几十载的剑门天险在邓艾的奇袭下瞬间成为摆设。一将功成万骨枯,邓艾部从阴平出发,抵达江油城时,大军只剩下不足两千人马。僵局就这样被勇敢打破,死棋就这样被奇计盘活。邓艾的突进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与孤勇。
说江油,于右任口中“才华九州横”的李白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我去往大匡山中的江油青莲镇,访李白故里。“岷山雄奇,逶迤北来,至天宝而结穴。涪盘交汇,奔腾南去,夹平芜以成气。紫柏之瑞气环绕庭前,匡团之秀色常盈襟袖。”匡,即大匡山。
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怀抱理想,出蜀远游。世事沧桑,人生无常。谁知,李白与故乡的第一次分别即成永别,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选择再不返乡,大概只是因为李白不愿家乡人看见自己落魄潦倒的模样吧。公元759年,为官路绝,心如死灰的李白开始最后一次漫游天下。最后的日子里,他“迥出江山上,观空天地间”,开始一步步归向他来时的天界——“仙子乘云驾马远,掉头一去别人间。”
薄暮冥冥,我从“李白故里”景区出来。回望,白玉石的李白雕像在醇蓝的天幕下,愈发清逸俊秀,一轮淡月不知何时已斜挂天空。我不止一次假设李白依然生活在今天,他的那些出口诗篇,他的那“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自信与狂傲是否会被误判为非主流的怪异?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能给予他学识与人格的尊严?
3
车至剑阁县,先前还只是微涛般略有起伏的浅丘突兀拔起,座座山峰之朝北处陡然下跌,像被天神的巨斧一板砍去了一半,丹霞地貌的山,血淋淋露着肉与骨头。
抵达剑门关景区。大剑山在左,小剑山在右,如两头雄狮蹲踞。大小剑山之间,峡谷深达百米,谷中乱石嶙峋,溪水奔腾。仰头望,大剑山垂直拔起,山体寸草不附。因背阴,山呈现出不真实的暗红色,红中带黑,铁一般冷峻。
登顶大剑山最高峰,只听得秋蝉在林间无休止鸣唱,其声嘈杂,就像剑门关内外几千年的厮杀声一直不曾消失。只见得天空中乱云纠缠,石壁巍巍,奇峰突兀,远方,山林屏列,座座皆如摩天利剑,剑锋所指,正是广袤的汉中平原。
过“一线天”,头顶云遮雾锁,天空瘦成一条苍茫白线。“石笋峰”,紧邻大剑山主体,却与主体保持了一米左右的距离。亿万年来,比人类先于这群山间穿过的是流水,是风。是它们,一点一点恒久地冲刷吹拂,才将“石笋峰”与大剑山隔开来,又一点点塑造出“石笋峰”一柱擎天的威武外观。只有时间才掌握了消亡与新生的密码。
突然,剑门关关楼似兀地跳出来,陡立在我的眼前。天空阔朗,古风浩荡。关那边,仿佛暗伏着甲兵万千,顿觉一阵带着锋利金属的血气扑面而来,给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压迫。剑门关就像一位战无不胜的将军,在这样一个从未被从正面(由北向南)攻破过的巨人面前,一种渺小感、臣服感油然而生。我拾级而上的脚步变得缓慢。每走一步,我都驻足四望,我隐约感觉大小剑山上数不清的石头、滚木、飞矢早已对准了我。
站立城门洞,穿越峡谷的风在洞口骤成一股,突然变烈。不是一股,是一股接着一股,似千军万马冲出来。这就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的剑门关!登上关楼,群山在望,眼底长安。我仿佛看见,诸葛亮和他的继任者姜维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中原,那里,有他们耗尽毕生心血却未能抵达的终点。
事实上,剑门关作为进攻桥头堡的动力,在蜀汉后期已明显衰减,它唯一的存在价值只是给孱弱而内忧外患的刘禅政权续命而已。剑门关固若金汤,剑门关也命似蛛弦。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如此真实地得以证验。
“难于上青天”的金牛古道上,邓艾用孤勇绕出一个大弯。历史并不总按某种设定按部就班演进,如一张紧绷的布帛,韬略与胆识是两把利刃,布帛裂开,剑门关,这个无敌巨人轰然倒下了。清溪垂泪,一个王朝旋即崩解。谷风呜咽,大一统的西晋就这样把剑门关和蜀汉政权踩在了脚下。
一处天险,总得附着上人的勇毅,才有其更浓酽厚重的底色。回望剑门关,遗迹惊人魄。忆烽烟弥漫,看古道蜿蜒,千年沧桑,一朝感叹。
4
剑门关外,就是绵延百里的翠云廊古蜀道。
翠云廊古蜀道始建于秦。“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大兴土木,彼时,蜀山砍伐殆尽。为平民怨,乃命人在金牛古道两旁植树。
翠霭共烟霞同辉,古柏与蜀道并行。放飞无人机俯瞰,翠云廊如一条苍龙在大地上奔跑,其尾朝向西南之成都,其头伸往西北之秦岭。行于廊间,蝉的嘶鸣波涛般汹涌,有乌鸦间或发出一两声怪音,低哑、沉闷。空无一人的翠云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气氛,轻薄而幽深,明朗而寂静。
古柏堪称三国文化的精神图腾,譬如我面前的这株——它苍翠遒劲,高大挺拔,粗壮上指,颇似史书和演义里的张飞形象,人们称其为“张飞柏”,让人不由得惊叹造化之神奇。诚然,这些树的命名大概率只是后人依据史书中的典故和树的造型而进行的对号入座式的穿凿,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树依然是千年前的它们。今人只见古时树,今树曾经见古人。一棵古树,比今天的我们更清楚历史的细节,也更懂得时间的长久与永恒。时隔千年,棵棵翠柏干虽龟裂,枝却错乱,叶也蓬勃,树庞杂的根系早已扎入时光与沃土深处,悄无声息地吮息着大地之养。
翠云匝地,古道通幽。古往今来,翠云廊上走过凯旋的将军,走过贬谪的官吏,走过旅人游子,走过绿林草莽,走过避难的皇帝,也走过潦倒的诗人。很难说,途经翠云廊的杜甫抵达成都武侯祠写《蜀相》“锦官城外柏森森”时,脑海里没有叠加他在翠云廊见过的古柏的影子;“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苏轼一生三次出川,其中两次踏上翠云廊金牛蜀道,走在这条路上的苏轼,是否预判过他未来的命运就跟他脚下的蜀道一样曲折凶险?
有些无底的谜语只能尘封。站立古树下,一个疑问在我脑海里冒出来:这些古树在千年时光中何以能躲过雷电风暴,躲过战火兵荒?古柏旁的一株树苗给出了答案。它还是那么脆弱,以致植树者不得不给它罩上一圈竹篾做的铠甲,以抵挡风袭和兽啃。看见它,我就看见了那些古树千年前的影子,也看见了这株树苗千年后拔土冲天苍翠一方的希望。
5
水,也是蜀道上极难逾越的天堑。
秦巴山脉自北而南延伸到川北,地形复杂,山体横亘,奇峰突起,峻岭相连,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只有嘉陵江以不灭的斗志,历亿万年岁月,把秦巴山冲开一道缺口,顽强扑向巴蜀大地。这大自然的杰作,就是古蜀道上闻名遐迩的明月峡。
伴随着中华历史长河一路走来的明月峡古栈道,经历过江山易主,见证过王朝更替,在兵火战乱中几次毁坏,几经修复,满身疮痍,又重负前行。明月峡古栈道,先秦建成,三国繁忙,至唐宋而兴盛,又于宋末毁坏,后元代修复,终在清初因“三藩战乱”被废弃。
“路出沙河,一径峭壁”,指的就是嘉陵江上的明月峡古栈道。岑参入蜀,作《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述见闻——“栈道笼迅湍,行人贯层崖。岩倾劣通马,石窄难容车”;袁枚江舟荡过明月峡,作《朝天峡》(即明月峡)——“滩转峡角来,双峙袤千丈。”曾经的明月峡古栈道,在倾斜山坡上凿孔架梁,其下利用斜坡造孔或平台置柱托梁,梁上铺木板。翻修后的新栈道,足有两米宽。人行其上,再也没了“仅能旋肘,莫并两肩”的险恶。古栈道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当年固定过木桩的孔洞等距离排列在绝壁上,那些硕大的柱孔就像历史的眼睛,深邃,邈远。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栈道虽好走了,那山却依然是令人惊悚的。山就在我的面前,垂直向上,不,甚至是悬在我的头顶,似乎随时都要倒压下来,顿觉石裂怒欲落,畏压不敢仰。
暴雨初霁,江水从峡口那边奔涌而来,发轫于秦岭深山的嘉陵江浑黄、浓酽。江中乱石穿空,或暴露水面,或潜伏成礁。由是观之,当年水上行舟之险,不输陆地栈道。栈道上方,老川陕公路(原108国道)成了明月峡景区的观光车车道。当年,为保障前方抗日,数十万筑路军民生生在绝壁半腰凿出了一条宽4至5米、长864米的半隧道,形成了著名的“老虎嘴”奇观。我眼前的“老虎嘴”通体赤黄,造型狰狞,似一只猛虎,已张开血盆大口,正欲将路过的行人、车辆一口吞咽。
江对岸,秦岭山脉和龙门山脉对撞积压,秦岭向南翘起,龙门山向北凸出,二者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人类地质史上的又一奇观——明月峡背峡。不时,有“和谐号”列车从江那边的山洞里哐哐冒出来,又钻进下一个山洞,那是我国历史上连通西北与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宝成铁路。
蜀道存兴废,明月照古今。每一种蜀道的迭代,都付出了血与汗的代价。历史在明月峡留下了六条道路——山间小道、岸壁栈道、江边纤夫道、江中木船航道、川陕公路道、宝成铁路道。这六条道路忠实反映了蜀地交通发展的面貌,也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些蜀道,或诞生于原住民生存的需求,或开凿于攻伐中原的梦想,或拓宽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局。
蜀道悠悠,岁月悠悠。何止“六道”?金牛蜀道旁,“新108国道”与“京昆高速”公路并驾齐驱。“西成高铁”穿蜀山,过秦岭,曾经需要数天才能走完的古蜀道,如今只需两个小时,更不用说,还有从成都飞往西安的客机,以科技的力量,生生把空中蜀道掰成了一条几乎笔直的线。蜀道,可以被狭义定义,也可以被广义理解。出蜀之道,皆为蜀道。东西南北,巴蜀大地条条大道通世界。让蜀道不再难,在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变成了现实。
6
我从蜀地的核心成都出发,试图完整走完蜀道,但丛莽榛榛,很多古老的蜀道今天已无法穿越。离开古蜀道,我的汽车在全新的高速蜀道上奔驰,一幕幕诡诈的、忠勇的、豪迈的、忧愤的故事如幻灯片,在我的脑海一一闪现。我想,古蜀道看似只是莽莽蜀山中一条瘦削的线,但这条线却是苍茫而幽邃的,有时光的显性与隐秘。显隐之间,那些于其上走过的身影,清晰如昨,又缥缈如烟。而正在其上走着的我们和将要走过的后来人,又正在或将要书写怎样的新蜀道故事?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