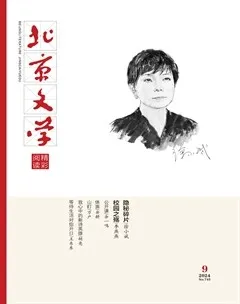山盯
这是一篇极具反转色彩,同时具有悬疑甚至恐怖色彩的小说。一对旅行路上刚认识不久的“情侣”,租车去沙漠中旅行,而女主人公在此过程中始终是谜一样的存在,她究竟有怎样的隐秘?
一
她只让梁昊叫她Jade。
到喀什已过中午,他们吃了烤包子和馕坑肉,囫囵吞咽下对方的基本信息,就去她订好的酒店办理入住。这是古城附近唯一的五星级酒店。景观大床房。她像是笃定能在火车上找到“旅游搭子”似的,像一颗成熟的果子,笃定能不偏不倚地砸中正巧口渴的人。
梁昊紧紧攥着行李箱,不自主地瞄向Jade。她眼角的一颗小痣,让她格外地美。仿佛是这颗痣,让他们即将要做的事情更添了几分美丽的罪恶。当他们的目光意外触到,她只是抿了抿嘴唇,默默把头低下。梁昊转身,透过观光玻璃鸟瞰喀什古城的全景。他们像乘着热气球上升,那些层叠矮楼,徐徐摊开一张泛黄的卷轴,连空气都在阳光里晕眩。
进了房间,梁昊帮她脱下外套,她却忽然说,你得稍微等我一会儿。梁昊说,怎么了?Jade说要处理个公司的文件。半小时吧,最多一个小时。你可以先洗个澡,休息一会儿。累了吧。梁昊有些不知所措,但嘴上还是说没问题,我也要你处理一个文件。他把体检报告发给了她。她点开瞥了一眼,笑了笑说,没关系,我相信你。光a63aad25888034ff4215b88761c89f21是听着她说话,梁昊就已经不得不后倾髋部,把身体微微屈拢起来。他坐到床边,期待着她能再说些什么。
Jade也在办公桌前坐下,打开电脑,像是刚反应过来,说,噢,但是我没有准备。准备什么?梁昊故意这么说。体检报告,她说。梁昊顿了f3d90efb221dada1fc367c516c6db831一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他们确实没有必要再向对方证明什么。一切只是出于道德。而道德这个词,用在他们两人身上又太奇怪了。像在烈日下一眨眼就会蒸发的水滴。
沉默了一会儿,为了缓解尴尬,梁昊起身,从行李箱翻出一个早先备好的普拉达纸袋。他把纸袋放到Jade面前,她愣住了。梁昊轻声说,见面礼。她笑着道谢。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奢侈品是信任。她已经给过他了。
洗过澡,梁昊赤裸着身体,在落地窗前静静地鸟瞰古城。正午尤其强烈的阳光,让原本沙黄色的城墙和建筑呈现出一种麦秆,甚至是趋近向日葵的金色。有几个孩子在狭窄的街道间踢球。梁昊发现她的颈前折射着阳光。Jade已经把项链戴上了。他终于按捺不住,俯身吻了一下她的脸颊。她的身体一紧,给了他一个浅浅的对抗的力。别急,她说,再等我一会儿。不好意思。别急。她又朝向电脑,锁住眉头。
她食言了,超时了几分钟。但梁昊等得心甘情愿。
那面沾满水滴和雾气的玻璃浅浅映出她的丰腴身体,像颜料未干的油画。Jade从画里走出,站在床边,吹了十多分钟头发。她的眉头是慢慢解开的,仿佛是慢慢从遥远的上海回到了此时此地,慢慢变回了自己。
他们的第一次是愉快的,像互相拆开一份心仪已久的礼物。那份激情透支着二人,罔顾他们只是在十几个小时前刚偶遇在一节通往疆域尽头的车厢。
蹊跷的是,她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让梁昊摘下了将二人的肉体阻隔的橡胶套,她竟然允许,甚至是强迫梁昊——留在她的体内。这让梁昊的身体产生了极细微的本能抗拒,但服从下来后,弥留在他的脊椎间的,只有难以言喻的满足的空白。
“我吃了三四年优思明了,别担心。”她是这样说的。
梁昊把她压在身下,手指在她仍有些湿润的卷发末梢打转。梁昊当然知道优思明,一款短效避孕药。他压制住他的喜出望外,也尽力隐藏着莫须有的猜疑。他只是心血来潮地问起她的真名。她喘着粗气,说,Jade,我叫Jade。很高兴认识你,她说,把窗帘拉开。
窗外是烈日,一张过曝的相片,标记他们的第一次照面。干燥的古城是一件巨大的、龟裂的、用他们的身体捏制的土陶。一群白鸽飞进蓝天,很快不见。远处有若隐若现的雪山。
出门已经是傍晚六点。
Jade告诉梁昊,喀什有至少三个小时的时差,天要到很晚才黑。多晚?不知道。十一点?梁昊不信。他们在古城边上的烧烤摊坐下时,夕阳带他们望见了看起来很矮的山。墨绿的,昏黄的,靛蓝的。那些雪山几乎正在融化。直到这时,梁昊都还不信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他甚至怀疑她调晚了他的手表。这女人像是有什么魔力似的。但那夕阳的确很美。她很喜欢身上租来拍照的民族服饰。
梁昊告诉她喜欢就留着,押金不要了。
她的眼神里闪现着一种满足,似乎不是因为金钱和漂亮衣裳,而是为了那份越出轨道的激情。梁昊呆呆地看着沿街店铺,招牌陆续亮起了汉字和陌生的维吾尔语文字。他忽然意识到有风吹拂在他的脸上。喀什的风。这已经是春天了。
他问起她后面几天的行程。
她说,我包了一辆车,我们去看雪山和沙漠。
他说这里像土耳其。她只是说,这儿像埃及。
二
起初,Jade说司机要迟到一小时,梁昊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回味着昨夜Jade乘在他身上的场景。她占据了所有主导权,从她的体内释放出的那个人,似乎连她自己都会感到陌生。又是一次性的姿势,又一次清空全部狂热。但梁昊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性。趁她在卫生间化妆的时候,他偷偷翻了她的包。他的确发现了一板优思明。淡黄色的药片也的确少了一颗。他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了。
她直到拔掉房卡才肯合上电脑。远远望见司机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呀,司机居然这么帅。梁昊的反应却是,这是我们的车?搞错了吧。
停在酒店门口的,是一辆崭新的兰德酷路泽。
“你知道这什么车吗?”梁昊说。
“不知道啊,”Jade说,“我选了最贵的,宽敞。”
司机摘下墨镜,扒住车门向他们招手的样子,简直像个皮肤黝黑的模特。
不管以哪种审美标准,那张脸都无疑是英俊的:眼窝深陷,眉宇刀削,两颊蓄着络腮胡,看起来在三十五岁左右。他的身高与梁昊相当,却比他魁梧许多,肩膀和大臂把纯黑色T恤撑满,小臂间旺盛的绒毛宛如沙棘。
梁昊更感兴趣的,其实是他那条卡其色的战术裤。在不知某年某欧美明星带起潮流之前,他大概只在战争片或者枪战游戏里看到过这样的裤子:两个鼓囊的口袋,膝盖上有护垫,裤脚扎进一双看起来厚重如船的大靴子。
没办法忽略的是,他的腰间,还别着一副深红色的牛皮刀鞘。
梁昊很难相信这等造型的男人,能安全地走在喀什街头。大概是个时髦的汉子;那把刀,大概率也只是件唬人的工艺品。上车之后,Jade很快替梁昊抛出了疑问。
“刀,刀还有假的?”那汉子说。
司机把小刀抽出,向后座亮出铓刃。刀身是黑色的。它的刃口更暗,或者说更亮,那种色泽,一般人是难以分别的。像一道深渊的裂口,能照出模糊的人脸。可Jade的脸上丝毫没有防备或恐惧,她甚至想试试刀的锋利程度。他们的司机并没有乍看上去的难以接近,小刀在他手中像是支铅笔似的掉转了首尾,雕刻有精致老鹰纹饰的刀柄被贡到Jade面前。
这是什么刀?她问。她看起来完全被吸引了。梁昊扯开问,怎么称呼,师傅?男人把墨镜架上额头,皱起眉,盯住梁昊说,随便叫我什么都行,就叫师傅吧。然后,他睥睨向Jade,挑了个眉,说,这是英吉沙小刀。
“英吉沙小刀……有意思,那我们就叫你英吉沙吧。好吗,英吉沙?”Jade说。
司机无奈地笑了笑,说,你要怎么叫都行。
梁昊趁抚刀柄时偷摸了一下Jade的手。刀柄磨损得很厉害,但梁昊意外地对那材质感到熟悉。他想起他爸有过类似的收藏。大概是某种大型动物的骨头。但梁昊没有向英吉沙确认。Jade握住小刀,对着梁昊眼前的空气缓慢地做了几遍切割动作。
梁昊问,黑钢?轴承钢?英吉沙又回过头来,说,哎,没想到,你还挺懂行。梁昊看了眼Jade,但她正专心地埋头欣赏小刀。不过,英吉沙说,我这把不是。梁昊说,那是什么钢?英吉沙把车点起了火,说,这个,哼,这个不能说。收起来吧,刀可不长眼睛的。去塔县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望山跑死马。
女人向梁昊使了个眼色,带着天真和一丝惊惶。梁昊收回她手里的刀,递还给了它的主人。透过墨镜,梁昊和英吉沙的眼神再次短暂地交错了两秒钟。他的眼神也很像是那把刀柄的质感。
望山跑死马。他们会一点一点靠近眺望过的山脉,然后灵巧绕过它们,从喀什古城去往帕米尔高原。当那些山突然降临到眼前的时候,像极了一群沉默巍峨的使徒。
梁昊迷恋那种压迫感,甚至有隐约病态。他竟能从中获得快感。但Jade却说,那些山体有些怪异,她随意抛出了一些胡乱荒诞的比喻。其中有一个是说,裸露的山岩像人脸。她还耐心地指出哪里是嘴、鼻子、耳朵,哪里是眼睛。梁昊隐约察觉出她摆着一种故作的轻松姿态。他说不上为什么。
在白沙湖边拍照的时候,Jade连续挂断了两个电话。她本来想着和牦牛合影,但一下子没了心情。等她上车,回过去电话,梁昊才知道是她母亲打来的。电话那头,似乎对此次出行并不知情。但她们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吵起来的。梁昊没有听清细节。应该说是Jade没有让他听清。
她最后说的话是:“我有数了,侬不要讲了。我有问题,好了吧。我有问题。”
Jade在电话里吵完了架,英吉沙问,你们是上海人?说这话时,他的双手短暂地离开了方向盘。她没有答应,反而问起了梁昊,哎,你是哪里人?梁昊说他是无锡的。
英吉沙惊讶道,你们难道不是一对吗?
他大概也从后视镜看到了,这一路,她那对雪白的腿始终都挂在梁昊的身上。上山路骤降的气温和白沙湖边成团纷飞的小虫,已经在她的腿上留下了淡红色的印子。
Jade的表情有些微妙,似乎还没有从争吵中缓过来,她说,一对什么?随便哪两个人都是一对。英吉沙说,还能是什么,一对情侣嘛。情侣?她重复了一遍,算是吧。她看了眼梁昊,说,算吗?英吉沙笑道,还要问他吗?梁昊打趣说,她是我姐姐。
司机回过头打量了一眼他们,随手拨弄了一下车挂件,“出入平安”晃荡起来。英吉沙说,呵呵,骗我,我不信。你们真有趣。她说,你也很有趣。你有女朋友吗?或者,老婆?Jade问得很无所谓,说出“老婆”时又像是在嘲笑什么。英吉沙笑着说,你觉得呢,姐姐?
他没有口音,但那低沉粗犷的声音很怪,仿佛它并不是从那颗石头似的喉结里发出来的。
三
也许是因为坐在左侧,Jade注意到了英吉沙耳后的文身:那是一种陌生文字。她好奇是什么意思。英吉沙笑着说,瞎文的,文身师没理解我的意思。梁昊说,所以原来想文什么。英吉沙说,命。Jade和梁昊都沉默了。
我以前练过一段时间达瓦孜,英吉沙解释说。Jade和梁昊都不知道什么是达瓦孜。就是走钢丝,走吊索。她问,真的?有安全措施吗?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她无意间看了一眼梁昊。没有的,英吉沙说完,很快把话锋一转,喂,你们来喀什后可吃过烤包子了?Jade说吃过了。英吉沙指了指副驾座位,这里有几个烤包子,早上买的,你们饿了可以吃。等会儿上雪山,最好吃点高热量的……这三天的路线,平台可告诉你们了?
没有,你自由发挥吧。Jade说。
英吉沙说,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些未开发的景区,但你们不能告诉平台。如果同意就去,就放在第三天。最后一站。
听了这话,Jade很高兴地坐起来,抱住主驾驶的头枕,手几乎碰到了英吉沙的耳朵,说,好啊,去那种无人区,怎么样?英吉沙不说话。她又淡淡地自言自语道,这儿有无人区吗?英吉沙依然没有回答。她摇下了车窗,静静地看山和天。梁昊穿过Jade披散的头发,主动去摸了一下她的后颈。她有些受惊地望了梁昊一眼,然后微蜷了点身,靠在了他的身上。
这种地方不能多待,她说。梁昊问为什么。她说,待多了就不想回去了。梁昊说,那就不回去了。Jade只是笑笑不说话。风太大了,吹乱了她的头发。梁昊让她把车窗关起来。但她不想。
车窗是英吉沙从驾驶座拨上的。车内很快安静下来。
女人忽然说,我也有一个文身。
两个男人静得出奇。梁昊看遍了她露出来的皮肤,最后只是盯着她的眼睛。仿佛那个文身在她的眼里。按理说,不该让梁昊来猜的:他们已经做过两次爱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熟悉了她的身体。印象中,她的身体是无瑕的。
一个汉字,她继续说,你俩猜一下吧。英吉沙回过头,放缓车速,久久地盯着女人而不看路,问,在哪里?Jade说,不告诉你,反正你看不到。英吉沙说,几个笔画?她思考了一会儿,说五笔之内。包括五笔吗?梁昊问。她又顿了一下,摇了摇头。一到四笔,她说,猜到有奖励。等我睡醒公布答案。
她趴在他的腿上睡了一觉。她包里的手机振个不停,梁昊帮她调成了飞行模式。可奇怪的是,手机振动的声音还在持续着。是从车前座的支架上传来的。梁昊发现,是英吉沙的手机来电,但被他接连挂断。
一路上,他和英吉沙无话可说。梁昊很快就看厌了外面那些大山。车速渐渐快起来,那些山依旧岿然,沿着窗穷追不舍。
Jade醒来后先看了手机。她有些责怪梁昊的自作主张,但还是开玩笑地说,我要是丢了工作,你负责啊。梁昊说这不是放假吗?她没反应,只是自顾自回着消息。到休息区,她说要去厕所。
望着女人的背影,英吉沙给梁昊递上一支新疆的雪莲烟,主动搭起了话。
“她说的那个文身……”
梁昊以为他想到了那个藏在Jade身体里的字。
“是不是文在那边?那女人的确有股骚劲。嗯?”
VXSzh+uaRsk4uZFsMnZUpqOcNHxsNroQgvXFDgiCT6k= 梁昊怔住了。他没想到这司机会说出这般粗鄙、失礼的话。
但不等梁昊反驳,英吉沙接着说:“但我可以告诉你,那娘儿们骗了你。”
“什么?”
“她在骗你。你没发现?”英吉沙笑着抹了一下鼻子,把烟吐在了梁昊的脸上。
“骗我什么?”梁昊已近乎不适了,他暗暗地往后挪了一小步,用余光打量四周。这鬼地方空旷得让人紧张,四周弥漫着沙尘。远处,有一队羊正穿过公路。
哪怕不愿意,他还是看到了英吉沙腰间,那个深红色的刀鞘。
“我不知道。但我看你们……就像看羊一样。没有什么逃得过我的眼睛。那女人一定有什么事情骗了你。”英吉沙说着掐灭了烟。他盯着梁昊,忽然就笑了起来,眼角挤出几缕粗糙的皱纹。他把手搭在梁昊的肩上,梁昊努力绷着身体没有后缩。他的手很硬,穿着外套也能感受得到。
“来旅游的,放松点。”英吉沙用手背拍了拍梁昊的胸口,“喂,你猜到那个字了吗?要我猜,我猜是……我猜是‘干’。哎,‘日’是几笔?”
Jade是快半小时后才回来的。她重重地关上车门,说,为什么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有信号。梁昊不知道她什么意思。看见她脸上的水还没有干,他说,你不怕把防晒霜给洗掉了。女人沉默不语。她打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但只是把相机当镜子照了一会儿。梁昊偷瞄到她的手机桌面上,有好几个学习英语单词的软件。
车开出一阵,Jade发了会儿呆,最终还是打开手机,按住微信语音键说,我看过了,这part是Catherine负责的。但很快向上一推,把说过的话撤销了。我现在在新疆旅游……说了一半也撤销了。最后,她软软地说,晚上,我闭眼前发给你,可以吗?说完,她锁了屏幕,转头发现梁昊正看着她。工作这么忙,梁昊说。女人的眼神像雪一样融化了。
一路上,她都没有再提起文身的事。
到冰川脚下,她开门,竟只是从行李箱拿出了电脑和一件厚衣服,很快坐回了车里。她把衣服盖在腿上,摇下车窗,对梁昊说,你上去吧,我不想去了,有点累。梁昊实在不解,但不想去违背她的意愿。
当他犹豫着该不该走的时候,女人第一次喊了他的名字。梁昊,她说,不好意思啊,你玩得开心点。梁昊点了点头,看见英吉沙摸了很久开关,才终于把座驾放倒。Jade避着坐到右边。戴我的墨镜吧,英吉沙对梁昊说,当心雪盲。梁昊拒绝了他。
徒步上山需要一个半小时。梁昊租了匹马。即便是假期,来这里的游客也并不多,两个人中就会有一个带着氧气瓶。他在山坡上看到很多垒起来的石堆,人们通过这种方式祈福。上山的整个过程都格外安静,梁昊在心里默默掂量着。他有些后悔,不该把Jade独自留在英吉沙的车上。
到山顶,他对着一面巨大的冰块发呆。旁边一块牌子说,这里是慕古塔格冰川,海拔4688米。这些冰冷、坚固的水体从远古时代就屹立于此。梁昊本以为自己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可雪反射着所有阳光,的确让他有些睁不开眼。他从纪念品店给她带回了一张明信片。
四
到塔县,他们住到一家骆驼主题的民宿。那些北欧风格的小木房之间,散养着四五头半死不活的骆驼。骆驼匍匐在角落休息,像几堆小沙丘;有人经过时,会齐齐地转过头来,虽然头顶的毛发遮住了它们的眼睛。
英吉沙吃不惯民宿老板准备的牦牛肉火锅,独自在一边吃了些凉透的烤包子。英吉沙提醒他们小心,那些骆驼比想象的凶猛。他还说,如果是遇见野生骆驼的尸体,千万不要靠近。梁昊并不问他为什么。而Jade一脸天真地说,竟然还有野生的骆驼。说出这话后她自己都笑了。她疲惫的眼神很快温驯下来。
这个夜晚,Jade的一举一动都满含歉意。她觉得白天扫了梁昊的兴。梁昊问起工作的事,她只是苦笑说,不归我管了。梁昊不知该怎么安慰,只是静静看着她卸下衣物。她腰间到臀部的弧度,几乎像一滴剔透的水珠。她的背部纯白如雪。梁昊依然找不到那个字。
梁昊说,你是不是在骗我。
Jade猛地转过头,眼神盈满乞求。
什么?她说。
梁昊说,文身。
Jade不语,又转过身,背对梁昊,屈膝蹲下,把蓬松如野草的长发笼络,撸成马尾交给男人,像是递上一扎花束。梁昊握住她的头发,终于看清了她后颈的文身。
“不。”梁昊说。
“不。”她说。
夜晚休息的间隙,梁昊想看会儿电视,却发现遥控是坏的。
但他没有告诉她,只是提议一起看会儿手机。起初,Jade说手机有什么好看的,但当梁昊提出他们可以交换手机看时,她忽然就有了兴致。她的表情告诉梁昊,她是喜欢这样的游戏的。在交出手机之前,女人敏捷地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操作完毕,Jade像一只被溺爱的宠物狗般夺走了梁昊的手机。
“哦——你还有置顶啊,‘可爱女人’是谁?”
她果然打开了微信。梁昊说,那是我妈。Jade迅速翻阅了梁昊的好友列表,接连询问都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八卦。她扫兴地刷起了梁昊的朋友圈。
“没劲,”Jade说,“你套路我,没劲。”
梁昊没有打开她的社交软件,只是随手点开了抖音。视频里很快蹦出几只小猫。Jade可能不会知道,他一点也不想打听她的花边新闻。他是真的想了解这个女人。
他打开了她的淘宝,她最近买了些进口的药品和补剂;不只是学英语的应用,连会议软件都有六七个;有个叫“蜗牛睡眠”的App,记录了她的平均睡眠时长只有不到五个小时。他甚至上网,看了她点赞过的视频。画面里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堵着镜头疯狂进食,吃得浓厚的妆容都花开了。
而Jade只是皱着眉,手指不停划着梁昊的手机屏幕。她的眼睛忽然眯起来,两颊露出可掬的笑,梁昊猜她想到了,是应该翻翻看相册。那里只有白天的山景。她会看到那块巨大的蓝色的冰。探索秘密的过程中,她仍不忘往自己的手机瞥上几眼,像是随时准备反悔。
梁昊最后点开了她的备忘录。他不确定有没有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因为她喊着“不好玩”夺回了手机,也还回了他的手机。但那两个字的确是扎眼的。
他不敢确定。
他不确定是不是“备孕”两个字。那个标题就在“喀什游玩攻略”的下面一列。像是一个注脚似的。
Jade按下锁屏,把手机压在了枕头下面。她盯着梁昊的眼睛,却迟迟没有开口。梁昊觉得自己得说些什么。
他问起她对英吉沙的看法。
“你不怕他吗?”
女人用手撑着下巴说:“怕?为什么要怕他。他挺帅的。”
“他有刀。”梁昊说,“挺神秘的。不是吗?”
Jade笑了笑说:“可这是在新疆。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而且我学过女子防身术哦。无限制格斗,听说过吗?哼哼——哎呀,你放心啦,我从正规平台找的司机,都有执照的。”
“你不要太相信陌生人了。”他纠结着,该不该向她坦明英吉沙的恶意。但他不想因此毁了她的旅程。他觉得她是期待那些风景的。她需要它们。她需要一次完美的旅行。她太疲惫了。他努力地想让她和自己都轻松一些。
他不断安慰着自己刚才是眼花了。
“你也是陌生人。”Jade转了个身,仰在梁昊的肚子上,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说,“那我应该怕你吗?”梁昊没办法回答。
夜深了。梁昊在半醒间感到,她已经不在他的怀里了。她抱着膝盖,蜷缩在靠墙角的床头。梁昊没有开灯,安静地过去抱她。她推开了梁昊,似乎在黑暗里微微摇头。他坐到床沿,借着屋外暗弱的灯光,摸出一根烟抽了起来。她也要了一支。火光照出了她脸上的泪痕,晶莹得像一层糖霜。
二人静坐,把烟抽得很慢。已经是凌晨三四点。
“上一次谈恋爱什么时候?”他问。
“刚毕业那会儿吧。工作后就没那个闲心了。”
“在上海一个人住吗?”
“嗯。”
梁昊起身点了灯,说:“如果有个人陪,会不会好一点?”
“哪方面好一点?”
“各方面。”
她好像真的考虑了一会儿,最后说:“不会的。”
“那现在呢?”
“现在?现在挺好的。”
梁昊沉默了很久。他用烟头把烟灰缸里的灰刮了个干净。
等到她打出哈欠,他才肯把他真正想的说出口。
“我们以后可以多出去走走。”
这时,女人第二次叫出了他的名字。她说:“没有以后了,梁昊。不是吗?”但她似乎很快就发觉把话说绝了,又说,“别想那些了。这样我也可以不去想。如果你真的想要……安慰我的话。”
说完后,她起身去拿桌上的包和纯净水。
“我忘记吃药了。”她朝着卫生间走去。
梁昊呆呆地看着门边的窗户。他有点恍惚,一时间分不清自己是在哪里。他想了很久才确定,自己是和一个陌生女人在喀什。他愿意相信备忘录里的那两个字是幻觉了。
他有点出神,直到淡紫色的窗帘背后,突然闪过一面黑影。
他神经一紧。那不是幻觉。梁昊回看了一眼卫生间,很快又盯了回来。可以确定窗是关着的。他慢慢起身,蹑着手脚靠近窗户,他很快在眼前描摹出了假想敌的暗红色模样。他发现自己的腿不听使唤,抖个不停。那影子还在窗后。勇气是在一瞬间莫名其妙涌上来的,他猛地拉开了窗帘。
眼前的景象,把他结实地吓了一跳。
Jade听见叫喊,从卫生间匆忙出来,伴随着虚弱的冲水声。
“怎么了?”
她看到梁昊手里捏着一尊尤其干净的烟灰缸。烟蒂都掉在地上,像被砍落的两截手指。
“啊,没什么,”梁昊说,“骆驼。骆驼醒了。”
他提起窗帘,骆驼的脸隔着玻璃,幽幽地浮出了黑夜。
五
后来的一整天,梁昊都跟丢了魂似的。
他没什么心思看沙漠了。尽管连绵起伏的沙丘的确像极了一群卧倒的裸女。那些胴体拥有无与伦比的曲线。在风中放荡,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她们的形状。而在沙丘间行走是困难的,那些低密度的地貌会把人的脚步吞下去。沙子太细密了。梁昊回头看,沙地之间没有脚印,只是像水面那样浮起几个浅浅的漩涡。
从始至终,梁昊想的都是前一天晚上民宿那个坏掉的遥控器,还有那个没有完全坏掉的抽水马桶。
他在那摊死水中发现了两颗淡黄色的药丸。
他摁了很久冲水按钮,才制造出一个小小的漩涡:很显然,她没有。梁昊没有选择当即和她对峙。那时她已经睡了,睡得很浅。她有一条手机消息,提醒她的电子宠物小猫需要喂食。
坐在后座,梁昊私藏着这个秘密,像怀着一捆引线已经受潮的炸药。他有意用冷淡的态度回应女人的话题。她很快意识到了梁昊的反常。他们的手再也没有碰到过一起。英吉沙似乎也注意到两人出了问题,关掉了车内的音响,不时吹起口哨。车内的气氛变得不太对劲。
沿途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的车辆。山在很远的地方站住。两边的沙漠像那些山彻底崩碎后的样子。梁昊没有注意女人是从哪一次下车后,坐回到了副驾驶。她也对窗外的景色失去了兴趣,又一次向英吉沙索要了他的刀,开始低头把玩。
回程的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被封锁了。由于绕行,英吉沙说他迷了路。梁昊怀疑他是故意的,但只是在后座自顾自看着手机。手机信号变得很差,导航也不管用了。女人却因此显得亢奋,有时把车窗全部摇下,把头探出去看成片的沙棘林和核桃树,有时细细抚摸着那把英吉沙小刀的全身。
车跑了很久,才到一个牧场。这时太阳已经悬在山顶。英吉沙下车,走到一群羊中间,远远地向一个老牧民招手。梁昊和她依然在车内静坐。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Jade说。
“知道什么?”
“优思明的事情。”
“嗯。”
“嗯。”她重复了他的语气。
“为什么?我搞不懂你为……”
这时,英吉沙开门,坐回了驾驶座,他很快点起火,说:“走错了,又走错了。”
梁昊以为Jade会暂时搁置他们的话题,但她还是接着说:“你放心。万一,我是说万一我怀了孕,不需要你负任何责任。你放心,我不是来讹你的。”梁昊期待过她的歉意,也想象过她会用下一秒就摔门离去的语气说出这话,但她却平静得像是个局外人,甚至笑了出来。她把小刀还给了英吉沙。英吉沙的嘴微张着,像含着一颗酸涩的杏子。他向后座的梁昊瞟了一眼,轻笑道:“别担心……你们没这么走运。”没有人再说话了。
回到塔县,天已经完全黑了。
是Jade提议喝点酒。那就喝吧。也许现在他和她需要的正是酒精。但在酒桌上,梁昊感到他们的角色悄悄发生了反转:似乎,英吉沙和女人才是来旅行的一对,不管是一对什么;而他自己孤零零的,只是个沉默寡言的司机。
她问起英吉沙最后一天的行程安排。
“想好去哪里了吗?”她问。
“什么?”
“明天。最后一站。”
“你想去哪里?”
“无人区。我说过了。”
“为什么是无人区?想追求刺激?”
Jade捋着头发点头。英吉沙已经摘下了墨镜。他的头顶正好是一盏白炽灯,这让他的眼珠里多了一点黑洞洞的光亮。
他说:“那就去看星星吧。没什么人知道那座山。但我知道。我也说过了,你们得保密。”
女人迷蒙着双眼说好。她的酒量比梁昊想象的更差。三瓶乌苏下肚,她已经趴在桌上不省人事。梁昊想把她扶回房间,她变得很重。
挂在梁昊身上,Jade把他错认成了英吉沙。
“英吉沙,”她抱住梁昊说,“梁昊挺怕你的……哎,你怎么把墨镜摘了。”梁昊搀着她说,“我是梁昊,你喝醉了。”她对着梁昊睁大了眼睛,笑得酒气四溢,又向英吉沙招手说,“嘿,梁昊,你看英吉沙,他喝醉了。”
英吉沙用他的刀割下一块羊肉塞进嘴里,点着头,咀嚼起耐人寻味的微笑。
Jade趴到床上时,都还觉得把她带回来的人是英吉沙。
“英吉沙……”她酥软地唤。
“我是梁昊。这就不认识我了。”
“我当然认识你。我怎么会不认识你。英吉沙,你认识Catherine吗?”她说。
“不认识。她是谁?”梁昊觉得这个名字耳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对啊……你怎么会认识她呢。我喝醉了。Catherine和她老公……去度蜜月了。他们去埃及了。Catherine怀孕了——埃及是不是也有很多沙漠?”
“是吧。所以呢?”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呐。她怀孕了。你到底有没有仔细听我说话啊?她怀孕了,被公司开的人就不是她,而是我了。她故意的。她一定是故意的……对不对?埃及也有沙漠,对不对?你先回答我对不对?”
“对。”
“不对……为什么是我呢……唉,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呀。不对。”Jade在床上伸展着四肢,像在沙漠里游泳,“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啊?很荒唐。”
梁昊沉默。
“没有什么事情能自己做主的。”
“世界就是这样的。”
“但还是有的。”Jade突然坐起来说,“是有的。”她笑起来。
“什么?”梁昊不知道她在笑什么。
“生孩子,是我能做主的。我的身体,我能做主的。”
她骄傲地摊开双臂,像是向空气索要一个拥抱。女人的反应让梁昊顿感寒意。
“何必要这样。”他说。
“哪样?”她又慢慢耷拉下来。
“伤害自己。”
“你是不是喝醉了,英吉沙。”
梁昊发现女人在改口“英吉沙”之前,含糊地吞掉了一个“L”。
“你在伤害自己。”
“我吗?”
“嗯。”梁昊俯下身去帮Jade脱鞋。她的鞋里带出了很多沙。
“我在伤害自己吗?你觉得我在伤害自己。伤害……你去过上海吗,英吉沙?你告诉我嘛……你干吗?脱我鞋干吗?”Jade踢开了梁昊。
“你应该把鞋脱了,很脏的。”
“应该?”
“嗯。”
“应该。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在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Jade的眼神忽然坚定了,“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说完,她又垮了下去。仿佛这寥寥几语,都已经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
“你想太多了,真的。我们没这么走运。”梁昊说,“就算你真的怀上了,孩子也需要个父亲。真的怀上了……也得考虑以后的事。对工作未必是好事,像Catherine……”
“没有以后了。”Jade打断了男人,一个字一个字说道。
“没有以后了。”她重复了一遍。梁昊再无话可说了。
“喂!”她重重地捶了一下梁昊的背,痴痴地笑着说,“没有人需要父亲。你说呢?”接着,她从背后挽住了他的腰。
“我说不好。”
“我的孩子不需要父亲。”
“你……”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女人打断了梁昊,她终于带着哭腔吼了出来,“这是我唯一能做主的事情了。你知道吗?这是唯一的,我能做主的事情了。”她仰面躺着,握紧的拳头抬起落下,像将一把刀不断地刺进柔软洁白的床单里。
“你大老远来新疆,就只是为了这个?”
Jade沉默了很久很久。后来,她像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絮叨着:“其实,我是喜欢你的……梁昊,我不喜欢我爸。”但她很快改了口,说,“我不喜欢我爸,英吉沙。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地开心过了。没有人对我不好……但我知道。我……我,我自己对我不好。没有人对我不好。”她慢慢用手盖住了自己的脸。
她的话最终都混入了越来越重的呼吸。
她睡着了。
梁昊离开房间,想着和英吉沙打声招呼,但英吉沙向他高举起酒瓶,不住地招手,梁昊于是和他对坐下来。那场面像是必须经历的某种审判。他开口说:“她是不是骗了你,嗯?”
后来英吉沙还说了些什么,梁昊多数都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事情,一件确切的事情,是英吉沙也讲起他的父亲,一个锻刀人,一个老瞎子。他还记得自己因此赌气似的又开了一瓶,他记得起子把瓶盖撬开的声音,像在他的背上拔起一个沉闷的火罐。
他跑厕所吐了两次,听见哪里放着流行曲调的外语歌。英吉沙始终稳坐在那里,面不改色,像一座山。梁昊盯着他放在桌上的那把刀,很多次,企图用眼神握住那质地熟悉的刀柄。但没有一次鼓起勇气。他眼中的夜晚是暗蓝色的,像是颜料盘上多种颜色混合的腐败结果。
催梁昊醒来的是骆驼的臭味。民宿老板正在清理它们的粪便。天已经亮了。他努力回想着烂醉后有没有和英吉沙提到Jade。起身碰倒空酒瓶的时候,他隐约感到,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敲了很久的门,才等来Jade。
四目相对,两人完全愣住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光着身子,正像是一只艰难站起的骆驼。回到房间,她抱着梁昊大哭了一场。
那些最难以启齿的话,最终没有从梁昊口中吐出来。
如果,她回答是呢?
如果回答不是呢?
他又独自走到了那块巨大的、变黑的冰块面前,发现Jade早已在那里呆呆驻足。
等她渐渐冷静下来,梁昊建议她报警。但她摇着头,慢慢盯到大腿和腕间的若隐若现的瘀青,突然对着梁昊笑了出来。那笑声几乎碾碎了梁昊。
她一遍又一遍地抖落着前一天留在鞋子里的沙,像是机械的动作。她对梁昊说,我们还有最后一站要去。她的神情,仿佛早就已经看过了漫天璀璨的星星,而那些星星,像所有死睡的动物在黑暗中猛然睁开的眼睛。可她还是说,我们上山去。两人都不清楚,是怎么在房间里度过了一整个白天。但她不知从哪里来的把握,确定英吉沙不会走。
那个男人的确没有走。
但他看Jade和梁昊的眼神,已经出鞘似的变过了。
车不知开出多久,路上就没有了灯。无人区阒黑寂静,打开天窗,头顶真的有那么多又那么亮的星星,像一场在空中静滞的大雪。车速起来,就连缀起成片缭乱的流火。
她依然坐在副驾,从始至终,平静得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梁昊尽力克制着恐惧和冲动,攥着后座扶手,试图用任何角度去观察那个男人。一路上,Jade和英吉沙讲着些奇怪的话,奇怪的比喻,尽管窗外已经太黑暗,她还是说,那些山太像人脸。
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那些山。
她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些山,在盯着他们看。
六
离开喀什之后,梁昊就再也没有见过Jade。她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在他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他经常做到噩梦,但那些梦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他不知道该不该庆幸,因为他明白,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感到轻松。
他有时会幻想,这件事就会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不会有第四个人,或者说,第三个人,知道那天晚上的骆驼民宿,还有第二天晚上的无人区,究竟发生过什么。
直到半年后的某天,他看到了一则奇怪的新闻。
塔县当地警局收到一伙驴友求救,他们在某无人区探险时,其中一人被路边一具突然爆炸的骆驼尸体炸伤了。救援很快赶到,伤者并无大碍,但需隔离严防疫病。警察严肃教育了这帮哈,并给他们科普了些基本的生物常识。此类事件极难杜绝,只好暂时封锁那片无人区,在周边多竖几面牌子,最后,草草地搜刮了一遍附近区域残留的骆驼尸体。
但让梁昊毛骨悚然的不是骆驼。
让他感到像是被一把刀刺穿身体的,是他在那个摇晃的报道镜头里,隐约看到了山脚下,似乎依然停靠着一辆覆满灰尘的兰德酷路泽。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