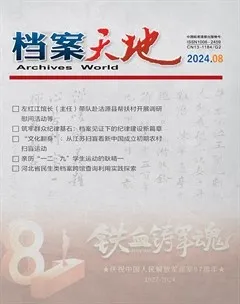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保护:从现存挑战到未来展望
在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中,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占多数,其历史变迁、道德伦理、宗教仪式、民风民俗、传统艺术和工艺传承主要是以口语传记的方式向后世流传。这些口述历史档案具有丰富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参考[1],能够在复原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填补正史不足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生的文化环境及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护风险不断加大,加之掌握与传播本民族文化的特定群体大多年事已高,若不重视并抢救相关口述历史档案,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传承将是毁灭性的破坏。自2010年国家档案局将云南省指定为全国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的试验区以来,云南省政府和省内专家学者一直在积极推进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紧急保护活动。在“十二五”期间,云南省已经逐步实施并完成了对哈尼、白、傣、傈僳、佤、景颇、布朗、阿昌、拉祜、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等15个云南省特有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紧急保护[2],2021年印发的《“十四五”云南省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要鼓励采集口述材料、新媒体信息”。在云南地区口述历史档案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现有保护研究和实践中的不足,以便吸取经验教训,探索更有效的保护方法与途径。
一、口述历史档案的概念和研究综述
(一)口述历史档案的概念
随着档案机构在口述史料的收集与管理方面的参与不断加深,口述历史档案这一概念在档案学领域应运而生。对目前学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口述历史档案是旨在挽救和保护历史记忆,通过有组织地采访相关事件的亲历者或知情者,并且用规范的方式进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重要资料。这些档案包括文字、录音、录像、照片及数字化资料等多种形式,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的保存价值[3]。
口述历史档案的载体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早期主要依赖于人脑记忆,后期则以声像档案作为主导,辅以纸质材料,形成了多样化的载体形式并存。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分类中,基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档案可被分为有文字记录和无文字记录两大类。特别是那些无文字记录的档案,因其珍贵性而迫切需要得到保护。由于这些档案缺乏书面形式的记载,它们仅以知情者的记忆形式存在,因此,一旦知情者离世,与之相daHt7sxakR2C52Z9oNffRvuo8Agaty2vNzYDnw6a5Sk=关的档案信息亦将随之遗失。
(二)研究综述
在采集工作方面,王治能自1995年就提倡口述历史档案的采集应采用多形式和多方位的方式,并且强调要系统搜集没有书面文字的民族的口述历史档案,还主张建立相应的组织政策,以支持和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4]。其《论收集无文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和陈子丹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浅论》,均对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还介绍了云南省一些档案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做法。这些方法虽然不够全面,但是依旧具有借鉴价值。之后,黄琴、段睿辉和徐国英等学者都提出了应该从保护意识建立、强化工作水平的角度完善相关政策保护,采取有效的人才培养手段以进行收集保护工作。云南省档案局在2015年10月发布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采集与整理方法研究》的报告,针对采集整理方法进行了阐述,同时提到云南省档案局整理了少数民族口述史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并建立了档案数据库。
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徐国英提出应该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以强化材料的整合效率[5]。赵局建等人强调,当前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数据库应该遵循实用、规范、标准、可扩展的原则进行建设[6],并且在《云南石林彝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中进一步补充了“数据库应该随着民族文化发展变迁而呈现动态兼容的特点”[7]。
在开发利用方面,黄琴和华林等人都提出应该构建保护与利用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8]。郭胜溶等人则对实现档案价值意义进行了分析,提出应该连接构建相关的价值体系[9]。在前人基础上,黄存勋等人提出应该将口述历史档案与有关渠道相互整合以发挥其最大价值[10]。
二、出现的问题
结合研究现状中提及的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保护具体实施方面的困难和目前保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总结如下问题:
(一)征集工作难度大
征集工作难度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层面的难度,要收集有价值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首先要找到继承了民族文化与技艺的特定身份的长者。云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大都分散广泛,远离主要城市的农村地区可能缺乏有效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同时,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体系,而口述历史档案征集需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沟通和交流,因此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很可能造成工作人员在征集时难以准确理解和传达信息的情况。交通不便和语言不通都在现实层面给实地征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二是思想意识层面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口述历史档案的特殊性上。口述历史档案与书面档案不同,其以口述方式传承历史和文化,通常被保存在个人或家族的记忆中。因此,征集口述历史档案需要与当事人建立信任和密切的关系,花费不菲的时间和精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少数民族的土司、东巴、毕摩、和尚、长老、巫师、民间艺人日渐衰老,对于他们来说,口述传统是其文化认同和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都更倾向于在自己本民族内部传承和保护口述史料,以维护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使针对口述历史档案采集的访谈往往面临着老人因风俗禁忌不愿意接受或在访谈过程中对关键信息讳莫如深的情况。征集人员要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建立信任、亲近社群和克服文化壁垒等,这也增加了征集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度。时间不等人,纳西族中东巴老人的相继离世导致许多东巴古籍变得难以解读,使大量珍贵的东巴口述历史档案面临无法继续传承的困境。如何在尊重受访人意愿和当地民俗习惯的同时,采取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式方法对正在流失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进行抢救和保护,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配套数据库建设不完善
在开展基于数据库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有学者分别从意义、内容、原则及重要性、必要性等方面,对数据库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在具体数据库建设的设计实现和方法要求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罕有学者从系统和全面的视角出发,对基于数据库构建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整理工作进行研究。首先,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数据库建设很可能存在技术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控制不足等问题,即不同地区和机构在建设数据库时,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导致数据库之间不能相互兼容和操作;在数据采集、录入和整理过程中,因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其次,完整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由不同形式的载体组成,在对它们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数据库的过程中,除了存储这些材料,还需要在数据库的建设中保证所存储口述历史档案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对于多民族地区,数据库建设如若缺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支持,也将限制少数民族群体对数据库的使用和建设的参与。陈子丹曾在《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研究》一文中倡议立即实施有效措施,收集那些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语言的音频资料,建立一个完整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库,以供学习和研究之用。这一想法给未来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保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向。
(三)保护成果缺乏利用共享意识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抢救、保护与保存,最终目的不仅在于确保这些宝贵的历史口述资源不会破坏或遗失,更是为了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价值,让更多人共享和受益,进而延续少数民族的社会记忆和历史传承。然而,很多承接保护工作与研究的机构经常忽略了这一点。例如,在云南省档案网站内的检索中,使用“口述”作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25条记录,但仅有1条与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相关。相比之下,红色档案系列如《云南中共党员口述历史》和《云南省全国劳模口述历史》等口述档案的成果却能够被用户方便快捷地检索并使用。某东巴文化研究所作为研究东巴文化和东巴口述历史档案的重点单位,其网站首页却无法加载,这无疑阻碍了人们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相关口述历史档案材料的获取和利用。无人问津地被存储在数据库中,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就无法为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通过便利和深化对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利用,才能实现其活化利用和长期保存,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的口述历史和文化遗产,并且使全社会对其工作有更深刻地了解,增强人们对它的保护意识。同时,通过对口述历史档案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加强,也可以为利用活动提供更为可靠和丰富的资源,形成良好的循环发展关系。
三、解决对策
(一)加强合作,顾及伦理问题
征集工作如果要顺利开展,现实层面的难度可以通过政府扶持、设立专项研究小组和开展田野调查等方式解决。思想意识层面的困难,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当少数民族人民更愿意在本民族内部保护口述史料时,并不意味着其保护意识淡薄,相反却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主性和自我保护需求。因此,在开展口述历史档案征集保护工作时,应该尊重当地的文化自主性意愿,在维护少数民族权益、赢得其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从而进行有效征集。可以与当地社区的代表、长者、族长等进行对话,了解他们对口述历史档案保护的看法和期望,通过族群参与的形式,如座谈会等,征集和记录口述历史资料;可以动员少数民族青年及学生加入进来,做好牵线搭桥工作,找寻关键长者来参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和翻译工作,或者考虑为这些特殊群体“建档立卡”,以便予以特别关注和重点追踪。同时,我们还要重视口述历史档案采集中的伦理问题。以活人为研究对象的口述历史档案采集项目涉及的伦理问题大体可以归为充分尊重受访者对自己言行负责的权利,并且努力防止或降低可能对他们造成的任何伤害[11]。开展访谈是采集口述历史档案的主要形式之一,但访谈过程中提供的信息有时未必准确,有时只能部分公开,有时受访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有效对话。因此,访谈者应该在充分尊重受访者言行的同时,在访谈前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访谈相关的资料,注意访谈强度和与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相关的禁忌,力求客观严谨地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实用性,避免对访谈对象造成伤害。
(二)完善配套,保证真实可读
目前,建设配套数据库支持口述历史档案保护工作迫在眉睫,首先应注重建立标准的数据录入和记录规范,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为今后的研究和数据分析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从本身特性来看,整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工作不仅包括将口述的音频和视频资料转写成文本,还涵盖对收集到的如文字记录、照片等各类资料进行系统地整理和归档[12]。因此,需要针对产生的配套材料建设一个综合性、可持续发展的数据库系统,收录内容还应包括口述的历史记录和相关的人物传记、社会背景资料等。考虑到没有书面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濒危状态,建议将语言文字资源库作为配套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征集口述历史档案的同时,收集、整理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有声资料和文字材料,保证口述历史档案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保存配套材料并建立数据库与保全电子档案的流程有相似之处。电子档案保全需要在保管文件的同时,对对应的软件版本和操作系统进行存档,这样才能保证再利用时有适当的工具和环境进行识读,实现对档案文件的“可用”“可读”。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是通过民族语言进行信息传递的,若想要对口述历史档案进行后续的开发和利用,就需要保证口述历史档案本身,即民族语言能够被识读。只有未雨绸缪为其建立对应的语音库,才能预防后续开发可能出现的无人能懂、无人能用的窘境。此外,配套数据库建设或可参考档案的双套制管理,相关保护机构建立专门的口述历史档案关联数据库,保留原有环境信息中的外部元数据,完成相应的数据著录与挂接。原因是在采集口述历史档案的过程中形成的音频文件经过后续的存档和编撰,其本身的形式可能发生转变,变成了一部分文字或直接的编撰成果,所以需要建立对应的数据库,将相应文件进行保存,确保它们之间的追溯关联性。
(三)以用促保,维护原生环境
相关机构应当积极引导本民族的人对口述历史档案材料进行学习利用,配备专门的少数民族相关人才,并且提升对云南地区口述历史档案蕴藏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意识。只有同时注重人才培养和资源开发利用,才能进一步深化当地文化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打造文化品牌,为当地原住少数民族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开发利用得当的基础上,才有利于对产生口述历史档案的原生文化环境进行保护。
结语
综上所述,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首先需要尊重和合作,可以通过建立共同目标、加强沟通、动员青年人才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文化自主性、保护主动性,以及与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的良好局面。其次,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配套数据库的建设应综合考虑材料采集整理、多语言支持和标准化、规范化等,确保口述历史档案的有效保护、研究和传承。最后,在重视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同时,应增强共享利用意识,拓宽公众接触、获取这些档案的途径,使人们认识到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价值及其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陈子丹,周知勇.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浅论[J].云南档案,2004(2):24-26.
[2]陈子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研究[J].兰台世界,2012(32):4-5.
[3]子志月.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3.
[4]王治能.口述档案:档案工作的新领域——我们的做法和体会[J].中国档案,1995(4):26-27.
[5]徐国英.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保护措施探究[J].兰台世界,2014(11):87-88.
[6]赵局建,杜钊,朱玲.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数据库建设探讨[J].兰台世界,2012(8):14-15.
[7]赵局建.云南彝族口述档案数字资源建设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20.
[8]华林,关素芳.云南少数民族档案遗产保护机制的构建[J].中国档案,2010(2):30-32.
[9]郭胜溶,赵局建.民族文化生态变迁视角下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保护研究[J].档案与建设,2019(9):31-34,54.
[10]黄存勋,张瑞菊.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有序化建设的宏观探索[J].贵州民族研究,2015,36(11):196-199.
[11]李娜.当口述历史走向公众:“公众口述历史”中的伦理问题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2016(3):94-105.
[12]雷鲁嘉.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采集及其保障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8.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