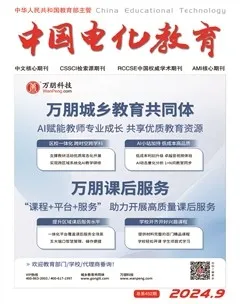人口负增长时代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摘要: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乡村小规模学校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学校的基本类型。从教育自身发展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一主导性任务要求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从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看,人口质量提升“窗口期”需要及时促进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发展前景迷茫、规模效益衰减、资源效能不足和管理模式异化等现实困境,制约着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为此,应主动适应人口质量红利期新形势,从前景规划、学制整合、标准多维、资源提效和管理赋权五个方面应对现实困境,积极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人口负增长;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适应人口发展趋势的区域教育结构优化与政策调整研究”(项目批准号:VGA230004)研究成果。
人口规模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面实现普及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规模与分布直接影响到学校的资源配置和规划布局。从人口自然增长率看,2016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峰值(6.53‰)后,2017—2023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降低,分别为5.58‰、3.78‰、3.32‰、1.45‰、0.34‰、-0.60‰、-1.48‰①。在2022年我国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正常发展条件下因人口转变阶段变化而形成的首次人口负增长,中国开始步入一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负增长时代[1]。从出生人口数量看,早在2017年我国经历了最近一次人口出生高峰(1841.81万人)后,2018—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分别为1526.68万人、1438.38万人、1198.81万人、1062万人、956万人、902万人②。在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生源自然减少,农村学校规模进一步缩小,小规模学校成为农村学校的基本类型。党和国家在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方面作出诸多政策努力。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办好两类学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2]。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相对较低,是人口变动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短板弱项。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问题成为当前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中的重要议题。
一、人口负增长时代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三重依据
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伴随着学龄人口规模的减小,小规模学校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学校的基本类型,这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从教育自身发展看,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农村教育的短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一主导性任务要求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从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看,我国人口数量红利逐渐转向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提升进入“窗口期”,需要及时促进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成为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之要和释放人口质量红利之需。
(一)小规模学校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学校的基本类型
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小规模学校在存在重心、存在数量和存续时间上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表明乡村小规模学校不是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而是作为农村学校的一种基本类型存在,必须在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的基础上予以发展,不断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
从存在重心看,小规模学校存在重心将不断上移。在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农村学龄人口规模减小,农村学校规模将发生变化,农村学校呈现小规模化发展趋势。一方面,一些标准规模学校会逐步缩小,逐渐发展成为小规模学校。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有些以往标准规模的乡镇小学已经变成小规模学校。另一方面,一些小规模学校将会进一步缩小甚至被撤并。伴随着农村学校小规模化发展趋势,小规模学校的存在重心将不断上移,可以预见小规模学校的存在重心在宏观上将会呈现“自然村—行政村—乡政府所在地—镇政府所在地”的发展轨迹。
从存在数量看,小规模学校将大量存在。虽然经历了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后,原有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被大量撤并,但随着农村学龄人口减少,新的小规模学校不断出现。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农村地区仍然占据较大比重,是服务农村学龄人口的主要教育场所。这从教学点占校点的比例上可见一斑。据统计,2020年我国农村小学校数为128772所(镇区42687所,乡村86085所),农村教学点88694个(镇区9501个,乡村79193个)①,农村小学教学点占农村校点总数(农村小学校数+农村教学点数)的40.79%。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农村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农村地区地广人稀的地理学特征将会更加明显。而小学适龄人口就近入学的政策决定了学校服务半径不能过大,这意味着在地广人稀和边远偏僻的农村地区,除撤除零人学校外,只能就近有序地撤并一些规模过小的学校,绝对数量减少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将会以更加分散的形式存在,以方便小学适龄人口就近入学。
从存续时间看,小规模学校将长期存在。一方面,由于农村和农村人口不会消失,小规模学校作为农村教育服务提供方将长期存在。一直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虽然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农业逐步实现现代化,但“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在空间分布上,很多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方便的教育是必须要为这些人口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教育城镇化进程逐渐放缓,人口乡—城流动因素对乡村小规模学校规模变化的影响逐渐减弱。2022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同年,全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为83.47%,其中小学教育城镇化率为81.09%,分别高出城镇化率18.25个百分点和15.87个百分点②。义务教育城镇化率和小学教育城镇化率均先于城镇化率进入“诺瑟姆曲线”的第三个阶段③,城镇化发展将逐渐趋于稳定,城镇因人口向城流动产生的学龄人口增长趋缓,农村学校生源未来不会因城镇化而无限减少。
(二)优质均衡主导性任务要求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2021年底,我国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工作重心由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优质均衡发展成为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主导性任务。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最短板。进入以优质均衡发展为主导性任务的教育发展阶段,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就外部发展条件看,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教育资源供需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从需求侧看,随着学龄人口数量减少,教育资源需求量将逐渐减少。从供给侧看,一方面,由于部分教育资源调整周期滞后于学龄人口变化,在一段时间内教育资源供给会出现过剩现象。比如,在师资方面,有学者预测,与2020年相比,2035年小学教师过剩约150万,初中过剩约37万[3]。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家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不断提高,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将不断扩大。在这一发展背景下,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将得到优化,义务教育发展逐渐由规模效益提升为先转向教育质量提升为重。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阶段,应积极回应这一转变,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就自身发展情况看,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最短板,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阶段,必须做好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随着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城乡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教育质量差距依然明显,乡村小规模学校仍然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最薄弱的环节。一直以来,乡村小规模学校为农村弱势群体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了底线保障。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但从总量上看农村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仍然较大。有学者按常住人口预测,到2035年,仍有1/4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小学学龄人口规模为1302万,农村初中学龄人口规模为719万[4]。这部分学龄人口的教育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程。未来,需要在满足农村学龄人口就近入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阶段,乡村小规模学校要努力回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时代诉求。
(三)人口质量提升“窗口期”需要及时促进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降低,人口红利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的特点会愈发明显。有学者预测,我国名义劳动供给量将从2020年7.447亿人持续下降到2050年5.659亿人;有效劳动供给量将先升后降,2020年7.447亿人,2028年达到峰值7.529亿人,2050年降至6.431亿人[5]。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教育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途径,在人口质量提升“窗口期”需要及时促进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农村人口素质,释放农村人口质量红利。
从发展机遇上讲,需要及时抓住人口质量提升“窗口期”。在出生人口减少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农村学校被动出现大量小规模班级。小规模班级对提高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小规模班级是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将“小规模”视为农村教育的“问题”,当小规模班级在一些农村地区大量出现时,相关教育主体缺乏挖掘小规模班级教学优势的意识,缺乏挖掘小规模班级教学的能力准备。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应抓住人口质量提升“窗口期”,及时挖掘小规模班级教学优势,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释放农村人口质量红利。
从发展可行性上讲,随着农村学龄人口下降,农村学校小班教学优势愈发凸显,只要具备挖掘小班教学优势的意识,采取恰当的发展方式,就能将小班教学优势转化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实质效果。班级规模小,意味着教师对每个学生个性化关注机会更加充分,有利于开展个别化教学、差异化教学和定制化教学,提高学生学与教师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6]。美国田纳西州STAR项目通过进行大规模随机实验发现,在各年级和各学科小班(13—17人)的学生平均成绩均超过了大班和有教学助手大班(22—25人)的学生[7]。在最近一段时间人口质量提升“窗口期”,广大农村地区会呈现出学龄人口减少而教育资源投放规模相对稳定,出现大量小规模班级的情况,相关教育主体要抓住机会加强小班化教学培训与教研,提升教师小班教学能力,把小班的潜在教学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提高小班教学质量,促进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乡村小规模学校仍然是我国义务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往往面临着发展前景迷茫、规模效益衰减、资源效能不足以及管理模式异化等现实困境。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分析这些困境。
(一)发展前景迷茫:撤留不确定性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心态
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和现有人口向城流动的双重影响下,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许多乡村小规模学校面临撤并风险。由于难以把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以及缺乏学校撤并标准,乡村小规模学校自身无法判断面临多大撤并风险。这种撤留不确定性使乡村小规模学校很难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容易陷入发展前景迷茫的困境,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心态。
一是,教育管理者普遍对乡村小规模学校采取保守型资源投入策略,客观上传递出“等待撤并”的消极建设心态。现阶段,教育管理者倾向于将资源优先投入到标准规模学校。而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或是大范围撤并,或是置于政策关注、资源分配和管理链条的末端,对其学校发展采取相对忽视的态度[8]。而且许多教育管理者认为,即使不断向乡村小规模学校投入资源,教学质量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教育努力难见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向小规模学校投入资源是不明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资源往往仅能维持学校基本运转,大部分乡村小规模学校处于“为保留而保留”的状态。
二是,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担心学校撤并,影响教师工作状态。一方面,学校撤留的不确定性影响青年教师职业规划,使青年教师无法静心从教。部分青年教师忙于寻求更好的工作出路和发展前景,甚至希望利用学校撤并的机会调到县镇工作,其教学投入难以保障。另一方面,学校撤留不确定性潜在地影响年长教师,特别是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的年长教师,影响他们在乡村学校工作年限累积的连续性。年长教师通常不愿意离开他们熟悉的乡村学校教育环境,撤留不确定性意味着他们熟悉的教育环境和人际关系随时会发生改变,年长教师容易产生失落、不安与焦虑的工作情绪。
三是,家长难以信任和认可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倾向于将孩子送到县镇读书。在许多农村父母的教育价值位序中,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优先于就近入学。与城镇学校相比,农村学校教学质量普遍相对较低,加上乡村小规模学校随时面临撤并风险,稍有条件的家庭往往会选择将孩子直接送到县镇读书,或者上完小学低年段后转学到县镇学校。条件稍差的家庭即使让孩子留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其父母对学校教学工作的配合程度和支持程度也比较低。
在教育资源充分供给困难、教师工作状态欠佳、办学质量认同度低等多重不利因素叠加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风险进一步增加,撤并风险增加强化了相关教育主体对学校发展前景的迷茫。在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中,难以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二)规模效益衰减:生均式配置标准难以满足小规模学校资源需求
合理的资源配置标准是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尚未出台关于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专门性文件,乡村小规模学校参照的资源配置标准①多是以理想学校规模为假设,即使考虑到乡村小规模学校“小”的规模特征,也仍简单地以生均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在乡村小规模学校生源减少的发展趋势下,资源配置规模效益日益衰减,生均式资源配置标准无法满足乡村小规模学校资源需求。
一是,当前学校建设标准容易造成按标准基础设施配置超标与现实中配置不足并存的问题。一方面,《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考虑到了农村学校年级不完整的客观情况,专门设置非完全小学(1到4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每班30人)的建设标准。但乡村小规模学校最大规模为100人,即使保留四个年级,班额也达不到30人。另一方面,一些教学辅助用房(如科学教室、远程教育教室、计算机教室)和生活用房(如开水房)并未纳入到非完全小学必备校舍用房范畴,乡村小规模学校实际教学需求与师生在校生活的基本需求在相关政策中并未得到充分考虑。
二是,以师生比为依据的编制核算标准存在教师“超编缺人”问题。当前政策虽然支持乡村小规模学校按照“师生比与师班比相结合”的方式核算教师编制,但由于缺乏量化的执行标准,在实践中仍以师生比作为教师编制核算的依据。教师教学活动面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个学生,而是班级。相较于标准规模学校来说,小规模学校虽然每班学生数量少,但相应的课程与教学任务并未随之等比例减少,按现行标准配置教师,学校教师总量已满编制甚至超编,却不能满足甚至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9]。由于班级规模过小,即使按照“师生比与师班比相结合”的方式核算教师编制,也无法解决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
三是,公用经费拨付标准的“临界点效应”造成小规模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公用经费短缺问题。“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的拨付标准潜在地将100人作为小规模学校维持正常运转的底线学校规模,有待进一步论证。而且,直接以这一学生数量节点作为拨付标准,仍然过于“简单”。从理论上说,在1—100人这个规模区间内,这一拨付标准对于规模越小的学校实际收益越大,规模越大的学校实际收益越小[10]。在这个学校规模区间内违反了学校规模越大所需运转成本越高的经济学假设。
(三)资源效能不足:资源“缺配套、轻使用、难见效”问题突出
资源效能涉及资源的有效配置、高效利用以及最终是否能够转化为有效教育服务等环节。当前,我国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资源效能释放不足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缺配套、轻使用、难见效”,从不同环节制约着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一是,配套资源配置不到位。由于分散采购或者资金不足等原因,资源配置尚未形成完整的链条,配套资源配置不到位,资源配置的“最后一公里”受阻。一方面,有些资源不能独立运行,只有资源配套才能投入到使用环节。现实中,常常面临的情况是有些资源已经配置到位,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资源难以及时应用到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另一方面,有些资源虽然能够独立运行,由于配套资源不到位会使不同资源之间的匹配性、衔接性、协同性差,资源功能潜力难以充分挖掘。
二是,已有资源使用率低。即使资源配置到位,受教师使用意愿和使用能力的制约,乡村小规模学校资源使用率普遍偏低。研究发现,学生学业表现受到资源使用率的影响[11],简单的资源政策对提高学生成绩收效甚微[12]。也就是说,即使资源配置到位,如果资源使用率低,已有资源也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教育资源使用率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学辅助性用房使用率低。调查发现,小规模学校图书馆“经常开放”“偶尔开放”和“很少开放”的比例分别为54.7%、21.1%和24.2%,而大规模学校的比例分别为83.0%、12.2%和4.8%[13]。另一方面,数字化教育资源使用率低。有研究发现,在“数字化教学资源利用”状况和“提升学生数字化资源利用”状况方面,农村学校教师均显著低于城市学校教师[14]。
三是,教育资源使用效果不佳。资源效能的发挥最终会体现在教学过程和效果上。在教师端,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使用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较高,尤其是在数字化教育资源的使用上,容易给教师造成技术负担。在学生端,由于尚未形成常态化的教育资源使用氛围,一些教育资源的使用,尤其是数字化教育资源,在教学活动中往往会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降低学生课堂专注度。数字化资源使用对教学质量提升的贡献度并不明显,甚至起到干扰作用。
(四)管理模式异化:中心校统筹模式限制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空间
有效的管理模式是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实行“县教育局—乡镇中心校—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管理模式,中心校统筹管理中心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人、财、物等各项事宜[15]。这种管理模式的初衷是为加强乡镇中心校和小规模学校一体化办学,发挥乡镇中心校统筹、辐射和指导作用[16]。但在乡镇中心校统筹管理小规模学校实践中,教育资源“雁过拔毛式”的“留足效应”明显,乡镇中心校变相成为这种链式分层管理模式的受益者,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空间被压缩。
一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经费可达性受阻。目前,多数乡村小规模学校不是独立的财务核算单位,财务账户通常设在乡镇中心校,中心校负责小规模学校教育经费的实际管理与分配,小规模学校经费可达性在数额和时间上双重受阻。在经费分配上,中心校校长通常会采取优先满足中心校发展需求的经费使用策略。尤其是当县财政吃紧,下拨到中心校的教育经费有限时,中心校可能会延迟拨付或截留小规模学校教育经费。甚至一些中心校不会拨付任何“货币”形式的公用经费,而是以“物化”形式的教学用品来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转[17]。在经费报销上,乡村小规模学校财务报销通常要经历“小规模学校—中心校—县教育局—中心校—小规模学校”的报销流程,报销过程繁琐且时间成本高。
二是,乡村小规模学校优秀教师可达性受阻。在中心校统筹的管理模式下,政策层面要求中心校和小规模学校教师“一并定岗、统筹使用、轮流任教”,但是在实践中师资分配在中心校层面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留强逐弱”的特点。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中心校往往将优秀教师截留自用。优秀毕业生往往被留在较高层次的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很难分配到真正需要的学科对口的教师[18]。在二次分配过程中,部分中心校利用人事管理权将小规模学校表现优异的教师以招考等方式调到中心校任教,而将一些教学表现一般的教师下派到乡村小规模学校。这种调任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对教师教学的肯定机制和惩罚机制。
三是,两校校长管理效能发挥受阻。相比于标准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管理工作约束性因素更多,日常管理更具复杂性。中心校校长处于“身体离场,权利在位”的状态,缺乏对小规模学校发展实际需求的关注,很难充分挖掘小规模学校的潜在优势。而乡村小规模学校校长虽然“身体在场”,对学校发展有清晰地判断和需求认知,但由于“权利缺位”,小规模学校校长通常仅能维持学校基本运转,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容易滋生“平庸之恶”。甚至有些乡村小规模学校出现校长职位空缺,学校缺乏领导和管理,学校运转处于无序状态。
四是,乡村小规模学校低水平运转被合理化。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中,国家将教学点排除在外,教学点成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免检单位”,这意味着中心校掌握着教学点的人事和财务等权利,却不用担心其办学质量是否达标。甚至一些村小学被人为降成教学点,既能够规避评估验收不合格风险,也可以增加中心校经费来源。
三、人口负增长时代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在新的人口变动形势下,乡村小规模学校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应从前景规划、学制整合、标准多维、资源提效和管理赋权五个方面协同发力,努力突破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序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一)基于学龄人口变动趋势分类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农村学龄人口数量与空间分布决定着乡村小规模学校生源规模,影响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撤留。考虑到撤留不确定性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前景,应基于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科学研判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前景,做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中长期规划,分类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首先,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变动动态监测机制,为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规划提供数据支撑。利用信息化建立县域学龄人口变动的动态监测机制,实时监测、及时更新县域学龄人口变动情况。动态监测工作应以家庭为单位,重点监测县域成人与中小学生的空间分布,获得涉及广泛背景的、最小分析单位上具有内在关联的、在时间上连续的县域人口及其学龄人口信息[19]。
其次,根据县域内学龄人口变动的动态监测数据,结合地理区位因素,将乡村小规模学校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建设型、保留型、过渡型和撤并型,明确建设型、保留型、过渡型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性任务。在地广人稀、人口相对稳定、学校间距离较远的农村地区,如进入城镇化后半场的农业主导的县的广大农村地区,小规模学校是农村学校的基本类型,要持续建设好小规模学校。保留型教学点,主要分布在地理位置偏远、地形状况复杂、交通条件不便等大山区和深山区[20]。如果保留型乡村小规模学校生源趋于稳定,应从教师队伍、教育经费、办学条件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过渡型乡村小规模学校生源呈现减少趋势,未来撤并可能性较大,应着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学校教学质量和安全。
最后,及时把不同类型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规划转化为科学规范、具体可行任务书和时间表。加强常态化监督管理,保障各项发展任务落实到位,有序推进县域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
(二)积极探索实施乡村小规模学校“幼小一体化”的学制改革
稳定生源规模有助于降低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风险,拓宽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空间。基于乡村小规模学校多为不完全小学的现状,以及未来生源规模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统筹农村幼儿园与小规模学校办学是乡村小规模学校保持规模、稳定生源的有效策略。一方面,学前儿童年龄普遍偏小,身体自我保护和生活自理能力较弱,不适合走读或寄宿,他们就近入园的需求更为迫切。另一方面,如果学前儿童选择到乡镇入园,他们后续会更倾向在乡镇上小学,乡村小规模学校将面临潜在生源流失风险。因此,应统筹农村幼儿园和小规模学校办学,积极探索乡村小规模学校“幼小一体化”的学制改革。
一是,抓住人口素质提升的“窗口期”,优先考虑将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这是探索“幼小一体化”学制创新的关键步骤。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一直存在前拓还是后延的争论。考虑到教育阶段越高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越低,并且教育阶段越低需要政府承担更大投入事权责任[21],国家应加强个体早期教育投入,优先将农村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这是探索“幼小一体化”学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二是,建立学制改革实验区,以试点方式有序推进学制改革。在当前教育实践中,一些村小学已经附设幼儿园,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办学标准,只是将幼儿园和小学简单地机械组合,并未实现真正的“幼小一体化”办学。作为一种学制改革,应在农村地区遴选一批办学质量较好的幼儿园和小规模学校作为学制改革实验区,成立专家组指导学制改革。在办学规范性上,一方面,科学设置“幼小一体化”后的合理学校规模区间,防止一体化办学后学校规模仍然过小而增加额外运营成本和管理负担。另一方面,规范一体化后的学校学制,要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就近入学方便性等因素,对一体化后学校年级设置下限进行科学论证,统一设置标准,比如实行“3+2制”“3+3制”“3+4制”等,减少学制设置的随意性。在办学功能性上,做好幼小区分和衔接,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不仅要警惕幼儿教育出现“小学化”倾向,而且要在幼儿教育大班阶段做好小学入学的过渡教育。
(三)建立以班级数量为基础、考虑多个调节指标的资源配置标准
资源配置标准是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合理的资源配置标准有利于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考虑到生均式配置标准无法满足乡村小规模学校资源需求,应充分理解乡村小规模学校“小”的规模特征,认识到学校教学活动通常是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人财物的使用与消耗多数是在班级层面产生的这一基本事实。建立以班级数量为基础,考虑学生数、年级数、学科数等多个调节指标的资源配置标准。
在各类用房的配置方面,重点对普通教室进行功能性改造和结构性调整。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学校建设之初多数是按标准学校规模建设的,当学校生源规模减小后,已有校舍建筑并没有因此缩减。基于乡村小规模学校班级规模小的现实以及生源减少的趋势,乡村小规模学校基本不存在教室拥挤或不够用的问题。因此,在满足每个班级普通教学用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校舍建筑,对剩余普通教室进行功能性改造和结构性调整,满足教学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的需求。
在教师配置方面,构建以初次配置为主,二次配置为辅的教师配置标准。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教师储备充裕,为优化教师结构提供了条件。相关定量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分配中,在现实既定班级规模下“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与“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之比约为2:1[22]。教师教学工作主要是在班级层面开展的。在区域教师初次配置时,应基于校际教师工作量均等原则,以班级数量为基础,适当考虑学生数、年级数、学科数,进行区域师资配置。在二次配置中,通过县域教师交流轮岗、中心校教师走教,弥补乡村小规模学校初次教师配置的短板。通过建立县域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数据库,进行教师与学校之间双向匹配,实行按需轮岗、按需走教。首先,保障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数量充足;其次,优化教师结构,努力做到学教对口;最后,通过优秀教师轮岗逐步实现区域内师资素质分布均衡。
在公用经费拨付方面,应以班级数量为基础,充分考虑学校层面与学生层面的公用经费需求。从公用经费开支范围看,班级层面产生的开支主要包括教学业务与管理、文体活动、水电、取暖、部分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教师层面产生的开支主要包括教师培训、交通差旅等;学校层面产生的开支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邮电等。如果教师数量主要以班级数量为基础进行配置,那么考虑班级层面产生的费用就客观地考虑了教师层面产生的费用;学校的日常维修维护主要是为班级教学服务的,从班级层面考虑公用经费拨付也可以兼顾这一方面。可见,公用经费拨付以班级数量为基础,充分考虑学校层面与学生层面的公用经费需求,可以更好地满足小规模学校教育教学需求。以甲乙两所学校为例,甲校学生数270人,6个班级,每班45人;乙校学生数90人,6个班级,每班15人。若按生均拨付公用经费,甲、乙两校公用经费拨付数额之比为3:1,但由于两校班级数量一致,在教育实践中班级层面产生的公用经费大致相当。若按班级数量拨付公用经费,两校公用经费拨付数额之比为1:1。考虑到公用经费的开支主要是在班级层面产生的,公用经费拨付标准以班级数量为基础,考虑学校层面与学生层面的需求更加符合小规模学校实际运转情况。
(四)构建“配套到位—使用规范—效果导向”的资源提效机制
资源作为学校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只有被激活才具有教育服务功能。考虑到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发展过程中资源效能释放不足的困境,应构建“配套到位—使用规范—效果导向”一体化的资源提效机制,努力实现教育资源挖潜增效,将教育资源转化为教育服务,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
首先,保障配套资源配置到位,提高资源配置完整性。配套资源既关系到资源能否投入使用,也影响到资源功能潜力的发挥。根据教学活动的实际需求,构建全环节、全链条的“一揽子”资源配置服务体系,保障配套资源配置到位,打通资源配置“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要严格把控配套资源的适配性,增强不同资源之间使用的协同性和衔接性。防止因配套资源缺乏适配性影响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
其次,规范资源使用,形成资源使用常态化的教学氛围。教师的使用意愿与使用能力是在资源使用环节影响资源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一方面,通过专门化培训、沉浸式体验、即时性实操,不断提高教师对资源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能力。另一方面,要求教师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必须按照课程标准、教学方案使用相应的教学设施设备,并将资源使用情况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中,促使资源使用逐步内化为教师教学的规定动作和专业素养,实现教育资源与教学活动的深度融合,逐渐形成资源使用常态化的教学氛围。
最后,建立资源使用效果评价制度,实现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和资源使用方式的持续改进。充分关注教师与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评价和反馈。在教师端,将使用频率、使用满意度、持续使用意愿以及改进需求等指标纳入评价制度;在学生端,重点评估学生上课体验以及学生学业表现。其中,学生学业表现不仅要纳入考试成绩,还应将学习投入、学习策略、学业自我效能感等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基于资源使用评价结果,分析资源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资源使用问题进行正确归因,根据不同原因及时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调整,同时促使教师不断优化资源使用方式,提高资源使用效果。
(五)赋予乡村小规模学校独立法人资格使其具备“行政户口”
学校独立法人资格意味着在法律上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具有教学、人事、行政及财务等自主权,能够使学校管理更具主动性、灵活性和高效性。乡村小规模学校因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和被动性,应尽快分批认证乡村小规模学校独立法人资格使其具备“行政户口”,赋予乡村小规模学校相应的办学自主权。
首先,对县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摸排登记,包括学校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教学质量等基本情况,建立县域内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与管理数据库,全面了解现有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现状。
其次,根据摸排情况,综合评估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现状,设置以学校规模、生源稳定性、教学质量等指标为依据的学校独立法人资格认证标准,分批认证乡村小规模学校独立法人资格,赋予相应的办学自主权。尤其是在财权方面,与非小规模学校一样,对小规模学校设置独立的财务账户,通过移动支付实现全过程留痕,保证支出经费金额可追溯、用途可追溯、责任可追溯。针对一些大中型修缮项目,采取县域统筹的方式,进行统一评估和统筹建设。
最后,对难以达到认证标准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充分发挥乡镇中心校统筹作用的同时,适度扩大乡村小规模学校管理自主权,激发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自主性和积极性。此外,基于移动支付的留痕性和可溯源性,建议同样设置独立财务账户,缩短经费拨付链条。
参考文献:
[1] 蔡昉.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3-23+59-82.
[2]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 htm,2024-07-01.
[3] 乔锦忠,沈敬轩等.2020—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12):59-80.
[4] 张立龙,史毅,胡咏梅.2021—2035年城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预测[J].教育研究,2022,43(12):101-112.
[5] 胡耀岭,徐洋洋.中国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人口研究,2024,48(1):22-39.
[6] 秦玉友,綦文惠.乡村小规模学校质量提升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人民教育,2023,(22):54-57.
[7] Finn J D,Achilles C M.ennessee’s Class Size Study:Findings, Implications,Misconceptions [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99,21(2):97-109.
[8] 庞丽娟,金志峰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原因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24):28-35.
[9] 秦玉友.农村教师编制、结构与配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38-39.
[10] 秦玉友.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评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343.
[11] W mann L.Schooling Resources,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 Performance: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3,65(2):117-170.
[12] Hanushek E A.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chool Resources on Student Performance:An Update [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97,19(2):141-164.
[13] 赵丹,陈遇春,赵阔.优质均衡视角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困境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2):157-167.
[14] 刘月,曾妮,张丹慧.教师数字资源利用的鸿沟现象及其弥合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大样本教师数字素养调查的数据[J].中国电化教育,2023,(10):106-110+119.
[15] 杨东平.改善“小学校”既要政府发力也要自身努力[N].中国教育报,2016-04-12(04).
[16] 国办发[2018]2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Z].
[17] 张金龙,秦玉友.小规模之痛:农村教学点发展困境与应对政策——当地教师的声音与“规模效益”实践取向批判[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2):116-124.
[18] 周晔.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专业水平结构的问题与对策——基于甘肃省X县的调研[J].教育研究,2017,38(3):147-153.
[19] 秦玉友.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推进中县域教育发展战略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24):1-7.
[20] 邬志辉.教育扶贫的“最后一公里”[J].光明日报,2016-07-05(14).
[21] 蔡昉.把生育支持纳入民生政策体系[J].劳动经济研究,2022,10(6):3-6.
[22] 秦玉友,赵忠平,曾文婧.义务教育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结构研究——基于全国10省20市(县)的数据[J].教师教育研究,2017,29(4):39-45.
作者简介:
秦玉友: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教育政策。
綦文惠: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教育政策。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and Promotion Path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in the Era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Qin Yuyou, Qi Wenhui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small-scale school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he basic form of rural school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tself, the leading task of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require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From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window period” of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need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time. At present,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generally have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of confused development prospects, declining scale efficiency, insufficient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alienation of management mode, which restri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from five aspects: prospect planning, school system integration, multi-dimensional standards, resourc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management empowerment. Keywords: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4年5月30日
责任编辑:李雅瑄
① 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中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② 2017—2020年为“七普”数据,2021—2023年根据抽查数据测算。
① 数据源于教育部官网“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中的“小学校数、教学点数及班数”。因2020年之后,教学点数量未区分城乡,故使用2020年数据。
② 2022年义务教育城镇化率和小学教育城镇化率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义务(小学)教育城镇化率=城镇义务(小学)教育在校生数/义务(小学)教育在校生数。数据源于教育部官网“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中的“小学在校生数”和“初中在校生数”。
③ 根据“诺瑟姆曲线”(城镇化发展S形曲线),城镇化率增长呈现出先慢后快再慢的增长趋势。当城镇化率低于25%的时候,城镇化处于发展初期;当城镇化率处于25%—70%时,城镇化处于高速增长期;当城镇化率高于70%时,城镇化处于发展后期。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和小学教育城镇化率远高于70%,按照成人人口与教育阶段人口同步城镇化的预期,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与小学教育城镇化率应该放缓。参见:Raymond M. Northam. Urban Geography[M].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1975:65-67.
① 乡村小规模学校资源配置标准主要依据《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国标50099-2011)、《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教基[2017]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27号)等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