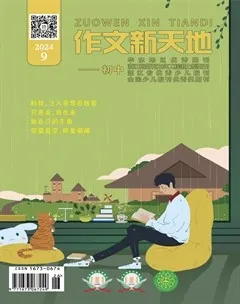仰望夜空,群星熠熠
这是一个崇尚成功的时代,我却将目光和敬意投给了失败者。
——《不朽的落魄》自序
2023年暑假,一个蝉鸣声声的下午,我收到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寄来的一本书。小心拆开包裹,入眼是黑底暗纹、素雅大气的封面,居中竖排五个沉稳的金色行书“不朽的落魄”,右上角是竖排的“徐海蛟著”,左上角与作者名字对称的位置,是同样竖排的三列小字“十三个”“科举落榜者”“和他们的时代”。看到这句话的瞬间,想到此刻各大公众号、自媒体正在疯狂推送的各种高考消息,我不由得会心一笑: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出版这样一本书,真是意味深长啊!
我翻开书页,很快沉浸其中。读着读着,一个个或高大或瘦弱的身影,随着作者鲜活、蕴藉、诗意的文字,朝我徐徐走来:那个,是冷雨夜乘一叶孤舟,漂浮于湘江上的贫病老人杜甫;这个,是骑一匹瘦驴,肩背锦囊,在山野小径孤独前行的清瘦少年李贺;那个,是风流倜傥、才思敏捷,正在陪游太子的文学青年“温八叉”温庭筠;这个,是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终其一生追寻内在宁静的“桃花庵主人”唐寅……还有同学们熟悉的吴承恩、张岱、蒲松龄、吴敬梓,以及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姜夔、王冕、徐渭、金圣叹、顾炎武。《不朽的落魄》一书,讲述的就是这样十三个不同时代、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文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干,生命的小舟却又在一个41c3db2db4f56d95501f501043190d44相似的巨大漩涡中沉浮起落”(作者语)——这个巨大的漩涡,名为“科举”。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使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改变了命运,也是一千多年来衡量个体成功、家族成就的最重要的标志。然而,这十三人,无一例外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有人甚至一再失败,没有一个抵达科举的彼岸。同时,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走出了科举之外的另一条路,开掘出个体生命的宝藏:杜甫以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沉郁顿挫的诗风,成为一代“诗圣”;唐寅先经历牢狱之灾,又漫游江湘浙闽,于36岁那年顿悟归隐于桃花坞,成为兼收并蓄、自成一家的书画家“唐伯虎”;顾炎武生活在时局跌宕的明末清初,一生颠沛,却始终身体力行地“崇尚实践、反对空谈”,他走遍大半个中国,为后人留下三十多种、四百多卷著作,在经、史、文、哲各个领域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象最深的是张岱。作者对这个有癖、有疵、有深情和真气的“痴人”情有独钟,字里行间充满了欣赏和敬意。张岱出身于世族大家,自诩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梨园鼓吹、古董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且每一项都钻研精进。他幼年文才早露,然科举之路不顺,从16岁折腾到38岁,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落榜的理由竟是“不合试牍”(答题格式不对),实在匪夷所思!明亡后,张岱回望靡丽奢华、浮华似梦的前半生,写下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艺术性极高的小品文,更在亲历国破家亡之后,以三十余年的心力完成了三百万字的历史巨制《石匮书》,为世间留下一部“史家笔法”的大明历史。在作者徐海蛟眼里,张岱用自己的人生选择,回答了“什么是高贵”——真正的高贵,是面对命运的劫难,仍能保持精神独立,并创造出不朽的价值。
不仅是张岱,书中的十三个“落榜者”“落魄者”,都有着高贵的品格、不屈的意志。他们就像闪耀在历史夜空中的一颗颗明星,慰藉着人世间的迷惘者、痛苦者、失败者。他们有时与读者对话,有时又自言自语,倾诉心声。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谁说命运的责难不是奖赏呢?人生的路不止一条,生命还有更多的可能。”(作者语)
囿于写作目的,当然不能也不必说尽人物的全部经历,因此写作内容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本书的视角非常巧妙,作者围绕“科举落榜”这一共同点,选择人物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阶段、事件,写出了每个人特有的气质和精神,读来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传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七下课文《伟大的悲剧》即出自此书)。茨威格喜欢以小角度看大历史,为世人展现的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或杰出人物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格鲁希在滑铁卢之战中的一念之差;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等人在冰天雪地中面对死神的最后阶段;思想家西塞罗面对独裁者的屠刀,为民主振臂一呼的时刻……茨威格眼中的“英雄”和“重要时刻”,与世人的价值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不知道徐海蛟决定为这些“不朽的(科举)落魄者”作传的时候,是否也受到过茨威格的影响?
要把相隔千百年的人物写得鲜活生动,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还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典籍、传记文章,更需要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度、历朝历代的官员制度、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等等,可以想见作者为此要付出多少心血。自称“南方书生”的徐海蛟,是一位宁波作家。他热爱写作,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山河都记得》《故人在纸一方》《亲爱的笨蛋》等著作十余部,从散文、小说到儿童文学,均有涉猎。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众多文学奖项。
(童红霞,浙江省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