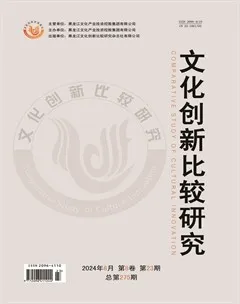新媒体视域下“非遗”女书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摘要:江永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尤为显著。然而,由于传承方式的脆弱性、地域性限制及传播思维的落后,女书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面临着诸多困境。该研究通过对女书文化的传承历史、现状及其面临的传播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创新内容、拓展渠道、提高素养和增强互动等传播策略。研究发现,新媒体为女书文化传播带来机遇与挑战,要求我们在内容创新、渠道拓展、团队专业化及互动增强等方面下功夫。通过实施这些策略,期望能够提升女书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非遗”女书文化;新媒体传播;传承与保护;传播策略;地域性限制;交互型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b)-0038-05
Research 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Relics Female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MA Yitong, ZHOU Hongwei, LI Qingf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only gender character in the world, Jiangyong Nushu has its unique cultural value and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However, due to the fragility of inheritance mode, regional restrictions and backward communication think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Nushu culture 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heritanc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of Nushu culture,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innovative content, expanding channels, improving literacy and enhancing interac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new media bring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Nushu culture, which requires us to work hard in content innovation, channel expansion, team spe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enhancemen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it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of Nushu culture,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Nvshu cultur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Regional restrictions;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mode
江永女书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妇女专用文字,是汉语方言的音节文字。它的发展、传承及其为符号承载的文化信息构成了女书风俗。女书记录的语言是女书流行与众不同的永明土话。女书文字呈长菱形,笔画纤细均匀,似蚊似蚁,民间叫它作长脚蚁字或蚂蚁字[1],因其专为妇女所用,也仅在妇女之间传承,学术界便将其称为“女书”。
1982年,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女书文化,女书正式进入学界视野,由此正式开始对女书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迄今已经40余年。2006年“江永女书”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40多年的研究与保护中,江永女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逐渐从江永走向世界舞台,但同时,女书文化的研究与保护痛点诸多,如因其“人死书焚”这种传承方式带来的研究资料缺失、传播区域化界限明显、难以吸引大众关注等困难。棘手的传播困局也是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共同困境。
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新媒体技术以其独特的传播优势,正在逐步改变着文化信息的传播格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女书文化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来说无疑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于变局中育新机,是探寻女书文化传播新格局的根本逻辑。
本研究旨在探索如何把握独特时代条件下的新型传播模式,打造“非遗”女书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分析“非遗”女书文化的传承历史及现状,总结“非遗”女书文化在传播方式方法和路径选择上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打通新媒体时代“非遗”女书文化的传播渠道。
1 “非遗”女书文化传承概况
1.1 “非遗”女书文化传承现状
1982年,宫哲兵教授在1983年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3]。1983年,江永县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永州市政府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自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宫哲兵教授发现女书,女书正式进入学术视野,国内外研究者络绎不绝,此后40余年,女书文化逐渐由单一的遗产保护转向文化保护与商业化同行,女书文化衍生品与女书文旅产业蓬勃发展。2015年江永县人民政府颁布《强力推进江永女书文化抢救保护与产业发展》,针对江永女书文化抢救保护工作进行相关指导,并对女书产业未来发展提出具体举措,大力发展农、文、旅三项结合产业[4]。
但在女书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也中面临一定的困境和瓶颈,比如,传承人的相继离世和女书文化传统中“人死书焚”的习俗导致的实体材料断层。但随着女书材料数字化的不断发展,相当数量的材料被重新保护收存以供后人研究和学习。
1.2 “非遗”女书文化传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女书文化传承现状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一方面,女书文化的传承正逐渐从单一的女书保护向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转变[5]。一些地方已建立了女书生态博物馆、女书园和女书数字博物馆等,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女书文化为一体,实现了高效存储及检索功能,成为女书文化资源信息数据库。此外,一些非遗传承基地、非遗展示馆和表演场馆的设立,也为女书的传承提供了更多平台和机会。
另一方面,女书传承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首先是女书传承面临着时代冲击。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社交平台和移动设备的普及,妇女们获得信息和交流的途径更加丰富多样,女书作为一种文字的社会功能价值被大大削弱。2004年随着女书最后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老人的辞世,女书进入以保护为主的人为传承时代[6]。其次,女书文化传承与当地传统文化存在割裂情况,面临着失真的危险。女书浸染着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保护和传承离不开当地独特的传统民族风情习俗[7]。然而,目前女书的传承绝大部分局限于对女书文字的学习和文字构成的研究,对产生的背景与当地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并没有进行过多深入探讨,使女书传承逐渐脱离了其相对应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
1.3 女书文化传承价值
女书文字以其独特的象形美、造型美与意蕴美,展现出了显著的美学特质,进而被赋予了深刻的审美意义。女书文字呈长菱形,字体秀丽绢细,造型奇特。这种独特的字形和书写方式使得女书在视觉上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展现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字体柔美、语言优美、作品美观[8]。女书的审美价值还体现在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上,女性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与情感世界中,凭借细腻的感知,创造了专为女性所用,涵盖看、读、唱、写、绣等多种交流方式的独特文字符号,以满足她们多样化的需求,具有极高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可以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素材和资源,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女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民间地域风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女书文化在女性结交文化、传记诉苦文化、歌堂文化、婚嫁文化、女红女秀文化等多个领域均有呈现[9]。从女书文化中,我们还可以提炼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诸如尊老爱幼的伦理观念、夫妻和睦的家庭美德、言传身教的教育智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等。这些传统美德的呈现,不仅丰富了女书文化的内涵,也为人们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女书文化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女书对于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源起、女性文化和民族的流变,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10]。它描绘了女性从沉默到自我表达,再到对话交流的过程,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中的地位和意义都是其他女性文化无法比拟的。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保护和传承女书文化有助于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感和持续感紧密相连,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认同建构基因。女书文化所蕴含的女性的智慧、团结、勤劳、宽厚等品德同国际妇女解放运动争取两性平等、反对歧视女性等理念相契合,蕴藏在女书中的女性身份认同融入了更广泛的世界文化认同,从而有助于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2 “非遗”女书文化传播困境
2.1 代际传播方式脆弱
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民间文学、戏剧/音乐/舞蹈/体育等文化、传统节日及工艺技法等为表现载体,传承的品质和完整度受限于传承人的主观意志和自身素质,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以人为中心的代际传播使得该“非遗”文化极有可能会随着一代人的风华落幕而辉煌不再,传播的力度和范围也时移势迁。女书文化也面临这样的困境,随着2004年最后一位自然传承人阳焕宜老人的离世,女书在社会功能上失去了作为沟通工具的使用价值,转而进入非自然传承阶段,即更加依赖传承人之间的活态传播。
2.2 地域性限制
我国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带有地域色彩,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土高原的陕西汉子激情演绎安塞腰鼓,西湖烟雨中的采茶人经由九道工序只为制得一杯上好龙井……这些极具地域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长在其所属的文化环境内的,一方面享受着地域带来的独特红利,但另一方面又无法脱离地域的限制[11]。女书发源地位于湖南省南部江永县,这里属南岭山脉的山地丘陵区,山川地势大体为“七山半水二分半田”。相对闭塞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之当地人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使得江永女书仅流传于江永县本地和周围地区,对于大众而言知名度较低。
2.3 传播思维落后
由于女书“非遗”文化传承人群体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部分传承人排斥当下新兴传播方式,不能够与时俱进,陷入一种内漩涡式的自我欣赏。以易于成为传播热点的女书文创产品为例,目前的女书文创产品仍以书画、帕面等传统呈现形式为主,所面向的受众群体大部分为对女书有一定了解和基础的“圈内”人,以收藏目的为主,受众群固化、产品缺乏互联网思维、对下沉市场完全忽视等问题积弊已深,整体呈现古板、颓靡态势[12]。
3 新媒体对“非遗”女书文化传播的影响
3.1 新媒体视域下“非遗”女书文化传播的机遇
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对传媒格局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许多新媒体平台自身既是具备通信功能的重要通信技术平台,又是兼具跨媒体传播功能和可移动的媒体平台,为信息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近年来,以短、平、快为特征的短视频迅速走红,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生产转向维系话题导向和内容质量,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延长话题的长尾效应,这为用户加入女书相关话题讨论、参与话题的二次生产奠定了一定基础。主流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强互动性则为受众提供了参与女书文化传播的机会,这种强互动性的创作交流带动了女书文化的“微传播”。“微传播”既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也不同于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而是一种裂变传播,其传播速度更迅捷,传播密度更深密,传播方式也更便利。
除了对用户自主生产内容的重视之外,在新媒体影响下,互联网用户更看重内容生产的社交属性。热点话题往往能够成为当下青年群体的社交突破口,若话题本身具备一定引发社会讨论的属性,则更易成为用户进行网络自我呈现的工具。用户通过评论、分享、点赞、二次创作等方式参与到女书文化的传播中,在交流碰撞过程中形成社群效应,形成全新的“女书文化交流圈”,促进文化共鸣、共建,使女书文化更为广泛地向大众渗透。同时,“非遗”女书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资产。
3.2 新媒体视域下“非遗”女书文化传播的挑战
女书作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化现象,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与新媒体追求快速消费的特点形成了矛盾。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量巨大,内容更新速度快,用户的注意力容易被段落式、娱乐式的“碎片化信息”分散。在快节奏的信息流中,人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深入了解女书,女书文化的深度内涵难以得到充分展示,导致女书文化的传播效果受限。
此外,碎片化传播惯性导致零散信息泛滥,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传播内容日趋娱乐化与商业化。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女书文化的内核在传播过程中被简化或曲解,女书的独特价值和深层意义因为追求点击率和浏览量而被忽视,形成表象化的女书文化狂欢,甚至出现造假字、假文本、造假女书村及学术造假等一系列的“博眼球”操作,从而导致大众对女书文化及文化圈产生误解,加深文化与受众之间的隔阂,偏离了女书文化传播的根本目的。
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女书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另一挑战是数字鸿沟,即不同群体在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方面的差距。这种差距可能导致一些非遗传承人无法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尤其在女书传承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下,老一辈女书传承人缺乏参与新媒体传播的经验,无法将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保护、传承,从而使女书文化爱好者、后来传承参与者无法获得重要的文化信息和资源,阻碍文化传承发展的进程。
4 新媒体视域下“非遗”女书文化传播策略
4.1 创新方式: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
女书文化传播的痛点之一就是后继力量疲软,由于传承人群体老龄化明显,中青年力量薄弱,女书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呈现出明显落后于互联网时代的趋势,如以枯燥的科普、会议记录等形式为传播主体方式,体量冗长、趣味性弱、内容质量差等现象普遍存在。所以女书文化要想在新媒体时代中走出符合自身特性的特色传播之路,要做的就是创新传播方式。
当下互联网传播具有快节奏、个性化、社会化传播等特性,“非遗”女书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应做到顺势而为,以谋求年轻受众的关注。例如,在短视频赛道选择追踪实时热点进行创作,多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精简内容提高视频质量,采用沉浸式体验或文化短剧等形式进行短视频内容创作,带领意向受众身临其境式地体验“非遗”女书文化的内涵与意义。
4.2 拓展渠道:开辟全媒体传播矩阵
以往女书文化传播主要阵地为女书文化相关产业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湖南江永县当地的官方文旅平台等,传播途径较为局限,受众群体单一固化。在新媒体时代,“非遗”文化本身即可作为强有力的文化IP进行宣传,构成全媒体传播矩阵。“非遗”女书文化IP化是全媒体营销的第一步,以文化IP为阵地,在抓好现有流量基础上,将宣传重心逐渐转移至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热门社交媒体平台,与众多KOL联动广泛开展话题营销。同时,坚持以政策为导向,联合江永官方文旅平台,在宣传非遗女书文化的同时为江永文旅引流,以实现以文促旅、文旅共进的宣传格局。
4.3 提高素养:选拔专业化传播团队
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和专业技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议程设置和传播效果达成。此处的“专业化”不仅指选用在传播和宣传方面具有较高才能、丰富经验的精英人才,也包括对女书文化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具有热情并经过系统学习的高素质人才。只有当传播者发自内心地认可、认同“非遗”女书文化的理念内涵时,才有可能创作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才更有可能打动人心。任何文化的传播都不能流于表面,切中受众痛点的推广才是最容易引发共鸣进而引发二次传播的契机。任何文化的“破圈”离不开背后专业而真诚的传播团队。
4.4 增强互动:重视交互型传播模式
当互联网的内容创作主导权从专业生产者转移到用户身上时,交互性就开始成为移动互联时代最不可忽视的传播规律之一。微博热搜、抖音热点、直播互动等途径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与受众进行实时交互的方式手段。从单纯的观念输出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传播模式,交互型传播能最高效地进行“非遗”女书文化IP推广宣传。
互动的行为路径由内容生产者—受众—内容生产者构成,受众对内容生产者的积极反馈对于内容优化、结构升级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当代“非遗”传播者的必然选择。某些主播接地气、近群众,真实展现乡土之间自然流露的国风古意,切实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宣传,人民群众才愿意高举之。“非遗”文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可视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双向奔赴。
5 结束语
通过梳理女书文化传承历程,以及对新媒体在女书文化传播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对“非遗”女书文化的新媒体时代传播进行了全面探讨,归纳出创作高质新内容、开辟传播新矩阵、培养专业新团队、打造传播新模式等策略。关注新媒体技术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与发展,不断优化和完善传播策略,相信女书文化这一璀璨的中华文化瑰宝,定能在新媒体的助力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刘洋洋,闫静.从女性身份认同到文化认同:女书档案资源的价值流变与开发利用策略[J].档案学研究,2023(3):104-111.
[2] 刘彤.新媒体为传统文化传播带来机遇和挑战[N].中国教育报,2014-09-24(6).
[3] 贺军.非遗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研究:以江永女书为例[J].传播与版权,2022(7):89-92.
[4] 谭世平.江永女书的跨文化传播对策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10):80-82.
[5] 何华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6] 杨慧君.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构建[J].语言战略研究,2023,8(6):63-73,5.
[7] 毕心凝,张玉容.新媒体视域下非遗纪录片的差异化创作策略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3,14(17):237-239.
[8] 周子煊.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策略研究[J].新闻文化建设,2023(2):62-64.
[9] 林宜竹,陈晓玫,吴键洪.新媒体经济视域下非遗服饰的传播发展路径研究[J].化纤与纺织技术,2023, 52(2):4-6.
[10]吴丽.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4(4):12-14.
[11]余鸿,杨永建.基于ERG理论的农村人才回引模式创新[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 18(3):94-100.
[12]洪明云.在幼儿教育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策略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1):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