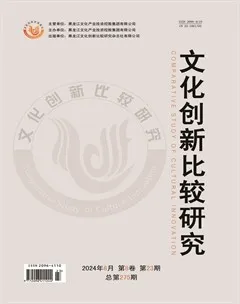“差点儿VP”的论辩与预期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该文将从语义角度对“差点儿VP”进行探析。首先,引用论辩理论推断出“差点儿”是具有积极义的正向论辩算子;其次,引进预期理论,指出在特定语境中,说话双方会对事件实现的可能性进行预判,“差点儿”能够在不同事态的指引下,反映出相异的预期状况:当“VP”代表好的事态时,话语含遗憾义,当“VP”代表坏的事态时,话语则含庆幸义。论辩理论和预期理论间既存在联系又有区别,共同作用于“差点儿VP”结构中,帮助推进其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揭示。最后,将“概率”作为副词研究的语义特征,根据该会话中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推断其具有反预期性。得出结论:在正向心理期待和反预期性特征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差点儿VP”完整语义的构建与识解。
关键词:“差点儿VP”;乐观原则;论辩理论;预期理论;概率;反预期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b)-0020-0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bate and Expectancy Theory of "Almost VP"
FENG Xuey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concept of "almost VP" from a semantic perspective. Firstly, by citing argumentative theory, it is inferred that "almost VP" is a positive argumentative operator with positive connotations. Secondly, introducing the expectancy theor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a specific context, both speakers will predic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vent being realized, and "almost" can reflect different expected situation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hen "VP" represents a good situation, the discourse contains regret, and when "VP" represents a bad situation, the discourse contains happiness. There are both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rgumentative theory and expectancy theory, which work together in the "almost VP" structure to help reveal its linguistic commonalities and individualities. Furthermore, by studying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probability" as an adverb,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event in the conversation has anti expectedness based on its likelihood of occurrence. Conclusion: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and negative expectations,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lete semantics of "almost VP"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Almost VP"; Optimistic principle; Debate theory; Expectancy theory; Probability;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沿袭朱德熙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差点儿”的释义为:“副词,表示某种事情接近实现或勉强实现。如果是说话的人不希望实现的事情,说‘差点儿’和‘差点儿没’都是指事情接近实现而没有实现……如果是说话的人希望实现的事情,‘差点儿’是惋惜它未能实现,‘差点儿没’是庆幸它勉强实现了。”[1]这个结论也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被称为“企望说”。
1 论辩理论与预期理论概述
“论辩理论”是1989由杜克罗特提出,该理论主张语言不只是表达具体内容、传递言语信息,并且具有一定的“论辩性”。所谓“论辩性”,概括来说,即某个字词、短语、句子具有一种论辩潜能,能够为听者提供适用的线索,引导其推理出预期的结论。这也是在日常言语会话中形成的产物:言者企图用话语影响听者的思维、态度甚至行为,而听者也努力贴近言者想要传递的信息、情感。对话双方在特定语境中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出认知协调的意境状态,帮助呈现出较好的互动效果。
荷兰语言学家费尔哈亨于2014年发表的《交互主观性的构建:话语、句法与交际》中补充到论辩还具有“方向性”[2],提出正值和负值两种类型。比如英语中的barely 与 almost的字面意义是相近的,前者指的是“只差一点就没能到,勉强达到”,后者则是“只差一点到,几乎已经达到了”,都表示在临界点左右,前者在右、后者在左,从而得到的论辩方向是截然相反的:barely表示虽然达到了,但说话人认为不是靠自身稳定发挥达到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而是一种消极的心态;而almost就有着相反的感情色彩,即虽然没能达到标准,但说话人坚信自身有实力能够达到,这次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得出结论:barely 是一种负向的论辩方向,而almost是一种正向的论辩方向。
综上,说话人凡持有积极的心态,不论结果如何,所运用的语言单位都具有正向的论辩方向,即持有正面意义的立场,含有正向心理期待。
1.1 论辩理论与“差点儿VP”
袁毓林证明“差点儿VP”的断言意义是预设和推演的合取结果,即“接近,但是没有VP”[3]。“差点儿”在用法上与almost相近,都表示“只差一点就到了”,结果都“没VP”,都是一种否定性副词。那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差点儿”同样也是正向论辩算子呢?通过举例来分析。
例1:他<差点儿>打破纪录,只怪运气不好,下次肯定没问题。
例2:?他<差点儿>打破纪录,可能只是运气好,下次就不一定了。
抛开语境,区分不开例1、例2前半句的语义,但结合后半句可知,例1表达的是“almost义”,而例2表达的是“barely义”,不难发现日常生活中听到前半句,听者可以很自然地顺接到“差一点达到,但未到”的语义,即例1这种情况,很少或者几乎不会出现例2这种语义解读,这在后文“预期理论”板块将会引用“概率”具体分析原因。
例3:他<勉强>打破了纪录,纯粹是运气好,下次就不一定了。
例4:?他<勉强>打破了纪录,下次肯定还没问题。
与“差点儿”形成对照,“勉强”本身带有“barely义”,表明说话人相信自己有能力打破纪录,持有消极的心理态度。所以,承接否定小句“下次就不一定了”更自然,如例3;而承接肯定性小句现实中就会定义为歧义,会引起小句间语义的不连贯,如例4。
“差点儿”同“勉强”的情况截然相反,“差点儿”后可跟随两类情感意义的词:一是消极义的VP,“差点儿VP”表示VP所指示的事件实际并没有发生,说话人内心也不希望事件发生,因此含有某种“庆幸义”; 二是积极义的VP,此时“差点儿VP”则表示说话人其实希望事情实现,但只是接近实现,最终并没有如愿实现,含有“遗憾义”。比如,说话人说“差点儿落榜”,“落榜”是消极意义的VP,其内心肯定不希望落榜,听说双方处于一种积极性的认知状态,因此能够顺利传达“庆幸自己没落榜”的语义。反之,若说话人说“差点儿上榜”,“上榜”是积极意义的VP,听话人也能顺利接收“说话人为没能上榜感到遗憾”的信息。
再结合袁毓林所说:“语言表达的组配限制的理据是人类心理的乐观原则,即通过心理实验所证明的‘乐观假设’,人总是乐于看到和谈论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好的事情、好的品质,摒弃坏的一面。这也造成一种普遍的人类倾向,往往积极评价的词语要比消极评价的词语用得更频繁、多样和随意。”[4]“差点儿VP”符合乐观原则,不管VP是积极意义的还是消极意义的,说话人都持有乐观的情感态度,听话人也孤注一掷地做出积极的判定,认为说话人是朝着好的方向进行陈述的,便能够与说话人达成认知协调,进而完成整个结构的语义识解。综上可得出,“差点儿”含有一种正向的心理期待。
1.2 预期理论与“差点儿VP”
上文说到“差点儿VP”有“接近,但是没有VP”的语义,但是其比“接近VP”包含的语义特征要更丰富、多元化。渡边丽玲提出“差一点”式所叙述的事件在言者心中属于非寻常的事件,比如“摔倒”“落榜”“考满分”等,对于言者而言,他并不会经常发生这些行为[5]。与论辩理论不同,这里在意的不是VP是否积极,而是侧重于VP是不是寻常事件,这属于接下来要说的“预期理论”的范畴。
范晓蕾认为实际语境中“差点儿VP”常伴有语境预期,即“在特定语境里,言谈双方预先持有的信息,是对事件实现的可能性或合理性的预期状况”[6]。具体而言,它指的是会话中“VP实现”的惯常状况、标准规范等问题皆已是说话双方预先所持有的共识,这种建立在有共同背景信息的基础上的对话现象,属于“语用预设”。首先,上文提到“差点儿VP”就反映了惯常状况,对说话人而言不是常用的事件;其次“差点儿VP”也是有固定的标准的,不能是模棱两可的,“落榜了”就是已经没考上,“摔倒了”就是已经摔过了,不能是要摔不摔的状态;最后,结合论辩理论可知,作为一个正向论辩算子,说听双方都努力往积极方向靠近,达成认知协调,即持有共识。以上三点证实“差点儿VP”有VP的语境预期,预期理论的加成可以增加语言的表达功用,达到不同的效果,如果不引用其他相关变量,单纯看“预期”可分为三类。
一是预期以内,即听者的认知背景与说话人保持一致,说话人传递的信息与听话人预期是一致的,就能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良好沟通效果,让听者有强烈的参与感,形成接受前的期待定向,能够快速理解、帮助识解。听者接受信息时所具有的主体条件和期待心理导致其接受范围相对确定,并因此构成了接受可能实现的限度。他能够敏感地感知与自身具有“同构性”的话语。
二是预期以外,即听者的认知和说者不同,或有细枝末节不一致,不一致的是部分就是反预期信息,这类信息可以给听者带来出其不意、预料之外的新奇体验,利用文学理论的术语可以称为“超出期待视野”,虽不能构成默契,但能设下悬念、制造反转,给听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三是听话人没有预期的新信息,即“中性信息”,也就是说者说话是不带有任何情感偏向的,不刻意地去引导受话人,任其自由地思考、理解和判断,也就是减弱了“交互性”,增强了个体作用力。
以上是不结合任何变量的情况,本文将在正文第二部分中结合“概率”探析其属于什么类型的预期,具有何种特点等。
1.3 “论辩”与“预期”关系辨析
1.3.1 “论辩”与“预期”的联系
不论是在论辩理论还是预期理论中,“差点儿”都具有相同的特征。
一是说者对“差点儿VP”的VP事件都有明确的情感判断。论辩理论中,其随不同性质的事件类型,表庆幸或表遗憾;预期理论中,说话人在说话前也是确定好想要打造的解读效果,再甄用恰当的词语。
二是听者对语言有一套相近的解读模式,都要积极地配合说者的引导和指向。论辩理论中,如若听者不配合,就无法准确判断“差点儿摔倒”是“庆幸没摔倒”还是“遗憾摔倒了”;预期理论中,如果听者拒绝接收说者的“预期信息”,可以正确理解表层语义,却无法更深层次地进入最佳对话效果。
三是说听双方都有各自的认知背景,不论一致与否,说话人积极引导,听话人积极推理,相互作用,构成完整的语境。
正因为二者有共通之处,所以将论辩理论和预期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也能共同为“差点儿VP”语义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为语义的识解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1.3.2 “论辩”与“预期”的区别
在听说双方的主观交互性方面,二者有无法割裂的联系,但论辩理论和预期理论存在不同的侧重点。上文也有提及,“和论辩不同,预期在意的不是VP是否积极,而是侧重于VP是不是寻常事件”。
具体而言,论辩理论侧重于“主观性”,即说话人对所描述的事件的定性,是积极义的“差点儿VP+”还是消极义的“差点儿VP -”,在语义上分别指向“遗憾”和“庆幸”,但在情感上都是积极向上的,是正向的心理期待,通常在充满希冀的语境中出现,反之则会用“勉强”类词语替换;而预期理论则更倾向于“客观性”,即原先生活经验影响VP事件,该事件发生的次数越多,越能达到正预期,发生的次数越少,则越能靠近反预期。而“差点儿VP”中的事件往往是不寻常的、较为罕见的,所以更偏向后者,接下来将引用“概率”的概念进一步探析这则规律。
2 “概率”及“差点儿VP”的反预期性
2.1 “概率”及其四大类型
某事件在同一条件下出现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情况时,表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量,我们称其为“概率”。《现代汉语词典》中概率的释义是“子集量/总集量”,分子表示对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分母表示该类事件发生的整体可能性大小。
张谊生对副词进一步细化,并设立了“概率副词”这类词汇;石定栩、孙嘉铭通过对比频率副词“常常”与概率副词“往往”,得出概率副词的基本特征[7];陈振宇对“概率”在汉语中的作用进行了归纳,使用自动蕴涵计算并设计了“主观性指数”的衡量指标,帮助区分主观副词和客观副词[8]。周韧根据语义结构理论,将“概率”作为虚词分析的语义特征,探析“果然”类和“确实”类确认义副词在句法上的异同[9]。
概率副词是概率模糊而主观的表达:说话人使用副词,在该事件发生前说话人对其实现可能性就有了判定。如“张三<经常>去那家超市买东西”,不以具体数量来客观描述,而是用副词“经常”表示去的次数之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观性。虽然“概率”只能主观地表达事件发生的频率,却也能对预期理论做精细化表述,可利用概率问题来对预期进行分类。
凯特·科恩的研究涉及有关预期数值的问题,其中假设正预期事件取值为1,反预期事件取值为0。概率数值的引入,不仅能区分事件的正、反预期,说话人利用其主观能动性,还可以在除整数取值外,从0到1之间的小数点取值,得出更精确的结论[10]。比如同一个句子“我<果然>通过了考试”,说话人事先准备充分,对自己的成绩充满信心,认定某个事件实现的概率过半,那么0.5≤“果然”的预期真值<1,甚至可以根据自信程度缩小范围,0.5≤“果然”的预期真值<0.7或者0.7≤“果然”的预期真值<1等任意个区间。但这也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具有主观性,说话人根据自身的语感判断会得出不同的数值,可以说每个个体对概率数值的判断会有一定差异,影响因素有很多,如生活经验、情感态度、个性喜好等。
综上,引入概率特征后,可把预期事件按发生的概率从高至低分呈:正预期事件、高概率预期事件、低概率预期事件及反预期事件。其中,正预期事件即真值数值为1的事件,即发生的事件完全在说者的预料之中;高概率预期事件是0.5≤预期真值<1的事件,根据个体情况不同,在此基础上区间还可能变化;低概率预期事件是0≤预期真值<0.5的事件,区间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反预期事件则是数值为0的事件,即结果和预期背景相反的事件。假设概率副词为“×”,那么“×摔倒”就是“没摔倒”,“×没考过”就是“考过了”。代入“差点儿”符合条件,初步推测“差点儿”可能具备反预期性。
2.2 “差点儿VP”的反预期性
海涅和胡内马尔提出反预期概念,随后有关研究也层出不穷。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吴福祥指出:“反预期揭示说话人的视角和态度,是语言主观性的集中表现。”[11]进一步发现,还能通过语序或结构式等语法手段来展现反预期性。参看上文,“差点儿VP”必须有预期语境。
例5:我差点儿赶上末班车,明天一定能赶上。
例6:?我差点儿赶上末班车,明天就不一定了。
在实际生活中,听到前半句,可推测出例5类语义概率显然要大于例6类语义的概率,例6虽合乎语法规范,但语义逻辑不合规,往往会这样表达:“勉强赶上末班车,明天就不一定了”。分析这两句的语义结果,例5是“没VP”,例6是“VP了”,前者是反预期,后者是正预期。
再者,实际言语环境中“差点儿VP”指代的VP事件绝不可能是合预期事态,在形式上就表现为它会排斥与“果然”类的合预期副词组合搭配,但却能与“居然”类的反预期副词自由搭配。例如:
例7:张三平时成绩很好,大家都相信他能考上清华,<*果然/当然/自然>差点儿考上了清华。
例8:张三平时成绩不好,大家都认为他这次也考不好,但他<居然/竟然>差点儿就考上了清华。
观察发现“VP——考上清华”是该格式的语义核心,是“果然”“居然”指向的目标成分。两则语例的结果都是“没考上,但距离考上只差一点”,但例5的前提是张三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按照正常发挥的水平是完全有能力考上清华的,如果这里用合预期副词搭配,不符合语义逻辑;而例8前提是本来大家就对“张三考上清华”这个事件不抱期待,结果张三只差几分就考上了,是超出预期的,所以和反预期副词适配。
这也就表明了“差点儿VP”中的VP与合预期义冲突,与反预期义相容。既然“VP”是反预期事态,且是格式中的语义核心,那么“差点儿VP”的语义“接近VP,未达到但快达到”自然也就具备了反预期性,可以说“差点儿”编码了反预期性,是一种反预期标记。
3 正向心理期待和反预期性:“差点儿VP”的完整语义构建
综上所述,论辩理论多倾向于“差点儿”的语义构建和识解,“差点儿”可被视作一个正向论辩算子,那么“差点儿VP”体现了言者持有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且听者也会默认“差点儿”是个正向的表达,因此其会将结果自然而然地往好的方面去考虑,即当“VP”代表好的事态时,虽然“差点儿VP”表示的是该状况最终未能实现,话语中包含遗憾意味,但说话人的心态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听话人将其意义识解为“没VP”;反之,当“VP”代表的是不好的事态时,“差点儿VP”表示该状况未实现,说话人的话语中透露幸亏没有发生,听话人将其意义识解为正向的“没VP”,即没有发生才是好事。因此,通常是说话人在积极的态度下输出“差点儿”,并引导听话人对整个句子结构做出正向的语义解读,起到传递正向情感的互动功能。
预期理论则多强调“差点儿VP”中的“VP”语义的构建与识解,VP发生的概率高低影响了“差点儿”的预期类型。由于“差点儿”后通常顺接不寻常事件,是始料未及的、难以想象的事件,如“本只能考10分的张三,这次考试差点儿考了满分”,“差点儿VP”中的VP明显是反预期事件,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差点儿”是反预期标志,具有反预期性的特征。
具有正向期待性的“差点儿”与反预期事件“VP”共同构建出“差点儿VP”的完整语义,论辩理论和预期理论同样能在语用上起到作用:一是给说听双方以积极的话语情感方向,帮助在具体语境中理解对方的态度;二是“反预期”的反转魅力能给听者带来独特的语感体验,“差点儿VP”是“没VP”,再加上两种不同语义的识解,能打破常规的期待视野,产生新奇的解读感受。
4 结束语
本文探求的是找到论辩理论与预期理论的关系,以及利用二者的功能去识解“差点儿VP”的语义,得出使用该结构时,描述的总是罕见的、不常发生的事件,反映的总是积极正向的情感态度。随后,进一步引入“概率”的概念,对其反预期程度展开探究,完整地构建出“差点儿VP”语义识解框架。同时,本文也力求为论辩理论、预期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范例、语料数据,但是对于事件罕见的程度,即事件发生的具体概率数值,还需进一步寻找语料,充实论述。
参考文献
[1] 朱德熙.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 ARIE V.交互主观性的构建:话语、句法与交际[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3] 袁毓林.“差点儿”和“差不多”的意义同异之辨[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6):66-75.
[4] 袁毓林.“差点儿”中的隐性否定及其语法效应[J].语言研究,2013,33(2):54-64.
[5] 渡边丽玲.“差一点”句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81-89.
[6] 范晓蕾.再说“差一点”[J].中国语文,2018(2):207-222, 255-256.
[7] 石定栩,孙嘉铭.频率副词与概率副词:从“常常”与“往往”说起[J].世界汉语教学,2016,30(3):291-302.
[8] 陈振宇,王梦颖,陈振宁.汉语主观副词与客观副词的分野[J].语言科学,2020,19(4):395 -410.
[9] 周韧.汉语副词语义分析中的概率特征:以一组确认义副词的辨析为例[J].汉语学报,2022(3):2-18.
[10]凯特·科恩.语义学[M].2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11]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J].中国语文,2004(3):222-231,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