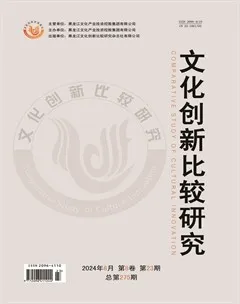原著文学与改编电影中的不同叙事语法比较
摘要:电影叙事学研究起源于文学叙事学研究,然而电影发展至今,早已将文学叙事学理论进行了充分的“电影化”的改造,如今,文学场域和电影场域中的叙事语法已经存在显著差异。该文以《潜水钟与蝴蝶》的原著文学与改编电影为例,从经典文学叙事理论出发,从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和叙事视点三个维度对文学叙述语法和电影叙事语法进行比较分析,分别阐释了在进行影视改编时,如何对文学中叙事语法的不同维度进行电影语言的编码,并得出结论:经过对不同叙事语法的运用,文学语言比电影语言更加抽象,而电影语言比文学语言更具灵活性与表达张力。
关键词:电影改编;叙事语法;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视点;《潜水钟与蝴蝶》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b)-0006-06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Narrative Grammars in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and the Adapted Film
—Taking 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as an Example
JIANG Wenx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film narratology originated from the study of literary narratology. However,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theories of literary narratology has been fully "filmized". Nowaday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arrative grammar between literary field and film field. Based on classical narrativ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takes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of 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and the adapted film as examples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from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narrative time, narrative space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to explain how to encode these narrative grammar of literature into film languag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narrative grammars, literary language is more abstract than film language, while film language is more flexible and expressive than literary language.
Key words: Film adaptation; Narrative grammar; Narrative time;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perspective; 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电影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其叙事性与文学的叙事性有着相当程度的渊源关系,电影叙事学理论研究也一直受到文学叙事学研究的影响,电影叙事学领域的学者常常运用文学叙事学相关理论术语与结构框架,以文学叙事为基准,分析电影叙事相比于文学叙事的异同之处。这些异同在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中表现尤为明显。电影《潜水钟与蝴蝶》改编自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鲍比的同名自传体随笔集,描写的是作家在突发“闭锁综合征”而全身瘫痪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本文通过对原著文学与改编电影的对比,分析出二者在叙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叙事语法上的异同,探究这部电影是如何在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与叙事视点上进行电影化的改编,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使该片最终赢得第6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 叙事时间
热奈特在麦茨理论中的双重时间,即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基础上,架构出时间顺序、时距和频率三个维度。其中,时间顺序是指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时间顺序和在叙事中出现的伪时间顺序的关系;时距是指事件在故事中所发生的时长与在叙事作品中所占有的叙事时长(即伪时距)的关系,热奈特也称之为“速度关系”;频率是指事件在故事中发生的频次和事件在叙事中被重复的频次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架构运用在小说等强叙事性形式中,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指向,但用来分析《潜水钟与蝴蝶》的文学原著所采用的随笔形式,就需要进行更具创造性的灵活掌握。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由于《潜水钟与蝴蝶》带有自传体回忆录性质,因此在这部作品里可以将热奈特所指称的“故事”看作是鲍比的整个人生,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三个维度的分析。
1.1 时间顺序
就时间顺序这一维度,顺序和倒叙,或由热奈特称为“第一叙事”和“第二叙事”,在原著和改编电影中都被交错使用。但此处的倒叙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狭义范畴内的先交代结尾后讲述故事的倒叙,而是包括了插叙、省叙等其他非顺序的叙事形式。《潜水钟与蝴蝶》原著与改编电影中的顺序时间都体现为时光在鲍比日复一日地瘫痪与复健中流逝,而倒叙则体现在鲍比的回忆及幻想之中。虽然如此,原著与改编电影在时序的具体表现手法上还是有不小区别。由于原著采用随笔的形式,章节与章节之间的时间关联有时比较松散,并非每一章节都表现出明显的时间顺序,比如,在《爱吹牛的人》这一章,鲍比回忆起了他曾经的一个同学很爱吹牛。这一章节与前后文在情节上的关联不大,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述,是被插入的相对独立的一段回忆。这在文学上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手法,热奈特称之为“外倒叙”,因为它与“第一叙事”关联不大,也不会干扰“第一叙事”。与之相对的称“内倒叙”,指涉及“第一叙事”的故事线,并会对第一叙事造成矛盾冲突的叙事,比如,书中的《腊肠》这一章节中,鲍比通过护工经常说“祝你好胃口”这件事,伤感于他现在无法独立进食,进而联想到他曾经善于品尝美食,这与他如今的悲惨状况形成了强烈对比。在《潜水钟与蝴蝶》的改编电影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许多内倒叙的内容被保留了下来,而外倒叙的内容则全部被删除,比如,电影中有一大段描写鲍比幻想自己大口吃东西的场景,而并没有出现关于他爱吹牛的同学的身影。这是由电影的特性所决定的。普通的故事片很难表现与主线完全无关的外倒叙内容,因为这会造成影片结构的松散,让观众有机会跳脱出荧幕中的封闭空间,进行相对理性的思考,进而产生间离效应,这恰恰是故事片发展至今一直尽力规避的效果。
1.2 时距
就时距而言,热奈特提出了4种时间与伪时间的叙事组织形式,分别是停顿、场景、概要和省略。停顿是指叙事时间很长而故事时间为零,比如,细致描写物体的外表;场景是指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相等,比如,二人对话;概要是指叙事时间小于故事时间,比如,“他在香港住了一年”;省略是指叙事时间为零,而故事却已经发展了,比如,上一章节以“我下午五点钟回到了家”结尾,下一章节以“我早上九点钟开始上班”开头。《潜水钟与蝴蝶》的原著中主要被运用的是概要和省略的形式。这在客观上应该是由于作家只能通过左眼与人交流,很难运用“停顿”对每一个行为、每一件事物做出具体、详细的描写,也很难与人发生实际交流的“场景”。而文学中的概要和省略两种形式常被认为对应着电影语言中的蒙太奇与剪接。例如,原著中写到鲍比的亲朋好友在世界各地祭拜不同的神仙为鲍比祈福,这是典型的叙事时间小于故事时间,在电影中就被表现为一段各种教徒进行不同宗教仪式的平行蒙太奇,虽在电影语言上的创造性略显不足,但十分经典。而原著中的“省略”手法在电影中的表现值得更加着重地分析。比如,原著中用“是礼拜天了”这句话来开启《礼拜天》这一章节,它与描写医院平日状态的上一章节间一定存在着未被描述的时间空隙。文学作品只需要短短几个字就可以将这一时间跨度交代清楚,而在电影里,一些描绘空荡的医院的镜头被剪接在一起来表现礼拜天医院的特殊状态。然而可以发现,清楚地交代出这是“礼拜天的医院”的画外音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了这一信息的补充,观众只能看出这是非常规状态下的医院,但无法通过画面确切地知晓这些镜头描绘的是礼拜天,这证实了查特曼所提出的文学中的“省略”与电影中的“剪接”的区别——剪接“简单地呈现空间的转换……而不是叙事话语的组成部分。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并没有特殊的叙事意义。”也就是说,它必须借助特定的语境来表达被省略的时间跨度。电影对原著中所少见的“停顿”和“场景”也有一定的运用。一般情况下,在故事片中,停顿这一手法很少运用,因为它意味着运动的停止,这在追求流畅性动作的常规电影语言中不太受欢迎[1]。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潜水钟与蝴蝶》中,一个将近半分钟的“停顿”被用来表现窗户与窗帘,这一镜头虽然在叙事上稍显迟滞,但是符合人物瘫痪在床的身体状态,所以十分恰当。而“场景”的构建在电影中更加明显,不同于在原著中被一笔带过,鲍比与护工通过眨眼选字的方式进行交流的具体场景在电影中被实在地表现出来,此时,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一样漫长。这一方面展示了鲍比与人沟通的困难程度,另一方面,随着鲍比与护工配合愈加熟练,影片中二人沟通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仿佛暗示着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3 频率
就频率而言,热奈特将其分为4个主要关系类型,即讲述一次发生一次的事、讲述一次发生多次的事、讲述多次发生过一次的事、讲述多次发生过多次的事。在《潜水钟与蝴蝶》原著里,主要运用了讲述一次发生多次的事情这一手法,主要特点是经常出现一些特定词语,比如,“每一次”等。可以看出,作者描写洗澡和去露台上放风等,很多时候都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次”,而是指“每一次”,热奈特也称这种叙事手法为“反复叙事”。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描写时实际上忽略“每一次”的特点,只保留“每一次”间的共同点[2]。上面曾经指出,鲍比由于身体原因,很难对事物进行细致描写,所以他需要提炼出相似事件中的共性以凝练语言。这一文学风格在原著中可与作品内容相辅相成,因为它可以强烈暗示出鲍比瘫痪在床所感受到的困顿与枯燥,然而它却会对电影改编造成一定的困难,因为一般故事片强调的是要表达具体形象而不是抽象概念,在整体上追求真实感与现实感,因此电影需要反向对这些文学中提炼出的“共同点”进行再加工,添加具体细节,创造既生动又典型的具体形象。同时,电影画面的特指性很强,在影像上几乎不能做到“一次讲述多次发生的事情”,而只能做到“一次讲述一次发生的事情”。以洗澡的场景为例,电影中出现了一次鲍比洗澡的场景,那么这一场景所指的就只能是这一次具体的洗澡活动,而不能是之前或之后的某一次或每一次洗澡。当然,观众可以从这一次洗澡中推测出鲍比每一次洗澡的状态,但依然不能用这一次洗澡来指代其他时间的洗澡。在电影中想要“一次讲述多次发生的事情”,一般只能通过对白或独白,《潜水钟与蝴蝶》的改编电影就是采用了独白的手法,比如,鲍比的内心独白说道“我害怕星期天,在别人帮你打开电视时,千万不能选错频道,否则就是悲剧的开始,可能要等三四个小时才有个好心人来换个频道”,这里独白中的“星期天”显然是指在医院里的每一个星期天。
2 叙事空间
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空间”与电影作品中的“故事—空间”各自拥有鲜明的特点,构成了彼此的重要区别。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空间”长于抽象性,需要以读者的想象能力为中介,将文字还原成画面,因此文字可以不必具有很强的场景指向性,也就是说,文学中的事件不必被指明发生在某个具体地点,而仅是发生在读者意识领域,让每一个读者可以做出各自不同的想象。相比之下,电影中的“故事—空间”是十分直接、具体的,很难激发“无地点性”。在本书原著中,鲍比提到,有时爸爸“会打电话给我,他摇颤的手握着听筒,我听见他颤抖而温热的声音传到我耳畔”。这里只交代了动作,但是并没有交代动作发生时二人所处的具体空间,但在电影中,不存在可以在非具体空间中发生的动作,于是,画面中交代鲍比是坐在病房里的轮椅上,爸爸则身处家里书桌前,二人所处的空间都相对封闭,暗示二人被束缚在彼此所身处的空间的困境。
文学与电影中“故事—空间”的第二个区别在于银幕上的画面无论如何都会被限定在特定的边框内。此时,银幕上所呈现出的画面内容被称为“明确的故事空间”,而被排除在取景器之外的一切被叫作“隐含的故事空间”,也有学者称之为“场景”与“外场景”。更进一步来说,外场景与场景之间有着时间上的关联——外场景是场景潜在的过去或者未来。随着摄影机的移动或剪辑的使用,外场景有时会变成场景,场景也可能变成外场景,电影就是在这种外场景与场景的转换中产生的。然而,文学描写所引起的形象想象不被某种形式的画框所限制。虽然如此,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具有单线性,这意味着它不能在同一时间里既描写行为又描写环境,而必须在保持叙事连续性的基础上做出选择与牺牲[3]。在原著中的《轮椅》一章,病房中的环境是许多“穿白袍的人在我的房间里”,而这些人做的动作是将轮椅推进病房并为“我”穿衣服、把“我”抬上轮椅[4]。此时,环境与动作应该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在文字描写时则必定有先后顺序,鲍比选择的是先描写环境,再把几个动作连在一起进行线性叙述,以保持叙事上的连续性。读者在阅读这一段落时,会自动在脑海中将环境和动作组合在一起,解析出它们在时间上的同一性,且读者想象中的画面并不会有明确的边界。而在电影中,站满了医护人员的病房和鲍比被抬上轮椅的动作可以在同一个画面内被完整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画框的限制,摄影机不得不借助“摇”的手法,环视一周表现整个病房的场景,在此过程中,场景和外场景不断互相转换以形成视觉场景的完整性。同样,当病房内的画面为场景时,医院走廊在此时就被看作外场景,鲍比可能被推到走廊中,即走廊是病房潜在的“未来时”。随着动作的进行,鲍比真的被推到了走廊里,则刚才表示潜在未来时的动作转换成了正在进行时的动作,而在原著中,这一场景被描写为“推着我在这个楼层转一转”,只需“转一转”这样一个持续性的词语就能够表现一个在无限空间里的连续性动作,而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场景转换。此外,电影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外场景空间,来自难以定位的声音元素,这种声音元素具有从属的双重性,从声音的内容来讲其从属于陈述能指,而由于声音来源于一个银幕世界外的空间,从声音来源来讲又从属于陈述行为[5]。例如,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护工帮助鲍比在室外写作,但此时鲍比的声音“我决定再也不抱怨了……”出现在画外音中,这段声音是鲍比的内心独白,其内容从属于画面中的人物,但是“画外音”的形式让它仿佛并不直接来源于画面中的鲍比,而是来源于另外一个空间的陈述行为。
3 叙事视点
无论是在文学还是电影领域,作品的作者与故事的叙事者的身份都不容混淆。然而,由于《潜水钟与蝴蝶》原著的特殊文体以及作者本人的特殊状况,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只采用了一个叙事视点,即第一人称的“我”,且这个“我”既是作者,也是叙事者,又是主人公,因为作者声明了一个能够把他本人和叙事者联系起来的实际语境——他是一名闭锁综合征患者。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对应的应当是电影语言中主观视点镜头,然而,一部全部由主观视点构成的电影是很难想象的,它会造成“狭义的自知视点”,让整部电影无法跳脱出狭义层面的“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不仅可能带来叙事风险,比如,难以交代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可能带来美感缺失,比如,可观察空间过于狭窄。电影史上的《湖上艳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6]。为避免这一情况,《潜水钟与蝴蝶》的改编电影采用三种视点的混合表达,最终克服将第一人称叙事视觉化的障碍。
3.1 鲍比的主观视点
电影中依然以鲍比的主观视点为主,运用了大量的主观镜头,但这绝不仅是对原著主要内容的简单承袭,甚至可以说这些主观镜头是某种对纪实主义“电影眼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狭义上,在这些镜头中,摄影机真的代表了鲍比的左眼,即他唯一能对外交流的工具,甚至眨眼的效果也被真实地表现出来,让观众的视角几乎完全等同于鲍比的视角。广义上,这些主观镜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由于鲍比无法上下左右转动头部,那么镜头也自然就无法上下左右改变角度,只能运用固定机位,甚至如果对面的人站着,鲍比就无法看见她/他的头部,所以他们想要进入鲍比视觉的“画框”,就必须蹲下身来。同时,鲍比也无法与人交流,所以就很难通过交流操控其他人物行为,这就在某种层面上达到了一种维尔托夫追求的只展示、不参与的(伪)纪实效果。因此,在这些主观镜头中,摄影机作为机器眼让观众处于既主动又被动的位置。一方面,观众主动参与了叙事的建构,随着鲍比的左眼一起探索全新角度的世界;另一方面,由于视点主体的身体限制,观众也可切身体会到鲍比所感受的受限感,进而发现他的视角实际上是被动的、被他人操控的。在这一层面上,电影中的主观视角表达远比原著更能调动“读者反应”(reader-response),通过观众的主动参与和被动感受来建构完整叙事[7]。此外,电影中鲍比曾两次看到了玻璃反射中的自己,这虽然也是从“我”的角度去看,但看到的内容却是“镜像我”。鲍比曾表示,自己在瘫痪之后仿佛回到婴儿时代,表层含义是他的一切生活都需要靠人照顾,深层含义则表明他需要重新进行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拉康指出,人在婴儿时代形成自我认知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镜像阶段”,即辨认出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8],而鲍比在“重生”后,也必须再次经过自我再认这一阶段,而镜中的自己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恐慌感与陌生感。更进一步,将观众的位置也带入镜像关系之中,那么这两次对“镜像我”的凝视,实际上形成了多重镜像。麦茨将拉康的镜像理论运用到观众的观看行为中,指出观众“窥视”银幕的行为动机类似于观看一面缺少观者的镜子[9]。从这一理论出发,电影中凝视“镜像我”的镜头就会形成观众凝视鲍比、鲍比凝视“镜像我”的双重关系。此时,由于观众的视点等于鲍比的视点,观众实际上也通过鲍比的“自我凝视”直接与鲍比的“镜像我”产生了关系。
3.2 非人称叙事视点
影片中还插入了一些非人称叙事视点,即“全知视角”或“上帝视角”。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也可被看作故事与听讲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重要的约定之上的,即银幕上发生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而故事的作者并不能为故事的真实性做担保,故事中的角色作为叙事者——此时为有人称叙事——也会由于他对故事的参与或目击而减少叙事的客观性,甚至形成上文提到的“狭义的自知视点”,因此这种视点也是不可信的。此时,非人称叙事的叙事者被嵌入作者与听讲人之间的另一层次,承担起担保故事真实性的任务[10]。当然,这个叙事者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某一个人,而只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叙事者[11]。在《潜水钟与蝴蝶》中,第一人称视角只能让观众体会鲍比的主观感受,而非人称叙事视点则能让观众跳脱出鲍比的躯体,抽离于鲍比的个性与感受,不再与鲍比同甘共苦,而是与鲍比面对面,进行较为客观的思考。此时,观众可以选择不再认同或继续认同鲍比的行为与思想。如果故事试图让观众不再认同人物的感受,那么就可以让非人称叙事与人称叙事间产生反差、偏离,如果故事试图让观众继续认同人物的感受,那么非人称叙事就应该以其叙事同意、强化人物所叙述的内容。在《潜水钟与蝴蝶》中,叙事明显意在让观众继续认同鲍比的感受,比如,在鲍比与父亲通电话的段落,镜头采用了非人称叙事视角来表现鲍比由于自己无法发出声音,而只能通过护工费力地为二人进行翻译,这让观众在客观层面上对鲍比的身体状况进行了直观的评估,进而在再次进入主观视点时,能够对鲍比的体会更加感同身受。另外,在非人称叙事视点下,鲍比在故事世界中的重要性也有所下降,鲍比从“我”变成了“他”,而“他”只是故事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一只苍蝇落在了鲍比的鼻子上而鲍比无法把苍蝇轰走,在这一场景中,如果以主观视角来表达,则会强调鲍比鼻子很痒却无能为力的焦虑感,而影片选择从全知视角来表达,则把这一段落化解成了鲍比无聊生活中一段较为轻松的插曲。
3.3 感知视点与叙事声音的分离
《潜水钟与蝴蝶》电影中较为非常规的视点表达是感知视点和叙事声音的分离,这在原著中是不常见的,因为原著中作者与叙事者是合二为一的。然而,查特曼指出叙事视点是一种角度,叙事声音是一种表达,但“角度与表达不需要寄寓在同一人身上”。电影中有许多段落运用了这一表现手法,比如,镜头内容是鲍比与护工在船上阅读《基督山伯爵》的片段,但画外音内容是鲍比内心跟着护工一起朗读的内心独白,即画面视点是第三人称,而声音内容是第一人称。这被称为“公开叙述者声音的限制性第三人称视点”[12],这本来是起源于文学叙事领域的创作方法,后来电影创作领域也采用了相似的做法,且由于电影拥有视觉和听觉两条通道,就会使视点与声音的分离效果更加显著。早在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中,这种做法就已经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在叙事意义上,《潜水钟与蝴蝶》的这种做法使声音发生在故事之内,而视点则在故事之外,以一个独立的视点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和叙事者虽然短暂分离了,但叙事者还依然能够凝视人物思想,这无疑是一种暗示,即这个独立于故事之外的视点其实是鲍比被困于身体却想挣脱出来的自由灵魂。在美学意义上,这种手法使原著中的原文以声音的形式与电影新创造出的看似无关的画面并行,二者看似各行其是,但这种不对位实际上却更能突出画面与声音在精神层面上的共同之处,它“以极其严谨的形式进行美学上的抽象,通过文学与现实的互动来避免表现主义;电影属性看似减弱了,但其实增强了”[13],进而使电影避免了落入以影像来解释原著的陷阱。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和叙事视角构成的叙事语法在文学和电影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之间在总体上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区别,电影叙事与文学叙事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从文学叙事进入电影领域之时开始,电影就用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了电影化的改造,使电影语言比文学语言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表达张力。因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电影改编时,电影艺术家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打破文学语言的限制,发挥电影语言独有的叙事张力。
参考文献
[1] 西摩·查特曼. 术语评论:小说与电影的叙事修辞学[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8.
[2]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3-37,53-60,73-83.
[3] 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05-116.
[4] 让·多米尼克·鲍比. 潜水钟与蝴蝶[M].邱瑞銮,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105-107,91,50,1-3.
[5] Franois Jost. Vers de Nouvelles Approches Méthodologiques[C]. Dominique Chateau,André Gardies,Francois Jost. Ciné- mas de la Modernité:Films,Théories. Paris:Klincksieck,1981:80.
[6] 戴锦华. 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
[7] SEYMOUR C. The Cinematic Narrator[C]. Seymour Chatman.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Introductory Reading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74.
[8] 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21,136.
[9] 尼克·布朗. 电影理论史评[M].徐建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38-139.
[10]罗·伯戈因. 电影的叙事者:非人称叙事的逻辑学和语用学[J].王义国,译. 世界电影,1991(3):4-25.
[11]ROLAND B, LIONEL 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J].New Literary History,6(2):237-272.
[12]西摩·查特曼. 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2-57,91,81-89, 132,137-138,138.
[13]安德烈·巴赞. 电影是什么[M]. 李浚帆,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