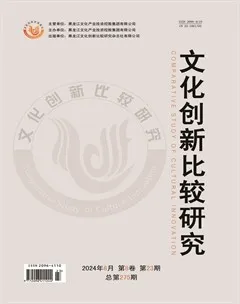论徐志摩散文中“浓得化不开”的色彩景观
摘要:徐志摩是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其散文结构自由、文风艳丽,具有诗化色彩,在文坛大放异彩。徐志摩散文建构了丰富多元的色彩景观,包括暗淡苍凉的冷色调、浓烈宏阔的暖色调,以及植根日常的中间色调。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具有状物造境、写人记事等功能,形成了艳丽的文风。徐志摩散文的色彩表现力一方面来源于作家的想象力与充沛的情感,另一方面来源于剑桥大学的自然及人文环境。该文分析了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景观建构,然后分析徐志摩散文中色彩的表现功能,最后探讨其色彩表现力的来源,旨在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徐志摩;散文;自然崇拜;色彩景观;表现功能;剑桥大学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b)-0001-05
On the "Too Dense to be Dissolved Color Landscape" in Xu Zhimo's Prose
ZHENG Yiran
(Xinyang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Xu Zhimo is a famous modern poet and essayist. His prose has a free structure, vibrant style, and poetic color, which has shone brightly in the literary world. Xu Zhimo's prose constructs a rich and diverse color landscape, including dim and desolate cool tones, intense and broad warm tones, and intermediate tones rooted in daily life. The use of colors in Xu Zhimo's prose has the functions of creating scenery and recording people's events, forming a vibrant literary style. The color expression of Xu Zhimo's prose comes from the author's imagination and abundant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lor landscapes in Xu Zhimo's prose, then analyzes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color in Xu Zhimo's prose,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sources of its color expressive power, aiming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and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Xu Zhimo; Prose; Nature worship; Color landscape; Expressive fun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浓得化不开”出自徐志摩小说集《轮盘》中的两篇小说,分别是《浓得化不开(星加坡)》《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要红,要热,要烈,就得浓,浓得化不开,树胶似的才有意思。”[1]在《浓得化不开(星加坡)》篇首,“浓得化不开”突出表现雨后的芭蕉心色彩浓郁,进一步用诗人的心与之作比,突出了自身浓烈的心绪与情感。除此之外,作家还用“浓得化不开”来形容“朱古律姑娘”身上浓郁而风韵的色彩,以及人的味觉与嗅觉。徐志摩其他散文同样充斥着浓郁的色彩、味道,以及渗透其中的浓郁的自然之情、爱恋之情与敬仰之情,其中对于大自然绚丽的光影声色的描写,是徐志摩散文创作中重要的文学现象。色彩描摹表现了奇景奇思,丰富了文学表达的空间层次。
1 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景观建构
新月派诗人、理论家闻一多提出了诗歌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诗歌主张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徐志摩同为新月派诗人,其诸多经典诗作都践行着这一审美标准,除此之外,他的写景抒情类散文也兼具“绘画美”与“音乐美”。徐志摩的散文时而浓墨重彩、富丽堂皇,时而清新雅致,宛如一幅幽远的山水画,形成了多元的色彩景观。受描写对象与作家心境的影响,徐志摩写景文中的色彩景观大体可以分为冷色调、暖色调及中间色调。
1.1 感时伤世,悲秋伤春的悲凉底色
伤春悲秋一词出自《李义山诗集笺注》,“自古逢秋悲寂寥”,可以说伤春悲秋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的独特情怀,徐志摩的《印度洋上的秋思》同样表达了关于秋的愁思。
《印度洋上的秋思》写于1922年,彼时作家在从香港到上海的轮船上,观海天之色,表幽愁之心。“昨夜中秋。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寂静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梢布篷上窸窸窣窣啜泣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2]这是全文的第一段,点明了季候、时辰、地点、气象,色调幽暗。“云母屏”即镶嵌着云母装饰的屏风。李商隐《嫦娥》一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意为镶嵌着云母装饰的屏风上竹影暗淡。李诗中的“云母屏”可以还原到日常生活中,为实指,徐志摩散文中的“云母屏”为虚指。作家把云比作云母屏风,一方面写出了当时云的特质,色彩惨淡,但在落日微光的照拂下,散发出云母一样的光泽;另一方面,由于云的遮挡,天色、水色都暗淡了下来,化成“暗蓝色”,从云层之变引出光影水色之变,气韵和谐,具有动态美。暗蓝色接近黑色,属于冷色调,海天一色,呈现出暗蓝色,通过大面积的色彩铺陈,作家渲染了一种宏阔而神秘的色彩基调。紧接着,作家把这种环境带来的凝重寂静的气氛具像化,以“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作比,生动传神,渲染了黯淡、寂静、庄严、孤独的气氛。大自然气象万千,造物神奇,随着时间的推移,雨的兴止,作家笔下的色彩也在不断变换,从雨前的“暗蓝色”,到雨中“沿边的黑影”,再到雨后“天色早已沉黑”“惨白的微光”“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以及长桥似的船烟,有声有色,层次分明。总的来说,作家以灵动之笔描摹中秋落雨之情景,色调幽暗冷峻,表现人生苍凉底色。
1.2 高山景行,日出日落的瑰丽色调
1923年,徐志摩创作《泰山日出》,后发表于《小说月报》。文末作家表明:“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泰戈尔是20世纪印度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博爱的人生观以及尊重个性、回归自然的文学观与徐志摩的思想契合。所以,这不仅是一篇写景文,更饱含作家对学界泰斗的敬仰之情,表达相聚的兴奋与期待。作者把泰戈尔来华访问,喻作泰山日出,希望能给当时混乱、落后的中国带来希望与光明。整篇文章色彩浓郁,壮思风飞,逸情云上,描摹了清晨云海气象。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作家借用高饱和度的形象表现浓郁的色彩,红、紫、橙、黄等色彩与光线变幻,绘就了一片瑰丽荣华的日出气象。除了给人以明亮鲜艳的色彩冲击之外,还传达了光与云的质感、气息,给读者留下了感受与想象的空间。总而言之,整篇文章充满想象与双关,洋溢着温暖张扬的色调,渲染了圣洁、宁静、畅达的抒情气氛。
在徐志摩笔下,日落与日出一样绚烂多彩,充满神性。
“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冲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它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剩这不可逼视的威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着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渐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光,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幻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3]这一段文字呈现了三个场景,均大开大合,恢弘开阔,明暗交接,色泽浓郁,青色抑或是金黄的麦浪、西天的变幻、灰白的羊群、太阳的金辉、乌青的天空、碧绿无际的草原、艳红的罂粟等大自然的光影声色给人以感官的享受。作家具有敏锐的色彩感知力,在他笔下色彩不仅是对事物外部面目的描摹,更是一种华丽的语言,承载着自然的神性。
1.3 植根日常,清新素雅的中间色调
大自然惊心动魄的壮丽奇景可遇而不可求,日常生活中的美景却是随处可见。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作家描写了剑桥大学旖旎的自然风光,笔触细腻,色泽清丽,宛如一幅清新雅致的工笔画。文中这样描写校友居:“它那苍白的石壁上春夏间满缀着艳色的蔷薇在和风中摇颤。”石壁苍白,蔷薇娇艳,两种色彩相映成趣。在日光照耀下,微风徐来,花影摇曳生姿,黑色也成了花的底色。这是一处局部特写,除此之外,作家还将视角聚焦于康河的两岸与七月的黄昏。康河两岸有常青的草坪、星星点点的黄花,还有垂柳、椈荫、行云、黄牛、白马等,色彩明丽,格调清雅。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像泼墨的山形,衬出轻柔瞑色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寥寥几笔,意境全出,宛如烟波浩渺的写意山水画。
除了日常实景的还原,作家还任凭想象的翅膀肆意飞扬,《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便是作家独坐廊前,对于风景以及理想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幻想。文中写到了晚霞的余赭、马樱、紫荆、藤萝、青翠的叶与鲜红的花、黄蓝相间的波光、浮游的白云、初黄的稻田,以及牧童、村夫、农妇等,生机勃勃,气韵和谐,充满烟火气息。作家将日常的景物写得有声有色,极具画面感与流动性。色彩的流动彰显了作家意识的流动,这些丰富多元的颜色与安居乐业的农民展现了作家的生活理想,也暗含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2 徐志摩散文中色彩的表现功能
“任何一种可视的客观存在都是有其色彩的,每一种色彩都会影响人们的主观感受,对人的感觉、记忆及情绪等方面起到不同的作用。”[4]在自然界中,万物的枯荣、季候的更迭、气象的变化都伴随着浓烈或暗淡的色彩,给人以审美的愉悦,留下鲜明的记忆。从古至今,色彩表达普遍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不同的色彩具有不同的气质,红色热烈温暖,紫色优雅高贵,蓝色忧郁神秘,多样的色彩能够增强文本的表现力。概括来说,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描写具有造境状物、写人记事的功能,同时也形成了其浓妆艳抹的文风。
2.1 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表现功能之造境状物
“在文学作品中,利用色彩来营造氛围,创造境界是十分有效的表现方法,作品往往通过色彩与特定的人物、情节、事物等相融合,构成一些独特的意象。”[5]受到表现对象的影响,徐志摩散文具有浓得化不开的色彩,尤其是光怪陆离的大自然。在《翡冷翠山居闲话》中,徐志摩说:“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徐志摩对大自然的崇拜溢于言表,这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其表现大自然鬼斧神工,造物神奇的同时,形成了返璞归真的自然美感观。徐志摩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可以说作家的笔一接触自然就焕发出无尽的灵感与才思。我们在他笔下可以领略康河两岸清新秀丽的校舍田园、泰山日出时华丽灿烂的光影星辰、山居独行时的纵情山水,可以感受富于变化的山水明月,肆意生长的花草藤蔓,云卷云舒,气象万千。作家不仅局限于对大自然实景的忠实描写,还常常将色彩与想象、感觉有机融合,烘托气氛,表达复杂微妙的情绪,营造独特的文学境界。此时,色彩不仅是表现对象,更成为一种写作策略,如阴郁暗淡的水色天光与中秋绵绵的愁思水乳交融,泰山日出的雄浑壮阔与高山景行的感怀相得益彰,冷暖色调与作家心境紧密契合。
2.2 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表现功能之写人记事
徐志摩散文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对于诗人、画家的赞颂,有对于已故亲友的悼念,还有的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路人。作家利用色彩对人物形象、性格进行塑造,不像大自然的瑰丽多姿,进入徐志摩文学视野中的人物往往都是素净的。比如,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作家写到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的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女郎穿着白色的丝绸裙子,戴着薄纱帽在康河泛舟,清风徐来,裙裾飘飘,帽影浮动。在绚丽多彩的自然美景中,简约素净的衣着尽显优雅、纯洁、高贵。这种色彩的映衬,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剑桥大学自由宽松的校园环境。又如,《巴黎的鳞爪》一文。在巴黎,作家有一段9小时的萍水缘。作家这样描写那位萍水相逢的女人:“穿一身淡素衣裳,戴一顶宽边的黑帽,在浓密的睫毛上隐隐闪亮着深思的目光——我几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尔到红尘里随喜来了。”女人坐在灯光最暗漆的屋角,素衣黑帽,这种阴暗的色调透露着一种神秘、孤寂、清冷的气息,与热闹的饭店格格不入,于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女人对“我”讲述了自己的感情史,英国丈夫、菲律宾情人无不薄情冷酷,坎坷的情路与家庭的变故致使女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灰暗的色彩描写与灰暗的人生相呼应,展现了一位可悲可叹的弃妇形象。“忘了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6]这是鲁迅在创作中常用的“画眼睛”笔法,通过刻画眼睛,传递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达文謇的剪影》一文中,作家通过“画眼睛”,传神地勾勒出了这位意大利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形象。作家用“清、蓝、淡、冷”形容达文謇的眼睛,给人一种世事洞明、睿智、纯粹的感觉,用词细腻精准。文中还写道:“他不喜欢鲜艳的颜色,不喜欢时新累赘的式样,他也不爱薰香。他的衣料是雷尼希的棉布,异样的整洁好看。他的黑绒便帽是素净的,不装羽毛,不加装饰。他的衣色是黑的;但他穿一件长过膝盖的深红色的斗篷,直裥往下垂的,翡冷翠古式。”他衣着整洁素净,抚弄着如金色丝绸般的胡须,开启智者的沉思,静穆、庄重,给人以距离感。
总的来说,色彩的表达植根于绚烂的大自然,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作家鲜活的生命意识,形成了艳丽的文风。在文学作品中,色彩描写承担着特殊的功能,上文提到造境状物、写人记事只是其中一个侧面。无论是沉郁苍茫,还是辉煌亮丽,都是人生底色。
3 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表现力来源
徐志摩把印象派的绘画技巧引入散文创作,用流动的色彩表达瞬间的印象,“徐志摩作品中的色彩描摹渗透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是作者充满爱与美的内心世界的折射。客观世界丰富多彩的形象与作家浓烈的情志相统一才创作出这样完美的艺术形象。”[7]因此,他的散文极具色彩表现力。这种色彩表现力一方面来源于作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充沛的情感;另一方面来源于剑桥大学的自然及人文环境。
3.1 从作家本身的角度而言
3.1.1 徐志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敏锐的观察力、活跃的想象力、幻想力和必要的推理力、领悟力,都是作家创作思维的重要能力……文学家不仅要感受人与自然的外观,还要感受自然界四时的变化和人物彼此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喜怒哀乐的内心波澜。”[8]在创作中,敏锐的观察力、想象力有利于作家还原生活中的印象与感觉,还可以根据创作需要,对生活中的素材进行选择、提炼与加工,形成全新的形象体系。徐志摩是一位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与活跃的想象力的作家,尤其是对于色彩的感知力。他在《我的祖母之死》中说:“我是一只不羁的野驹,我往往纵容想象的猖狂,诡辩人生的现实;比如凭借凹折的玻璃,觉察当前景色。但时而复再,我也能从烦嚣的杂响中听出清新的乐调,在炫耀的杂彩里,看出有条理的意匠。”[9]“不羁的野驹”体现了徐志摩散文的野马风气,文无定法,结构自由,思想自由。“凹折的玻璃”“烦嚣的杂响”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微不足道的事物,甚至可以说毫无美感可言,而作家却能从中发现诗意与美感,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敏锐的美的感知力与想象力。“炫耀”有夸耀、卖弄之意,多含贬义。在这里徐志摩用“炫耀”修饰“杂彩”,取其光彩照人、闪耀夺目之意,看似是一种陌生化的表达,实则还原了词汇原本的意义。“杂彩”与“条理”不相及,但作家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关联。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作家化整为零,化繁为简,理清思绪,写出空间感与层次感。
3.1.2 徐志摩具有充沛的情感
“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10]徐志摩浓烈的情感反映在创作中,具体表现为浓烈的个人主义与自然之情,以及炽烈的爱恋之情。并且,作家多用第一人称创作散文,便于直抒胸臆,释放情感。徐志摩对陆小曼的情意,在《志摩日记》中可见一斑。徐志摩表现个人主义与自然崇拜之情的散文更是不胜枚举,如《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印度洋上的秋思》《雨后虹》《天目山中笔记》等。活跃的想象力与充沛的感情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散文当中,想象力及其产物——形象都服从于表情达意的需要,想象力的极度发挥,形成了徐志摩散文自由自在的野马风格。正如相关论者所言:“作为一个感情充沛的诗人,感情的自由奔放,使他常常通过瑰丽奇特的想象来表情达意,把自己的感情熔铸入对想象事物的描写之中,这就使得他的散文风格绝不可能是严谨的,而必然是自由的。”[11]
3.2 从剑桥大学的自然及人文环境而言
徐志摩去剑桥大学之前,在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21年,由狄更生介绍,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作特别生,在这里生活、学习了约一年半的时光。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中,这样评价剑桥大学:“我在康桥的日子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康桥对于徐志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包括自然环境以及自由宽厚的学术环境。“徐志摩在剑桥期间,因为是‘特别生’,没有考试和获取学位的压力,所以生活过得相当轻松。他把大量时间用在游赏自然美景上,可以说足迹踏遍了整个剑桥。”[12]《我所知道的康桥》《再别康桥》等都是对剑桥大学自然风光的记录。这里让徐志摩认识到内心深处回归自然的天性,剑桥风光与诗人气质巧妙结合,使其在现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剑桥大学施行学院制、导师制,重精英教育与人文教育。他随心所欲地读书,与同学、老师坐而论道。在此期间,徐志摩的兴趣逐渐从政治学、经济学转移到文学。英国文学深受徐志摩的喜爱,如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人的创作。徐志摩在剑桥大学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如狄更生、罗杰·弗赖、罗素、奥格顿等。这些人的气质及创作成就,激发了徐志摩的文学灵感,也催生了他的个性主义和理想主义。
4 结束语
徐志摩散文为我们呈现了多样的色彩景观,这些浓得化不开的色彩植根于光怪陆离的自然,更源于作家对自然美感的敏锐捕捉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充沛的情感体验。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是写景造境、塑造形象的重要媒介,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自选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53.
[2] 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9:35.
[3] 徐志摩.巴黎的鳞爪[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
[4] 王琳.色彩与莫言的小说创作[D].青岛:青岛大学,2020:1.
[5] 黄珊珊.色彩与文学[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3:2.
[6]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7.
[7] 于昕蕙.便引诗情到碧霄:浅谈徐志摩散文的诗意美[J].理论界,2014(12):144-147.
[8] 张炯.论文学创作思维[J].文艺争鸣,2016(1):58-68.
[9] 徐志摩.自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119.
[10]徐志摩.泰戈尔[M]//王锦泉.徐志摩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34.
[11]许欣.论徐志摩的散文风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S2):77-79.
[12]刘洪涛.徐志摩与剑桥大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