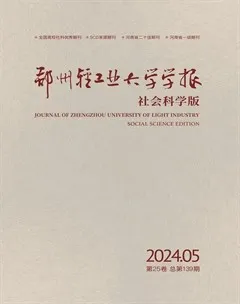多模态文化隐喻框架下文明互鉴理念的视像化构建及其软传播研究












摘要:多模态文化隐喻作为一种多感官修辞符号,其恰当运用将对“文明互鉴”等抽象概念的传播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中意两国团队联合制作的大型人文纪录片《穿越丝路双城记》,涉及大量多模态文化隐喻经典案例,强调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共鸣、价值共享和互动参与,是对软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浓缩。通过自建《穿越丝路双城记》图文数据库,运用概念整合理论,结合该纪录片的图像构图特点,发现该纪录片中多用道路隐喻、建筑隐喻和文化负载词隐喻来表征文化话语;这些多模态隐喻发挥不同模态符号的协同作用,共同完成表义过程,用目标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乐于接受的软传播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建构了“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中国国家人文形象。
关键词:多模态文化隐喻;概念整合;文明互鉴;软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5;H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5.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5-0037-12
伴随着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摩擦、贸易纠纷、生态恶化等全球性挑战接踵而至,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博弈策略。中华文化卷帙浩繁、博大精深,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如果各种模态之间对接程度低,将会造成对文化的稀释和曲解,参与世界对话的效力也将大打折扣[1]。多模态隐喻能够充分调用各类社会符号的意义潜势,立体塑造抽象理念,创造灵动叙事空间,带给观众丰富的感官体验,增强跨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号召力和阐释力,是行之有效的软话语策略[2]。但目前鲜有学者对媒体在讲述中国文化故事中如何恰当运用多模态隐喻等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
多模态文化隐喻作为一种多感官修辞符号,其恰当运用将对“文明互鉴”等抽象概念的传播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中意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团队于2020年联手制作的大型人文纪录片《穿越丝路双城记》(以下简称《双城记》),涉及大量多模态文化隐喻经典案例,强调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共鸣、价值共享和互动参与,是对中国“软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浓缩。本文拟从自建的《双城记》语料库中选取78条经典图文数据,勾勒出一条立体完整的隐喻链,采用隐喻学、符号学、传播学和数据科学的相关知识,对其文化寓意进行解读,以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有所助益。
一、概念整合与多模态文化隐喻
当代语言学经典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首次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问题,更是一种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许多生活现象的概念化都有其根深蒂固的隐喻形式[3]。隐喻不仅能够通过语言还能够通过图像、动作、声音等其他交流方式呈现[4],这种由多种模态共同参与、动态交互建构意义的隐喻就是多模态隐喻[5]。为进一步揭示非常规的、新奇的隐喻意义建构和推理机制,G.Fauconnier等[6]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隐喻结构至少存在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其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在源域和靶域空间共同输入的作用下,一种提取了两个空间特征及其抽象结构的类属空间随之形成,并在其统领下,通过组合、完善以及扩展方式,产生一种具有自身核心层创结构并揭示隐喻意义的合成空间。概念整合理论在充分继承概念隐喻理论要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时、在线地观察和衍推来源于多形式、多种源的隐喻类型,尤其对历经多维空间的交织与转换而达成的新颖、动态、立体的隐喻产品设定了较令人满意的阐释方案[7]。
文化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生活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同一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8]。隐喻是集体记忆里文化沉淀的一部分,扎根于特定语言使用的概念体系中[9]。可以说,文化隐喻是隐喻从语言现象的逻辑领域发展到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结果,是发掘某个群体潜在的价值与态度的思维工具[10]。基于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多模态文化隐喻是指以文化内涵、社会风俗和信仰哲理等为主题,由多种符号资源协同参与建构意义的隐喻,具有内核稳定性、语义隐含性、符号多元性和时空交互性等特点。也就是说,它在主题内容上蕴含文化寓意、传播目的上强调人文交流、视觉呈现上重视符号的多样化与动态感等。在文化语境中,多模态隐喻是多层次表达各个民族文化特点的工具,因其更加能够生动形象地传递人文理念,有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从而增强国际传播的可接受性,增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11]。
传统概念隐喻的映射关系为具体→抽象[12],但多模态隐喻中的源域和靶域皆为具体实物,其映射关系为具体→具体。这种具体→具体的映射关系在广告语篇中适用,因为靶域皆为具体产品[13],以允许其从物理世界的已知领域映射到社会、心理等未知领域,但它们通常是抽象而晦涩的[14]。因此,文化纪录片隐喻往往只呈现出源域,却把靶域的意象空间留给了话语实体,经过他们的联想与诠释,源域与靶域实现了话语勾连与接合,生成一个由文本域与映射域融合构成的层创结构[15]。根据扩展概念隐喻理论,当文化理念等抽象概念被设定为靶域,考察源域的属性与映射时,我们还需考虑当前语境[16],如语篇的上下文、当下的物理场景、当时的社会环境、主要实体的知识储备等,从而辨别出最佳关联的隐喻元素。
二、文明互鉴理念内涵与研究设计
古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蕴含着丰富的文明互鉴历史资源。新时代的文明互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旨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表明,文明互鉴既连通时间纵轴的历史与时代,又汇聚空间横轴的东方与西方,具有丰富的符号互动意义。因此,构建文明互鉴中国形象,应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质禀赋和优良基因,勾勒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绵延不绝的历史图谱,并将其形成过程中对其他文明的滋养以及中外文明互通中的融合发展全景展现出来[17]。鉴于此,本研究选取的语料是人文纪录片《双城记》,该片共50分钟,以平行视角方式再现了长安和罗马两大古都的璀璨文明,讲述了中意两国之间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古丝绸之路的时代内涵。该片在视觉和听觉上增加了更多的电影元素、更宏大的叙事场面和更生动的镜头细节,带领观众与历史对话、与文化交流,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多国联合实施宣传项目的典范,有力促进了该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文交流。
影视图像的初始状态一般由字幕、构图、颜色等多种模态符号组成,也是受众能感知到的自然或具实信息,这些模态符号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分离,同时被“镶嵌”于同一个场景,奠定多模态意义基础[18]。本文使用Python语言编写程序,爬取bilibili网站上《双城记》的声视频及其生成的AI字幕,然后匹配视频帧与字幕到Excel里,建立初始语料库。人工清洗后,共有802对有效图文数据。根据人文纪录片的隐喻特点,本文把文明互鉴理念设为靶域,以考察源域的跨域映射。基于含义及其所指对象的图文分类方法[19],本文将源域对象分为文字主导(VD)(指源域对象仅能够从文本模态获取)、图像主导(PD)(指源域对象仅能够从图像模态获取)、图文共现(VPD)(指源域对象同时出现在两种模态中)、图文协同(VD+PD)(指当且仅当将两种模态信息综合在一起考虑时才能决定是否充分呈现喻义)四种类别(见图1)。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在《双城记》语料库中,VPD占36%,VD占35%,VD+PD占11%,PD仅占2%。
本研究采用的是电影隐喻识别方法[20],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甄别隐喻。具体步骤如下:(1)反复观看视频,整体上理解《双城记》;(2)第一轮核查构成隐喻义的每个元素,初步标注并确定主题,具有隐喻性的词簇和图像统一从源域中抽取;(3)穷尽式检索语料库,结合当前语境清洗数据;(4)补充前两轮中遗漏的低频隐喻数据,最终确定具有隐喻性的图文数据对。笔者在自建语料库中识别出三大类隐喻:道路隐喻、建筑隐喻、文化负载隐喻。从总体架构来看,《双城记》中的三条纵向隐喻叙事链(“文明互鉴”是……道路)与两条平行隐喻叙事链(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相结合,形成立体叙事模式,潜移默化地让受众认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知识图景。
三、文明互鉴理念的叙事与传播逻辑
下文从自建语料库中选取78组经典图文数据,利用概念整合理论,结合当前语境与图像构图特点,解构纪录片塑造中国文化形象的视像化叙事逻辑。
1.道路隐喻
根据词源学解释,“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意为“脑袋指导走向”;“路,从足从各,道也”,意为“各迈各的脚步”[21]。《道德经》用“道”阐释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其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在《论语》中
不仅指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象征着宇宙和自然的普遍规律,是人类与宇宙和谐共存的基础[22]
。在中国人文理念的国际传播中,“道路”隐喻了人们执着追求和坚守的社会精神信仰、认真思考和探索的国家形象建构。《双城记》在开篇部分一气呵成地为受众构建了三条纵向隐喻作为该片的主隐喻。
(1)“文明互鉴”是一条沧桑久远的贸易通道
因应前景化是语言行为的非自动化,其特点是新颖独特、出人意料、非同寻常和独一无二,作为一种通用规则,任何人分析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时,必须聚焦于有趣和新奇的元素上[23]。“‘文明互鉴’是一条沧桑久远的贸易通道。”这则隐喻的源域中包含多个元素,但可辨别出该组图文的焦点为“道路”(见图2)。首先,文字模态点明了路线,即长安-河西走廊-葱岭-中亚西亚-古罗马。其次,图像的构图多为前景化:一是前景化汉王朝宫殿,而置于后方的太阳则被虚化,凸显通道起点是古都长安(见图2a);二是前景化古道,增强了画面的年代感(见图2b)、纵深感(见图2c)和绵长感(见图2d),引导受众视线渐渐地深入绵亘万里的广袤土地。而在西域古镇这一特定环境中,梁柱缝隙被置为前景,以引导受众视觉的焦点(见图2e),使整个画面具有一种“窥视感”,呈现出一段遥远而神秘的西域通道。再次,在沙漠征途这一画面中加入行进的骆驼商队背景(见图2f),以呼应喻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最后,这组图像被嵌入灰褐、灰绿两种冷色,烘托出古老苍茫的气氛。由此协同映射出:“文明互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条赓续传承的重要欧亚商道,一定有很多值得后人去挖掘的中西方历史文化故事。
(2)“文明互鉴”是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这则隐喻的喻义主要由图文协同构建,且画面多为特写镜头,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意象(见图3)。源域中的“丝绸之路”是一个抽象概念,也就是说,在这组图中,“文明互鉴”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丝绸贸易之“商道”这一具体物象,而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首先,在电脑绘制的地图上,若干节点由一条亮线连接,呈现东端为长安、西端为罗马的古丝绸之路,映射东西方文明的交往途径(见图3a)。通过模态协同方式,反映出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两河流域的文明都通过丝绸之路得以流传与交往、碰撞与融通,促进了各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图像中特写的中世纪罗马风教堂和古波斯拜占庭式教堂(见图3b)、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君权神授硬币图案(见图3c)等,与字幕协同映射抽象概念“东学”;而驼队脚下的大漠孤烟(见图3d)、驼队背上的驮篓货物(见图3e)和与驼队伴行的商旅队伍(见图3f)等特写画面与字幕协同映射抽象概念“西渐”。“生生不息的丝绸之路与相遇相知的中外民众是文明互鉴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这一理念具体而鲜活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3)“文明互鉴”是一张沟通东西方的复合路网
这则隐喻的源域中涉及大量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喻义主要由图像模态构建,较少使用文字模态。图像构图方式变换多样,颜色对比分明,使受众能从历史文化和地缘空间两个视角产生共鸣(见图4)。利用黑白色来表达被称为“东方庞贝”的交河故城遗址(见图4a)和中国历史考古实景照片(见图4b),复原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西域史实。而前景化的道路和绚烂的天空则将受众代入“构筑一张沟通东西方的复合网络”这一灿烂过程(见图4c和图4d),激活“丝绸之路是各民族和各大陆最重要的纽带”这一重要理念。另外,长安大雁塔(见图4e)和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见图4f)等模态符号重复采用特写镜头,以升华主题“两座并驾齐驱的历史文化名城长安与罗马,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一举成就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伟业”。这组多模态符号共同隐喻了:2000多年过去了,在这条中华民族开辟的中外人文交流之路上,人们或许只能看到残垣断壁、斑驳废墟,甚至只能看到沧桑土墩,但沿线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却依然延续,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2.建筑隐喻
人们通常用自身经历过的、熟悉的、具象的事物去理解眼前的建筑所表达的文化内容。建筑是人类精神与制度的物化,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观念,蕴含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思想和情感。施喻者与受喻者的文化经验不同,会引发建筑隐喻的多义性。为此,《双城记》中“长安-罗马”建筑隐喻作为其中一条平行隐喻链,多以文字模态为主导,辅以动态影像模态,利用多模态符号表征“和谐共生”“中正平和”“天人合一”等文化价值观。
(1)“文明互鉴”是家园
《双城记》在借助图文模态展示了司马相如诗句“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之后,模拟了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图,并以系列图文呈现家园的壮观画面(见图5a和图5b):八条河围绕的千里沃野,加上崇山峻岭和黄河天堑的守护,形成了漫长历史中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紧接着,运用同样模态方式展示了罗马城所在之丘陵地图、一条台伯河穿城而过、依山傍水的选址理念(见图5c和图5d),将处于不同时空的事物放入镜像输入空间。话语主体依据已有的认知框架对两个输入空间进行概念整合,不难理解《双城记》隐喻了:文明互鉴理念将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价值基础。
(2)“文明互鉴”是都城
位于汉朝长安城中南部的宫殿是对秦故宫的利用和改造,而位于居民区中心的古罗马广场则是典型的公共场所。画面利用宫殿(见图6a)和石洞(见图6b)作为前景框架,突出了汉代宫殿壮丽威严和帝国时期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场景,让图像更富表现力。同时,“中和自然、方正对称”的长安大街纵深全景(见图6c)和以罗马广场为中心的放射状圆形布局的罗马城俯视全景(见图6d)分别代表着中西方文明的秩序和制度、中正平和的中华民族气质和勇于打破常规的罗马创新精神。这两个输入空间构建的隐喻为:虽然汉长安和古罗马两个城市的形态有较大差异,但是其城市建设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根植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座城市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魅力。
(3)“文明互鉴”是民居
“民以居为安”是东西方文明先祖们共同拥有的生活智慧。不论儒家的“上下gXLJKK2deVZZkYXBJ8Ft+7ZBy5AjC9CZffqu9DOJG/0=与天地同流”,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把人与天地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天人合一的特征(见图7a)。受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影响,古罗马民居高直、空灵、虚幻的形象似乎直指上苍,启示人们脱离苦难罪恶的世界而奔赴“天国乐土”(见图7b)。中西方的居住理念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城市特质:中国庭院式组群布局追求均衡对称、层层递进的建筑方式(见图7c),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礼法观念;庞贝古民居的特点则是房间内逼仄狭小,而室外中庭才是家庭沐浴阳光、闲话家常的主要空间(见图7d),而且罗马人这种亲近自然的居住理念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几组镜头前后连贯起来,通过两个输入空间的共同作用,实现表征隐喻:文化遗产是祖先们留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守护文化遗产、推动文明互鉴有助于使文明充满生机和活力。
3.文化负载隐喻
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或习语,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累积而形成的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独特方式[24],通常涉及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等方面[25]。由于文化负载词镌刻着深深的文化烙印,其本身含有的隐喻概念很难成功地为目标受众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跨文化传播效果。《双城记》通过道路隐喻和建筑隐喻传达出文明互鉴核心理念后,采用大量文化负载词,形成另一条平行隐喻链“‘文明互鉴’是美美与共”,全方位讲述了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通过对文化负载词的分析,本文发现该隐喻包含着“文明互鉴”是民族特质、“文明互鉴”是民间友好、“文明互鉴”是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是民艺荟萃四个隐喻。本组隐喻多采用图文共现方式,视觉模态信息与文化负载词共同表征意义。为纪实再现或夸张表现特定文化喻义,这四组图像分别采用了几何、心理、主客观等多视角构图方式。
第一类是民族特质。具体包括:一是图腾,青铜龙和镏金龙是中华民族昂首腾飞的象征,狼和鹰代表罗马人追求的是强壮威武(见图8a)。二是雕塑,兵马俑与孔子像象征强大王朝和东方君子,是一种集体主义下的民族大义;西方雕塑则多表现自我价值和西方英雄,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见图8b)。三是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汉字就像被烙上中华民族的胎记一样,将多民族的中国紧紧凝聚在一起;起源于罗马的拉丁文则仿佛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根植于文明交融繁衍的沃土中,孕育了西方文字(见图8c)。四是法典,中国最早的、最完整的法典是《唐律疏议》,而欧洲大陆法系的鼻祖《罗马法》代表解决国际纠纷时的公平与正义(图见8d)。这组隐喻体现出:中华民族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地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根基则深植于古罗马的荣光之中。
第二类是民间友好。具体包括:一是商品,西汉时期养蚕和缫丝业盛况空前,镏金铜蚕是丝绸西行征服罗马人的印记;中国也从境外物产和技术中汲取营养,如《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从西域得到葡萄种子的唐太宗在收成之后酿酒与群臣共饮,甚是满足(见图9a)。二是人物,出使大秦的甘英、凿空西域的张骞、罗马派遣的使团、东来中国的马可·波罗等一代代先驱在长安与罗马之间探索出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之路(见图9b)。三是贸易,开元通宝与提供“飞钱”业务的“柜坊”使得唐代国际贸易空前繁荣,而奥斯蒂亚古城和马赛克精美图案则代表罗马也曾是地中海最繁华的商业贸易集散地(见图9c)。四是场所,如果说《罗马通史》记录的是罗马人迷恋在酒吧里的社交生活,那么《饮中八仙歌》彰显的则是唐人氤氲在酒肆里的豪迈性情(见图9d)。丝绸之路上生生不息的交往活动向受众传达这样一种理念:文化需要通过双方的交流而非单方的陈述,正是在长安与罗马的互学互鉴中,东西方文明才能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第三类是民心相通。具体包括:一是品格,罗马人信奉英雄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演讲和格斗是古罗马教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项技能;儒家文化则推崇真正的君子——文能执笔定乾坤、武能上马安天下(见图10a)。二是养老,汉朝时期古稀以上老人由国家亲赐鸠杖,古罗马帝国“战争创伤安抚体系”开创了西方社会养老制度的先河(见图10b)。三是历法,太阳钟是人类共通的计时方式,如古罗马方尖碑与中国古代日晷不谋而合;古罗马儒略历是国际通用的公历,农历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见图10c)。四是饮食,流传千年的陕西美食都是“烈火的结晶”,如葫芦鸡和肉夹馍;在罗马人的饮食观念里,保留大自然馈赠的风味才是最重要的,如火腿和披萨(见图10d)。这组隐喻与暖色背景一起,构成一幅幅美好祥和的画面,反映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第四类是民艺荟萃。具体包括:一是装扮,“酒晕”妆与艳丽华服一起勾勒出一个精致华美的唐代世界;受古希腊美学影响,起源于罗马时期的美妆则注重自然立体(见图11a)。二是诗画,西方绘画艺术注重焦点透视,如采用空气透视法的《蒙娜丽莎》;东方则注重散点透视,如线条流动多姿的《簪花仕女图》;当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苦思冥想他的《埃涅阿斯纪》时,万里之外的中国早在千年前就诞生了《诗经》(见图11b)。三是乐器,作为礼器的编钟主宰了中国的秦汉朝堂,罗马教堂里的管风琴则是声学和建筑学的完美结晶;中东乐器乌德琴,东传到长安变身为琵琶、西传到罗马变身为曼陀铃,使得两个不同特质的民族能够使用同一种乐器讲述各自的故事(见图11c)。四是戏剧,虽然秦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歌剧是殿堂级的高雅艺术,但二者结合的《图兰朵》却成就了中国和意大利的音乐传奇。在这组图文画面中,各种模态交相辉映,从而衍生出主隐喻: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密切合作,成为国家互利共赢的典范。
四、文明互鉴理念的整体意义及其文化形象建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双城记》整体意义是由文本域向映射域多次映射的、由多个输入空间构成的隐喻矩阵,在类属空间和关联空间共同作用下,选择性投射形成了一个新的合成空间,经由组合、完善、扩展而形成层创结构(见图12)。在多个隐喻场景中,喻体元素的选择和构图是话语生产者慧心巧思的结果,10个微型隐喻叙事块巧妙地融合成一个内容完整且意义深远的立体隐喻叙事链。这种柔和细腻的隐喻性话语将传播的信息生活化和情景化,具有生动灵活、个性十足、时尚性强等特点,重视表达方式的情感与理性诉求的双重协调,注重传播内容的亲和力、震撼力与鲜活性、新颖性,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中国所倡导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包容、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等理念。
从认知层面来看,前半部分的两组连续画面“‘文明互鉴’是道路”“‘文明互鉴’是建筑”集中展示了“文明互鉴”的途径、内容和成效等;后半部分的四组连续画面“‘文明互鉴’是民族特质”“‘文明互鉴’是民间友好”“‘文明互鉴’是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是民艺荟萃”则说明这一“中国方案”赢得了中意两国人民的支持和认可,进而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交流互鉴。《双城记》采用两城穿梭、层层递进、自然流畅的视觉安排,注重传播视角的平等性,以避免强制性灌输。特别是将政治色彩较浓的、容易受到受众自我心理防线隔离的信息转化为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传播,发挥“甜化”效应,使得原本生硬刻板的传播方式“软化”, 这种软传播方式有效地实现了人文中国形象传播的目的,一个“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出自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大意是说,多种颜色交相辉映,在互相映衬下更加彰显;各种声音一起合奏,在彼此交响中达到平衡与和谐。的中国文化形象跃然而生。
五、结语
与传统的文本式隐喻相比,多模态隐喻及其视觉传播策略更易激发情感共鸣,具有更强的感染力,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快捷地传达人文外交意图,提高人文交流理念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本文从概念整合理论视角出发,对《双城记》中多组连续画面进行解读,在影像多模态隐喻的层面上丰富了G.Fauconnier的概念空间要素理论,进而印证了多模态隐喻对“文明互鉴”的人文中国形象等抽象概念具有重要的概念建构和形象传播作用。同时,研究发现:多模态文化隐喻中画面元素的选择与构图要着重考虑跨文化交际性,以争取共情认同为切入点,恰当驾驭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运作空间和尺度,避免话语与权利距离过近,以免产生相反隐喻认知效果。本文对人文纪录片进行解读的意义也在于此,通过树立对人类共通体验的正确认知,正确理解其背后的国家意志,明晰以往对国家形象的模糊感知,消解由此导致的对国家形象不同程度的误解,并为未来国家形象的多模态话语呈现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谭文慧,朱耀云,王俊菊.概念隐喻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自塑研究:以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J].外语研究,2021,189(5):38-43.
[2] 席蕊.基于语料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模态视像化叙事建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12):96-112.
[3] LAKE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4] FORCEVILLE C.Non\|verbal and multimodal me\|taphor in a cognitivist framework:Agendas for research[M]∥URIOS\|APARISI.Multimodal Metaphor.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9:19-42.
[5] 孙毅,唐萍.多模态隐喻研究肇始:缘由与进路[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28(5):9-24,158.
[6] FAUCONNIER G,TURNER M.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New York:Basic Books,2002:120-135.
[7] 孙毅.世界国旗多模态隐喻要义诠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7.
[8] 宋鸿立.从西方史诗萌发之生相看汉民族史诗的文化功能[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6):169-171.
[9] GANNO J.Cultural metaphors:Readings,research translations,and commentar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112-116.
[10]孙毅,王媛.隐喻认知的具身性及文化过滤性[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136-143.
[11]刘曼.新媒体语境下国家形象的多模态隐喻研究: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疫情防控海报为例[J].外语研究,2022,39(4):23-28.
[12]LAKEOFF 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276-288.
[13]赵秀风,吴雨昕.能源危机政治漫画中蓄意隐喻的批评分析:以“健康与疫病”多模态隐喻场景为例[J].外语研究,2024,41(2):1-6,112.
[14]孙毅,周锦锦.认知隐喻学视域中汉英自我概念隐喻意涵重塑[J].外语研究,2020(37):13-21.
[15]陈薇,彭紫荆.“文化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与多模态叙事[J].中国电视,2020(2):83-86.
[16]KVECSES Z.Visual metaphor in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J].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2020,7(1):13-30.
[17]宋鸿立,宋雨倩.中外人文交流研究综述: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4):102-110.
[18]苗瑞.当代电影隐喻的多模态认知建构[J].当代电影,2021(3):41-47.
[19]KRUK J,LUBIN J,SIKKA K,et.al.Integrating text and image:Determining multimodal document intent in Instagram posts[C]∥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he 9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Hong Kong:Curran Associates Inc,2019:4614-4624.
[20]IBTZAEENS M,BORTMIR L.Going up is always good: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metaphors in a TV Ad with FILMIP,the filmic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J].Complutense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2020(28):189-201.
[21]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21-42.
[2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MUKAROVSKY J.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M]∥CHATMAN S.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aesthetics,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Washington: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64:41-53.
[2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232-239.
[25]BAKER M.In other words: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M].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1992:63.
[责任编辑:毛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