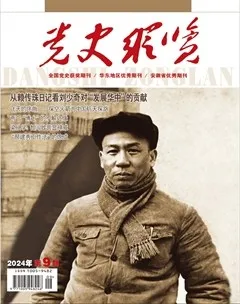善用文艺干革命的我军宣传鼓动家袁国平
袁国平(1906—1941),湖南邵东人,曾长期在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杰出的政工干部。他从小便才思敏捷,擅长吟诗作对,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师从著名戏剧家田汉,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参加革命后,袁国平更是以善用文艺形式开展军队政治宣传工作而著称,被毛泽东、陈毅赞誉为“我军的宣传鼓动家”,在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各个阶段,他都展现出了在宣传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对革命文艺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报纸撰文,提倡文艺革命化
1924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蒋介石担任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此外包括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一大批共产党人都在军校任职。此时的袁国平因老师田汉的邀请,到上海协办进步电影剧社“南国社”。打听到上海有黄埔军校秘密招生点后,素来怀有报国志向的袁国平便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并顺利通过。
1925年10月,袁国平乘船来到广州,继而通过了复考,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一团。1926年1月,袁国平又通过甄别考试,正式升为军官生,被编入政治大队第三队。
由于蒋介石的特别规定,新生入校即发登记表,登记入册后即视为加入国民党,所以袁国平一进入黄埔军校就成了国民党的一员,但他思想上还是更加倾向于共产党的主张,马列主义对青年袁国平极具吸引力。1925年12月,袁国平由于表现突出,被党组织秘密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当时国共合作背景下校内较为常见的“跨党”分子。在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规定军校任何学员“不许跨党”,要求“党内无党、校内无派”,“跨党”分子必须作出抉择,此时的袁国平毅然选择退出国民党,保留了共产党党籍。
大革命浪潮奔涌,军校生活紧张而充满激情。正如黄埔校歌所唱:“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素来爱好文艺的袁国平此时对文艺又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应提倡文艺革命化,反对资本主义文艺。于是,他在1926年6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新时代》第35期上发表文章《革命文艺谈》,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文艺的提倡。文中提出“只要是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一定含有充分的革命精神的”“我们提倡革命文艺,并不是在文艺园地里重新播种,却是使文艺园地里的枯苗复活”“我们现在应认定资本主义的文艺,已经快要死灭了,提倡革命文艺,就是文艺的复活运动”等观点,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文艺之园,是被重封密锁着的,只有资本家的姨太阔少,才能够自由自在地(的)徜徉其中,里面的园丁,也尽是被姨太阔少所收买的拜金文丐。”文中更是直接援引《共产党宣言》原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文艺和作家的局限性,批判类似泰戈尔那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把黄金当成文艺的代价一味去迎合资产阶级的嗜好,呼吁天才的作家“应赶快脱离传统因袭的束缚,走到这自由的创造路上来,大胆地呐喊前进,努力打破文艺之园的重封密锁,开始文艺革命化的工作”。同时,袁国平也对文艺革命化和文艺庸俗化进行了辨析,认为文艺革命化仍然应该保留文艺的本性,而不是“要把诗歌变成了口号,小说变成了宣言,戏剧变成了化装演讲”。可见,年仅20岁的袁国平便能成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分析革命文艺,并对资本主义文艺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此时的他已经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投身北伐,写话剧激发斗志
在黄埔军校期间,袁国平接受了专门的战时政治宣传工作训练。1926年6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为了给正在酝酿中的北伐战争培养政治工作骨干,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抽调300多名学员,借用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部分房子作校舍,举办战时政治训练班,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左派分子,而左派分子中绝大多数又是共产党员,袁国平就在其中。
训练班主任由包惠僧担任,熊雄和恽代英协助他工作。训练班主要是为了给北伐军培养政工人才,所以取消了以往的军事课程和操场训练,只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江一带的形势”“宣传要领和方法”等课程。袁国平等学员在训练班聆听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授课和演讲后,对军队中为什么要有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的范围、北伐战争中政治工作的目的和要求以及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训练班将参训学生每三人分为一组,各组成员每天下午轮流担任“主席”“演讲人”和“记录员”,进行模拟演练。各组通过反复训练,对主席风度、掌控能力如何,演讲人演讲姿势、内容、声调有何不足,记录员是否记下了重点问题等,互相观摩、点评,共同进步。袁国平的文才和口才本就出众,通过如此反复有效的训练,宣传工作能力更是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为之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展现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7月9日,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袁国平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随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8月,袁国平随宣传队来到湖南常德,帮助刚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贺龙部队改造和整顿队伍,增强革命性,提高战斗力,由此开启了近15年的军队政治工作生涯。9月5日,英帝国主义在四川制造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正在行军途中的袁国平闻此消息彻夜未眠,连夜赶写话剧《万县血》,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激发了军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第四军扩编为第四、第十一两个军,袁国平任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肩负起更繁重的宣传任务。
攻占长沙,民间曲艺来宣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从血光中觉醒,在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肆意逮捕和血腥屠杀。袁国平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并参与主持了对广州起义军余部的改编,创立了红四师,任党代表。
在率领红四师向惠东、普宁发展时,袁国平开始重视宣传品的作用。1928年3月攻打惠来县城时,部队屡攻不下,袁国平指挥部队开展政治攻势,让官兵向城内喊话:“我们都是穷人,要分土地呀!”“穷人不打穷人,你们放下武器吧!”同时,用放风筝的方式把标语传单送到城内,对敌人的斗志进行瓦解,惠来城不久即被攻破。1929年,袁国平任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他主持编印了《工农兵》杂志。该杂志作为湘鄂赣特委喉舌,宣传党的纲领、政策,其中的“红色的艺林”专栏,通过刊载短小通俗的新诗、小调等文艺作品,进行革命道理宣传、开展革命动员。杂志每期都配有漫画,将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和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1930年6月,袁国平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进一步发挥了他善用文艺干革命这一特长。
1930年7月,蒋、冯、阎、李军阀“中原大战”,湘桂军阀混战,此时的长沙守敌力量薄弱,红三军团于7月27日夜间攻占了长沙,一举控制全城,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攻占的唯一一座省会城市。红三军团刚进占长沙,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便意识到在新占领城市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第二天便派出政治部秘书长邱炳、青年干事邱一涵等去皇仓街38号接管《民国日报》,利用原有印刷设备创办《红军日报》。《红军日报》主编由袁国平和宣传干事左忠基担任,在短短的9天时间内连续出版6期,前3期4版一大张,后3期6版一张半,每期第一版固定刊登《共产党十大纲领》《土地政纲》以及红三军团布告、通告等,第二版刊登署名社论,均由袁国平、左忠基撰写。
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让更多群众接受,《红军日报》在《投稿规约》中明确要求:“来稿请用白话,尽期明了畅达,富有鼓动性为合格,凡迂长拘拗令人费解的文字,本刊均不采用。小说诗歌等作品注意于写实方面,空幻无着的文字,纵好只得割爱。”按袁国平要求,《红军日报》的消息标题大部分都是口语化的,新闻也多半是简短的,长者不超过600字,短者只有七八十字,而且注重口语表达,使文意顺达,浅显易懂。同时袁国平还注重运用当时广泛流行于湖南农村地区的戏曲、民歌、民间小调等民间曲艺形式来表达革命思想、宣传党的主张。从《红军日报》第二期起,在第四版文艺副刊“血光”专栏中就可见到用四川调编写的《革命伤心记》《共产党十大政纲》,用莲花闹曲调编写的《反国民党军阀混战》,用孟姜女哭长城十二月调编写的《工农兵》《妇女革命诗》《反对军阀战争》等,使得深刻的革命道理通俗易懂,且对仗工整、平仄押韵、易于流传,深受群众喜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三反“围剿”,军民共谱《胜利歌》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调集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朱德沉着应对,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一方面指挥留守赣南的红军配合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军前进;一方面命令还在闽西和闽西北的部队迅速收拢,回师赣南,诱敌至兴国、于都、瑞金、宁都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把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布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袁国平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从闽赣边界的黎川沿武夷山脉向南急进,先在于都银坑与红七军、红三军会合,接着奔赴兴国高兴圩,在半个月时间里来了个千里大迂回,随后投入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任务。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于8月7日至11日取得三战三捷,最终干净利落地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俘虏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
袁国平在参与指挥莲塘、良村、黄陂、高兴圩、方石岭的几次战斗中,领导各级政工干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认真贯彻毛泽东、朱德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激发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为红军取得一系列战斗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保证。袁国平根据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具体情形满怀豪情地创作了《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以下简称《胜利歌》),歌曲分成三大部分,共11段、218行、1528字。歌词生动形象,好记易懂,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将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过程酣畅淋漓地唱了出来。在整首歌最后一段,对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进行了准确而全面的总结:“三期战争获全胜,胜利原因要记清,第一莫忘共产党,共产党主张样样灵。第二红军团结紧,十人团结胜千人。第三群众力量大,群众拥护一定胜。学此经验和教训,不愁百战不百胜。”1932年初,由袁国平创作的《胜利歌》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政治部的名义印发,受到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仍然保存着当时出版的《胜利歌》64开小册子,为国家一级文物。
1933年初,当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军事“围剿”时,红一方面军各支队伍在战前动员和行军途中都高唱《胜利歌》,极大提升了队伍士气,激发了红军与根据地群众旺盛的革命斗志。如今,在会昌县周田镇半岗村一幢老屋内的墙壁上,还可见到红军干部用行楷体抄写的《胜利歌》,因字数之多、面积之大而被当地称为“苏区红军标语王”,足见《胜利歌》的深入人心。
皖南赴任,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南方八省14块游击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同陕北主力红军改编而来的八路军一同参与到对日作战中。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和特务营奉命于2至4月间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地区,集中进行组编点验和军政训练。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袁国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常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发给项英的电报中,毛泽东对袁国平开展政治工作的能力高度称赞:“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4月26日,袁国平到达新四军驻地走马上任,在军直属部队及3个支队排以上干部誓师大会上作了演讲,他宏亮的声音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把在场的官兵都吸引住了。袁国平在演讲中指出:“新四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敌后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共同协力抗战。”
1939年2月,已移驻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召开欢迎晚会,欢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视察新四军军部并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确定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在晚会现场,刚调来云岭工作的作曲家何士德在参会人员的热情提议下,用雄浑的男中音演唱了《歌八百壮士》,随后,陈毅也用法语即兴演唱了激昂的《马赛曲》,整个礼堂气氛热烈。欢迎会结束后,陈毅无比感慨地表示,新四军也应该有自己的军歌,能够让全军统一思想,激发斗志。军部几位领导表示赞同,建议陈毅先写出歌词,然后找人谱曲。
陈毅作为人民军队早期领导人,从北伐的铁血荣光、井冈山的坚定执着,到反“围剿”的壮怀激烈、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至今走过的每一步都深深印刻在他脑海中。他很快便写出了初稿,歌词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北伐军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前后十余年不懈斗争的精神,歌名取其历时的整数,名为《十年》。袁国平受副军长项英委托,主持了接下来的修改工作。在与叶挺、项英、陈毅、李一氓、朱镜我、朱克靖、马宁等同志进一步讨论修改歌词的同时,袁国平还积极与作曲家何士德交流谱曲。何士德谱出的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易唱,但战斗气氛不足。袁国平听后,对何士德说:“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并提议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最后一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都要重复两次,以增强歌曲气势,体现更强的力度和更加昂扬的斗志。何士德对袁国平的要求认真领会、消化吸收后,很快谱出第二稿。第二稿完成后,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反映,根据大家的意见,何士德再一次作了大修改,使得每段最后一句歌词连续唱三遍,每重复一次,音高都要高于上一次。
1939年7月1日,《新四军军歌》在文化队驻地新村试唱时,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均到场品评,听过后一致认为这一稿符合新四军军歌的风格,能展现出我军坚决东进抗敌和进军敌后的精神,袁国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通过!并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以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的署名发表在《抗敌报》上。新四军政治部还发出通知,将军歌印发至全军,组织教唱。新四军全体将士乃至根据地人民都从激昂雄壮的旋律中受到鼓舞。
这期间,袁国平对于抗战时期的革命文艺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为纪念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新四军抗敌剧社组织表演夏衍的四幕大戏《一年间》。演出结束后,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主持召开座谈会,袁国平作了总结讲话,对“我们现在的艺术观”“抗战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创作问题”以及“集体研究集体创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篇讲话稿后以《抗战中的艺术观》为题,在1939年6月11日《文艺》杂志第三期上发表。文中提到“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所以帝国主义时代布尔乔亚的艺术也与布尔乔亚一切制度文化一样的(地)日趋没落”,再一次呼应了他在《革命文艺谈》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文艺,已经快要死灭了”的观点,同时也回顾了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再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中国近代艺术发展历程,认为“艺术是受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的,并如何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而在抗战当前,“艺术应该为抗敌救亡服务,这是非常明白的一个真理”。对于“抗战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这一问题,袁国平提出了国防的、统一战线的、大众化的、集体主义的、新写实主义的这5点要求。而对于“创作问题”,袁国平也从创作与生活、理论与创作、内容与形式这3个角度出发,阐述了青年作家应该要深入抗战队伍去成为战斗一员、把握住一种前进的思想和理论、在内容上抓住生活的重点而不必拘泥于一定的形式的观点。与《革命文艺谈》相比,袁国平此时的革命文艺观与时俱进地产生了跃进,对于文艺如何服务于抗日救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加入抗战队伍的青年作家开展创作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奉命北移,《别了,皖南》成绝唱
1940年10月,国民党发出臭名昭著的“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尽管经过中共中央的斡旋,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是为顾全大局,皖南新四军部队仍遵照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北移。11月下旬,在中共中央下达皖南新四军部队必须在20天内开动完毕的命令之际,为了让广大新四军将士明白部队北移的重大意义,袁国平亲自动手,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动员提纲,即《向敌后进军宣传鼓动大纲》,并在结尾附上一首充满鼓动性的自由诗:“前进号响了,大家准备好,子弹要随时准备上膛,刺刀要随时准备出鞘。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向敌后抗战的大道。顽固派滚开,投降派打倒,日本鬼子碰到了,打完子弹拼刺刀。不怕山又高,不怕路又遥,山高总没有雪山高,路遥总不比长征遥,敌后进军胜利了,自由的中国在明朝。”该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进军的目标、意义以及一路上需要克服的艰难险阻,并与红军长征进行对比,极具鼓动性,最后一句“自由的中国在明朝”也带给人无限的希望!
1940年年底,袁国平将这首自由诗进行了修改,交给随军的作曲家任光谱曲,希望以此军歌为即将北渡长江的新四军将士打气,以开辟新的根据地。任光备受鼓舞,把自己同新四军和皖南人民的感情融入创作,几天之后充满激情的军歌《别了,皖南》便在寒风萧瑟中诞生。新四军将士们在紧张的北移准备中抽空学习了这首告别曲,可谁曾想这却成了英雄绝唱!
1941年1月6日晚间,正当奉命北移的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高唱着《别了,皖南》行走在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了国民党军共8万人的围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经过几个昼夜的激战,新四军不仅子弹、手榴弹打光了,粮食也所剩无几。13日,军部直属队的许多非战斗人员,在一个叫作石井坑的小山村,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任光不幸中弹牺牲。两天后,袁国平在突围时身中4弹,重伤难行。为了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不影响部队行动,他悄悄地摸出手枪,趁大家不备,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践行了“如果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誓言。
袁国平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就此定格在35岁,而由他主持修改和创作的《新四军军歌》和《别了,皖南》,却激励新四军将士在后来的斗争中重建军部,在敌后开辟出新的抗日根据地,并取得对日伪军作战的一系列胜利,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陈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