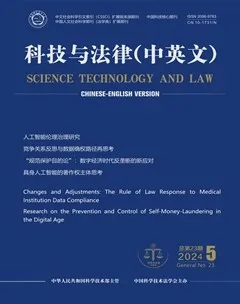竞争关系反思与数据确权路径再思考

摘 要:围绕数据权益保护,有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之分。但两种模式是否截然二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行为规制模式是否存在数据赋权的可能性,都值得再思考。司法实践中,竞争关系认定已经趋于泛化,其不适宜再被定位为实体要件或起诉条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重心应由“竞争关系”转向“竞争秩序”,由此竞争法上数据权益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对世性。权利和利益的分野并不在其采取的保护模式,而在其是否契合权益区分的法教义学标准。只要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清晰到获得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程度,行为规制模式亦可实现权利化。鉴于当今司法实践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权益,凝聚两种模式的共识,以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落地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或许是为一条可行路径。*
关键词:竞争关系;数据权益;行为规制权利化;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
中图分类号:D 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4)05⁃0025⁃12
利益保护存在权利保护以及行为规制两种模式:权利保护模式“设定具体权利类型以涵盖相应利益,并将相应利益划归权利人享有,赋予权利人一般性的排他可能性”;行为规制模式则“从他人行为控制的角度,来构建利益空间,通过对他人特定行为的控制来维护利益享有者的利益”[1]。围绕数据权益保护,同样存在这二者之分:权利保护模式肯定数据权利属性,主张赋予数据控制者以排他性的权利[2];行为规制模式则否认数据权利属性,主张通过规制他人行为从而维护数据控制者的利益[3]。但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是否截然二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行为规制模式是否同样存在赋权的可能性,都值得再思考。持数据权利保护模式论者反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路径的一大理由是其仅可解决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间的纠纷[4],竞争法上的数据权益由此具有非对世性,但事实上,数据权益纠纷中竞争关系的认定已经泛化。因此,本文将在对竞争关系全面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数据确权反不正当竞争法路径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一、数据权益纠纷中竞争关系的泛化
“按照通常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必须限于竞争者之间实施的行为,以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为同业竞争者(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的经营者)为前提。1”同业竞争亦是数据竞争纠纷中最常见的情形。例如,抖音诉刷宝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短视频服务,二者因刷宝搬运抖音短视频数据而引发争议2;丁香园诉医学界医生站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医疗行业资讯、药品说明书查询等服务,二者因医学界医生站盗用丁香园药品说明书数据而引发争议3。
在同业a5b4f87d932df4a8d9e6dcec04b6ae3d竞争的情形下,大多观点认为竞争关系是实体要件(本文称为“实体要件说”)4,如丁香园诉医学界医生案中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本案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5”。除此以外,还有部分实体要件论者认为竞争关系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学者就认为,“竞争关系应当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前置标准。[5]”有案件如抖音诉刷宝案中,法院虽未明言,但是将经营者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纳入“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予以考量6。
但在数据竞争纠纷中还存在其他可能:第一,二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种类虽不同,但有所重叠。如大众点评诉百度地图案中,大众点评是“城市生活消费平台”,百度地图主要提供导航服务,但二者均为用户提供商户信息和用户点评信息,因百度地图抓取大众点评商户信息和用户点评信息引发争议7。第二,二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种类完全不同,如微博诉蚁坊案中,微博提供社交网络服务,而蚁坊提供数据分析服务,但二者因蚁坊抓取微博数据而引发争议8。
为了使反不正当竞争法仍然能对这两类数据竞争纠纷予以规制,理论界和实务界试图扩张竞争关系的范围:第一,认为争夺相同的用户即有竞争关系,如大众点评诉百度地图案中,法院认为“即使双方的经营模式存在不同,只要双方在争夺相同的网络用户群体,即可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9”第二,认为破坏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并获得竞争优势(损害竞争利益并获取竞争利益)即有竞争关系,如微博诉蚁坊案中,法院认为“只要经营者的行为不仅具有对其他经营者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且其同时会基于该行为获得现实或潜在的经济利益,则可以认定二者具有竞争关系。10”第三,认为破坏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即产生竞争关系,如蚂蚁金服诉企查查案中,法院认为“即使经营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经营者也因破坏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优势与其产生了竞争关系。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应是采取此种思路⑫。
而随着竞争关系泛化,有的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中以各种理由和说法扩张竞争关系的解释,实质上已使竞争关系成为虚置”,故而应当“放弃竞争关系的要件地位”“不再将其作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要件”,但“可作为确定原告资格的考量因素”[6]。实践之中亦有其支持者,如微信诉科贝案中,法院认为“竞争关系既不应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亦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条件,但其仍具有原告资格意义。⑬”换而言之,此时竞争关系已由实体要件转变为起诉条件(本文称为“起诉条件说”)。
比起诉条件说更进一步的观点是干脆不要竞争关系,认为其既非实体要件,亦非起诉条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应当回归行为本身(本文称为“竞争关系废除说”)。如有学者认为“竞争关系已被消解和虚化,有的只是竞争行为。[7]”有的司法政策认为,“竞争关系并非认定不正当竞争或者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的条件。[8]”有的案件如“一起来捉妖”游戏诉虚拟定位插件案中,法院认为“对于不正当竞争之诉成立与否的判别,应着眼于经营者实施的特定行为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属性。至于经营者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并不属于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或认定不正当竞争的必要前提。⑭”
二、竞争关系并非起诉条件
近年来,在实体要件说、起诉条件说和竞争关系废除说中,起诉条件说比较流行[9–11],但本文认为,将竞争关系作为起诉条件既有违民事诉讼基本原理,亦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体系上的负效应。
(一)将竞争关系作为起诉条件有违民事诉讼基本原理
第一,起诉条件说“由行为而关系”的界定范式与起诉条件的审查模式不相符合。秉持起诉条件说的学者认为竞争关系的界定范式是“由行为而关系”,亦即竞争关系是因竞争行为而产生的损害与被损害的关系,进而成立民事诉讼资格中的直接利害关系[9]。依照这一逻辑,人民法院在审理不正当竞争纠纷时就只需要判断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可,竞争关系可伴随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成立而自然地推理得出。然而在我国,原告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首先审查的往往是原告起诉是否符合包括原告适格在内的起诉条件,而非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实体要件[12]。因而从这一层面来看,如认为竞争关系是起诉条件,其反而与实体要件说“由关系而行为”⑮的思路更为接近。
第二,将竞争关系等同于原告资格要件有违当事人适格理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解释‘其他经营者’的方式界定了损害与被损害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所以“竞争关系是原告资格条件,据以认定原告有诉的利益”[13]。有法院亦认为由于原告和被告“存在直接的市场竞争关系”,故原告“有权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对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提起诉讼。⑯”
但由竞争关系到原告资格要件的推理并非如此理所当然。有竞争就有损害,“仅就竞争优势和商业机会而言(下文第三部分将陈述竞争关系和竞争优势、商业机会的紧密联系——引者注),它们还不构成单独可诉的民事利益[14]。”“《反不正当竞争法》之所以给予保护,乃是因为他人攫取该利益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14]。换而言之,中性的竞争性损害本身并不足以产生“解决纠纷的必要性与实效性”的诉的利益,在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原告之所以能提起诉讼,并不是因为他受到损害,而是因为他可能因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受到损害。
并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已将竞争关系由同业竞争泛化至“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情况下,如将此种泛化后的竞争关系直接作为原告资格要件,不正当竞争之诉势必泛滥。有法院即指出:“如果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将市场经济活动中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关系等同于《民事诉讼法》中的直接利害关系,则既有可能使经营者面临不可预测的诉讼风险,难以激发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将架空《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使既有的民事诉讼法理论和诉讼实践受到严重冲击。⑰”
(二)将竞争关系作为起诉条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的负效应
如将竞争关系作为起诉条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关系既是实体要件,又是起诉条件的情形:
第一,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竞争关系显然是商业诋毁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为了避免在商业诋毁行为上出现竞争关系同时是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的悖论情形,起诉条件论者便对其学说以修正,认为竞争关系“通常不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性构成要件,除非法律对竞争关系有明确规定”[13]。但即便如此,仍会出现竞争关系在商业诋毁行为中是实体要件,在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中是起诉条件的吊诡情形。
第二,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即为“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上所述,起诉条件论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2条以解释“其他经营者”的方式界定了损害与被损害意义上的竞争关系[13]。那么“其他经营者的损害”便不可避免地同时构成实体要件(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中的损害)和起诉条件(原告的损害)的内容,并且竟然“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属于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中两个独立的争点。[9]”
而竞争关系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定位绝不仅仅只是名称上的变化,其在程序法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意义:
第一,提供证据责任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法释〔2022〕11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了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规范说”,其将民事实体规范分为权利发生规范以及权利对立规范,而主张适用相应实体法规范的当事人应就存在该规范的构成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15]。如将竞争关系定位为实体要件,无论是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条件,还是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竞争关系无疑都属于使得权利产生的要件事实,那么依照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由原告承担其与被告存在竞争关系的证明责任,进而应由原告提供证据。而若将其定位为起诉条件,虽然对程序事实的证明责任学界存在争议⑱,但没有疑义的是,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其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
第二,证明标准不同。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本证的证明标准在原则上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法释〔2019〕19号)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与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的证明标准采取较大可能性标准。亦即将竞争关系定位为实体要件,其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而若将其定位为起诉条件,其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
第三,裁判结果不同。如果认为竞争关系属于实体要件,那么当不具备此项要件时,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例如,30号指导案例的法院认为由于原告与被告“并不存在具体的竞争关系”,故原告“此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⑲。而如果认为竞争关系属于起诉条件,那么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当不具备此项要件时,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⑳。
总而言之,将竞争关系作为起诉条件,将不可避免地使得竞争关系既是实体要件,又是起诉条件。而竞争关系实体要件和起诉条件的不同定位将会导致其在提供证据责任、证明标准和裁判结果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矛盾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体系上的负效应。将竞争关系定位为起诉条件有违民事诉讼基本原理,亦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体系上的负效应,故而本文认为竞争关系不适宜被认定为起诉条件。
三、解释论视野下竞争关系向竞争秩序的转变
既然竞争关系并非起诉条件,那么其是否是实体要件?在解释论视野下,我们可以发现竞争关系亦非实体要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重心应当从是否构成竞争关系转变为是否扭曲竞争秩序。
(一)文义解释下竞争关系并非竞争行为构成要件
“任何文本的解释都始于对文字文义的解释”“根据一般语言用法获得的文义构成解释的出发点,同时也构成解释的边界”[16]。不正当竞争行为首先是竞争行为,有学者认为“竞争行为是相对性行为,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只能发生在竞争者之间。[5]”这种观点在同业竞争时代是完全合理的,但正如上文所言,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已经泛化,从同业竞争扩展到了“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标准,而这实际上已经消解了竞争行为的相对性。
一般认为,竞争的本质在于对客户即交易机会的争夺[5,11,17],因此“争夺交易机会”仍可为竞争关系的语义所涵摄。而竞争优势与交易机会密切相关,“竞争优势是获取商业机会的条件或者能力,商业机会是竞争优势猎取的目标。”“获取竞争优势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18]”可是如果经营者间仅存在“损害竞争优势”的关系,而其产品或者服务不可互相替代,那么难以想象二者可能争夺交易机会。例如,在微博诉蚁坊案中,微博提供社交网络服务,而蚁坊提供数据分析服务,二者的服务不可替代,即使蚁坊对微博的竞争优势造成损害从而导致微博失去交易机会,蚁坊也不可能夺取微博的交易机会而与微博的交易相对人产生交易行为。
由此可见,将“破坏竞争优势”的情形解释为具有竞争关系,其实已使竞争关系偏离竞争本质。一方面认为“竞争行为是相对性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发生在非竞争者之间的行为”甚至可以“无特定对象”,未免有些自相矛盾[5]。无怪乎有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以各种理由和说法扩张竞争关系的解释,而其扩张的理由越来越牵强,其实际目的无非是为了摆脱竞争关系在认定不正当竞争中的传统束缚,也说明竞争关系确已成为不必要的束缚和障碍,实现竞争关系的突破势所必然[6,9]。
其实,竞争关系并非竞争行为构成要件。还以微博诉蚁坊案为例,首先,行为相对人并非与之争夺交易机会的竞争对手并不意味着蚁坊的行为不属于竞争行为。蚁坊公司产品鹰击系统的优势之一即“监测窗口能实时动态显示数据,微博数据更新频率是秒级”,蚁坊抓取微博数据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与其他舆情监控产品争夺交易机会。其次,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便蚁坊通过与微博合作的方式获得其数据,亦不改变其攫取竞争优势进而夺取交易机会的目的,不影响其竞争行为的定性。简言之,经营者“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夺交易机会,所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经营行为归根结底是市场竞争行为”[6]也无不妥。竞争行为并不以行为人和作为其对象的经营者间存在“争夺交易机会”或“损害竞争优势”的关系为其构成条件。
(二)体系解释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对竞争关系界定不一
在法律解释中应当遵循“整体性”原则,应当将作为解释对象的表达法律的语言文字置于其所处的法的整体中进行理解,对法律概念之具体含义的解释应在法的整体中具有统一性,而所谓“整体”不仅包括法律文本之整体,而且包括法律部门之整体乃至法律体系之整体[19]。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制横向垄断协议,亦即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而根据《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号)第八条,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包括处于同一相关市场进行竞争的实际经营者和可能进入相关市场进行竞争的潜在经营者。”由此可见,在反垄断法上判断经营者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的关键在于界定相关市场,“科学合理地界定相关市场,对识别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等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21”同时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22和《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三条23可知,在反垄断法中替代性分析仍然是界定相关市场的基本依据,是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竞争关系的基本标准。
在反垄断法对竞争关系仍然秉持替代性分析基本思路的情形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却已泛化。一方面,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替代性的经营者间存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具有替代性的经营者亦可因损害竞争优势而产生竞争关系。在要求法律体系内的概念保持一致性的背景下,同一部门法甚至同为竞争法分支的两部法律,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竟然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其科学性存疑。
或许会有观点认为既然反垄断法是自由竞争法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公平竞争法[20],那么便可理解为何竞争关系在二者中的界定并不一致。但事实是,反垄断法亦维护公平竞争,反垄断法“追求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意图实现企业的最大自由,并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缔建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21];反不正当竞争法亦保护自由竞争[10],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自由竞争为主,而公平竞争为辅,市场自由竞争乃为原则,而以公平竞争之名干预市场则为例外[17]。因此,反垄断法是自由竞争法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公平竞争法这种区分看似周延,但事实上可能人为割裂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内在关联[10]。如果反不正当竞争法保留竞争关系,那么其应与反垄断法中的界定保持一致。
(三)历史解释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侵权法分离关键之一在于竞争秩序嵌入
反不正当竞争法起源于侵权法,为维护诚实经营者利益而创设,具有显著的侵权法血统:法国在运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处理不诚实商业行为的基础上,形成了反不正当竞争判例法;德国1896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创了专门立法先河,但由于只列举了五种行为,法院不得不援引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来处理层出不穷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而英国则是选择了普通法下的仿冒侵权之诉来保护竞争者[22]。
但随着时代发展,世界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共同基础逐渐已由保护“诚实企业主”演变至保护“未扭曲的竞争”[23]。我国亦是遵循此种路径,2017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第二条第二款的一个显著修改即将“社会经济秩序”改为“市场竞争秩序”,并将其置于“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前。这首先回应了实践中对经营者权益损害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间关系的争议,旗帜鲜明地反对“损害(经营者的)特定权益基本上就等同于扰乱秩序”此种对竞争秩序的简单理解,而更为强调竞争秩序的独立价值[18];其次,它不仅意味着竞争秩序具有独立于经营者利益的价值,而且意味着“维护健康的竞争机制是反不正当竞争的首要目标”“在三种利益发生冲突时……竞争秩序处于优越地位”[17]。由此竞争秩序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侵权法的分界点,“从强调竞争者保护到强调竞争秩序保护,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侵权法演变为了市场行为法。[24]”
由此可见,现代反不当竞争法之所以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扭曲了竞争秩序。然而事实是并非只有不正当地造成竞争者损害的行为才会因扭曲竞争秩序而被评价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示范规定》中即指出,“当某一行为并非针对从事该行为之人员的竞争对手时,它却可能通过提高该人员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来影响市场上的竞争。”例如,“当某驰名商标由非该商标注册人的人员用于完全不同的产品时,虽然该商标的使用者通常并不与注册人竞争,但使用这一商标却是与竞争相关的,因为该使用者不公正地获得了优于未使用该驰名商标的竞争对手的优势”[25]。反之亦然。
总而言之,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泛化的竞争关系已经偏离竞争本质远矣,与反垄断法上的竞争关系亦存在着体系上的牴牾,将其解释为起诉条件也有违民事诉讼基本原理,还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体系上的负效应。在此种情形下,与其固守竞争关系,不若直接放弃其要件定位,而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重心转变至是否扭曲竞争秩序。
四、权利保护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二分之反思
在放弃竞争关系要件定位后,竞争法上的数据权益就并非仅仅针对其竞争对手的相对性权益,而是获得一定程度的对世性。在此基础上,破除权利保护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截然二分的迷思,可以发现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行为规制模式同样存在赋权的可能性。
(一)权利保护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截然二分迷思之破除
区分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的观点,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利益保护的两种不同模式,但太过强调二者间的对立,则会忽视二者交融的可能性。以二者争议焦点之一的外部性理论为例,权利保护模式强调负外部性的危害性,主张“通过赋予数据主体以数据产权的方式将负外部性效应内部化”[2];行为规制模式则认为搭便车行为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不仅不会损害数据价值而且可以激发个体参与数据生产[3]。但事实上行为规制模式亦可对外部性加以规制而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经济学家即指出“政府可以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26],经济法学者亦撰文阐述“搭便车”问题的竞争法规制[27]。
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不仅在理论依据上相互交融,而且在规制范式上互有融合:第一,权利保护模式暗含行为规制蕴意。正如奥斯丁所言,“并不存在仅仅创设权利的法律……每一部真正赋予权利的法律,都明示或默示地规定了某种相对的义务,或一种与权利相关的义务。[28]”以所有权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一方面在第二百四十条从正面赋予所有权人以支配物的权利;另一方面在第二百三十五条至二百三十七条以物权请求权的方式从反面排除他人对所有权圆满支配状态的妨碍。物权请求权看似为物权人的权利,其实无异于通过控制他人妨碍物权圆满支配状态的行为,而为不特定人设定义务。这亦即“如果规定了权利受到侵犯时应采取的补救措施,则明确规定了相关义务。[28]”
第二,行为规制模式亦可实现权利保护。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的二分,暗含采行为规制模式保护的利益未上升为权利的言下之意,如个人信息就因采取行为规制模式而被认为未达到权利密度[1]。但事实情况是行为规制亦可实现权利化的效果,知识产权即“采取一种‘行为规制权利化’的技术路径,在对客体的特定利用行为上架构利益的保护空间”,如著作权的本质就在于“对复制、发行、表演、信息网络传播等利用行为的排他性控制”[29]。甚至有学者直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就可以被视为行为主义或具有显著行为主义特征的法律规制模式。[3]”权利保护模式虽然以物权为典型(本文将以物权为模型的权利保护模式称为“典型权利保护模式”),但绝非仅有这一条路径。
事实上,权利和利益的分野并不在于其采取何种保护模式,而在于其是否契合权益区分的三个法教义学标准:归属效能的核心在于将确定的权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排除效能的核心在于主体排除他人的一切非法干涉;社会典型公开性的核心在于使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的可能性,从而兼顾潜在加害人的行为自由[30]。以此种标准检视个人信息,可以发现个人信息权益内容归属于特定的主体,个人信息主体具有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效能,社会一般主体可识别个人信息权益,因而个人信息完全契合权益区分的三项法教义学标准,在性质上应为权利而非利益[31]。也就是说,即使是为行为规制模式所保护的利益,只要其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清晰到足以超越个案而获得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程度,就可以上升为权利,这即行为规制权利化。侵权行为法就具有此种权利创设的功能,如隐私正是在侵权司法纠纷的逐步积累中而脱离利益定性,而取得其权利地位的[32]。
那么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权益的性质究竟为何?事实上,保护客体由竞争者权利向竞争者利益的转变被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侵权法上升为社会法的标志之一。在域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经历了从“权利保护”向“利益保护”的过渡;而在我国,“权利一元保护”与“利益一元保护”之争也大致以“利益一元保护”逐渐成为通说而告终[33]。应当承认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利益有很大的模糊性”“是否保护常常取决于个案的判断”,故而“通常达不到权利的程度,只是一种不很确定、不很稳定的法律上的利益”24。
但正如上文所述,采取行为规制模式保护的利益如果经过个案的检验亦有上升为权利的可能性,“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承担赋权角色,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误解。[13]”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侵权法一样可以成为权利的孵化器,如体育赛事节目、游戏保护正是在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凝聚出权利保护共识,而进入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中的[34]。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利益不仅外溢形成权利,而且因禁止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产生的一些利益亦已达到了权利保护的密度,有学者即主张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权利”和“利益”双重客体,而在这些权利中尤以商业秘密最为典型[33]。如果脱离以物权为代表的经典财产权观念,可以发现商业秘密保护已经满足归属效能、排除效能以及社会典型公开性三项要件,在法律属性上应当属于权利的范畴[35]。《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即采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这一表述,《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第二款第五项亦将商业秘密纳入知识产权客体之中。
(二)典型行为规制模式、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和典型权利保护模式的关系
由此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可以保护利益,而且可以通过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创设权利。这种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是以物权为模型的典型权利保护模式外的又一赋权路径,上文陈述了二者在理论依据和规制模式上的诸多交融之处,下文将探讨二者在具体特征上的不同:
第一,二者权利生成路径不同。典型权利保护模式生成的权利如物权首先是自用权,然后才是排他权;而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生成的权利如知识产权则首先是排他权,然后才是自用权[36]。这从《民法典》的规定即可看出:对物权,《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排他权是其自用权的当然结论;与之相反的是,对知识产权,《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则是规定“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而“专有”来自英文“exclusive”,可以翻译成“专有的”,也可以翻译成“排他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知识产权并非自用权,而仅为排他权,其作用“并不在于确认权利人有为某种行为的自由,而在于排斥他人为特定行为”,并举一例论证:为他人拍摄全裸写真的摄影师,仅可阻止他人包括被拍摄者本人发表该摄影作品,而无权发表该摄影作品,因为这样做会侵犯被拍摄者的隐私权[37]。又如改进发明专利权人,虽然享有对改进发明的专利权,但是不得在未经在先发明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形下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换而言之,自用权与其说是知识产权本身权能,不如说是源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行为自由。
第二,二者权能涵摄范围不同。虽然典型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均可生成排他权,但其排他权的权能涵摄范围并不一致——典型权利保护模式生成的物权是全面排他权,而行为规制权利化的知识产权是有限排他权。物权人对物乃为圆满支配,而当物权人对物的圆满支配状态受到妨害或有被妨害之虞时,物权请求权即告发生。但是知识产权并非如此,一项特定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的行为,关键在于这项行为是否受到专有权利的规制,以及是否存在特定的法定抗辩事由[37]。例如,购买盗版书籍阅读和购买盗版软件使用二者貌似相同,但其法律性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前者并不属于《著作权法》第五章规定的任何一种侵权行为,而后者却为第五十三条第一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的规定所禁止。
第三,二者权利结构模型不同。典型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排他性的不同,归根到底源于其权利结构模型的不同,物权是典型的权利球模型,是物权人对物圆满支配的权利,其虽然可能因为限制物权或权利受到侵害而有贬损之虞,但当此种情形消除时即回复圆满状态[38]。这也就决定了,对他人干涉物的行为,法律原则上禁止,例外允许。而知识产权的权利模型是权利束,它由一个个互相平行的权利木棍扎成,如著作权就主要体现在对作品为发表、署名、复制等行为的控制上[39]。因此知识产权对行为的禁止其实仅为例外,这些例外之外的广阔范围均属他人行为的自由范畴。
总结前文,可以发现行为规制模式(图 1左圆)和权利保护模式(图 1右圆)与其说是矛盾关系,不若说是交叉关系,其交叉之处正是在于行为规制权利化(图 1两圆交叉区域)。25其中典型行为规制模式(图 1左圆交叉区域外的部分)通过控制他人特定行为来维护利益享有者的利益,但其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尚未达到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程度;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亦控制他人特定行为,但已获权利所要求的社会典型公开性;典型权利保护模式(图 1右圆交叉区域外的部分)则产生全面排他权,控制他人妨碍权利人对权利客体圆满支配状态的全部行为。
五、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下的数据确权
由此可知,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并非截然二分,利益保护存在典型行为规制模式、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和典型权利保护模式三种模式,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兼具权利保护特征和行为规制色彩,与数据权益保护相契合。
(一)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的选择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在数据的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保护模式之间,前者逐渐获得优势地位。但限于行为规制模式不可设定权利的传统认识,学术界的权利保护模式具有浓厚的物权法色彩,“数据所有权—数据用益权”[40]等物权路径自不待说。作为新型权利的“数据财产权”同样也深受物权影响。如数据财产权利用、收益、占有和处分的权能是对所有权权能的借鉴[41];还如虽然肯认了数据财产权的有限排他性,但对数据财产权的限制应以法律方式为之又映射出物权的权利球模型,而与行为规制外皆为行为自由的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迥异[4]。
物事实上可以排他,物权的排他性是法律确认的,而与之有所不同的是,数据事实上难以排他,数据财产权的排他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制造的[42]。这就决定了物权是全面排他,而数据财产权应是有限排他。并且这种有限排他性的实现,不应以对权利球的限制为基础,而应采取行为规制权利化的权利束路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物一权’理论已难以对新生演化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解释”,权利束理论“更有利于促进数据的权能分离与流通利用”[43]。
与学术界不同的是,实践中对数据权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行为规制模式实现的。物权路径早已在淘宝诉美景案中被人民法院以“物权法定”为由否定26。知识产权路径固然存在大众点评诉爱帮网案27等成功案例,但数据持有人和著作权人往往并非同一主体,在大数据时代要求数据持有人逐一获得著作权人授权显然不太现实,而格式条款的约定又有效力隐忧,故而在抖音诉刷宝案中法院明确指出,“著作权法对单一作品或者录像制品创作者的法律保护,并不适用于微播公司。28”因而总体而言,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兜底条款实现对数据权益的保护。
但“当前数据权益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是一种事后保护,没有预定的具体法益模式”,这种通过个案裁量进行个案保护的方式存在“不适宜大量、重复和反复的数据权益保护需求”“不利于事先建立系统、明晰和稳定的保护标准”等明显不足,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性选择,而不是一种终极性办法。[44]”同时一般条款的泛化又“有脱离并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上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架空,而无限膨胀法定类型之外的但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救济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危险。[45]”因此立法和司法解释尝试凝聚共识,赋予数据权益保护超越个案的社会典型公开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六条试图从解释论的角度凝聚实践中的共识,以实质性替代为核心构建数据利用行为规范;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则从立法论的角度,参考日本限定提供数据制度,以商业秘密制度为蓝本设计商业数据专条。2024年5月6日公布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十九条“经营者不得……非法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的表述与数据资源持有权相当契合。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新一轮修订仍然处于草案阶段,最终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亦删去了第二十六条,何为《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的“非法获取、使用”仍有待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数据权益行为规制保护模式在归属效能和排他效能上对个案的超越已是大势所趋,以“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构建数据产权正当其时。
(二)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下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
《数据二十条》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有学者将产权和权利保护模式等同,然而“数据产权”的表述本身即为行为规制权利化预留了空间。在产权理论的开创者科斯看来,不仅所有权是产权,而且禁止牛毁损谷物的行为或者允许牛毁损谷物的行为亦为产权,而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产权的初始界定不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46]。在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德姆塞茨看来,产权是一种“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通过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而使竞争者受损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诋毁他就不行了。[47]”而这类行为权利显然已经无法为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ownership)所涵盖,这样“产权”(property rights)作为一项新的范畴便应运而生[48]。
受到物权模式影响,笔者曾倾向于借鉴农地三权分置,以权能分离理论解释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49],但以此建构的权利体系稍有冗杂之感,远不如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清晰明了:
首先,“数据处理者对依法依规持有的数据进行自主管控”的数据资源持有权可以被解释为排他权。排他权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落地应当进行类型化的设计,提炼不正当竞争纠纷中特定行为的社会典型公开性,慎用一般条款和兜底条款设计,否则无异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或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在数据领域的简单重复,也难以称为权利化的实现。29而无法为类型化设计所保护的数据利益,仍然可以交由上述两条保护,在个案中逐渐积累权利共识。
其次,可将“数据处理者许可他人使用数据或数据衍生产品”的数据产品经营权解释为许可权,而“许可权,一定是从禁止权中派生出来的。[37]”如果行为不为持有权所排除,他人便可在不征得持有权人许可的情形下为之,持有权的排他范围决定了经营权的许可范围。许可权的行使,在初期可依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参照适用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30,待得时机成熟,便可纳入典型合同或与持有权一道专门立法。
最后,“数据处理者使用数据和获得收益”的数据加工使用权即为自用权。自用权的构建可借鉴知识产权“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自用权模式,只要《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未作明确禁止,即属数据处理者行为自由范畴。
六、结语
反不正当竞争法仅解决具有竞争关系经营者间的纠纷是认为其不能替代数据确权的一项重要理由。但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已经泛化,甚至经过分析发现完全可以放弃竞争关系,其既非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亦非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件,也非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的条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重心应由“竞争关系”转向“竞争秩序”。另一方面,权利和利益的分野并不在于其采取何种保护模式,而在于其是否契合权益区分的三项法教义学标准。只要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清晰到获得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程度,即使行为规制模式亦可实现权利化。在“所有权终结”的时代,在明确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淡化所有权”的情形下,鉴于司法实践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权益的现实,破除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截然二分之迷思,走出所有权思维定式,凝聚权利保护和行为规制的理论与实践共识,而以行为规制权利化赋予数据权益超越个案的社会典型公开性,或许亦为数据产权构建的一条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 叶金强. 《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的得与失[J]. 中外法学, 2017, 29(3): 645⁃655.
[2] 申卫星. 数据确权之辩[J]. 比较法研究, 2023(3): 1⁃13.
[3] 丁晓东. 新型数据财产的行为主义保护:基于财产权理论的分析[J]. 法学杂志, 2023, 44(2): 54⁃70.
[4] 王利明. 数据何以确权[J]. 法学研究, 2023, 45(4): 56⁃73.
[5] 焦海涛.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J]. 中国法学, 2017(1): 150⁃169.
[6] 孔祥俊.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定位[J]. 中外法学, 2017, 29(3): 736⁃757.
[7] 陈兵. 互联网经济下重读“竞争关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意义——以京、沪、粤法院2000—2018年的相关案件为引证[J]. 法学, 2019(7): 18⁃37.
[8] 陶凯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开启新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征程——在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07-09)[2024-03-18]. https://www.sohu.com/a/240265314_221481.
[9] 王艳芳.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解构与重塑[J]. 政法论丛, 2021(2): 19⁃27.
[10] 陈耿华.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竞争价值的理论证成与制度调适[J]. 比较法研究, 2021(6): 157⁃170.
[11] 吴太轩, 乔韵.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认定的反思与重构——以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平台竞争关系为切入点[J]. 电子知识产权, 2022(12): 68⁃83.
[12] 唐力. 民事诉讼立审程序结构再认识——基于立案登记制改革下的思考[J]. 法学评论, 2017, 35(3): 131⁃138.
[13] 孔祥俊. 理念变革与制度演化:《反不正当竞争法》30年回望与前瞻[J]. 知识产权, 2023(7): 3⁃31.
[14] 孔祥俊. 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原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9.
[15]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2.
[16]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黄家镇,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17] 孔祥俊. 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9.
[18] 孔祥俊. 《民法总则》新视域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J]. 比较法研究, 2018(2): 92⁃116.
[19] 付子堂. 法理学高阶[M]. 3 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0] 谢晓尧. 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1] 王日易. 论反垄断法一般理论及基本制度[J]. 中国法学, 1997(2): 89⁃98.
[22] 张占江.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范式的嬗变 从“保护竞争者”到“保护竞争”[J]. 中外法学, 2019, 31(1): 203⁃223.
[23] 弗诺克·亨宁·博德维希(Frauke Henning-Bodewig). 全球反不正当竞争法指引[M]. 黄武双, 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
[24] 张占江. 反不正当竞争法属性的新定位 一个结构性的视角[J]. 中外法学, 2020, 32(1): 183⁃205.
[25]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Model provisions on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M]. Geneva: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1996.
[26] N.格里高利·曼昆. 经济学原理: 微观经济学分册[M]. 8版. 梁小民, 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27] 冯术杰. “搭便车”的竞争法规制[J]. 清华法学, 2019, 13(1): 175⁃190.
[28] AUSTIN J.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9] 吕炳斌. 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参照[J]. 中国法学, 2019(4): 44⁃65.
[30] 于飞. 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J]. 法学研究, 2011, 33(4): 104⁃119.
[31] 孙莹, 郭凯. 权利抑或利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之辩[J]. 政法学刊, 2021, 38(3): 62⁃71.
[32] 徐银波. 论侵权责任法的创权功能[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9, 11(4): 47⁃56.
[33] 龙俊. 反不正当竞争法“权利”与“利益”双重客体保护新论[J]. 中外法学, 2022, 34(1): 64⁃83.
[34] 孔祥俊.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二元法益保护谱系——基于新业态新模式新成果的观察[J]. 政法论丛, 2021(2): 3⁃18.
[35] 张浩然. 数字时代商业秘密制度理论基础的再检视[J]. 知识产权, 2023(9): 88⁃107.
[36] 王宏军. 论作为排他权与支配权的知识产权——从与物权比较的视角[J]. 知识产权, 2007(5): 9⁃15.
[37] 王迁. 知识产权法教程[M]. 7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38] 许可. 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规范分殊[J]. 政法论坛, 2021, 39(4): 86⁃96.
[39] 喻玫. 数字化时代财产权建构范式的转变:著作权可分割理论的当代价值[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5): 100⁃104.
[40] 申卫星. 论数据用益权[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1): 110⁃207.
[41] 张新宝. 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4): 144⁃207.
[42] 孙莹. 企业数据确权与授权机制研究[J]. 比较法研究, 2023(3): 56⁃73.
[43] 张力, 何雨泽. 数据信托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展开[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2): 121⁃131.
[44] 孔祥俊.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建构——落实中央关于数据产权制度顶层设计的一种方案[J]. 东方法学, 2022(5): 15⁃29.
[45] 张建文. 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本质及其法律保护——兼评美景公司与淘宝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1(1): 35⁃191.
[46] 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1⁃44.
[47] DEMSETZ H.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2): 347⁃359.
[48] 胡乐明, 刘刚, 李晓阳. 新制度经济学原理[M]. 2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49] 孙莹. 论数据权益客体中的基本范畴[J]. 东方法学, 2024(1): 24⁃37.
Rethinking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nd Reconsidering the Path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for Data Rights Confirmation
Sun Ying, Yu Zhengyuan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alm of protecting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attern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pattern of behavior regulation. However, it is worth reconsidering whether these two patterns are strictly dichotomous and whether the pattern of behavior regulation, as represented by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holds the potential for data empowerm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so generalized that it is no longer suitable as a substantive requirement or a condition for litig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should shift its focus from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to "competitive order", thereby granting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a certain degree of universality under the Competition Law.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rights and interests does not lie in the pattern of protection adopted, but rather in whether it meets the three legal criteria for distinguishing rights from interests. As long as the allocation function and exclusion function are sufficiently clear to achieve a level of typical social obviousness, even the pattern of behavior regulation can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terests to rights. Given that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primarily protects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through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tegrating the consensus of both patterns then achieving the structural separ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the path of making behavioral regulation as the right may be a feasible path.
Keywords: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path of making behavioral regulation as the right; structural separ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数据确权和流转中的登记问题研究”(23BFX075);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大规模侵害个人信息损害赔偿责任的实体与程序研究”
作者简介:孙 莹(1982—),女,山东平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数据法学;
禹政远(2000—),男,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数据法学。
1 (2016)京73民终156号判决书。
2 (2019)京0108民初35902号判决书、(2021)京73民终1011号判决书。
3 (2021)沪0110民初3349号判决书、(2021)沪73民终912号裁定书。
4 实体要件,又称“本案要件”,是指当事人的实体请求能够成立的要件。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参照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201页。
5 同③。
6 同②。
7 (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528号判决书、(2016)沪73民终242号判决书。
8 (2018)京0108民初28643号判决书、(2019)京73民终3789号判决书、(2021)京民申5573号裁定书。
9 同⑦。
10 同⑧。
⑪ (2020)浙01民终4847号判决书。蚂蚁金服诉企查查案中,蚂蚁金服和企查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种类完全不同,蚂蚁金服提供金融服务,企查查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但二者因企查查抓取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中的蚂蚁金服清算数据出现错误,而引发争议。
⑫ 其第2条规定“与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市场主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经营者’。”
⑬ (2019)浙01民终9556号判决书。微信诉科贝案中,微信提供即时通讯服务,而科贝从事网络贷款导流业务,但二者因科贝破坏包括数据安全在内的微信生态而引发争议。
⑭ (2021)沪73民终489号判决书。一起来捉妖游戏诉虚拟定位插件案中,二者因为虚拟定位插件帮助游戏用户修改手机定位数据从而规避游戏机制而引发争议。
⑮ 实体要件论者认为竞争关系的界定范式是“由关系而行为”,具有竞争关系是构成竞争行为的前提条件,因而先审查原告和被告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⑯ (2017)闽01民终594号判决书。
⑰ (2016)京73民终156号判决书。
⑱ 有学者认为诉讼法规范亦可分配证明责任,李浩. 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参照《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仅实体法规范可以分配证明责任,胡学军:证明责任中国适用的限缩——对“程序法上证明责任”在本土适用性的质疑,《法学家》2022年第2期。
⑲ (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0046号判决书。
⑳ 在域外则有所不同,日本法上当事人适格是诉讼要件,不具备此要件的,应以诉讼判决驳回诉。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导读版):下册》,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21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的通知》(国反垄发〔2009〕3号)(以下简称《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二条。
22 《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
23 《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相关商品市场,是……由需求者认为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一组或一类商品所构成的市场。这些商品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关系……”第三款规定“相关地域市场,是指需求者获取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商品的地理区域。这些地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关系……”
24 (2007)深中法民三终字第3号裁定书。这是行为规制模式的常态,本文将此种所保护利益的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尚未达到社会典型公开性的行为规制称为典型行为规制模式。
25 “通过对他人特定行为的控制来维护利益享有者的利益”这一经典定义得出的结论,叶金强.《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的得与失,《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第650页。如果认为“对他人行为的控制”即为行为规制,那么行为规制模式实际包含权利保护模式。
26 (2017)浙8601民初4034号判决书、(2018)浙01民终7312号判决书。
27 (2010)海民初字第4253号判决书。
28 同②。
29 一般条款设计例如《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兜底条款设计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之所以放弃类型化设计而采取一般条款设计或许是因为受限于部门规章定位而难以超越《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则无此顾虑。
30 例如数据服务合同可以参照适用承揽合同的规定,孙莹:论数据权益客体中的基本范畴,载于《东方法学》2024年第1期第34页。又如数据许可使用合同可以参照适用技术许可使用合同的规定。
- 科技与法律的其它文章
- Regarding the Regulatory Sandbox Route and Mechanism for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lf-Money-Laundering in the Digital Age
-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The Rule of Law Response to Medical Institution Data Compliance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的行为规制逻辑选择与路径建构
- 具身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主体思考
- 论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