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当代先锋文学中坚力量,呈现新时代文学教育硕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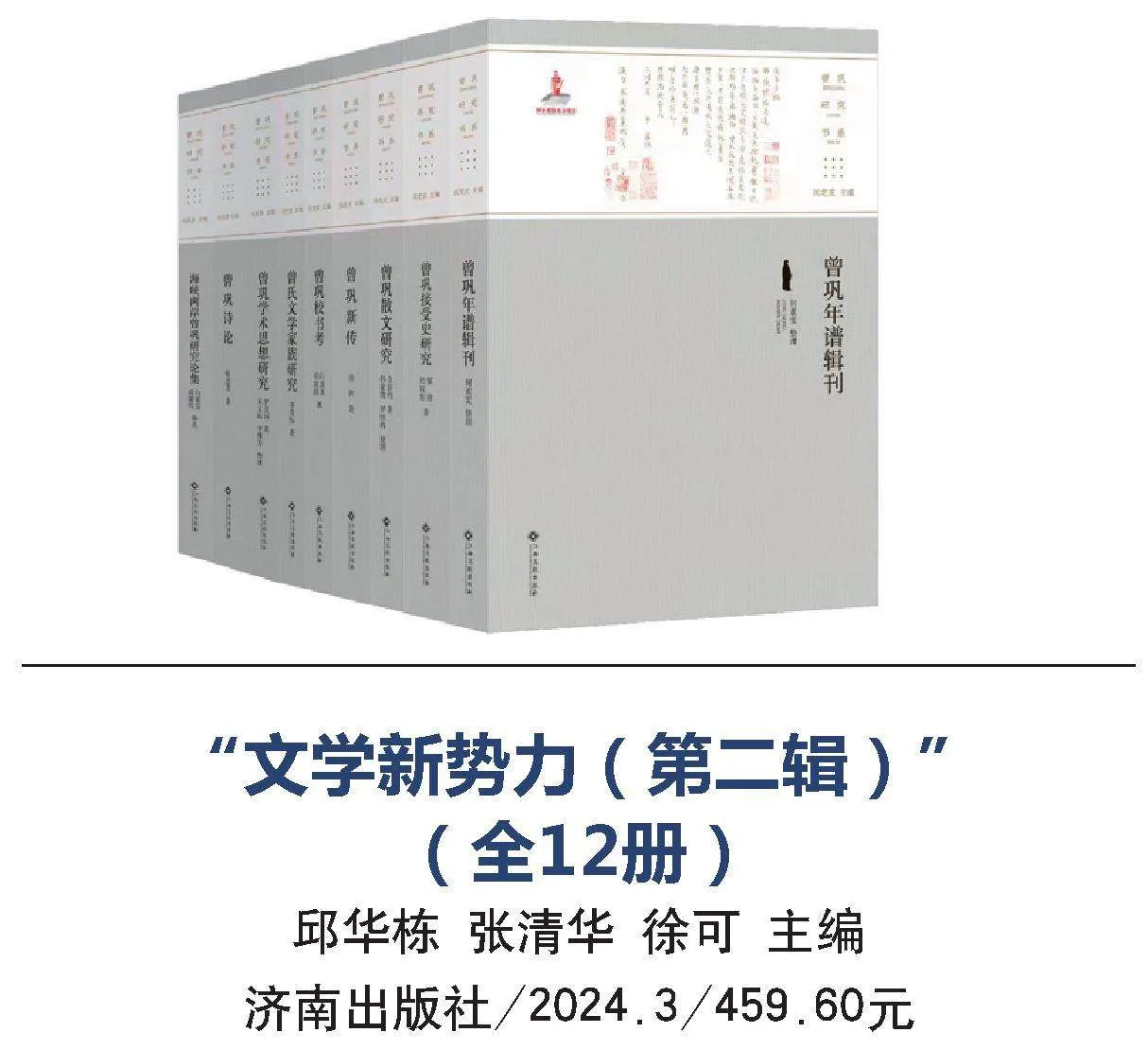
本系列坚持“择新、纳新、出新”的定位要求,围绕“新”字深挖新作者、新精品,遴选了由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得主舒辉波等人领衔的优秀青年作家的优质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集结成册,旨在向读者展现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和新时代文学的丰硕成果。
2012年10月,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再度激发了国人的文学激情,也唤醒了高校在文学教育方面的梦想,其中就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因为一段至关重要的学缘,莫言曾于1991年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此刻,作为母校的师大自然倍感荣耀,遂立刻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并邀请莫言前来担任主任。中心成立之初,其核心职能——文学教育和创作人才的培养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需要稍加追溯前缘,才能说明这套文丛的来历。1988年,由当时在研究生院任职的童庆炳教授牵头,由北京师范大学提供学制条件,牵手中国作家协会直属的鲁迅文学院,共同招收了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那时的学位制度相对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各种规章还没有现在这样严格和完善,所以运作相对容易,招生考试环节也相对宽松。由此,一批在文坛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便被不拘一格,悉数收罗。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除刘震云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的本科毕业生外——并未受过很正规的教育,刘震云几乎是唯一一个出自正宗名门的学员。余华只在浙江海盐上过中学;莫言之前虽有两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习经历,但更早先却连中学教育都未受e8g2xh/zcyoFgPG2KfM9+w==完整;迟子建等差不多也都只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其他人我们未做过严格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中大多数未曾上过大学。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些人是那时中国文坛最具希望的一批作者,是青年作家中的翘楚,是未来文坛的半壁江山。从这里出发,20年过后,他们的确未负众望,为中国文学争得了至高荣誉,也几乎成为一代作家的代言人。
很显然,这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一个共同的记忆,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两所学校引以为豪的历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拾昔日文学教育的前缘,找回这一无双的荣耀,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因了以上的缘由,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方经过认真研究,参考过去的合作模式,从全校不多的单招单考的硕士名额中拿出20个交由文学院和国际写作中心,寻求与鲁迅文学院合作,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于2017年秋季正式招收了“非全日制”学术型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为了省却复杂的学科规制,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二级学科下设立了“文学创作方向”,并采用了“学术导师”加“创作导师”联合授课的培养模式,为学员创造更为合适和充分的学习条件。鲁迅文学院则为他们提供居住和学习的物质条件,以及日常的管理,并拟在培养方案中结合鲁迅文学院的讲座制培养模式,两相结合,尽显特色互补的优势。
同时还必须指出,有几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支持了这项事业: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特别是董奇校长,对推助写作中心的文学教育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制定相关体制机制方面也给予了诸多指导。晚年在病中的童庆炳教授多次勉励我们,要传承好过去的经验,大胆探索,争取把工作尽早落到实处。中国作家协会和协会党组,特别是铁凝主席,也给予了热诚关怀,时任书记处书记、分管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吉狄马加同志则在工作中给予了非常具体的关心和指导。参与该项工作,制定合作规划、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以及负责日常服务管理等诸项事务的,便是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负责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的两位笔者。整个过程中,要想实现两个职能完全不同的单位之间的密切合作,在所有培养工作的环节上都无缝对接,是一个至为琐细的工作,难以尽述。好在两校之间目前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切都在愿景之中。
迄今为止,该方向的研究生已经招收了3届共56人,从总体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在学员中,有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乔叶、鲁敏,有多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获得者,还有“70后”“80后”广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像东紫、杨遥、朱山坡、林森、马笑泉、高满航、闫文盛、曹谁、曾剑、王小王,等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已经有了相当出众的成绩,或是十分丰富的经验,然而他们共同的诉求都是对“充电”的渴望,所以因了冥冥中某种命运的感召,汇聚到了一起。
关于文学教育,历来分歧明显、众说不一。有人坚称“大学不培养作家”,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大学的使命很多,成败的确不在于是否出产了一两个作家,但这话的“潜台词”值得商榷——其意思里是有偏见或轻蔑的,是说“你培养不了作家”“作家不是谁都能培养出来的”。这当然也对,没有哪个大学敢说自己“培养”了几个作家,而只能说,他们那儿“走出了”哪些作家和诗人。然而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文学教育的无必要呢?似乎也不能。因为按照上述逻辑,我们也可以反问,大学不能培养作家,难道就可以“培养”经济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法学家吗?谁又敢说他们“培养”了哪些伟大和杰出的人物呢?
很显然,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都是很难通过“订制”来培养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学必须为人才提供成长和受教育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宣称大学“不培养作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当代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变革和作家的成长与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在大学教育的草创和荒芜时期也出现过许多作家,但他们要么是从战争年代的洗礼中锻炼出来的,要么是在长期的自学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没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文学道路多舛,艺术成长和成就受到了限制,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正是后来教育的全面恢复与发展,才使得文学事业出现了人才辈出、蓬勃兴旺的局面。
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作家是无法培养的,但文学教育是必需的。当然,文学教育对于高校而言,其目标确乎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素质养成的环境条件,这才是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引进著名作家执教的核心意义所在。换句话说,能不能出产一两个作家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其培养的人才是否具备写作的能力,能否成为文学的内行才是重要的。传统的文学教育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所培养的读书人大都是既能够研究又可以写作的双料人才,就像在新文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大学的文学教授也多是集学者和作家两种身份于一身的。
无论如何,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办班这一培养模式的目标是直接而干脆的,就是“培养作家”。当然,这培养不是从“育种”开始的,而是“选苗”和“移栽”的过程,甚至有的就属于“摘果子”。即便是后者也不是无意义的,当年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人早在入学之前就是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了,录取他们无疑算是“摘果子”,但谁敢说系统的阅读与学习、大学综合环境下的熏陶成长对于他们后来的写作没有助益?所以,我们坚信这一工作是有意义的。
最后再来说说这批作为“文学新势力”的新人。显然,他们大多属于“80后”至“90后”的一代,较之他们的前辈,这批新人的主要差异在于代际经验的不同。前代作家的成长期大都经历过历史的大波大澜,童年也大都有原初和完整的乡村生活经验,所以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总体性经验”支配和支持的一代作家。比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可以说寄寓了他对于农业社会生存的全部感受和想象,也寄寓了他对于现当代中国历史巨变的记忆与理解。这种具有总体性和原生性的经验与美学在下一代作家这里早已变得不可能,他们都命定地处在某种“晚生”和“后辈”的自我想象之中,不得不在碎片化、个体化的历史经验与记忆中探索前行。
这些都并非新鲜的话题,只是重复了前人既成的说法,但这也是所谓“新势力”的根基与合法条件。“新”在哪里,又何以成为“势力”,这是需要我们想清楚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势力”其实就是指:一是有新的文化特质,他们在文化上所拥有的“新人”特色或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但一定是更具有个性、自主性和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拥有新知和新的经验方式的一代,是用新的思维与视角看待人生与世界的一代,是在网络信息时代生存和写作的一代;二是有新的美学属性,这些属性自然更难以总体性的概括来描述,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具有陌生感的一族,是难以用传统范型所涵盖和统摄的一族,是游走和不确定的一族,是空间化和个体性得以充分彰显的一族,当然,也是相对琐屑和相对真实,相对平和和相对日常性的一族。有时我们觉得是这样满足,但有时我们又会觉得,他们离着理想的文学,离所谓普世的“世界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旁观者说一千句,不及读者自己去观照、去体味其中的丰富和微妙。“总体性”之不存,我们的概括也自然显得苍白无力,不如读者们自己去一一打量和细细辨识。
看,这就是“文学新势力”,他们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