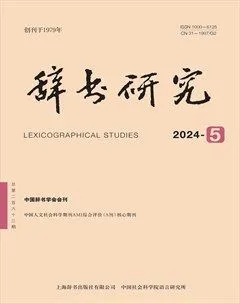《吕氏春秋》“夕室”考释
摘 要 《吕氏春秋》“夕室”当理解为“豫室”,即豫乐之室。“正”非与“夕”相对,故旧说“夕”之“邪夕”“夕暮”之说并不可取。“正坐”当与“豫室”形成反对关系,且与二级标题《季夏纪》及三级标题《明理〈制乐〉》所论至乐之道关系密切。从《吕氏春秋》文本设计的衔接与篇题所涉时令关系上看,“夕室”居于季夏之末,孟秋之初,与《管子·戒》的记载一致,故应当理解为“豫室”。
关键词 《吕氏春秋》 “夕室” “豫室”
一、 《吕氏春秋》“夕室”旧说辨正
《吕氏春秋·季夏纪·明理》载有“夕室”一词:
五帝三王之于乐尽之矣。乱国之主,未尝知乐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赏得为主,而未尝得主之实,此之谓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其所谓正,乃不正矣。
高诱注“夕室”为“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徒正其坐也……”“悲人所为,如坐夕室,自以为正,乃不正之谓也”。但高诱的解释未能与《明理》文意相贴合,遭到了学者的质疑。明人方以智言“夕”“邪”同,“谓宫斜而正其坐也”,章太炎《新方言》及胡绍瑛说与方说近之。清惠栋言“夕室”为“西向之室”。李宝洤就指出:“言为人主而不明乎乐之道,犹正坐于夕暮之室中。注似迂回。”李氏批评高诱注“夕”有道德评价的色彩而以“夕暮”释“夕”。高亨先生引字书“夕”乃“邪”也,未及详论。结合《明理》篇及其所属的二三级标题,我们能够发现自《仲夏纪》《大乐》始论乐,至《季夏纪》《制乐》七篇,广述音乐的教化之功、治政之用。而《明理》篇旨在申说妖异之兴灭在人事之善恶,当明于治乱之理。具体到《明理》,《明理》篇的篇首和篇末均言国之正与不正和乐与不乐之关系,国治则可得至乐,尽乐之乐。李说虽较为平易,但将“夕”解释为“夕暮”也应该是望文而训,“正”与“夕”的关系迂远且与乐道无涉,是说难从。萧旭先生(2016)认为“夕”为“邪”义,“夕室”乃倾斜不正之室,然未必就是邪向西,并批评陈奇猷先生的说法乃臆造之论。我们认为萧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陈氏之论与高注等问题一致,均是与乐道关系并不密切。清人毕沅无说,乃据梁仲子援引《晏子春秋》注“夕室”,其文曰:
景公新成柏寝之台,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公召大匠曰:“室何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宫何为夕?”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晏子对曰:“古之立国者,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蹙然曰:“古之臣乎!”
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据《明理》篇“夕室”解《晏子春秋》“室夕”,“夕”与“邪”为语转,又“夕”有“西”义,并以《周礼》郑玄注为说。王氏两说并存,我们认为当以后说为是。“夕室”与“室夕”为同素逆序词,二者是否已经凝结成词还有待商榷,但《吕氏春秋》与《晏子春秋》的用法显然并不相同。陈奇猷先生(2002)则想统合王氏二说,言朝室乃邪向东之室,夕室乃邪向西之室,并认为未得主位者实非人主,自以为正而实不正。我们认为陈氏之说不仅忽视了二者用法的具体差异,且主位之说也缺乏依据,有附会之嫌。王利器先生(2002)指出《明理》篇乃沿袭《子华子·孔子赠》:
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齐,而俱王于天下,明旌善类而诛锄丑厉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诚也。精诚不白,则无以王矣。其在后世,以急刻而责,恕以讹伪,而课忠言,非其愿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旦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悬而黑之募也,是纵桌于陆而发轫于川也。
“旦坐”,《明理》篇作“正作”。王利器先生(2002)认为“夕”与“正”相对,必为“邪”义,并以《左传·庄公十九年》“夕室”,杜预注地名说及《经典释文》“夕”为“朝夕”之“夕”说俱非是。如果从正反用词的角度看,“黑”“白”反对,“旦”“夕”反对,“夕”当必为“夕暮”之“夕”,而非王利器先生(2002)所言的“邪夕”之“夕”。然“正”“旦”音、形、义均不近,这两个字的异文关系及《子华子》与《吕氏春秋》二者的文献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故“正”“夕”相对之说乃误解之见,而应将“正作”与“夕室”视作相反关系。我们认为,《吕氏春秋》“夕室”旧说均存在着瑕疵,需要发现新的对读材料,寻找新的解决思路。
二、 《左传》中“夕室”的破读
传世文献中除去《晏子春秋》外,还有《左传》的材料。《左传·庄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
《庄公十九年》“夕室”,杜预注其为地名,《经典释文》言“夕”为“朝夕”之“夕”。清人沈钦韩提出新说,乃死者之所,清人刘文淇、日人竹添光鸿以及章太炎赞同沈说,但对“夕”之具体含义以及“夕室”乃冢墓之所的具体缘由看法不一。宋华强先生(2010)《新蔡葛陵·楚简初探》则据新蔡楚简,以简文中的地名“上邜”“下邜”重申杜说。袁金平先生(2012)则据清华简《楚居》简4—5中记载楚人夜晚在楩室中祭祀的活动,认为《左传》“夕室”之“夕”就是《楚居》简文中的“”,即“夕()室”。以此,袁文推测“夕‘室’可能是由冢墓和相关附属建筑(用于设祭)构成的一种祭祀场所”。为了更好地说明,我们将相关简文移录于下:
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以祭。惧其主,夜而纳,抵今曰=(,)必夜。
据简文,我们认为袁文的“夕室”新说有其理据,颇具新意。而无论是地名说还是墓室祭祀说,《左传》中的“夕室”都无法与《吕氏春秋》中的“夕室”合观。而《左传》“夕室”之名的诸多新说,也提醒我们可以从假借破读的方式来理解和认识“夕室”。
三、 《吕氏春秋》“夕室”新说的提出
如前所述,《吕氏春秋·季夏纪·明理》中的“夕室”既应与二级标题《纪夏纪》和三级标题《明理》所倡言的乐道相关,同时又应与“正坐”形成反对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三级标题《明理》,清孙锵鸣认为“今本《明理》篇文乃《制乐》篇文,《制乐》篇‘今窒’以下至末,乃《明理》篇文”,刘咸炘先生认可其说。(转引自陈奇猷 2002)若是说成立,则篇旨与乐道之关系更为显豁。由上,我们认为“夕”应读为“豫”。北大汉简《荆决》“美人夕极”,整理者将“夕”读为“怿”,王挺斌先生(2022)读为“豫”,从通假惯例上看,王说为优。张富海先生亦提及中山王壶铭“游夕㱃飤”当读为“游豫㱃飤”。(转引自王挺斌 2022)无论从音理还是从实例上看,“夕”与“豫”都可以通假。除此之外,本则“夕室”居于《季夏纪》末篇,后乃接续《孟秋纪》。《吕氏春秋》的文本设计上有一个特殊之处,即通过前后相衔的方式将篇目之间联系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管子·戒》正有一则与文本设计和时令关系密切的材料:
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亡荒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
黎翔凤(2004)引清人孙星衍说:
《晏子·内篇》:“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声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黎氏又引清人宋翔凤说:
古读“夕”如“豫”,此言“夕”,犹《孟子》言“豫”也。
因此,从文本衔接与时令关系上,“夕室”也应当可以理解为“豫室”。“豫室”即“豫乐之室”,与乐道相关,且于“豫室”之中“正坐”,正可成相反之义,即《明理》篇“其所谓正乃不正矣”。需要强调的是,“豫”往往被视作和乐之豫乐,但若依我们的理解,《明理》篇“豫室”之“豫”取“游豫”之豫乐义也。
参考文献
1. 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一).成都:巴蜀书社,2002.
5. 王挺斌.战国秦汉简帛古书训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6. 萧旭. 《吕氏春秋》校补.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6.
7. 袁金平.《左传》“夕室”考辨.深圳大学学报,2012(2).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