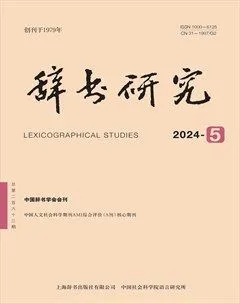上古汉语情态词“必”的性质与来源新探
摘 要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辨析了上古汉语情态词“必”的句法属性和语义功能,认为概括词“必MOD”包含了五个词项,其中,三个是情态助动词,两个是情态副词;继而调查并分析“必”作为典型实词的各项用法,论证了情态助动词“必”的源头是“保证、确保”义的及物动词“必”,而非单独做谓语的形容词“必”;最后指出形容词“必”同样来源于及物动词“必”。
关键词 情态词“必” 词类属性 语义功能 历史来源 上古汉语
一、 引 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上古汉语时期出现于“(NP)必VP”句式且表达“必须、必然、必定”等情态意义的“必”。例如:
(1) 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左传·僖公七年》)
(2) 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左传·桓公六年》)
(3) 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左传·成公七年》)
关于情态词“必”(简称为“必MOD”)的句法语义属性,前辈时贤多有讨论,但目前仍存在两个亟待确认的问题:其一,“必MOD”到底是助动词还是副词?其二,“必MOD”能表达几种类型的情态义?关于情态词“必”的历史来源,学界的关注相对较少,目前仅有的几项研究(如巫雪如 2018;徐鋕银 2019)观点较为一致:考虑到上古汉语中存在着与
“必MOD”(暂且不论它是助动词还是副词)语音相同、语义密切相关的形容词“必”(以下简称为“必ADJ”),可认为“必MOD”是由“必ADJ”转化或演变而来的——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当时的语言系统之中还存在一个及物动词“必”(以下简称为“必V”),它与“必MOD”“必ADJ”均同形且语义相关,同样有可能是“必MOD”的源头。因此,上古汉语情态词“必”的来源及产生过程,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本文将重新检视前人提出的各项证据,据此辨析上古汉语“必MOD”的句法属性和语义功能;继而全面调查并分析“必”作为典型实词(动词或形容词)的各项用法,探究并论证“必MOD”的真正源头及产生过程。本研究所用语料主要是代表先秦汉语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二、 “必MOD”的句法语义属性辨析
关于上古汉语情态词“必”的词类归属,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部分学者(马建忠 1983;吕叔湘 2017;周法高 1972;李佐丰 2005;姚振武 2005;谷峰 2010;徐鋕银 2019)认为“必MOD”是副词(由于它表达情态意义,故而属于情态副词或语气副词),另一些学者(章士钊 1925;魏培泉 1982;胡裕树,范晓 1995;朱冠明 2008;巫雪如 2018)则认为“必MOD”是情态动词或情态助动词。从“必MOD”在上古文献中的用例来看,它既具有同于助动词、不同于副词的句法表现,也具有同于副词、不同于助动词的句法表现——这是造成学者们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然而,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引起重视:能表达多种情态意义的“必MOD”是一个多义词,讨论多义词的词类归属,应当以“义项/词项”[1]而非“概括词”为单位。[2]因此,先要确认的是“必MOD”有几个义项,继而逐一考察各义项所对应的词项“必”的分布特点,方能确认其词类属性。
(一) “必MOD”的语义
在“必MOD”所表达的多种情态意义之中,已得到普遍认可的至少有两种:一是通常被归为道义情态的“必要”义,表达“强制要求实施某行为或实现某事件”;二是通常被归为认识情态的“必然”义,表达“某个命题必然为真”。
具体来看,“必要”义的用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表达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或说话人的权威决定了的某事件是被强制要求实现的[如例(4)],即典型的“道义必要”(也被称为“义务”);另一类表达客观环境或条件决定了的某事件是被强制要求实现的[如例(5)],即“条件必要”(也称为“环境必要”,参看范晓蕾 2020)。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语义主观性的强弱,但主观性本就是个连续统,不易找到“截然可分的标准或界限”(巫雪如 2018)274。
总之,上述差别不足以将“必要”义切分为这两个义项,道义必要和条件/环境必要只是“必要”义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的语用义。
(4) 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左传·僖公七年》)
(5) 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左传·成公十八年》)
“必然”义也涉及两种不同情况。典型情况是,说话人根据所掌握的知识推测某命题一定为真[如例(6)],该命题所述事件通常是单一、具体的事件——这类用例属于典型的“认识必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当特定的客观条件得到满足时,某事件一定发生——这类用例是对客观规律或惯常情况的叙述[如例(7)],所述事件通常是类事件。后一类用例所表达的意义被部分学者称为“(客观)条件必然”,有的学者甚至将其从认识情态中独立出来,与“条件可能”义组成一个单独的情态语义类型——“条件情态”(参看范晓蕾 2020)。如果出于“建构一个逻辑严密的情态语义分类体系”的目的,将上述两种用法分别归入认识情态和条件情态是合理的。但从义项划分的角度看,同一词形所具有的认识必然用法与条件必然用法不宜切分为两个义项。两种用法的差异主要在于所述事件的特点及语义主观性的强弱。既然认识必然用于单一事件、具体事件,条件必然用于类事件、惯常事件,那么二者所出现的语境就是互补的,不构成最小对立——应将二者视为同一个义项(“必然”义)在不同语境之中的变体。
(6) 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7) 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左传·庄公二十年》)
还有一些用例中的“必MOD”表达“承诺决意”,即主语承诺或决意做某事[如例(8)—例(10)]。Palmer(2001)、彭利贞(2007)将这类用法归入道义情态,范晓蕾(2020)则将其视为认识情态词的语用义(即归入认识情态)。
(8) 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左传·成公七年》)
(9) 子恶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吾无以酬之,若何?”(《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0) 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吕氏春秋·爱类》)
仔细揣摩承诺决意用法的相关用例,会发现:尽管有些用例的语义解读存在争议,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用例绝对不能解读为道义情态(“必要”义)或认识情态(“必然”义)。如例(8)中,巫臣说“我决意让你们疲于奔命以死”——所要表达的既不是“特定的规则、规范、权威或客观条件强制要求‘我让你们疲于奔命以死’这件事实现”,也不是“我(巫臣)”对自己未来行为的一种推测,而是主语具有强烈的意愿去实现这件事。再看例(9)。前文讲到费无极对子恶说:“令尹子常想去你家饮酒。”于是子恶说:“我身份卑贱……如果令尹一定要屈尊前来,对我的恩惠就太大了,我没有东西用来答谢,怎么办?”“令尹将必来辱”是一个假设条件小句,既不是说“令尹必须来”,也不是在推测“令尹一定会来”,而是说“如果令尹决意要来,那么恩惠太大……”——因而此例也是表达主语有意愿做某事。更有力的证据是例(10)“欲必击其爱子之头”:“欲”义为“想要”,表达主语的意愿,“必”同样表达主语的意愿,故二者可以并列连用,表达主语有强烈的意愿去实施“击其爱子之头”的行为。“必要”义、“必然”义的“必MOD”即使与意愿义动词(或助动词)“欲”连用,也只能出现在“欲”之前,不可能出现在“欲”之后。[3]
总之,“承诺决意”应被视为“必MOD”的一个独立义项。它表达的是主语的意愿或意志(参看谷峰 2010)74,其语义与传统上所说的意愿义情态助动词(或动词)十分接近,可归入“动力情态”。为简便起见,下文称之为“必欲”义。
(二) “必MOD”的词类属性
“必MOD”词类问题的争议点在于它是助动词还是副词。首先要明确情态助动词和情态副词的鉴别标准。朱德熙(1982)针对现代汉语助动词提出了五条界定标准。我们从中选取了可用的标准并做了必要调整,[4]又参考了蔡维天(2010)、朱冠明(2008)用以区分助动词和副词的标准,最终得到了可用以鉴别上古汉语情态助动词的五项特征:[5]
Ⅰ. 其补足语必须是陈述性短语;[6]Ⅱ. 能被否定副词(“不、未”等)修饰;Ⅲ. 能够单说(作为对话中的答句),或者能允准其补足语的删略;Ⅳ. 语义带有程度性的情态助动词还能被程度副词修饰;Ⅴ. 表达情态意义。
副词与助动词一样,都出现于陈述性短语之前;[7]情态副词恰好也表达情态意义,因而Ⅰ、Ⅴ两项不能用以区分情态副词和情态助动词。Ⅱ、Ⅲ、Ⅳ三项则是助动词具备但副词不具备的形式特征,应给予重点关注。
有哪些特征是情态副词具备但情态助动词不具备的呢?有关古汉语情态词的若干研究指出:情态副词所处的句法位置较高,否定副词、时间副词及其他状语一般在其后;情态副词不能进入定语小句和“所VP”结构。(魏培泉 1999;谷峰 20105-6;巫雪如 2018266)
下面将分别考察“必要”义、“必然”义、“必欲”义“必MOD”在文献中的句法表现并辨析其词类属性。
1. “必要”义“必MOD”
在先秦文献中,“必要”义“必MOD”能被否定副词“不”所修饰。例如:
(11) a. 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楚国何为?必杀令尹。(《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b. 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左传·哀公六年》)[8]
(12) a. 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
b. 韩、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郑,兵休复起,足以伤秦,不必待齐。(《战国策·秦策三》)
(13) a. 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吕氏春秋·情欲》)
b. 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战国策·赵策二》)
“必要”义“必MOD”还能进入“所VP”结构。例如:
(14) 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孙子·虚实》)
(15) 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管子·七臣七主》)
上述用例的存在足以证明“必要”义“必MOD”是助动词而非副词(符合情态助动词的特征Ⅱ,不符合情态副词的特征),这在朱冠明(2008)、巫雪如(2018)、谷峰(2023)等研究中已有提及。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另一项证据。请看主要见于《论语》的一类句子——“必也X乎/也”。
(16)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论语·八佾》)
(17)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18)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
(19)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
(20)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
(21)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应当如何分析“必也X乎/也”句的句法结构?有以下三种可能的分析方案:
A. 将“必也X乎/也”视为判断句谓语;“必”是谓语的一部分,其词性可能是情态助动词或副词;“也”是插入“必”与“X”之间的句中语气词。然而此分析无法成立。因为无论在情态助动词与其补足语之间,还是在情态副词与其所修饰的中心语之间,都不可能插入语气词。
B. 将“必也+X乎/也”视为“X乎/也,必也”经过主谓倒装之后的句子,“必”独立做谓语,其词性可能是形容词。这种分析也很难成立。如果“X”本是主语,就不该带句末语气词“乎”。上古汉语中真正的主谓倒装句的主语或者不带语气词,或者带“也”。[9]
如:大哉,尧之为君!(《孟子·滕文公上》)甚矣,吾衰也!(《论语·述而》)“乎”没有句中语气词的用法。因此,“射乎”“正名乎”等结构不能看成主语。
C. 将“必也”和“X乎/也”看成两个小句,构成“条件—结果”复句。(参看李运富 1987)作为假设条件小句的“必也”是“必VP也”省略了补足语VP之后的形式,“必”是表达“必要”义的情态助动词。“必也,X乎/也”义为“如果一定要……,那么就是X了”。从上下文来看,这种解读十分通顺且准确。如例(16)意为:君子无所争,如果一定要争的话,那么就是“射”了。例(19)意为:得不到言行中正的人并与他交往,如果一定要交友的话,那么(交往的对象)就得是狂放和狷介的人了。例(21)意为:在审理案件方面,我跟别人没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要让民众没有争讼之事。
C是唯一能成立且合理的分析。“必也,X乎/也”句式中的“必”正是“必要”义“必MOD”,
它之所以单用,是因为省略了补足语VP——这说明“必要”义“必MOD”能允准其后补足语的删略,符合情态助动词的“特征Ⅲ”。总之,这再一次证明了“必要”义“必MOD”是助动词而非副词。
最后来看一类比较特殊的用例,简称“必毋VP”句。例如:
(22) 王曰:“吾欲以国累子,子必勿泄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23) 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4) 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韩非子·用人》)
(25) 愿王之使人反复言臣,必毋使臣久于勺(赵)也。(《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使韩山献书燕王章》)
以上画线句均表达“禁止”义(要求听话人不要实施某行为),“禁止”义其实是否定性的道义情态义——相当于“必须不”或“不可以”——故而将此类例句置于本小节末尾来讨论。我们要问的是,句中的“必”和“毋”分别是什么性质,承担何种语义?
可以确定的是,“必毋VP”中的“毋/无、勿”是表“禁止”义的情态否定词,[10]因而既属于否定副词,也属于情态副词。而“必”显然不是表推测的“必然”义或表达主语意志的“必欲”义。如果将其视为“必要”义助动词,那么“必+毋/无/勿”就是两个道义情态词连用。无论在上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时期,语义类型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情态词连用都是被允许的,但如果二者词性不同,则必须是情态副词在前,情态助动词在后。[11]“必”“毋/无/勿”连用则是情态助动词在前,情态副词在后,与上述语法规律相违背。由此可见,“必毋VP”句的“必”不是“必要”义助动词。更合理的分析是:“必”也是情态副词,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祈使语气[12]——其语义虽然比较接近道义情态(“必要、必须”义),但比后者更虚。整个句子的道义情态义主要是由情态否定词“毋/无/勿”来传达的。
2. “必然”义“必MOD”
“必然”义“必MOD”能被否定副词“不”或“未”修饰,还能进入定语小句和“所VP”结构,这些都符合情态助动词的特征而不符合情态副词的特征。例如:
(26)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27) 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韩非子·存韩》)
(28) 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韩非子·八奸》)
(29) 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战国策·秦策三》)
但否定副词“不”也可以出现在“必然”义“必MOD”之后。例如:
(30) 而今以加知矣,则虽炀己,必不危矣。(《韩非子·难四》)
(31) 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吕氏春秋·先识》)
谷峰(2023)认为例(30)、例(31)这类用例中的“必MOD”是副词。本文以为不然。情态副词固然只出现在否定副词前,但(一部分)情态助动词在否定副词前后均可出现。正如蔡维天(2010)所言,“不”的句法分布比较自由,可在认识情态词前后重复出现。因此,不能将“‘必MOD’之后是否有‘不’”作为判断其词性的依据,可作为依据的仍然是“在‘必MOD’之前能否再加上‘不/未’”。答案是肯定的[如例(32)、例(33)]。总之,出现在“不”前的“必MOD”仍是助动词。
(32) 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荀子·荣辱》)[对照例(30)]
(33) 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荀子·正论》)[对照例(31)]
有学者认为,出现于名词或形容词谓语句的“必MOD”是副词。(杨伯峻,何乐士 2001;徐鋕银 2019)本文以为不然。用在名词性或形容词性谓语核心前的“必然”义
“必MOD”同样能被否定副词修饰[如例(34)、例(35)],足以证明它是助动词而非副词。
(34) 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墨子·尚贤下》)
(35) 善者民必福(富),福(富)未必和。(《郭店简·尊德义27》)
“必然”义“必MOD”可出现在时间副词“终、恒、将、且”之后,此时显然是情态助动词。(巫雪如 2018)266例如:
(36) 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左传·襄公九年》)
(37) 国家之敝,恒必由之。(《左传·襄公十三年》)
(38) 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39) 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从也,且必恐。(《战国策·赵策三》)
但有些用例中的“必然”义“必MOD”出现在时间副词“将”“且”之前。例如:
(40) 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韩非子·说难》)
(41) 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破赵军。”(《战国策·赵策三》)
时间副词的句法位置是固定的(在TP层)。我们已知作为情态助动词的“必然”义“必MOD”位于一系列时间副词之后[例(36)—例(39)],那么出现在时间副词“将、且”之前的“必然”义“必MOD”就一定不是助动词。上古文献中也未发现在“必将/必且VP”之前加上否定副词的用例。因此,“将、且”前的“必然”义“必MOD”应被分析为情态副词。[13]“必然”义情态副词“必”可能是由“必然”义情态助动词“必”进一步语法化而来的。
由以上讨论可知,“必然”义“必MOD”与“必要”义“必MOD”不同。对“必要”义“必MOD”来说,可明确鉴别出词类属性的用例(“必”与鉴定字共现,或出现于鉴定结构,或删略VP)均证明“必”是助动词,由此可推知其他用例中的“必”也是助动词。(参看谷峰 2023)64但对“必然”义“必MOD”来说,在可获得明确鉴别的用例中,一部分是助动词,一部分是副词(且二者词义一致),也就无法直接推知其他用例(“必”未与鉴定字共现,也未出现于定语小句等鉴定结构)中的“必”是何种词性——这是因为,在古汉语研究中无法采用内省的方式获得语料,在面对一个“无标记的”“必VP”句(“必”为“必然”义)时,无法确定在“必”前加上否定副词或时间副词能否成立,也无法确定在“必”后加上时间副词能否成立。
3. “必欲”义“必MOD”
“必欲”义“必MOD”[14]可出现在意愿义助动词“欲”[15]之后,说明“必MOD”是助动词。例如:
(42) 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吕氏春秋·爱类》)
(43) 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史记·孟尝君列传》)
“必欲”义“必MOD”也可出现在“欲”前[如例(44)、例(45)],此时仍应视为助动词。“必欲”义“必MOD”和意愿义“欲”都表达主语的意愿、意志(属于动力情态),两个语义类型相同且句法位置相当的情态助动词连用时,其相对顺序是比较灵活的。
(44) 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国语·楚语下》)
(45) 大王若不察臣愚计,必欲快心于赵,以致臣罪,此亦所谓胜一臣而为天下屈者也。(《战国策·中山策》)
“必欲”义“必MOD”还出现在“将”之后。例(46)、例(47)的“将”可能是意愿义助动词[16]或时间副词——无论是哪一种,其后的“必MOD”都不可能是情态副词,只能是助动词。
(46) 若佐新军而升为政,不亦可乎?将必求之。(《国语·周语中》)
(47) 子恶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吾无以酬之,若何?”(《左传·昭公二十七年》aplIErdcsyqmHaiiwXYf8Ir8iZkz64rAQYFJwBWiCX0=)
总之,“必欲”义“必MOD”也是情态助动词。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上古汉语时期的概括词“必MOD”包含了五个词项:① “必欲”义助动词“必”;② “必要”义助动词“必”;③“必然”义助动词“必”;④ “必然”义副词“必”;⑤表达强烈的祈使语气的副词“必”(“必毋VP”句)。
三、 “必MOD”的来源:是形容词还是及物动词?
“必MOD”的五个词项之中,两个副词词项可能来源于助动词的进一步语法化。[17]因此,要探讨“必MOD”的源头,关键是搞清楚三个助动词词项的来源。
巫雪如(2018)认为情态助动词“必、宜”分别来源于形容词“必、宜”,其派生过程是:在“NP+VP,必/宜”的基础上,首先将主语子句(NP+VP)外置,随后将子句的内嵌主语NP提升为主句主语。然而,任荷(2023)已指出这一句法派生过程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语料不支持助动词“必”来源于形容词“必”的观点。
“必欲”“必要”“必然”义助动词“必MOD”在上古早期文献中已广泛使用,而
“必ADJ”单独做谓语的用法出现较晚。“X必ADJ”句不见于《诗经》《左传》《论语》《国语》《孟子》等早期文献,只见于《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等战国晚期文献。(参看谷峰 2023)115至于《论语》中的“必也,X乎/也”句,我们在前文已做了辨析,确认这个“必”是“必要”义助动词,不是形容词(详见上文“‘必要’义‘必MOD’”小节)。
总之,助动词“必”并非源自“X必ADJ”句式中的形容词“必”。
先秦汉语中还有一个及物动词“必”,在《左传》《孟子》等早期文献中即有用例。如例(48)“非敢必有功”,义为“(我)不敢保证有功劳”。“必”是一个及物的实义动词,义为“保证、确保”。例(49)—例(51)的“必”也是及物动词,只不过用在了“可”后,故而有被动义。例(49)说的是:“‘立为嗣君’能够被保证吗?”例(50)说的是:“丢掉百姓已经几代了,以此要求事情成功,这是不能保证的。”(参看沈玉成 1981)例(51)说的是:“不能保证得到(中道),故而思其次。”
(48) 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9) 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左传·闵公二年》)
(50) 懿伯曰:“谗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51) 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
本文认为,这个及物动词“必”正是情态助动词“必”的来源。从及物动词“必”到助动词“必”的句法转化很容易实现:起源结构是动词“必”带上一个由指称化结构(指称化了的VP)所充当的补足语(宾语),随着语义重心的后移,此结构发生了重新分析,VP被重新分析为陈述性短语,“必”转化为助动词。
由“保证、确保(某事件实现)”义滋生出“必MOD”的三种情态义也很容易实现。有生主体凭借自己的意愿或意志来保证某事件实现,即为动力情态“必欲”义;说话人凭借权威或规则来确保某事件实现,即为道义情态“必要”义;说话人凭借所掌握的知识来保证某命题(“事件已经实现或将会实现”)为真,即为认识情态“必然”义。至于从“保证、确保”义动词滋生出三种情态义的具体路径是辐射式(比如:“保证→必欲”“保证→必要”“保证→必然”)还是链条式(比如:“保证→必欲”“必欲→必要”“必要→必然”),目前还未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论证,姑且存疑。[18]
四、 余论:形容词“必”的来源
本文论证了情态助动词“必”的源头是“保证、确保”义及物动词“必”,而非“X
必ADJ”句式里的形容词“必”。但在战国晚期文献中确实存在单独做谓语的“必ADJ”。我们不禁要问,“必ADJ”从何而来?
在《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文献中,及物动词“必”能带NP宾语,表示“确保某事物”。如例(52),意为:“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性命”。
(52) 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荀子·议兵》)
这种用法最常出现在描述赏罚或法律法规的语境之中。即,“必”与刑罚或法律类名词组合,表示“确保刑罚或法规一定执行”。例如:
(53) 故明主必其诛也。(《韩非子·五蠹》)
(54)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韩非子·守道》)(“必完法”是“必法”且“完法”之义)
通过反宾为主的方式将“必NP”去及物化,就得到了“NP必”——大多表达“刑罚或法律一定被执行”,如例(55)、例(56);有时也表达“事物是确定的、固定不变的”,如例(57)。
(55) 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韩非子·饰邪》)
(56) 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韩非子·内储说上》)
(57) 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兽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吕氏春秋·别类》)
上述“NP必”句式中的“必”即可视为形容词。
及物动词“必”也可以带一个指称事件的小句宾语(记作IP),义为“保证、确保某事件的发生”。例如:
(58) 今媾,楼缓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战国策·赵策三》)
(59) 韩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辅伯婴以为乱。(《战国策·韩策二》)
通过反宾为主的方式将“必IP”去及物化,就得到了“IP必”——通常表达“某事件的实现是必然的”。例如:
(60) 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韩非子·难三》)
(61) 如弗予,[其措兵于魏]必矣。(《韩非子·十过》)
(62) 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战国策·赵策二》)
上述“IP必”句式中的“必”也可视为形容词。
总之,始见于战国晚期文献的形容词“必”同样来源于“确保、确定”义及物动词“必”,是通过反宾为主的途径发展而来的。
附 注
[1] 王宁(1994)指出 “要想把词汇意义与语法类别统一起来找到它们的对当关系,必须确立另一个单位——词项”,“词项是指载负一个义项的语音或书写形式”,“词项小于多义词”。该文所说的“多义词”即为拥有多个义项的概括词。
[2] 值得注意的是,谷峰(2023)在讨论“必MOD”的词类归属时大致是以义项为单位的,我们赞同此做法。不过本文对“必MOD”的义项划分与谷文不同,在几类关键用例的处理和辨析上也有 一些新的看法。
[3] 下此断言的依据是已知的语法规律:“(主体)意愿”义属于动力情态,而道义情态词和认识情态词的句法位置均高于动力情态词。真实语料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未见到“必要”义“必”与“欲”连用的用例;“必然”义“必”与“欲”连用时均出现在“欲”前。而“承诺决意”义“必”既能出现在“欲”前(如《战国策·中山策》:“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也能出现在“欲”后[如例(10)]——这个“必”与“欲”是近义词,均表达主语的意愿,因此可以并列连用且相对顺序不固定。
[4] 朱德熙(1982)的五条标准之中,有两条不适用于上古汉语,即“不能带后缀‘了/着/过’”和“不能重叠”(上古汉语时期尚未产生后缀“了/着/过”,普通动词也极少重叠)。其余三条则要加以调整。
[5] Ⅳ只适用于带程度义的助动词。Ⅲ固然是重要特征,但由于古代汉语语料的限制,单说的用例和VP删略的用例不易找到,故而无法保证每个上古时期的助动词都能满足Ⅲ。
[6] 这条与朱德熙(1982)的第一条(“只能带谓词宾语”)类似。之所以未采用“谓词宾语”的说法,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当代句法学理论视角下,将助动词之后的VP称为“宾语”并不合适。以典型助动词“能”的起源过程为例:学界公认的是,“能”一开始是普通动词(典型的词汇性范畴),其补足语既可以是NP,也可以是发生了指称化的VP。此时的“能+VP”确实是传统语法所说的述宾结构,指称化了的VP充当动词“能”的论元;但后来“能+VP”得到了重新分析(语义重心后移),“能”被重新分析为助动词(其语法化程度高于普通动词,介于词汇性范畴与功能性范畴之间),VP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常规的动词组,不再是一个指称化结构,虽然仍充当“能”的补足语,但不再是“能”的论元(词汇性动词的补足语才是论元,助动词的补足语其实是传统语法所说的谓语核心),故而不宜称之为“宾语”。其二,上古汉语时期,NP也可以比较自由地做谓语(判断句谓语或描写说明句谓语),此时NP本身仍是体词性的,但其所构造的短语是陈述性短语(可认为NP发生了陈述化)。助动词不仅可出现在VP前,也可出现在发生了陈述化的NP之前,故而将其后成分称为“陈述性短语”(而非“谓词短语”)更加准确。
[7] 但它们与其后VP之间的句法关系不同。“助动词+VP”是“中心语+补足语”结构,“副词+
VP”则是“附接语(即修饰语)+中心语”结构。
[8] 句义为:如果我行,不必杀掉一个大夫;如果我不行,也不必杀掉一个公子。
[9] 因为“也”有句中语气词的用法,可用在主语之后表停顿。
[10] 通常认为上古汉语中的“毋/无、勿”表达情态否定。但吕叔湘(1984)指出,有些用例中的“毋/无、勿”不含禁戒义,仅表达一般否定(相当于“不”)。那么,“必毋VP”句中的“毋/无、勿”是哪种用法?根据例(23)、例(24),可判断是情态否定用法。例(24)三个小句并置,后两个“无”显然都表达情态否定(不要让近世的君主倾慕古代的贤人,不要指望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第一个小句中的“无”应该也是情态否定用法。例(23)的画线部分虽分属两句,但由并列连词“且”连接,“无使季氏葬我”的“无”是禁止义,“无以冕服敛”的“无”亦然。
[11] 例如:“他大概会去。”“大概”是认识情态副词,“会”是认识情态助动词。
[12] 谷峰(2023)115称之为“在祈使句中加强语气的‘必’”。
[13] 谷峰(2023)64也将“将、且”前的“必然”义“必”分析为副词(称之为语气副词)。
[14] “必欲”义是“必MOD”的一个独立义项,请参看第二节第(一)部分的举例及论证。
[15] “欲”既可带名词性补足语,也可带谓词性补足语,通常被视为动词。本文认为,当它带谓词性补足语时,其性质与助动词并无区别。当“欲”与表达主语意愿的助动词“必”或“将”连用时,既可出现在后,也可出现在前(见正文及下一条附注),正说明它的语法化程度与“必、将”基本相当。
[16] 胡敕瑞(2016)引用古书用例及相关注释,指出“将”有意愿义动词的用法。我们认为分析为助动词更好,因为其后只能出现谓词性补足语。意愿义“将”经常与“欲”并列连用,且语序可互换。例如: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韩非子·喻老》)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雠。(《战国策·燕策一》)
[17] 词项④显然来源于词项③;词项⑤可能来源于词项②,也可能直接来源于实词“必”。
[18] 谷峰(2023)115根据情态语义发展的规律判定“必”先有“必要”义,再由“必要”义滋生出“必然”义。我们认为未必如此。从“保证、确保”义与“必欲”“必要”“必然”义的语义关联来看,由“保证、确保”分别滋生出三种情态义也是说得通的。多种汉语方言的材料也显示,“保证肯定”义动词是汉语方言“认识必然”义情态词的直接来源之一,如:山东郯城话的“保准”,上海话的“保定”“保证”,洛阳话的“管保”“管许”,等等。(范晓蕾 2020)
参考文献
1. 蔡维天. 谈汉语模态词的分布与诠释之对应关系. 中国语文, 2010(3).
2. 范晓蕾. 汉语情态词的语义地图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3. 谷峰. 先秦汉语情态副词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4. 谷峰. 上古汉语语气副词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5. 胡敕瑞. 将然、选择与意愿——上古汉语将来时与选择问标记的来源. 古汉语研究, 2016(2).
6. 胡裕树, 范晓. 动词研究.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7. 李运富. 《论语》里的“必也,P”句式. 中国语文, 1987(3).
8. 李佐丰. 古代汉语语法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9. 吕叔湘. 论毋与勿. //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10.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11. 马建忠. 马氏文通.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12. 彭利贞.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3. 任荷. 上古汉语情态助动词“宜”探源. 语言研究, 2023(2).
14. 沈玉成译. 左传译文. 北京:中华书局, 1981:489.
15. 王宁. 先秦汉语实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分类. // 高思曼, 何乐士编. 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 1994.
16. 魏培泉. 庄子语法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82.
17. 魏培泉.论先秦汉语运符的位置.//Peyraube A,Sun Chaofen (eds.)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ris: CRLAO,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9.
18. 巫雪如. 先秦情态动词研究. 上海:中西书局, 2018.
19. 徐鋕银. 上古及中古汉语应然、必然类情态词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20. 杨伯峻, 何乐士.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上)(修订本).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1:213.
21. 姚振武. 《晏子春秋》词类研究.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2. 章士钊. 中等国文典. 上海:上海书店, 1925.
23. 周法高. 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上).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 1972.
24.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61.
25. 朱冠明. 《摩诃僧祇律》情态动词研究.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90-91.
26.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2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