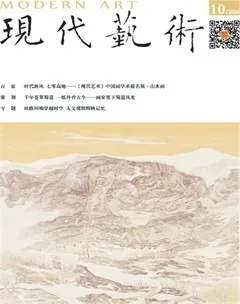《河西走廊》: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的三重意象
一条河西走廊,半部中国历史。“河西走廊”这一概念不仅是地处大山、大河与大漠之间的空间坐标,更彰显了兼具历史学与人文地理学意味的丰富文化积淀。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纪录片《河西走廊》,正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牢牢把握住这一文化维度。影片不仅梳理了河西走廊甚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历史,更以史诗风格的艺术手法与影像书写展现了其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值得探讨的是,“时间性的空间”在《河西走廊》的影像书写中既表现为历史叙事的主轴,也是展现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的关键,并构成影片中关于文化记忆的三重核心意象——“走廊”“人”“路”的美学基础。借助这三重意象,《河西走廊》以独特的影像呈现方式,展现了历史与当下的时间绵延,从而追溯与求索留存于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深处的故事、精神与内涵。
“走廊”:记忆空间的时间交叠
所谓“走廊”指的是建筑中上方有屋顶的过道,本就是空间性的概念。而地理概念上的“河西走廊”,简称“河西”,意指黄河以西、祁连山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的狭长地带,因形似一条走廊而得名。在纪录片《河西走廊》中,走廊一方面是对“河西走廊”这一概念的指代,另一方面是构成影片中建构文化记忆的核心意象之一。而通过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河西走廊表现为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空间,影片实现了多重时间的交叠,从而在历史叙事的时间线索上形成“编年”与“古今”并举的格局。
“编年”指的是纪录片在宏观维度的历史叙述逻辑。影片以编年史的时间划分为线索,展示了河西走廊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时刻,其史诗式的叙述跨越了汉、三国、两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以河西走廊这一局部性、地方性的空间折射出横跨上千年历史时间的风云变幻。质言之,河西“走廊”的意象被呈现为一个记忆空间,形象地说,它就像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
而“古今”指的是纪录片在中观层面的历史观照情怀,尤其体现为对绵延的历史时空的感叹。较为典型的如第3集《驿站》的结尾,影片以黑白纪实影像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河西走廊边疆农垦举措,与近两千年前汉代所实施的屯田驻边政策遥相呼应。而这种古今呼应,或依照影片所言“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印证出河西走廊独特的历史价值与战略地位。但影片并非止步于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而是将视角引向“逝者如斯夫”式的感慨。
“人”:文化认同的长时段形塑
如果说“编年”与“古今”并举的框架在宏观维度构成《河西走廊》历史叙事的时间线索,那么与之相对照的,是以个体生命的微观维度支撑并深化了历史叙事的细节。影片通过“人”的意象,将个体的短暂生命时间融入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将个体的记忆纳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整体当中,而这一融合过程主要是通过对文化认同的展现来实现的。简言之,“人”的意象所传达的文化认同,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且是在长时间尺度上不断塑造和演进的。
“人”,在这里首先以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为代表。从汉代打通河西走廊、开启丝绸之路的刘彻、张骞、霍去病等,到清代负责国防事务、具有国际视野的林则徐与左宗棠,他们构成了河西走廊古今历史的主线。尽管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命短暂,无法目睹河西走廊在后世的历史发展全貌,比如英年早逝的霍去病无法见证河西走廊畅通后商旅往来的盛况,但他们所留下的文化影响却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例如第5集《造像》以鸠摩罗什的生平为核心,讲述了他被软禁在凉州城长达十七年后,如何进入中国腹地,并尽余生之力翻译佛教经典、塑造佛像以弘扬佛法。而正是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个体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河西走廊乃至中华文化留下了延续至今的重要文化遗产。
同时,“人”也体现在那些原本被史书记载所略过的普通人身上,影片不仅关注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还将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推向历史的台前。例如,在第3集《驿站》中,驻守敦煌悬泉置驿站的普通官吏与和亲的解忧公主曾几度在驿站中“擦肩而过”,二者人生轨迹的交叠情境的还原,得益于晚近出土的汉代简牍,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生活史的微观视角。在第7集《敦煌》中,影片以未曾记载于史书的“李工”作为敦煌壁画万千画师的代表,表现出他从长安西迁至敦煌、在220窟中留下旷世杰作的过程。
从生活和文化史的角度,影片还原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微观历史图景,深刻印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念。
“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观照
纪录片《河西走廊》所呈现的第三重核心意象是“路”,与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中趋于中心化的“路”意象不同,纪录片所要表现的“路”具有互联、互通、互惠的意味,它既指代空间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更指向理念意义上的“发展道路”。
所谓“路”的第一重含义是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属于其发端之处,也属于其联结的沿途各个国家和民族,具有世界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意义。因此《河西走廊》的历史叙述将西域各国商人、西方传教士的视角也纳入其历史叙事中,关于河西走廊的文化记忆书写并不仅限于中国史的范畴。
“路”的第二重含义,指向河西走廊背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影片将河西走廊作为沟通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多民族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区域,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整体性的局部”,由点及面地展现其对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文化贡献。如在第4集《根脉》中,影片展现了两晋与南北朝时期西迁河西走廊的中原士人学子,他们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到了河西走廊,而此地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让这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得以延续,甚至在漫长的积淀中反哺了中原地带。
“路”的第三重含义直指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多集中历史叙事的尾声之处,均以河西走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发挥的当代意义作为升华,而第10集《宝藏》更是直接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河西走廊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建设蓝图中工业化与能源战略方面的关键一环。
结语
从宏观到微观,从个体到集体,从空间到时间,纪录片《河西走廊》借助“走廊”“人”“路”的三重核心意象,为我们勾勒出历史叙事的文化记忆之维,而“文化”的确是影片历史叙述与内涵传达的落脚点。纪录片《河西走廊》所传达的重要观念是:在时间的滚滚洪流面前,有文化能够超越时代变迁的沧海桑田、穿透个体生命的转瞬即逝。而河西走廊所映照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发展历程,亦将继续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