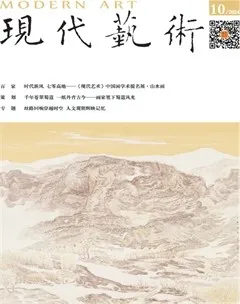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视角应用初探
叙事视角是创作者关注纪录片故事的一种角度,同时也代表着创作者讲述纪录片故事时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叙事学与电影、纪录片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西方现代小说文学理论诞生以来,创作者以何种姿态观察故事、以何种角度理解故事、以何种立场讲述故事就一直是叙事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不论是对商业模式纯熟的戏剧片,还是小众先锋派的艺术电影,或是追求理性、客观、真实的纪录片而言,有故事的地方就有讲述,有讲述的地方自然就有立场。当我们谈论纪录片叙事学的时候,除了谈论叙事的结构、修辞、方法之外,实际上应该首要关注的便是叙述者的叙事视角。它是创作者运用镜头讲述故事的开端,也是导演运用光影创造意义的前提。同一个故事,不同的叙事立场对于情节的表现往往会由于创作者主观的表达方式而生成截然不同的艺术成品。叙事视角的变化也影响着观众对于内容情节和叙事人物的理解认知。
“全知视角”下的历史题材还原
纪录片是最具有文化特色和人文意涵的艺术品类。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国家历史、塑造民族集体观念的重要途径,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活动影像史书。作为一种高品质的文化代表,无论是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民族的、世界的,只要与人类文明文化有关的范畴,皆是纪录片创作的灵感来源。作为一种最大程度实现“物质现实复原性”的影片,作为非虚构影像的指代,纪录片不仅是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观照,也是对世界万物带有人文精神的关怀。近年出品的众多精品历史题材纪录片例如《大河之北·文华燕赵》《史记·华夏风云》等作品,制作水平精良,艺术造诣高,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兼备,一经播出便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它们有些从纵向时间线索上梳理中华文明的更迭,有些从横向断代层面上还原某一时间段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以独特的视听语言讲述着属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故事。
对于大多数历史题材纪录片而言,由于历史事件是已然发生、既成事实并且不会更改的,因此经常采用的是纪录片叙事视角中的“全知视角”。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他著名的叙事学理论书籍《叙事话语》中反复强调了叙事视角的重要性。“热奈特将全知视角这一名词称为‘零视角’,意即纪录片叙事中并无明晰可辨的‘叙述人声音’,叙述者并非纪录片中的角色,与纪录片的事件进程没有关联。这种叙述可以灵活转换视角,而且视角、视野比较广阔,创作者可以跳出主客观条件和时空的限制,自由度更高。”“全知视角”由于创作者在讲述时展现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姿态,以及非聚焦式的全面讲述方法,又被称为“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对较长的时间背景下表现错综复杂的人物互动关系或讲述宏大的历史题材更为擅长。《河西走廊》《故宫》《长城》《何以中国》《津门往事》等纪录片皆是采用“全知视角”对宏大历史题材进行还原记录。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拥有着文献纪录片的气质,擅长运用文献资料来推动叙事。影像起到了支持、见证、证实的功能,如果史实材料非常丰富,有时甚至可以主导纪录片故事的发展。
例如,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制作的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创作者通过每集五分钟的时间,借助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国宝文物之口,来讲述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带领观众体会国宝背后的中华文化和独特的中国审美。该片摒弃了传统历史纪录片机械的旁白科普、专家介绍的叙事模式,针对每件国宝独特的生长环境、器型特点、历史渊源,采用高清三维数字扫描、多光影采录技术、数字拓片、多光谱采集、全息投影等高精尖技术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地将有关国宝的历史文献进行故事化重新编排演绎,让观众可以作为一个参与者身临其境而非旁观者,了解国宝的前世今生。叙事者在全知全能的视角下讲述历史更为方便,也更易于将庞杂繁琐的信息进行归纳梳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知视角”的纪录片更为基础,更贴近于早期“格里尔逊式”的阐释型纪录片。最惯常的叙事手法即为毫无争议的解说词贯穿始终,画面成为了声音的佐证,纪录片中呈现的故事被讲述者滴水不漏地建构在观众脑海中,几乎不存在任何悬念。
“限知视角”下的历史题材表达
除了“全知视角”以外,另一种经常被使用的视角是“限知视角”。如果说“全知视角”擅长将历史卷轴以一种气势磅礴、通天晓地的姿态铺陈开来,那么“限知视角”则会将历史长河中那些值得记录的璀璨瞬间以一种更加深邃、隽永的方式书写铭刻下来。纪录片中“限知视角”的限定性,实际上是创作者基于自身立场,对于故事题材的一种人为取舍过后的、有选择的真实复刻。它的视野不再像“全知视角”那般俯瞰一切,而是聚焦于某一个或多个具体的点上进行观察。“限知视角”经常混合着内聚焦和外聚焦两种方式,“内聚焦分固定式(不离开一个人物的视点,这意味着视野的限制)、不定式(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和多重式(根据不同人物的视点多次讲述同一件事);而外聚焦是指人物和事件被某个天真无知的目击者从外部观照,对思想情感不作解释。”由此可见,相较于《人类大历史》《维多利亚时代》《我的中国》等纪录片中全知全能、掌控一切的讲述方式,“限知视角”只会基于个体的所见所闻和镜头记录下的光影来讲述故事,永远不会展现镜头外未知的东西。
尽管大多数历史题材纪录片擅长并且热衷于使用“全知视角”来还原真实,但“全知视角”也并不是完美的,它同样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例如,“全知视角”在阐释事物的时候,会受限于创作者的知识框架和逻辑思维,导致接受者对于事实真相的理解片面单一;“全知视角”过分追求创作者的叙事能力,而忽略甚至轻视了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实际上是一种对接受者思辨性的压缩。这种单向的、灌输性的叙事往往会使部分习惯质疑和思考的观众产生抵触心理,进而影响纪录片的审美传播。
近年来,伴随着纪录片拍摄手法的创新进步,许多宏大题材的纪录片也开始尝试使用“限知视角”进行叙事,淡化阐释型纪录片类似说书人的叙事口吻,挖掘观众在“限知视角”之外的独立思考能力。2020年,伴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许多纪录片导演敏锐地将镜头对准了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各行业形形色色的故事上,其中就包括了曾经拍摄过反映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普通百姓生活的知名导演范俭。作为一名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范俭第一时间察觉到疫情的暴发在今后中国的历史上会留下一道重重的痕迹,它需要被镜头记录,也需要被历史所铭记。在这种创作意识的影响下,范俭导演深入武汉疫情一线,拍摄完成了《被遗忘的春天》。在短短67分钟的影片中,观众并没有感受到传统纪录片那种无所不知、自带安全感的讲述,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充满未知性、猜测性的方式,以陪伴者、倾听者的姿态,深入武汉某社区的三组家庭中,去记录他们在疫情中的悲欢离合,启发观众从情感层面去感同身受思考和共情。“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限知视角”在信息的处理广度和容量上是有限的,但这种对于事实的聚焦却蕴含着创作者自身的态度和观点。
无论是“全知视角”还是“限知视角”,任何一种叙事视角实际上都代表着一种立场和“见证”。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根据表现对象的具体类型,也不应仅局限于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应在双向互动的创作反馈中尝试更加立体化、多样化的叙事视角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