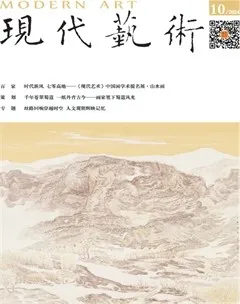从细微探秘心宇
金心明
1970年生于浙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研究会副主席,西湖画会艺术总监,寒之友社艺术总监。
“世界”是时间和空间所能指示的最大概念,据说要三千个大千才能组成。世界那么大,反正是我所不能确指而梦见的那种大。“世界”同时又是每个人的内心,以及由内心而起的各种想象。
我有着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我常常为之自省。倏忽人间五十三,要在古代,早已到白发苍颜的年纪了。
而现如今自己尚能以笔墨手段苟存于世,心向高远,作自我观。忆往昔,我自十岁起涉足书画,以学技艺为目的。初习唐楷《九成官》,覆纸描摹,以求形似。
画学《芥子园画谱》,山水、人物、花鸟都临。当然还有各式连环画,尤以王叔晖的《西厢记》临摹最多。
诵《千家诗》,读《古文观止》,无非是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囫囵吞枣而已。还有刻印,工具书是《常用字字帖》四本,入手即创作,什么“闻鸡起舞”“书山有路勤为径”一类的励志词。时间和精力以及兴趣爱好尽付于此“非正道”,其后果只能是正道的学习一塌糊涂,全班近乎倒数。我在所谓的“从艺”小路上踽踽独行,小学到初中的几年时间里,几乎画遍了从家到学校数里山路上的各式树木——樟树、栋树、乌桕树、苦槠树、皂角树……当然,山坡上最多的还是枣树,曲里拐弯的枝丫,方折刚劲,在寒冷的冬天暮色里与我相守。这是我打发小时候漫长时光的独特方法,似乎也是我全部的、狭隘的世界。尽管世界上有道路万千条,但每个人却只能走一条极其狭窄的小路,或许,那条路上的风景是我们内心无穷的渊薮,不知心里的世界是否也在大千的世界里?为此常自戚戚焉。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只能是世界上一个个细微的特例,没有可能重复的个体感知塑造出独一无二的我们。当我回首往事,记忆起那些只有自己能辨别的音色声味,似乎是穿越了一个深邃的隧道而来的被隔离了外界的单一体验。那么,我所能触碰到的世界有多大呢?无非是那一条蜿蜒的小溪,一池清凉的荷塘,一座苍茫的小山,如此而已。
时间的茫然像一列飞驰的火车,不给你停歇的机会,不给你左右的遐思。我有时候也会陷入思考,思考时间的长短,思考时间在世界中的距离,但总是让人觉得蜷缩在一个静止的片段里,走不出来。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单一的艺术思索过程中,从西方哲学到宋词元曲,从浮世绘到信天游,从时间的纬度到空间的拓展,从天马行空的游离到大江南北的穿越,上下求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折腾青春的力量是试图突破自我世界的愿望。然而,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无从被突破的世界。
偶尔仰望星空,那点点闪烁的清冷光点是数百年前的信号,恍若隔世。我梦想遨游太宇,不想落入笔墨的窠臼,沉入深渊,隐入尘烟。
不可复制的过往成就现如今我笔下的字和画,冥冥中似乎是时间给予的结果,也或许是空间赋予的能量。我的自由只在当前、眼前、心手之间,我把我的全部描述成一个似是而非的存在。或许,我的世界只能如此,心念和身意共同构筑了一个如此的大千世界。
认识心明兄好多年,近些年似乎更懂得他的那份诚心了。无论是搞艺术还是做人做事,他的品性都可以从其艺术作品里读出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你能一出手就是你自己,变得像自家的那种气质。”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千锤百炼。”这让我想到了历代画家中的陈洪绶、弘仁、金农、齐白石等画家,一看就是自己。而心明的山水、花鸟、书法也同他们一样,识别度很高,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他讲过:“山水画就是意造自然,不能被自然景象所役,顺应自然的合理性,却又要合乎自我意识和自我审美。”的确,这也是每一位艺术家要面对的课题。
面对山水、花鸟、书法、篆刻、文字等多方面的创作,心明的做派多是守护。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脉,以承传为本,寻找自我。他不仅仅在艺术创作上有范,还喜于收藏字画和古玩,也迷恋出版。其收藏多以明清以来,尤以民国的字画为主。他不问名家大佬还是乡野村夫,甚而藉藉无名者,有眼缘时,也乐意购置。在他如今的画室里,常常能欣赏到我们不常见且不知名书画家们的意外之品,读来很是养眼养气。这样的玩味状态,心明是随自我的心性在玩、在消遣,有一种古代文人的生活状态。很多时候,他对时下许多热闹的展览不是那么关心,显得自我边缘化。虽然杭州常常有许多名家大展,他却像当年齐白石先生不去故宫看名画的观点一样,有点保守主义,不太去关注什么经典的东西,不太关注有名的东西,喜欢在自己的那份情趣和审美区间里去把控,保持着一点点纯真调性,这也就是心明那份可贵的诚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子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