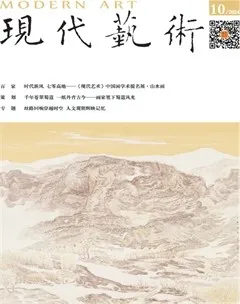回归诗意 向阳而生

龚仁军
二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山水画会秘书长,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第一批“巴蜀画派”艺术实力代表人物。美术作品曾多次荣获“齐白石奖”“巴蜀文艺奖”“四川文华奖美术奖”等国家级、省级奖项。美术作品发表在《美术》《美术观察》《美术大观》《中国画收藏》《四川美术》等专业期刊。
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我一直致力于探索水墨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下的新的表现语言与形式,我想以此文表达和分享一下这些年来我在绘画道路上的创作理念和所观所思所想。
题材与物象,巴蜀自然与人文融合下的独特人间桃源
写生是中国画创作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历代创作上有成就的画家非常重视写生。元代黄公望《写山水诀》提到:“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写生观中,实际上是把对自然的深入观照和细微体悟放在首位,并使自然山水与画家心灵互融神会,最终达到顾恺之所说的“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目的。五代荆浩十分注重生活,居于太行洪谷,和自然朝夕相对,写生松树“数万本”后,“方如其真”。唐代张璪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北宋山水画家范宽在悟出“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而“移居终南太华,遍观秦中诸奇胜”之后有《溪山行旅图》的力作。清人石涛针对清初复古之风盛行而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他半生云游,饱览了大江南北的名山胜水,才有了他那些标新立异,风格多变的山水画。近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一生游览了无数名山大川,学问既高,见识又广,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故画面浑厚华滋,独具风貌。
巴山蜀水形态丰富多样而气质独特,南北兼容,在中国大地间最是独一份的存在,或雄奇险峻、壮丽深邃,或灵动变幻、氤氲缥缈,给人千地千面之感,物象风景又随分明的四时、地域变化而不同。四川的文化,也呈现南北融合包容,汉、藏、羌、彝、回等多民族分布而居的特色,令画家们可以轻松见识多样化的在地人文生活景象。这些丰富的自然和人文之景,都让我深深陶醉和喜悦,沉浸感受这片土地之美。在这些多元迷人的景致当中,最令我喜爱和心驰神往的是独特的羌藏村落民居和散布在四川的原生态古镇。我想描绘我们所处的时代下保留着的、生动淳朴的人间桃源。
羌藏村寨题材,以前少有人表现,而我想持续地表现四川这独一份的羌藏文化走廊上的村落与自然风光。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大大小小的羌寨。阿坝州理县杂谷脑河下游两岸是羌族聚居地之一,是一个快乐而美丽的地方,也是人生难得遇到的一方净土。川西的桃坪羌寨、大岐村、色尔古藏寨、蒲溪乡、奎寨、尔瓦寨……我几乎到过这一带的各个羌寨。这些依山而建的房屋、造型奇特的楼阁,热情好客而又善良淳朴的人们,以及他们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常常令人感动。此外,藏区苍茫高远的天地、庄严肃穆的寺庙、神秘圣洁的白塔、华丽多彩的臧楼都令人印象深刻,心驰神往。正因这些多元的物象,我画了“羌藏”系列、“飘动的经幡”系列、“古村彝歌”系列等,坚持了十多年,反复描绘,乐此不疲。
另一类我最喜爱描绘的题材是四川的古镇,因为它更能展现出一种人文情调与诗意,更能唤起人们对岁月沧桑的记忆,或者说印上时代的烙印。四川的古镇常常修建在一条小河旁,保留了不少的古建筑。奇特的吊脚楼、古老的面房、临街的小店、精巧的小桥、高大的黄桷树、赶场天拥挤的人群、水中自由自在游泳的鸭子……一切都那么亲切,那么自然地融入画面。这些充满了宁静平淡的田园气息、质朴自然的美景,让我想捕捉刻画下最令人心动而永恒的美的瞬间。
古镇当中,我最为钟情的当属川南小镇,福宝、龙华、仙市等,难得保存了原汁原味的当地生态,造型各异,饶有趣味。它们雄秀不同,或遮或显,皆临水而建,参差错落,令人饱看不足。福宝当地风貌十分原生态,古镇布局富有变化,整个镇呈现龙的造型。吊脚楼多,楼是木质结构组成,楼层高的依山而建,足足有四五层高,这样多的元素契合我的心性,勾起我创作的欲望。
笔墨、水法和构图,用新形式语言捕捉表现水墨山水的光与影
我国优秀的文人画传统、近代山水名家以及大自然是我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我的斋号是三师学堂,其一,师古人,中国文人画水墨山水优秀的传统,如元代王蒙、倪瓒,明代张宏,清代石溪等大家;其二,师今人,杰出的今人必定学习了古人精华,并在观念、技法上延伸出了自己的特色,如黄宾虹、陆俨少、李可染、傅抱石,当代浙派画家何加林、林海钟、张捷、张谷旻、丘挺等人,他们都强调画家的性灵、笔墨趣味和神韵;其三,师造化,这也是最重要的,到大自然当中去感受生活,然后通过手下的画笔表现触动心灵的东西。
艺术贵在创造,中国画的当代笔墨与形式语言的创新我认为也需要借鉴西方的形式语言。比如,西方现代艺术从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提供给我形式构成、点线装饰以及表现技法上的许多灵感。我爱莫奈作品之严谨雅致,勃纳尔作品之装饰厚重,梵高作品之律动炫目,波洛克作品之斑驳闪耀,其经典之作至今百读不厌。
立意、构图和笔墨是水墨山水画的灵魂,不宜鲁莽下笔,须三思而后行。当我思考如何表现羌藏地区的村落时,我钟情于那里阳光的明媚,建筑的奇特,人性的质朴。那么如何用新的形式、笔墨水法来表现这一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我一直探索用水墨的特色语言来表现物象在阳光下互相追逐、光影律动变化的感受,反应色彩的晕染浸润和跳跃变化,就好似一切都笼罩在迷蒙氤氲的不同色相的光雾之中,达到一种浓淡相宜、清新雅致、浓厚华滋的美感效果。
色彩方面,我喜用淡墨和宿墨,敷以赭、红、黄、青等浅绛色来渗入、晕染和装饰,提亮整体氛围印象,表现生机和活力。我也甚爱用颜料残渣,在宿墨中渗入少量的彩,让墨色透出阳光的闪烁。最后的画面效果,在留白、色块与水润的相遇或者碰撞之处,正是那穿透空气和视觉呈现的阳光斑驳的感觉,有评论家称之为“阳光水墨”的效果。我想让观者透过我的画,感受到大自然阳光、空气与色彩的味道,体会到触动我心灵的祥和之美。
这种水墨实践,一路走来至今,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偏好:首先,构图上喜好以大面积几何块面为主,造型上让物象与周围的环境、地域特点融为一体,排列组合,平面化铺陈开来,甚至铺排满整个画面,留白较少,呈现放大或者特写的装饰效果;其次,视点和构图上,喜欢采用高视点全景式俯瞰,对角线或者灵动变化的“之”字形构图,让观者的视点生活有趣,随之变换;最后,再用点、线穿插其间,水墨互破,淡色晕染,节奏变化,画面浓浓淡淡、虚虚实实,营造氤氲的光影印象气氛。画民居、园林时,观其景,察其情,多以表现主义手法,略带装饰之趣,抒写胸中之意趣。
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在艺术创作这条路上,任何探索都会付出心血与代价,需要持续探究和求新的勇气与实践。
风格与趣味,简淡天真之美的诗意审美回归
传统中国文人画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追求神韵和意趣,倡导诗情画意的风格,兼具文学性、哲学性和抒情性,产生了一代代师法自然,重视写生的优秀画家。“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家需要创新变法,不固守传统,表达个人审美和风格趣味。这些精神,我深以为意,画家的能力与使命,就是在几尺方寸之间,创造得于心的图像和传递美的感受,关键是情思和趣味。
画者所难得者唯趣。明代性灵派袁宏道就曾说道:“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美学大家王国维所描绘的诗词境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我所追求的画意也是如此,难得的是冲淡平和、宁静娴雅的优美意境,使得画中有情,情中有景。
画家需要保持对美的事物的敏锐感知力和捕捉能力,从平凡的景物中以他独到的眼光去寻觅美的物象,再运用技法与形式结合,表达自己的视角感受。我认为,一部作品的视觉观就是这件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当代社会,生活节奏紧促,压力丛生,平凡的人们心为形役,阳光与愉悦难得,能在纷纭的尘世诗意地栖居更是难能可贵的。
我在四川高原聚居的羌族、藏族老百姓的生活中,在四川和其他地区乡村古镇的生活中看到了一种自然和诗意的回归。恬淡的田园之美,建筑的律动之美,人性的质朴之美,在阳光下烟云流动,万物呈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唤醒人们最为自然的感官,令心灵为之深深感动和陶醉。
近年来,我将自己的视觉感和对生活的感怀融进了这些景物,极少画人,直接单纯地画山峦、云朵、田野、林木、吊脚楼、民居、道路、牛羊、鸟群、池塘、溪水、鸭子等元素,造型排布,样式变化多样,加以颜色,形成不同的画面调子,类似有形式感和节奏感的音乐,形成画面的节奏和韵律。每幅画调子和视觉感不同,好似不同的田园牧歌,文眼则安放作为画题。我的创作如《幽居图》《村居图》《吉祥家园》等,便是这种尝试,笔墨更加简单清新,专注进行光与墨色的实验,来谱写不同时光、不同气候氛围下流动着的简朴与单纯的美。
画画是一辈子的事,生命不息,画画不止,我愿一直做一个向阳而生、回归简淡诗意的山水画家,用我的眼和心,手中的笔和墨,去细细诠释天地世间最觉祥和美丽的居所家园,去尽情演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生命安居的精神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