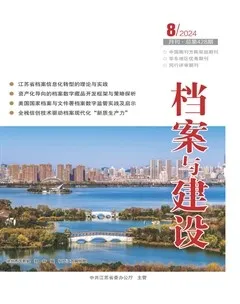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的遵循:价值、困境及出路
摘 要:从明清契约文书整理的相关成果来看,当前研究探讨多集中于“归户性”整理方面,而来源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来源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按档案来源进行整理和分类,保持同一来源档案不可分散、不同来源档案不得混淆,遵循来源原则对保障契约文书的完整性,保持契约原有整理方法和体系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在实践中,遵循来源原则也面临着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在前端已被破坏,来源信息追溯困难,整理、出版中有关信息被删节等困境。为了突破困境,在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中应尊重契约的原貌和原有整理方法,尽最大可能开展研究补充与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密切相关的信息。
关键词:来源原则;明清契约文书;完整性;关联性
分类号:G270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on the Collation of Contract Fil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alue, Predicament and Solution
Zhao Hui 1, Zhong Wenrong 2
( 1. Library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2. School of Social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
Abstract: From the relevant results of the collation of contract fil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s of collation focuses on the way of "Gui Hu".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a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was not paid high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collation. The core thinking of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is that archives should be arranged and classified by the provenance, the archives coming from the same provenance should’t be divided, the archives coming from the different provenance should’t be mixed together.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is valuable on the guarantee of the integrity and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arrangement methods. In the practice,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also fac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damaged integrity and relevance of the contract files on the front-end, the difficulty on tracing sourcing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loss during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and so 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keep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contract files and the original arrangement system, and do more researches to supplement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ntract file integrity and relevance.
Keywords: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Contract Fil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Integrity; Relevance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明清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整理、出版为学界探讨区域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宗族史等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在相关成果中,影响比较大的如:《徽州千年契约文书》《闽南契约文书综录》《明清经济契约文书选辑》等。就有关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方法而言,以问题、年代分类整理的方法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在整理和出版中保证契约文书的完整性和关联性成了关注的重点。“归户性”整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整理方法,其核心内容为强调契约文书与具体的形成者、保存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文书的归属性,逐渐在实践中得到了推广。学界对于“归户性”整理开展的专题性研究比较多,如《关于民间文书“归户性”整理的理论初探》[1],该文对“归户性”的定义、“户”的不同解释及民间文书“归户性”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等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契约文书的归户性研究方法》[2],该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入阐述了“归户性”整理的三个具体方法:绘制人物关系图、划分结构单元、进行田野考察并与相应区域的民事习惯进行对比研究。
但从档案学科的角度,是否存在相应的整理方法或原则,可以作为本学科特有的方法,输出到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实践,有待思考。与“归户性”整理高度受关注的情形相比,学界对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的价值、困境及应用的出路等相关问题却缺少专题性的讨论。本文欲在此方面做一些梳理,以阐明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出版中的重要价值,扩大来源原则的影响力。
1 遵循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的价值
1.1 明清契约文书的形成者及来源获得充分重视
契约作为记录经济活动中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具有“表示昭守信用,保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3]的基本功能。契约的形成与特定的主体、标的物、价格、规则及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中充分重视契约文书的形成及来源,尽最大可能还原契约文书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各种潜在联系,是全面解读契约的关键环节。来源原则“按来源标准整理档案,保持档案与形成者之间的来源联系”[4],有利于保持契约文书的原始信息。
检寻目前有关成果,对契约文书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丰富多样。如按时间顺序开展整理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5],有利于分析契约的发展脉络,为不同时期契约的对比分析提供基础。但如果只掌握了时间信息,依然无法充分了解契约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深入挖掘契约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网及复杂的交易规则、制度、管理等内容。还有按照主题来编排的《徽州文书类目》[6],该书将所收录文书划分为3种、9类、117目、128子目。如“1.1土地、房屋、耕牛等事产买卖文书”类目之下再细分为卖田契、卖地契、卖山契、卖塘契、卖屋基契(包括卖房屋契)等14个子目。这种方法“把所有学科性质内容相同的文书聚集在一起, 便于研究者从各自不同专业学科角度出发进行专题研究和对比跟踪”[7],但割裂了契约与来源的关联,突出内容特征,离开了契约来源的分析,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随着明清契约文书整理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整理者开始重视契约的形成者和来源要素,如《徽州文书》的作者刘伯山在整理过程中就坚持不做过多的分类,充分尊重契约的来源。“不管类别和内容的异同, 将同包(批)收购的文书配一个编号集中在一起, 辅之征集地点、时间等信息, 从而最大限度保证同一个地点的文书得以汇集不散, 有利研究者依据地域线索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8]在此整理方法的影响下,许多整理和出版成果,以一地、一户作为整理的基本单元,如《清水江文书》[9]以平鳌寨文书、岑梧寨文书、林星寨文书、魁胆寨文书等作为整理的基本单位,保持了一地之内契约的关联性,为分析和研究区域范围内相关问题提供了翔实的信息。此外,徽州文书的整理者认为:“从来源上看,徽州文书档案是从民间一户户民宅中流传出来的,有的是一户人家形成和保存的关于本户的文书,有的是保存在人户中关于一个宗族、一个会社的材料。” [10]这种按照一个人户的材料来源开展整理的方法,在《石仓契约》[11]《大屯契约文书汇编》[12]中也得到了充分应用。
综上所述,遵循来源原则为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中充分重视契约的形成者与来源关系,最大限度追溯契约形成过程中的各种潜在关系、规则及意义提供了保障。
1.2 明清契约文书的完整性有了充分保障
来源原则尊重“全宗完整性”。“全宗完整性”指“全宗是有机整体,整理档案必须维护全宗完整性,做到同一全宗档案不可分散,不同全宗档案不得混淆”[ 13]。契约文书的完整性一般而言是“齐全完整”,包含五层含义:第一,契约所包含的各要素无残缺。第二,在各项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契约及与契约相关的辅助文件、附件齐全完整,各文件之间的联系通过有效的方式得以固化。第三,一次完整交易活动或一个交易主体所形成的契约有机地、按顺序排列在一起,内容上具有关联。第四,契约内容上的关联性不被破坏。第五,不同来源的契约文书不能混杂在一起进行整理。
契约文书的完整性一旦被破坏,发现契约关联性的可能就极大地降低了。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黟县五都四图榆村的邱三赐曾买了一个叫胡履丰的人所卖的一块风水地,形成了一份赤契。这份赤契是包在一张包契纸里的,在同一包里还有另外三份契约,分别是:明天启四年三月初十日胡奎卖风水地与程氏赤契,在这份契纸的对折另一面还写有一份立推单;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程百达等卖风水地与叶名下赤契;道光十五年十月叶赏龄卖风水地与胡名下赤契。” [14]从所引材料来看,在契约的整理中,契约保存者将一宗地的买卖、转卖、再转卖交易所形成的所有契约有机地叠放在一起,完整地展现了该宗地数次易主的过程。这种整理方式,坚持以宗地作为线索,将宗地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全部契约有机排放在一起,保持了宗地交易的契约的完整性,生动地展示了宗地交易的细节和脉络,为研究不同时期土地交易的程序、规范、价格及差异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目前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充分利用契约绘制契约当事人之间人物关系图谱,这需要大量完整的信息才能完成。如果契约的完整性得不到保障,开展契约内在信息的分析将举步维艰。整理者曾言:“在散件文书中,关于立契双方及中见人之间关系的线索很少、关联信息缺失,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姓名就是孤零零的两三个汉字,换成张三、李四、王五都不影响契约在文义上的完整性。” [15]
1.3 明清契约文书原有的整理体系得以保留
在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中遵循来源原则也包含着对契约文书原有整理体系的保留和继承。从大量的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实践来看,原有的体系应该指契约的形成者或者契约的持有者在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整理方法及系统。古代文书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形成和保存,应有其特定的整理方式,如按《千字文》进行整理。《千字文》用于契约编号,在史书中有许多记载,如《宋会要辑稿》孝宗乾道七年二月一日的诏书:“……昨降指挥专委诸路通判印造契纸,以《千字文》置簿,送诸县出卖。可令各路提举司立料例,以《千字文》号印造契纸,分下属部郡,令民间请买。将收到钱专委通判拘收,并充上供起发。” [16]按《千字文》编排在明清契约文书中也有相应的实例,如“休宁县档案馆收藏徽州文书档案4240多件……都图按千字文的顺序编写,有甲、乙、丙、丁、天、黄、宙……”[17]。又如目前已经公布的大量明清契约文书的契尾中,都有明确的《千字文》字号。《慈溪契约文书》中“052嘉庆二十五年七月 大贵卖田契(连契尾)1-2”图版中有“布字叁仟陆佰叁拾伍号”[18]。类似的情形在明清契约文书中比比皆是。
在契约文书整理中尽量保持原有的整理体系,这一原则已经被许多整理者所坚持。如《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的整理者所言:“本书编者主张尽量保持文献和档案原来的系统和内在联系,不打乱文献原有的系统。” [19]又如“关于民间文书归户性整理的原则和方法,基本的认识是尽量保持文书收集时的原有面貌和内在系统性,一般不对文书重新分类” [20]。冯学伟在整理《福建洋坑许氏文书》中也提到:“由于文书产生的原始家族在保存文书时做了分类,把相关联的文书叠放在一起保存,且收集、整理前基本保持了原样,这种没有被破坏的‘文书链’,不但能够看出传统社会里产权的转移机制,还为分析同一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流转情况提供了可能” [21]。综上所述,在大量的明清契约文书整理、出版实践中,保持文书原有的体系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
2 遵循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和出版中的困境
2.1 契约文书在流转中被割裂、拆散
许多明清契约文书在发现、收藏的过程中,经过多次转手,其完整性由于各主体的不同动机和行为而遭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有书商和文物贩卖者为了牟利将契约拆开销售,徽州文书就面临这一状况,“这些书店的整理,尤其是它们的分散出售,人为地、无意识地将有关联的文书档案拆散,卖到各个单位,破坏了原有文书档案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如当时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形成的一批元代到明初的文书档案,即被拆散分别卖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即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安徽省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移交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肥师范学院(后移交给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至于同一户、同一件事情形成的文书档案,分别卖给两家以上的比比皆是” [22]。《田藏契约文书粹编》的整理者田涛也感叹那些完整的契约被生硬拆散的现象,“但仍有一些契约是几经转手才收集而来,其中有的小贩心怀商贾旧习,或将契据一分为二,或者以假充真,或者随意粘贴,以掩饰残缺,这些都给我们的整理工作带来了麻烦”[23]。
此外,契约的完整性也可能因收藏者有选择地购买而被破坏。如田涛在谈及契约收藏的缘起中提到:“最初发现的契约,被选入《田藏契约文书粹编》的,已经寥寥无几,一则因残破缺损较为严重,另外河北、山西一带后来成了我亲自采集的地点,发现了更多的资料,但是为了纪念我与那些来自农村朋友的友谊,我还是从中挑选了几种。” [24]
总之,明清契约文书的发现、整理和出版,要经过多个环节,涉及多个主体和多个程序,书商和收藏者基于各自动机对契约有目的、有选择性地进行购买和收藏,给契约的完整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这种破坏对于明清契约的完整性而言是不可逆的。
2.2 契约文书在流转中相关来源信息保留困难
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出版过程中遵循来源原则也面临着契约文书来源不明的困境。明晰来源是建立全宗的基本前提条件。明清契约文书来源不明的情况多出现在文物市场买卖的场合。由于文书收购者没有详细地记载收购的相关信息,导致在契约整理、出版过程中一旦要追溯相关信息便困难重重。如各地在整理明清契约文书中出现的所谓散契的情况,这种情况多是由于来源地、所有者、持有者等信息不完备,在整理和研究中面临不小的难度。“但由于编者的疏漏,未能将文书产地(村寨)名称和文书的原来持有者姓名等信息标明和区别出来,以致给利用者带来了不便。” [25]
2.3 契约文书整理、出版中未遵照原貌
遵循来源原则,也面临着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整理者和出版社对完整性缺乏认知的挑战。因为在整理出版中,一些整理者或出版者认为契约中的信息并非都是有用的,如在整理出版中有将契约与契尾分开,保留契约而弃契尾于不顾的情况。“然而,在现已出版的一些土地契约资料集的编辑者们似乎更重视草契,将契尾视为‘官样文章’,甚至只编取草契的内容,而将契尾搁置一边。” [26]此外,在出版中根据主题的需要,剥离那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也对契约完整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在契约的转录和出版过程中,契约所包含的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印章,也可能由于整理者的不同认知而被移除。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如在整理和出版中,对于契约包含的印章、符号信息,不做完整转录,或者仅做简单说明。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契约中的符号、印章及其展现的版式、书写格式是理解契约内容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无关全局的信息,可能正是解读契约关键信息的重要证据。如徽州文书的整理中,研究者充分应用印章的信息,还原契约年代缺失的遗憾。“文书上所钤官印,可帮助我们确定其所属朝代。” [27]在整理实践中,一些少数民族契约文书包含对于今天的整理者来说可能无法判断其真实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在整理、出版中,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被删节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契约的完整性。
3 遵循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和出版中的出路
3.1 通过有效方式保留明清契约文书的相关背景信息
根据来源原则的要求,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需要获得更多关键和有用的背景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并没有出现在契约的文本上,而是与契约的保存环境、保存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的整理者,为了补充契约保存过程的信息而开展相关工作,“一是对持契人及相关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的访谈。我们注意到,以往出版的契约文书对契约与持契人的关系及契约保存过程的记载是脱节的,或根本就没有后一部分内容。而吉昌纸契,其规模性凸显的事实提醒我们,在搜集契约文书的同时,记录下保存过程及相关背景。……另一方面,通过每一位持契人‘保存’经历的再现,发现其中的相似点,再比较与其他屯堡村寨的不同点,这对于解读屯堡社会深层的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屯田制度与其他子系统的结构关系、变迁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8]。吉昌契约文书的整理者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地收集了契约保存过程以及保存者有关契约来龙去脉的相关信息,弥补了契约文本无法直接展现的信息缺憾。通过收集这些保存者及保存过程的信息,多元、生动展现了契约的形态,为契约内容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和可能。
3.2 充分尊重明清契约文书原有面貌和整理体系
遵循来源原则也要求在明清契约文书的发现、整理中能够保持契约的原貌,不做过多的处理。在实践中,整理者在相关原则的指导下已经开展了许多探索,如《赣南民间文书》第一辑提到:“本辑文书的归户性与系统性强。除兴国县买契契税文书和上犹县寺下周氏文书不具归户性外,其他32户均具有归户性。32户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兴国县兴江乡南村张家地周氏文书,达520余份。这些文书中,有些文书原本就保存在契箱之中,有些还有包契纸,在整理的过程中,为了不打乱这些文书的顺序,同一包契纸内的文书放在一起排序。”[29]
遵循来源原则也要求整理者尽量保持文书已有的整理体系,这一点前文已略有提及。从大量的成果来看,明清契约文书确有许多在发现之前就经过一定的整理,而且这种整理体系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用明晰的文字进行记录并展现出来。清水江契约文书的整理者张应强对此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分析,其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我们接触到的民间文书多为经过分类、折叠扎包悉心收藏,而在后来进行分类收藏的过程中,对一些类型的每件文书的特定位置或标注了提示性文字甚或添加了清验时间等; 在不同的乡民家中看到的文书,或许有不同的分类方式,甚或这些分类也看不出其中包含的一以贯之的标准或规律,但我们坚持在初步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保持文书原状及原有分类,以保护被分为同类的所有文书可能的内在关系不被打乱。” [30]此外,一些研究者也提到:“例如有些徽州文书,它是由同一类纸包(包纸)包在一起,比如田契,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但在一个纸包或是箱子里。如果将其拆开重组,用之前的归户依据整理,可能会破坏文书资料原来的归户性。” [31]
3.3 对明清契约文书来源信息进行全面考订和补充
遵循来源原则也要求在契约的整理中尽最大可能全面考订契约文书,通过不同的渠道补充契约中未曾记录的信息。这些做法大大弥补了契约文本的局限,可以为生动地解释契约背后的各种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背景提供保障。
遵循来源原则也要求契约的整理者在无关联中寻找各种关联,为还原契约的历史面貌而不懈努力。如天海斋的收藏者,坚持对收藏的契约文书进行科学研究,弥补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契约被分散、割裂的缺憾。“在收藏过程中,契约文书的品相虽有良莠,但知其可修复,且深感片纸只字皆有历史信息,不可随意散逸,更不可人为拆分归并。凡有幸经眼的福建家族契约文书,尽可能原汁原味的完整结缘入藏。期间在不同时间、不同来源收藏到同一家族不同房支的契约文书,或收藏到同一村不同家族的契约文书,不断缀合历史信息的过程,是为一乐,亦感保护文化遗存之意义。”[32] 又如《赣南民间文书》的整理者,面对契约文书信息不足的情况,充分利用“地图、地方志、地名志,结合田野调查,针对文书中所涉及地名进行一一考证,还原文书生产和使用的地理空间,达到归户目的”[33]。
4 结 语
在明清契约文书的形成与保存过程中,契约文书的形成者、持有者、管理者就已经坚持将具有同一来源的契约文书有机地排列在一起,不破坏契约的原有联系,这一思想应该来源悠久,不是短期内出现的。只不过这些契约整理思想在中国漫长的档案管理实践中并未得到古代档案管理者明确的记载,或者由于史料的缺失而语焉不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的档案理论界在关注来源原则时未能将之与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尤其是古代档案分类整理实践进行比较。今天我们强调建立自主中国档案学科体系和学科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藏,是不可估量的源泉,值得进行深入挖掘。
作者贡献说明
赵辉:论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资料查找、撰写、引文校对;钟文荣:全文的构思,论文第三部分撰写及全文统稿。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0]徐国利.关于民间文书“归户性”整理的理论初探[J].安徽史学,2015(6):12,12-16.
[2][15]冯学伟.契约文书的归户性研究方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6):97,102.
[3]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序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
[4][13]冯惠玲.档案学概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219.
[5]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王钰欣.徽州文书类目·目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0.
[7][8]张晓峰,周伟.徽州文书分类整理要点和疑难解析[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8(2):59,58-59.
[9]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一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0][17][22]严桂夫,王国健.徽州文书档案[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59,24,11.
[11]曹树基,潘星辉,阙隆兴.石仓契约(第一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2]吕燕平.大屯契约文书汇编[M].贵阳:孔学堂书局,2020.
[14]刘伯山.徽州文书的遗存及特点 [J].历史档案,2004(1):125-126.
[16]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760.
[18]章均立.慈溪契约文书[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8:2.
[19]龙泽江.清水江文书整理的分类标准探析[J].兰台世界,2012(14):5.
[21]冯学伟,王志民.福建洋坑许氏文书·内容简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3][24]田涛.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1:4,1.
[25]张新杰.清水江文书整理的语言学分类标准探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3):54.
[26]安介生,李钟.清代乾隆晋中田契“契尾”释例 [J].清史研究,2010(1):107.
[27]王钰欣.徽州文书类目·前言[M].合肥:黄山书社,2000:7.
[28]孙兆霞.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前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
[29][33]朱忠飞,温春香.赣南民间文书·前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
[30]张应强.方法与路径: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实践与反思[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1):39.
[31]黄伟.方志编纂视域下的清水江文书整理新路径[J].上海地方志,2023(4):15.
[32]王涛.天海斋藏福建家族契约文书(第一辑)·前言[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2.
(责任编辑:孙 洁 陈 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