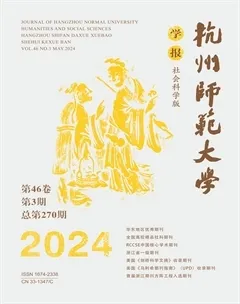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认定:条件、标准与限度
摘 要:制定程序是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要件之一。在附带审查制度中,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首先应该满足附带审查诉讼系属成立这一客观条件,具体表现为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两个方面。基于附带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当事人诉讼程序权利的保障,以及诉讼效率与主动审查能力的限制等缘由,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也存在当事人诉讼理由处分的主观条件。区别于个体化的行政程序,群体性、政策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具有一定的克制性,因此“正当程序”不宜作为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标准。“严重违反制定程序”认定标准,是一个兼容形式与实质审查的审慎标准。在适用的内在逻辑上,包括程序“范围”上的有限审查与“程度”上的实质审查两个方面;在构成的影响因素上,需要综合考虑制定程序的价值功能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两个方面。制定程序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化之间的勾连关系,既产生了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正当性问题,也形成了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豁免即限度问题。“法律效力”“实体权益”与“合理事由”是制定程序违法认定限度的具体判别基准。
关键词: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有限审查;实质审查
中图分类号:D925.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4)03-00113-12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4.03.011
一、问题的提出
“安徽华源医药公司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行政纠纷案”(简称“华源案”)①系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以来的首个司法案例,自公布之日起,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该案中,法院围绕争议行政规范性文件《关于申请注册新增零售或批发服务商标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新增服务的通知》”)第四条有关过渡期的规定是否违法,创设性地提出了“主体”“权限”“内容”与“程序”四项认定要件。针对该案件,在学理上除了内容要件上的违法认定存在争议之外②,有关程序要件的违法认定,也备受争议。比如,在法院要不要进行程序审查这一问题上,有学者就提出了否定意见。 如王春业教授认为,程序审查,与法院自身功能不相适应,也将使得法院承担了更大的政治风险,应采取以内容审查为主、其他审查为辅的审查原则。参见王春业《从全国首案看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徐肖东博士则认为,程序只适合评价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不宜成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要件。法院如果认定制定程序违法,“那么法院是判定其违法,而不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显然这在很多情况下会得出‘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行政行为违法’的假命题!”参见徐肖东《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认知及其实现机制——以陈爱华案与华源公司案为主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
不过,201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简称“《行诉法适用解释》”)的出台,否定了此种观点。《行诉法适用解释》第148条不仅明确规定法院可以依据“违反法定程序”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性,而且还进一步细化了违法认定的内容与标准。 《行诉法适用解释》第148条第1款规定:“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四)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公开发布程序,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
事实上,“华源案”还隐含了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相关的其他议题。这些议题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同样引起了理论与实践的认知冲突。
首先,制定程序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要件之一,法院有无主动、全面审查的义务?在“华源案”中,法院系根据原告的附带审查申请,对《新增服务的通知》开启合法性审查(依申请审查)。但在具体审查过程中,法院并没有受限于原告提出的违法主张(主体、权限与内容违法),而是独立地提出了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四项要件:“主体”“权限”“内容”与“程序”。然而,当原告提出对《新增服务的通知》制定程序的合法性不持异议时,法院径直回避了程序审查。 一审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是如此表述:“由于原告华源公司明确表示对于《新增服务商标的通知》的制定程序的合法性不持异议,因此,对《新增服务商标的通知》第四条关于过渡期的规定是否合法的审查重点在于:商标局是否是制定……的合法主体、商标局制定……是否超越法定权限……关于过渡期的规定在内容上是否合法。”二审法院虽然未对制定程序予以阐释和回应,但在结果上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认定。“华源案”显然表明,在附带审查过程中,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法院也需要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即法院只需审查原、被告之间的争议部分,无需进行全面审查。[1]但是,有观点持反对意见。其认为,法院的审查应当主动、全面,“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限制”;“不仅要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法冲突,还应审查该文件的制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现实有效” 参见黄学贤《行政诉讼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探讨》,《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亦可参见“王乐宝与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行终77号行政判决书。。
其次,制定程序作为行政程序的一种类型,法院是否也可以依据“正当程序原则”,直接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在“华源案”中,法院虽然最终没有进行程序审查,但是附带性地提出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二重标准:“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或者遵循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华源案”的审理法官采用与行政行为一样的程序违法认定标准。这种观点也获得了学理上的回应,如有学者指出,“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中,有一系列的顺序、步骤、方法、时限的程序要求,尽管具体文件的制定程序有所差别,但应遵循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要求”[2](P.44)。但是,也有观点表示反对。其认为,“自然公正原则虽然在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方面作出一些限制,但并不适用于委任立法”;“在法律法规未规定、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简阳市人民政府未组织听证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故,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支持”。 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袁志芬与简阳市人民政府案”,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20行终31号行政判决书。亦可参见“陶淑华与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行终203号行政判决书;“胡爱玲与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122号行政判决书等。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明确提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监督管理”,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5号),也均将制定程序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基本要件。因此,如何从学理上阐释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有关的条件、标准,并进一步分析由此引发的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限度等,已经成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过程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条件
从“主体”“权限”“内容”与“程序”四项要件的提出,到基于当事人对制定程序的合法性不持异议,而将审查对象聚焦在当事人争议的其他要件上,“华源案”事实上提出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条件。
(一)客观条件: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诉讼系属的成立
不同于备案审查,在附带审查过程中,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一个方面,无论是依申请被动审查还是依职权主动审查,还是当事人对制定程序是否持有争议,法院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性,在客观上,首先必须存在一个适法的诉讼。即形成一个管辖法院审理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的诉讼系属。诉讼系属,体现的是法院对特定案件进行审理的一种状态。[3]一旦案件被提起而产生诉讼系属,一方面,将发生管辖、当事人、诉讼标的恒定与禁止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法律效果[4];另一方面,法院也必须对原告通过“诉”所表达的保护权利要求做出应答[5](P.170)。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所规定的“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一并请求”的审查要求,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诉讼系属的成立,应该满足两个条件: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
行政行为可诉,以及原告有权且仅有权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是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诉讼系属成立的首要前提。行政行为诉讼不成立,或者原告单独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直接审查之诉,都无法产生附带审查诉讼系属。[6](P.146)在“高岭伟与石家庄正定新区管理委员会案” 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行初63号行政裁定书。中,法院就指出:“《征收公告》,只是把征收范围、征收补偿方式、安置区位置、现场办公地点等内容进行了告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对此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起诉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原告要求审查《正定新区宅基地及房屋征收实施意见(试行)》,因起诉的原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要求审查上述《实施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审查。”在“陈秀荣等与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案”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行终字第02538号行政裁定书。中,起诉人陈秀荣认为被告制作的《昌平区2015年平原地区造林工程拆除腾退实施方案》在制定程序和内容上均涉嫌违法,侵犯了起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该方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其理由在于:“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属于附带审查关系。本案中,起诉人直接申请撤销行政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法律规定。”
与此同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同样制约着附带审查诉讼系属的成立。我国《行政诉讼法》目前还没有全面放开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限,附带审查范围被限定在“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从文义上理解,超出这一范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原告将无法提出附带审查请求。在“郭慧敏与佛山市禅城区财政局案”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行初424号行政裁定书。中,法院就认定:“原告所请求行政诉讼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是党内文件,并不在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之内。”在“邹慧楠与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案”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行终1560号行政判决书。中,法院更是直接指出:“本案不涉及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天津市人社局无需向法庭提交386号文件制定程序的相关材料。”除此之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还意味着,法院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依据”关系,无论这种“依据”是部分“依据”还是全部“依据”。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行终1273号行政判书。而“依据”所表达的深层次要求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得到行政机关适用,并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行初671号行政判决书;周乐军、周佑勇《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识别基准——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在“林碧兰与宁乡县国土资源局案”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行终568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向法院提出附带审查但被驳回,法院认为:“因宁乡县国土局回龙铺管理所在答复中并未直接引用上述条款作为答复结论的依据,答复中虽然体现了两个规划性文件,但并非作为据以作出结论的依据,对答复结论没有实际影响,因此该请求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应当审查的条件,该院不予审查。”
(二)主观条件: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诉讼理由的处分
当行政规范性文件进入附带审查诉讼系属,法院是否必然要进行程序审查?
1.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启动的实证状况
考察司法实例发现,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违法认定的启动实践,状况较为分散,甚至存有矛盾。
首先,法院遵循对抗式诉讼结构,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争议为前提,确定是否进行程序审查。在“佛山市新村经济合作社与荷城街道办事处案”参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行初286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以“明府办〔2019〕31号文亦存在制定程序违法以及条文内容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情况”为由提出附带审查,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请与被告的抗辩,将制定程序单列为一项“争议焦点”,予以审查。
但也有相反情况,即便原告向法院直接提出制定程序违法、被告提出制定程序合法的主张,有的法院仍会回避程序审查。在“黄连好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人民政府案”参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粤71行终2299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就直接提出了“穗南开管办〔2013〕8号、穗南开管办〔2013〕9号文件制定过程中未征求公众意见,制定程序违法”的主张,但法院仅认为:“该规定没有与上位法直接冲突,亦无超越上位法已规定的事项范围、处理方式的种类和幅度等内容”,未进行程序审查。
其次,法院未遵循对抗式诉讼结构,在原告并未提出制定程序违法主张的情况下,主动进行审查。在“番禺南英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案”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行终1635号行政裁定书。中,原告向法院申请对穗府办〔2010〕35号文件相关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且仅主张内容违法。法院依据《行诉法适用解释》第148条的规定,对制定程序也进行了审查。
但也有相反情况,在“祝志辉与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东湖大队案”参见南昌铁路运输法院(2019)赣7101行初876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没有提出制定程序违法的主张,法院根据《行诉法适用解释》第148条的规定,认为制定程序是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基本要件。然而,在审查过程中,法院最终只是作出了“与道交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上述规定不相抵触。据此,足以判断南昌管理通告的合法性”的实体审查结论,对制定程序未予以回应和阐释。
2.当事人诉讼理由的处分与制定程序的违法认定
如果说法院规避原告的诉请,在审查过程中未回应或说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性,难以符合诉讼的基本要求;那么,要求法院严格按照“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四要件进行全面审查,虽然可以一次性确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却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本文认为,从附带审查制度的定位来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宜根据原告的诉请来确定,而将法院的主动与全面审查,确定为一项“努力义务”。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由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功能所决定。当下,我国设立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主要目的在于“适用”而非“撤销”。即“通过原告的‘一并请求’权的赋予,启动了人民法院针对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向其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从而实现了依托行政诉讼制度,激活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效力审查以及作出相应处理的原有机制,但并非形成了一个新的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机制”[7](P.170)。《行政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合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法院不能“撤销”,无需在判决主文部分确认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只是决定是否“适用”。
其次,有利于保障当事人正当的诉讼程序权利。随着行政诉讼标的识别从“一体化”向“相对化”转变,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程序权利,“行政行为个别违法性说”逐渐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行政诉讼标的识别标准。 参见梁君瑜《论行政诉讼中的重复起诉》,《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陈鹏《行政诉讼标的的相对化识别——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阐释》,《法学家》,2023年第4期。与“整体违法性说”不同,“个别违法性说”主张,当事人在后诉中仍然可以争议前诉未曾判断过或者主张过的违法事由。因此,在行政撤销诉讼中,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主要由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决定。[8](P.342)从《行诉法适用解释》第68条关于“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属于“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可以看出,制定程序违法一般仅作为原告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一个诉讼理由。如果法院负有全面审查的职责,基于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的“争点效”之约束,将会产生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重复审查禁止的效果。[9]此时,原告无法在后诉中再次提出附带审查请求,法院也不能再次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最后,受诉讼效率和主动审查能力的限制。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将以往的“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改为“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新增“解决行政争议”;删除“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中的“维护”仅保留“监督”。其中,将“正确、及时”改为“公正、及时”,意味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需要兼顾公正和效率”[10](P.5);而争议的存在是启动诉讼程序的动因,解决争议是法院的根本任务,公正、及时审理案件最终要落实到解决争议[11](P.3)。然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繁琐、涉及对象群体广泛,程序审查需要对大量事实证据进行调查与举证,这需要制定机关的实质性参与。如果实行无差别化的主动与全面审查,法院难以保障诉讼效率和解决行政争议。
总之,基于附带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及诉讼效率与主动审查能力的限制等因素,当行政规范性文件进入附带审查诉讼系属,如果当事人对未主张制定程序违法或者对制定程序的合法性不持有异议,法院可以不予以审查。抑或者可以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也存在当事人诉讼理由处分的主观条件。
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标准
当程序表现为一系列的顺序、步骤与方式,违法认定标准的确定与选择,不仅决定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应履行程序义务的内容及其程度,也决定了法院对制定程序进行违法认定的权限及其边界。
(一)“正当程序”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标准的限制性
在我国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违法之“法”的判定,经由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已经成为一种通说。[12]如果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程序没有得到“实定法”的明确规定,法院也可基于司法能动主义立场,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审查行政程序的合法性。[13]因此,“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共同构成了行政程序违法认定的标准。然而,法院不宜依据“正当程序原则”直接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性。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正当程序原则”主要适用于个体化的权利主张。法院适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前提条件,源于个体权利发生现实的损害[14],这便与群体性的、政策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形成显著性的差异。作为“从‘在特定案件中决定私人人身权利的司法判决’中归纳出来的普遍规则”[15](P.72),“正当程序原则”其实是法院通过古老的自然正义,将保障人性尊严的内在价值,融贯于宪法规范之中,从而获得司法适用的正当性。
起源于英国自然正义的“正当程序原则”,最初主要包含两个基本规则: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排除偏见);人们的抗辩必须公正的听取(听取意见)。[16](P.95)历经发展,“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虽然从传统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由权,逐渐向“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就业”等社会权发生转变[17],但它仅针对个体化的权利主张,未有向群体性的行政立法领域发生扩张的趋势[18]。
其次,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认定具有克制性。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的是不特定多数对象,虽然制定过程也强调参与,但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是以促进权利保障为目的,凸显对人性尊严的保护;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则是以提升民主基础为目的,政治意义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法院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可以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能够满足最低限度的法治要求[19],但也会在“实定法”缺位的情况下,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了额外的程序要求。这对于具有政治意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来说,法院难以承担此种职责。
通过比较观察可知,“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中的限制性立场,目前也是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基本共识。比如,英国行政法就“并未承认一般性的或群体性的规则制定参与权利。除非咨询程序是制定法所要求的,否则法院通常并无热情去弥补这一缺陷”[20](PP.388-389);在德国,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要求同样仅限于“法定程序”[21](P.294)。
在美国,1915年“Bi-Metallic Investment Co.v.State Board of Equalization of Equalization”案 参见239 U.S.441 (1915)。的大法官霍姆斯就提出了“正当程序”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中的限制性原则。当美国丹佛市拒绝给予地产所有人听证机会而被认为违反了正当程序时,霍姆斯驳回了这一主张:“如果一项行为规则适用于多数人,那么要求每个人在制定它时都应该有直接的发言权是不切实际的。《联邦宪法》并未要求所有的公共法案都要通过市民会议或市民大会制定……如果政府要正常运转下去,在这类问题上的个人争论必须是有限的。”霍姆斯所提出的谦抑审查立场,在之后著名的“United State v.Florida East Coast Ry” 参见410 U.S.224 (1973)。与“Vermont Yankee Nuclera Power Corp.v.NRDC” 参见435 U.S.519 (1978)。等案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确立与发展。“United State v.Florida East Coast Ry”案因听证“形式”而产生。“United State v.Florida East Coast Ry”案认为,既然法律授予州际商业委员会应在“举行听证”后发布规则,那么该委员会如果仅进行书面评议而没有履行提供口头提交证据和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程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驳回了这一主张。他们认为,“经听证”与《行政程序法》第553条(c)款所规定“经听证后基于纪录”之间具有明显区别,如果法律在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时未明确规定要履行“经听证后基于纪录”程序,那么法院便不能直接将这种程序要求强加于行政机关。“Vermont Yankee Nuclera Power Corp.v.NRDC”案同样涉及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是否可以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高于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一次予以了否定:“法院不能向行政机关强加自己认为是‘最好’的程序要求”,“即使除了《行政程序法》之外,本法院四十多年来一直强调,程序规则的制定基本上应由国会赋予具有实质性审查责任的行政机关自行决定。该原则是国会授权的结果,因为相比于法院或国会本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熟悉他们所管理的行业,他们更适合设计适合该行业特点和行政机关任务的程序规则。”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严重违反制定程序”认定标准
根据2018年《行诉法适用解释》第148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公开发布程序,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构成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因此,“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成为一个专门适用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标准。
1.“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标准的适用逻辑
对于该标准的适用逻辑,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范围上来看,“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标准包含着有限审查的基本立场。“严重”本身就具有范围上的限缩。即,并非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的任何程序与制定过程中出现的任何程序瑕疵,都会构成制定程序违法。在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有着非常严苛与全面的程序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制发,重要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严格执行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决定、向社会公开发布等程序。”但并非违反这些要求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就一概违法或无效,法院需要根据程序类型作进一步区分,有的程序是强制性的、有的程序则是指导性的。[22]比如,在“远安县洋坪镇兴达砂石料厂与远安县水利局案”参见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5行终75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备正式的文号和形式,制定程序违法。但法院认为,文号和形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而言并不是强制性的程序——“其本身存在的形式问题并不影响规范性文件本身的效力,即使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也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标准”。
其次,从“程度”上来看,“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标准也包含着实质审查的基本立场。“严重”本身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的裁量词汇,与“轻微”或“一般瑕疵”相对应。即,行政机关不仅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且相应程序的履行还要“充分”。如果程序履行不够“充分”,存在“形式化”与“走过场”等严重瑕疵,导致程序履行不具有实际效果,同样可能构成“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比如,在“王传龙等与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案”参见济南铁路运输法院(2020)鲁7101行初23号行政判决书。中,被告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主张行政规范性文件已经在政府网站上予以公布,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认为:“该现代传媒公告方式虽并不明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但对于相对封闭的农村而言,传统的张贴公告方式仍具有积极意义,行政机关在使用现代传媒方式进行公告的同时,应继续采用张贴方式予以公告,以便于那些尚不习惯于接受现代传媒方式的极少数被征收人知晓公告内容。”
2.“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标准构成的影响因素
“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标准的构成,还需要进一步考量制定程序的价值功能与行政规范性文件自身的法律地位。
首先,制定程序的价值功能。哪些程序是强制性的、哪些程序是指导性的,其程序重要性的判断,与程序所承担的功能息息相关。法国学者对此就强调,对程序重要性的判断,不仅要看它们的来源,是规章条例、法律还是普遍原则,而且要看它们的实际功效。[23](P.808)根据价值目的的不同,有学者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区分为作为过程的程序和作为装置的程序两大类。前者主要由规划、起草、审批和发布等流程环节组成,主要目的在于证明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与运作过程的科学合理性;后者主要由听证、公听会、立法理由说明等程序组成,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和调整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保障国民的民主参与。[24]其中,《行诉法适用解释》之所以明确规定“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公开发布程序”属于“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是因为“批准程序涉及规范性文件在行政机关内部的被认可性、权威性和慎重性以及行政机关本身的一致性。公开发布程序涉及规范性文件的正式性以及对外的效力性”[8](P.698)。但除了“批准、发布”等作为过程的程序之外,在作为装置的程序之中,以公众参与为核心所形成的立法草案公告、立法意见公开征求与评论、立法理由说明等程序,往往也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程序。因为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允许公众广泛参与,经由异议的提出与评论、理由的解释与说明等,不仅有利于强化公众的理解,也有助于消除行政规范性文件执行过程中的障碍,从而可以确保行政决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参见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郭庆珠《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正当性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第112—115页。
其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从实质法治的角度考量,不同法律属性、对公民权益影响不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所应履行的程序要求就不同。“规则制定是一种极其多元化的政府行为;没有一个系列的程序可适用于所有场合。”[25](P.79)一般说来,那些承担起行政立法功能、深刻影响公众权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严重违反制定程序”认定标准的适用强度,就要明显高于那些承担起细化执行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现实意义,以及未实质性创设权利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因此当行政机关在制定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政策的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公众参与”程序,就容易产生制定程序违法质疑——“事实上各方参与不够充分,参与的途径和参与的有效性都严重不足,这直接造成最终所选定的方案并没有表达公众的意见和诉求,使得该项决策的执行缺乏民意支持”[26]。但“若一项规则没有产生环境影响、未对较小团体造成重大影响……或者不涉及新搜集的信息,那么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就无需承担原本应履行的程序性义务”[25](P.78)。在“潘强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案”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2402号行政判书。中,当法院确认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目的在于解释法律、法令以具体应用”,“是为了解释商标法第四条的具体应用,与该法律规定衔接,以更好地发挥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利益,维护稳定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商标局并未增设新的权利义务,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对商标法的上述规定如何具体应用进行解释”,即便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仅履行了“公开发布”程序,法院也认为原告主张的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理由依据不足。
四、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限度
法院为什么要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性,既产生了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正当性问题,也形成了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豁免即限度问题。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程序豁免
法院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正当性,与程序在行政合法化中的作用息息相关。
从行政法的发展历程来看,按照“传送带”传统模式,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效力均由立法决定,行政程序没有独立的法律意义。相反,程序还被置于旨在“促进行政机关准确地、不偏不倚地、合理地适用立法指令于特定案件或各类案件”[27](P.8)的依附性地位。“传送带”模式,从宪制“结构”出发,严格区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能权限,试图借助立法机关为行政权的取得、行使而设置的控权规则,来建构行政合法化基础。不过,“传送带”模式采用的职能权限划分控权方式,虽然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它无法有效应对无处不在的裁量。裁量,不仅意味着不同技术手段的选择,也意味着相互竞争社会价值的衡量,在处理裁量过程中,政治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多重职能”状态。[28](P.303)
之后发展出的“专门知识”理性模式,程序的独立地位得到承认。这种以“技艺”为导向的行政合法化模式主张,受过专门训练的行政官员在处理政策问题时,具有立法机关和法院所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但程序被认为是法院的专长。出于知识局限,法院不得不接受行政机关的实体判断,程序成为控制行政权的最后屏障。[29]“专门知识”理性模式采用的程序控权方式,使得制定程序成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化的关键因素。然而,事实上的结果是,在很多重要的决策领域中,大量程序资源的消耗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30]脱离了实体内容的程序控制,法院反复要求的程序义务最终只会让司法审查陷入程序“空转”。
直到一种专注于行政程序自身的“多元利益”参与模式,行政合法化危机才得到有效缓解。在吸取前两种模式经验基础之上,“多元利益”参与模式首先承认,行政裁量就是一个分配不同利益的政治过程,进而主张程序的本质是过程性和交涉性的,其实质是反思理性。[31](P.32)通过强调行政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实质性参与,实现程序与实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满足行政权行使的正当性需求。正如美国著名程序法专家马肖所言,如果行政决策与立法行为的宏观政治脱离过甚,以至于无法满足民主理想,那么,民主理想可能蕴涵于(至少是部分地蕴涵于)确保利益相关人参与行政决策形成过程的行政程序之中。同样,如果理性分析不宜于证明在相互竞争的价值之间作出选择的正当性,那么价值可能得以体现于多元主义的、讨价还价的行政管理方法之中[32](P.20)。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部的公众参与,可以基于大众民主而实现“行政自我合法化”[33](P.35)之外;通过内部的机关参与,也可以基于自我监管实现“担保行政合法性”[34]。譬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批准”程序,体现的是其他机关(尤其是上级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参与权能[35](P.337);“集体讨论”程序,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具体体现[36]。
由此可见,通过一种交互性的多元利益沟通方式,遵循外部公众参与程序的“行政自我合法化”与内部自我监管程序的“担保行政合法性”双重进路,在制定程序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产生了合法性勾连,这是一种基于行政程序自身而让行政规范性文件获得合法化的过程装置。然而,制定程序在与生俱来的资源和时间上的成本消耗,如果过度强调,将会严重限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大量听证会导致程序重复和时间拖延”;集体讨论程序的过度强调,也“会降低行政效率、纵容行政懒政”。参见Hamilton R. W. “Procedures for the Adoption of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 The Need for Procedural Innovation in 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 California Law Review,1972,60(5);关保英《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质疑》,《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对于那些不需要满足“行政自我合法化”或“担保行政合法性”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来说,无差别化的程序要求,既无必要也不可行,由此可产生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豁免。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豁免,是指在特定情况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可以免除程序要求,从而豁免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过程中的程序责难。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限度的判别基准
1.“法律效力”基准
程序设置,一般仅针对具有外部法律效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制定的内部规则,无需施加强制性的程序要求。如果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行政机关的自我负重,法院往往无权干涉。在“李士海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案”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行终384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主张《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基准》未履行《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所规定的程序要求,制定程序违法。但法院认为:“该文件系上海市公安局针对治安行政处罚过程中本市公安机关如何行使裁量权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并无法律规定要求此类规范性文件必须在发布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上诉人认为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不具有法律授权的行政内部规则,诸如解释基准或者裁量基准等各种解释性规范,无法直接产生外部拘束力,其制定以及相关的程序要求,应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在实践中,解释性规范因为具备确定法规范外延或设置构成要件的功能,虽然常常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但这种依据仅是起到一种媒介作用的间接依据,真正决定行政行为效力的是上位法规范而非解释性规范。[37]因此,行政机关在适用解释性规范的过程中,需要与上位法规范一道,共同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不能单独适用。[38]在德国,这种内部行政规则的制定被认为是“行政之家产”[39](P.220),“制定程序简单、迅速,原则上没有什么手续要求”[35](P.608)。在美国,其《行政程序法》第553节针对“涉及行政机关内部管理”的规则、“解释性规则”与“一般性政策声明”等,明确设置了“公告—评论”程序豁免的例外条款。理论上认为,“第553节关于例外程序的规定属于授权性质,行政机关并不负担必须适用例外程序的义务。行政机关对是否利用例外程序有自由裁量权”[40](P.273)。
2.“实体权益”基准
程序设置,一般也仅针对那些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制定的诸如程序性规则或技术操作指南等,同样可以免除程序要求。在“卢福旺与中山市城乡规划局案”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20行终89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主张《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制定程序违法,不能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但法院认为,该《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是一种“技术操作规程”,属于《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所规定的程序豁免范畴,由此否定了原告的诉讼主张。
“法律效力”与“实体权益”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般来说,按照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制定影响公民实体权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获得法律授权。因此,“法律效力”与“实体权益”往往共同成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基本要件。比如,《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但事实上,二者并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体两面,而分别属于不同面向。因为,“内容的普遍性不等于效力的普遍性”[41]。“法律效力”以法律授权为前提,“实体权益”则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内容上的一种事实状态。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与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均可能涉及同一对象;而不涉及“实体权益”的程序性规则同样可能产生约束力。[42](P.366)因此,行政规范性文件在立法性与非立法性上的区别,关键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效力,“正因为是基于议会立法授权制定的,所以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才可能具有那样的效力”[43](P.125)。换言之,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如果不具有影响相对人“实体权益”的内容,仅涉及一些程序性或技术性事项,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往往无需内部程序的合法性担保与外部程序的民主性加持,由此而可同样产生程序豁免。“程序性规则”与“解释性规则”一样,也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第553节明确规定可以程序豁免的范畴。
3.“合理事由”基准
“法律效力”与“实体权益”豁免基准,都是基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身而进行的判断,但除此之外,如果出现其他特别的“合理事由”,也可能产生程序豁免。
程序设置,如果严重抑制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功能的履行,尤其是明显阻碍公共利益的实现,那么程序履行的必要性,就需要得到慎重考虑。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通过明确上位法模糊的法律概念、细化上位法宽泛的裁量空间,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还有助于确保行政公平、规范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对此,戴维斯教授很早便提出,“与敦促立法机关公布更有意义的标准相比,限定过度裁量权更有价值的方法是较早且较频繁地运用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权”[44](P.60)。但是,在面对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如果施加过于机械化的程序要求,可能会产生“立法僵化”,最终迫使行政机关不得不放弃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转而寻找其他替代的、较少参与的监管方式,以规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日益僵化的程序构造。[45]通过“合理事由”设置程序豁免的例外条款,是有效缓解行政规范性文件与行政灵活性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方式。
维护“公共利益”,是程序豁免最为凸显的“合理事由”。其中,诸如为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等,都属于“合理事由”的具体表现。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当需要行政人员对缓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迅速做出反应时,公告可能会产生旷日持久的参与。但有必要反复重申,只要不准参与不仅不过分,而且真正在公共利益范围之内,例外似乎并不违背民主原则”[46](P.283)。在我国,为突出这类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避免繁琐程序带来不必要的迟延,《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2019年修订版)直接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排除在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范畴之外。而像《湖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79号)〕等地方政府规章则明确规定,如出现“为预防、应对和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或“为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紧急命令和决定”等紧急情形,需要立即制定或施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经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简化程序要求。除此之外,如果制定程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而言,具有显著的“非现实性”与“非必要性”,也可能会成为制定程序豁免的“合理事由”。根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的一份解释报告,“非现实性”主要是指,公开化的程序要求,会不可避免地阻碍行政机关职能的履行;“非必要性”主要是指,某些事项影响甚小,对公众而言并不需要获得知晓及参与,比如仅涉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轻微修正。[47]在审查实践中,美国实务部门又进一步予以细化,除了“紧急情况”之外,如具备“事先的通知会破坏法定计划”或“程序豁免本是国会意图”等,也可以作为支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豁免的“合理事由”。[48]
五、结语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认定,“华源案”以及其他司法案例所折射出的复杂形态,既体现了附带审查制度的特殊性,也体现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多重性。以“适用”为导向的附带审查,为了实现保护当事人诉讼程序权利、保障诉讼效率与解决行政争议等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除了需要满足附带审查诉讼系属成立的客观条件之外,也存在当事人诉讼理由处分的主观条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对象具有一般性,加之政治与政策因素的加持,制定程序的违法认定具有克制性。因此法院不宜通过“正当程序”标准,额外增加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要求。“严重违反制定程序”标准,是一个兼容形式与实质审查的审慎标准。它既涉及制定程序价值功能的判断,也涉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地位的考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认定也存在限度。在面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诸如内部规则、程序性与技术性规则,以及为维护公共利益或其他特殊情形等状况,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可以免于程序要求,从而产生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豁免。
参考文献:
[1] 朱芒:《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要件——首例附带性司法审查判决书评析》,《法学》,2016年第11期。
[2] 张浪:《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问题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修订的有关思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 包冰锋、耿换芬:《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系属理论之解读》,《民事程序法研究》,2011年第6辑。
[4] 刘学在:《略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系属》,《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5] 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7] 应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
[8]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
[9] 周乐军:《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重复审查”》,《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5期。
[10] 江必新:《新行政诉讼法专题讲座》,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11] 马怀德:《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12] 章剑生:《再论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2009—2018)》,《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
[13] 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14] Searchinger T.“The Procedural Due Process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The Courts’ Inverted Analysis.”The Yale Law Journal,1986,95(5).
[15] 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杨明成、陈霜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16] 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17] 杨登峰:《法无规定时正当程序原则之适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8] Victor Rosenblum.“Widening the Scope of Due Process.”Update on Law-Related Education,1981,5(1).
[19] 郑博涵:《检视与完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标准化路径研究》,《东南法学》,2017年第1期。
[20] 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卫东、李凌波、石红心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1] 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拖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2] 何海波:《论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23] 让·里韦罗、让·瓦利纳:《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24] 朱芒:《行政立法程序基本问题试析》,《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25] 科尼利厄斯·M·克温:《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刘璟、张辉、丁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 杨尚东:《行政决策合法性追问的个案解读——以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的行政决策为分析样本》,《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7期。
[27] 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28] 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9] Shapiro S. A., Levy R. E. “Heightened Scrutiny of the Fourth Branch: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Requirement of Adequate Reasons for Agency Decisions.”Duke Law Journal,1987(3).
[30] Pierce, Richard, J. “The Choice between Adjudicating and Rulemaking for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Energy Policy.”Hastings Law Journal,1979,31(1).
[31]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
[32] 杰瑞·L.马肖:《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33] 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与制度分析的框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
[34] 章剑生:《作为担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内部行政法》,《法学家》,2018年第6期。
[35] 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36] 叶必丰:《集体讨论制度从组织法到行为法的发展》,《法学》,2022年第6期。
[37] 朱芒:《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功能结构》,《法学家》,2023年第6期。
[38] 周佑勇、周乐军:《论裁量基准效力的相对性及其选择适用》,《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39] 汤德宗:《论行政立法之监督——“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章起草构想》,汤德宗:《行政程序法论》,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40]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41] 黄宇骁:《也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
[42] 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苏苗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43] 平冈久:《行政立法与行政基准》,宇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44] 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毕洪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45] McGarity T. O. “Some Thoughts on ‘Deossifying’ the Rulemaking Process.”Duke Law Journal,1992,41(6).
[46] 沃伦:《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王丛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47] Kim J.“For a Good Cause: Reforming the Good Cause Exception to Notice and Comment Rulemaking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George Mason Law Review, 2011,18(4).
[48] Kevin Hartnett Jr.“An Approach to Improving Judicial Review of the APA's ‘Good Cause’ Exception to Notice-and-Comment Rulemaking.”Buffalo Law Review,2020,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