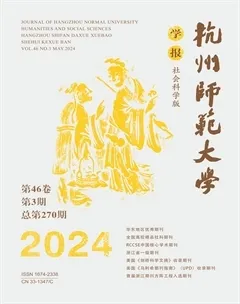永恒还是永续:由王船山的宇宙观说起
摘 要:宇宙论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而宇宙观是宇宙论的基础部分。王船山对于宇宙观有高度的自觉。他通过反思已有的宇宙观,提出自己的宇宙观。在他看来,老子、《易纬》、邵雍的宇宙观实质是“天地有始说”,而“天地有始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其认为天地有“始”“终”。通过对天地无“始”“终”的论证,王船山确立了自己的“天地无始说”的宇宙观。对于王船山的宇宙观,若以时、空为视角,可以推知其非“永恒”的宇宙观,乃“永续”的宇宙观,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宇宙观亦为“永续”的宇宙观。这样的分析凸显了王船山乃至整个儒家宇宙观的特点,有利于把握王船山哲学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特质。
关键词:王船山;时空;永恒;永续;宇宙观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4)03-0012-09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4.03.002
就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讲,“宇宙论”是必要的部分,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或“舞台”。那么,何为“宇宙”呢?《尸子》论及“宇”“宙”之义如下:“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1](P.27)“宇”表示空间义,“宙”表示时间义;两义合在一起即为“宇宙”概念,时间和空间是“宇宙”概念的关键词。与“宇宙”相关的一个汉语概念是“世界”,“世”为时间义,“界”为空间义;“世”对应“宙”,“界”对应“宇”,故“宇宙”与“世界”为大致相同的概念。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汉语概念是“天地”,在究极的意义上,“天地”与“宇宙”“世界”为同指。关于“宇宙论”何指,冯友兰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Cosmology)(狭义的)。”[2](P.3)其实,“宇宙论”的内容还有层次之别,基础部分称“宇宙观”,指对宇宙的总的根本的观点。从哲学史来看,哲学家的宇宙观并不相同,造成不同的重要原因是对时、空的理解有异。
尽管“宇宙论”“宇宙观”两个概念译自西方哲学,但是相关思想为中国哲学所固有。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儒学,还是道学、佛学,相关探讨均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容。就儒家来讲,明末清初王船山的相关思想颇具代表性。
一、天地有始说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反思”而“建构”。[3](《前言》,PP.1-3)同样,他的宇宙观也是通过反思以往宇宙论而确立的。王船山关于以往宇宙论的反思对象为老子、《易纬》和邵雍三者的宇宙论。
老子是中国学术史中宇宙论的开创者,他以“道”为本原建构起中国最早的宇宙论。老子宇宙论的实质是“道生万物说”:“道”先天地生,它包含“阴”“阳”二气,二气相合化生万物;万物亦包含“阴”“阳”二气,它们相互交汇、激荡,形成多样却谐和的世界图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PP.174-175)那么,何为“道”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4](PP.100-101)“道”乃“混成”,虽创生天地万物,为天地万物本原,却无形无象、无姓无名,勉强称其名为“道”。对于这样一种宇宙论,张岱年认为,因老子始“乃有系统的宇宙论”,故之前为中国的“先宇宙论时期”。“最根本的乃是道,道先天地而有,乃在上帝之先。道更非谁之子,而是一切之究竟原始,道才是最先的。……老子是中国宇宙论之创始者。以天为最高主宰的观念打破后,宇宙哲学乃正式成立。……老子以前,可以说是先宇宙论时期。自老子始,乃有系统的宇宙论学说。”[5](PP.4-5)因为老子宇宙论的这种开创地位,王船山不可能回避它。
《易纬》根据《易传》和《老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论。《易传》有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6](P.289)《易传》这段话虽是讲筮法过程,但其中透显出宇宙论思想。《易纬》则将其所透显的宇宙论凸显出来。首先,“易”作为本体,分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层,宇宙演化相应地分为四个阶段:“太易”时还未有“气”;“太初”时“气”初生;“太始”时形象初显;“太素”时形已具“质”;经过四个阶段以后,“乾”“坤”和“天”“地”便得以形成,从而开启了万物生化过程。[7](PP.81-82)其次,万物生化过程为:“易”或“太极”作为本体,化生天地、四时、八卦、万物,展现为一幅宇宙演化生成图景,此乃“易之德”。其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7](PP.79-80)
邵雍作为道学的奠立者之一,创建了系统的宇宙论。其宇宙论的重要特点是,明确地讲明宇宙及万物均有“元”,而“元”即“始”,故而称“元有二”——“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太极也;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8](P.1240)宇宙之始源自“太极”,万物之始源自“生”即化生。首先,“太极”为天地(宇宙)本原,天地源自“太极”。具体来讲,“太极”寂然不动,但有“动”“静”之能;“动”“静”发动,“天”“地”产生。其次,万物源自“太极”之演化。具体来讲,“天”分“阴”“阳”,“地”分“柔”“刚”;“阴”“阳”“柔”“刚”为“四象”,“四象”交错变化遂生万物。邵雍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8](PP.1238-1239)
王船山研究了上述三种宇宙论,但并不赞同其思想,还逐一进行了批驳。
关于老子的宇宙论,王船山深不以为然,其理由有二。其一,“道”非“混成”。老子所谓“混成”,只说明了“道”的存在状态,而未揭明“道”之“妙”,即“道”之为道的“所以然”——“一阴一阳之谓道”。他说:“若夫‘混成’之云,见其合而不知其合之妙也。故曰‘无极而太极’,无极而必太极矣。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各有其时,一动一静,各有其纪,如是者乃谓之道。”[9](P.823)其二,“道”非先天地生。“道”就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之另一物。假如说“道”“先天地生”,意味着“有道而无天地之日”,那么此时“道”存在于何处呢?显然,这当中存在逻辑错误。“使先天地以生,则有有道而无天地之日矣,彼何寓哉?而谁得字之曰道?天地之成男女者,日行于人之中而以良能起变化,非碧霄黄垆,取给而来贶之,奚况于道之与天地,且先立而旋造之乎?”[9](P.823)“碧霄”指蓝天,“黄垆”指黄泉,“贶”为赠、赐。基于两点理由,王船山认为老子的宇宙论不可信。“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今曰‘道使天地然’,是先天地而有道矣;‘不偏而成’,是混成矣。然则老子之言信乎?……非也。道者天地精粹之用,与天地并行而未有先后者也。”[9](PP.822-823)
王船山亦反对《易纬》的宇宙论,其理由也有两个方面。其一,《易纬》以“太极”先在于“阴阳”,割裂了“太极”与“阴阳”,而“太极”与“阴阳”实不可分,因为“太极”就在“阴阳”之中,它通过“阴阳”以呈显。“太极”在“阴阳”之中,与“道”在天地万物之中是同一道理。他说:“哀哉!其日习于太极而不察也!……使阴阳未有之先而有太极,是材不夙庀,而情无适主;使仪象既有之后遂非太极,是材穷于一用,而情尽于一往矣。又何以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也乎?……故曰‘太极有于《易》以有《易》’,不相为离之谓也。”[9](PP.1024-1025)“庀”乃治理义。割裂“太极”与“阴阳”,无论从学理上讲,还是就《易》之原典讲,均为不确之论。其二,《易纬》“绌有以崇无”,落入佛、道异端之窠臼。王船山说:“《乾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危构四级于无形之先。……故不知其固有,则绌有以崇无;不知其同有,则奖无以治有。无不可崇,有不待治。……彼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纷纭者,虚为之名而亡实,亦何为者耶?……呜呼!毁《乾》《坤》以蔑《易》者,必此言夫!”[9](PP.1024-1025)这里,“绌”通“黜”,为废除义。王船山的意思是,“太易”“太始”“太初”“太素”均为“亡实”之“虚名”,《易纬》以“虚名”来治“有”,乃无稽之谈。实际上,“太极”乃“有”而非“无”,故《易纬》以“太易”“太始”“太初”“太素”这样四级“虚名”来解释“太极”乃“危构”——不仅不切实际,且对于《易经》“乾”“坤”之地位、作用造成毁灭性的诬蔑。
关于邵雍的宇宙论,王船山坚决反对其“元”“始”的主张。在他看来,邵雍所谓“元”“始”通过“开辟”之说以体现,而“开辟”之说实乃“有生于无”,故与佛、道异端之“邪说”无异。“邵子谓天开于子而无地,地辟于丑而无人,则无本而生,有待而灭,正与老、释之妄同,非《周易》之道也。”[10](P.277)邵雍以学《易》、阐《易》为宗旨,而王船山认为其违背“《周易》之道”,可见其批驳力度之大。其一,依《周易》,“太极”通过“阴”“阳”动物化生万物,“乾坤并建,以为大始,以为永成”[9](P.989),“太极”就在“阴”“阳”化生过程中,而非先于化生过程的另一物。“《易》在《乾》《坤》既建之后,动以相易。若阴阳未有之先,无象无体,而何所易耶?邵子‘画前有《易》’之说,将无自彼而来乎!”[9](P.42)若“太极”在“阴”“阳”之外,则其必为“无象无体”者,而“无象无体”者何以能化生万物呢?其二,邵雍所谓“开辟”之说不能证实,而不能证实者即“愚见”。“吾无无穷之耳目,不能征其虚实也。吾无以征之,不知为此说者之何以征之如是其确也!”[10](P.467)换言之,邵雍“开辟”之说的前提是“天地有始终”,其乃基于“小者”即对具体事物之观察而有;若基于“长者”即对整个天地万物之观察则不会得出这种观点。故,《易经》不以《坎》《离》两卦为首,而以《乾》《坤》两卦为首;不以《坤》为终,而以《未济》为终。“天地而无毁也。藉有毁天地之一日,岂复望其亥闭而子开,如邵子之说也哉!成之小者不足以始,故《易》首《乾》《坤》而不首《坎》《离》;毁之长者不可以终,故《易》终《未济》而不终《坤》。”[9](P.975)其三,邵雍的宇宙论以“天地有始终”为前提,“天地有始终”以肯认“先天”为预设,而这种“先天”的预设是错误的。王船山说:“邵子之学,详于言自然之运数,而略人事之调燮,其末流之弊,遂为术士射覆之资,要其源,则先天二字启之也。”[10](P.436)
在王船山看来,无论是老子、《易纬》,还是邵雍,其宇宙论均以“天地有始说”为特征。所谓“天地有始说”,是指认为天地有开端然后万物发生的观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既言“天地有始”,那么自然意味着“天地有终”,故所谓“天地有始说”之完整义乃“天地有始终说”。进而,“天地有始说”的实质有二:其一,天地万物本原为先在的独存物;其二,天地万物为“有”,天地万物本原为“无”。在王船山看来,这两点均为无端之臆测和无征之“愚论”。人们所能知者只是:宇宙时刻都在创生,时刻都在死亡,生和死乃无限过程。他说:“天地之终,不可得而测也。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终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见其始;其终也,人不见其终;其不见也,遂以为邃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将来之日,有万物皆尽之终;亦愚矣哉!”[9](P.979)质言之,“终”“始”均“不可得而测”,“臆测”天地之前有始、之后有终,此乃“天地有始说”的学理根源。
上述便是王船山对已有宇宙观的反思和批驳。那么,王船山何以批驳这些宇宙观呢?换言之,他持何种宇宙观呢?
二、天地无始说
在上述批驳当中,“天地有始说”乃王船山给三种宇宙观的定性,而“始”和“终”是其批驳“天地有始说”的两个关键词。关于这两个词的含义,《说文解字》释“始”为“女之初也”,意即初为女人;《说文解字》释“终”为“絿丝也”,意即把丝缠紧。 参见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60、273页。由此引申,“始”乃“起头”“最初”义,“终”乃“末了”“完了”义。王船山认为,所谓“始”和“终”,仅就具体事物言,或者说只有具体事物有“始”“终”问题。“万物各以其材量为受,遂因之以有终始。”[9](P.976)因为具体事物均须依条件存在,故其必然有“由无到有”之“始”、“由生到灭”之“终”的过程。就“始”讲,万物乃“阴”“阳”二气交葛互动而化生,此为“由无到有”;就“终”来讲,万物乃“阴”“阳”二气“几近于无”,此为“由生到灭”。王船山讲“始”“终”是就具体事物而言,他的言外之意是,尽管具体事物有“始”“终”,但“天地”却无“始”“终”。“事物有终始,心无终始。天之以冬终,以春始,以亥终,以子始,人谓之然尔;运行循环,天不自知终始也。”[10](P.306)从一年四季来看,春为“始”,冬为“终”,但春与冬却是循环不已的;从每天时辰来看,“子”为“始”,“亥”为“终”,但“子”与“亥”却是循环不已的;总之,从感性观察来讲,天地运行是循环不已的,无所谓“始”“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王船山所论“天地”,乃万物之总体即“万有”,实际上即指“宇宙”或“世界”。
除了通过对年之季节和天之时辰的感性观察,王船山还从义理上阐明天地何以无“始”“终”。其一,一物之终乃是它物之始,一物之始乃是它物之终。例如,曾子易箦[11](PP.186-187)即既“终”又“始”——曾子身体由“天”赋予,此为“始”;曾子之死虽可言为“终”,但其实乃其身体“归还”给“天”,故死亦可言“始”。其二,无论是“始”,还是“终”,它们均非刹那完成者,而是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始”和“终”均是逐渐完成的。关于这样两方面,王船山说:“凡自未有而有者皆谓之始,而其成也,则皆谓之终。既生以后,刻刻有所成,则刻刻有所终;刻刻有所生于未有,则刻刻有所始。故曰曾子易箦,亦始也,而非终也。反诸其所成之理,以原其所生之道,则全而生之者,必全而归之。”[12](P.754)其三,万物均由“气”所生成,而所谓“终”并非“气”之消失。“始无待以渐生,中无序以徐给,则终无耗以向消也。其耗以向消者或亦有之,则阴阳之纷错偶失其居,而气近于毁。此亦终日有之,终岁有之,终古有之,要非竟有否塞晦冥、倾坏不立之一日矣。”[9](P.976)在“终”之时,虽然“气”有损耗、减少,甚至“气近于毁”,但终非“倾坏不立”、绝对地无。因此,他反对董仲舒关于“冬至”无“阳”、“夏至”无“阴”之说。“谓十一月一阳生,冬至前一日无阳者,董仲舒之陋也。”[10](P.306)王船山还反对庄子关于“有始”“未始”、“有”“无”之论。庄子从时间、空间两个角度表达了相关思想——“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13](P.79)就时间来讲,如果“有始”,那么就会有“未始”之时,进而会有连“有始”“未始”都还没有的时候;就空间讲,如果存在“有”,那么就会有“无”,进而会有连“有”“无”都不存在的情况。在王船山看来,庄子之错误在于他认为“未始”“无”乃“无气”,实际上“未始”“无”亦非“无气”。“道家说‘有有者,有未始有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者’,到第三层,却脱了气,白平去安立寻觅。”[14](P.493)
王船山进而认为,所谓“天地之始”即“天地之终”,二者乃“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因为它们均源于“阴”“阳”彼此消长,而无终“卒于阴之理”。“天地之始,天地之终,一而已矣。特其阴中阳外,无初终乘权之盛,而阳之凝止于亢极以保万物之命者,正深藏以需后此之起。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于道,物必肖其所生。是道无有不生之德,亦无有卒于阴之理矣。”[9](P.953)具体来讲,“终”即是“始”,“始”即是“终”,所谓“天地之始”“天地之终”便无区别,故而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道无有不生之德”。质言之,天地乃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的无止境化育过程。正因如此,《周易》六十四卦当中“既济”后为“未济”,意指天地究竟是无始无终的。王船山说:“夫天,吾不知其何以终也?地,吾不知其何以始也?天地始者,其今日乎!天地终者,其今日乎!观之法象,有《乾》《坤》焉,则其始矣;察之物理,有《既济》《未济》焉,则其终矣。”[9](P.992)之所以言“乾”“坤”为始,只是从“象”的角度言之,而非从“理”的角度言之;若从“理”的角度言之,天地并无终始。基于此,王船山认为《易·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之论,与天地无有终始之“理”相悖,故非“圣人之书”而乃他人伪作。“抑无不生,无不有,而后可以为《乾》《坤》,天地不先,万物不后。而《序传》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则未有万物之前,先有天地,以留而以待也。是以知《序卦》非圣人之书也。” 参见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院,2011年,第1092页。不过,公允地讲,王船山对《序卦》的批评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序卦》在上述所引内容之后还有句话:“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两句合在一起足以表明,《序卦》并非持“天地有始说”。
综上所述,王船山以“始”“终”两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坚持所谓的“天地有始说”,以确立“天地无始说”。就王船山的宇宙论来讲,“天地无始说”乃其宇宙观,宇宙观是其宇宙论的基础部分。以这种宇宙观为基础,王船山展开了宇宙论。关于变化之始,“乾坤并建”“以为大始”。他反对“先乾后坤说”,主张“乾坤并建说”——“乾”“坤”在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分,在作用上没有主辅之别。“《乾》《坤》并建于上,时无先后,权无主辅,犹呼吸也,犹雷电也,犹两目视、两耳听,见闻同觉也。”[9](P.989)关于变化之情,“日新之化”乃“天地之德”。运动是永恒的,不仅“太虚者,本动者也”[9](P.1044),而且万物亦无有不动者,故“天地之化日新”。“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10](P.434)关于变化之源,“一阴一阳之谓道”。“动”乃造化之几——天地之所以“四时行”“百物生”,皆源于“动之一几”,而“动之一几”在于“阴”“阳”相互作用,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率由于一阴一阳之道以生万物,父母率行于一阴一阳之道以生子。”[14](P.324)
三、永恒与永续
虽言“始”“终”是王船山批驳“天地有始说”、确立“天地无始说”的关键词,但仅言这两个关键词并不能穷尽其宇宙观意蕴,因为这两个关键词的主语乃“宇宙”(世界、天地),故所谓“始”“终”之有无,乃就“宇宙”而言。本文开头引用《尸子》所言,表明“宇宙”概念以时、空为关键词。其实,宇宙观还有一个关键词——“万有”即万物之总体。这样,“时”“空”“万有”三者便构成“宇宙”概念的核心内容。不过,不同哲学家对三个核心内容及其关系的理解并不相似,故而形成不同的宇宙观。尽管如此,以时空为视角审视宇宙进而审视王船山的宇宙观是合理的。
讲到时空,则必有时空之内和超越时空两个面向,而不是仅时空之内一个面向。这个问题可从科学发展和宗教观念两个方面来看。
就科学发展来看,三种理论可为重要参考。其一,现代宇宙学最有影响的学说“宇宙大爆炸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宇宙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出现的。具体地讲,时间和空间一同出现于137亿—138亿年前的大爆炸。[15](P.88)其二,另一种宇宙学理论“多重宇宙论”。这个理论认为,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宇宙,各个宇宙之间都存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16](P.217)其三,“黑洞理论”。“黑洞”是宇宙的一个“奇点”;在这个“奇点”中,所有物质及其规律包括相应的时空都崩塌了。 参见卡西莫·斑比《广义相对论导论》,周孟磊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6—127页。所谓“物质及其规律包括相应的时空都崩塌了”,指物质及其规律包括原有的时空已不再有效了。总之,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表明,时空并没有穷尽宇宙,时空亦有其“始”“终”。
就宗教观念来看,三大世界性宗教均认为时空有其“始”“终”。如,基督教《圣经·创世记》认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所谓“神创造天地”,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创造时间;二是创造空间;三是创造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可见,时间和空间不是本有的,而是上帝所创造的;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亦为上帝所创造,天地万物都存在、生活在时空之中,以时空为存在、生活条件。[17](PP.1-2)同样,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亦有相似的“创世记”,亦认为时间和空间均非原有,而为真主所创造;人与其他动物均生活在时空当中,以时空为生存条件。[18](PP.254-255)再如,佛教虽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那般的“创世记”,但有关于世界(地球)起源的理论——“天”从下至上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三界共有二十八层天,其中“色界”的第三天为“光音天”,人所生存的世界(地球)产生于“光音天”。 参见梁踌继校注《增一阿含经》,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61、177、178、325页。可见,在佛教看来,时间、空间亦并非本有,而仅仅存在于“色界”之“光音天”;人类生活于“光音天”,以时间空间为生存条件。
当然,无论是现代科学理论,还是宗教观点,都是经验所无法证实的。然而,经验证实并非唯一的求知途径,而且经验往往不可靠,故不能通过经验获得真理。因此,不能依经验证实否定现代科学和宗教观念的可能性。既然现代科学和宗教观念具有可能性,那么它们关于时空的观点可为我们审视宇宙观提供一个新视角。由此来讲,依据传统的“有”并不能证伪“无”的存在,亦不能如王船山所言“无”为无稽之谈的“臆测”。质言之,“有”之外存在“无”,“无”是超越时空的另外一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不同于传统的时空之内的世界。再由此来讲,传统的“宇宙”“世界”概念外延亦应有变化——它不仅包括“有”,亦应包括“无”,为“有”“无”之两面的统一体;它不仅包括“万有”即天地万物之总体,还包括“万有”之外的与天地万物不同的“万无”。质言之,对《尸子》所谓“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1](P.27)的“宇宙”应予以重新理解,不能局限于原来的时空和“万有”之义。“宇宙”“世界”外延的扩大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它推动了人们对于“永恒”概念的反思。
以时间和空间为视角审视宇宙,必然涉及“永恒”概念。“永恒”是何义呢?“永”,《说文解字》释:“永,长也。象水巠理之长。”[19](P.240)“永”本义为人在水中向前游;“巠”同“经”,指水脉。可见,“永”为水脉长远之义。“恒”,《说文解字》释:“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19](P.286)“恒”乃永久义。“永”和“恒”合在一起为“永恒”,意为永远、恒久。由于“永”“恒”两义相近,故常以“恒”字代“永恒”一词,其义不变。
超越时空者称为“永恒”,在时空之内者称为“永续”。关于“永恒”和“永续”的含义和区分,余志民如下辨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相对于超越时空的永恒,在现世之中的永远延续则可称之为‘永续’。这种永续,不同于西方哲学着眼于永恒彼岸的构建,而注重在现世之中的历史传承。” 参见余志民《中西哲学略述》,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第31页。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余志民在此以“永续”笼统概括中国哲学,以“永恒”笼统概括西方哲学;这种说法实际上不确切,因为中国哲学中亦有主张“永恒”的流派,西方哲学中亦有主张“永续”的流派。因此,我们在此只是取其关于“永续”与“永恒”的观点,而不取其以“永续”与“永恒”来笼统概括中西哲学的观点。余志民以“超越时空”言“永恒”,以“现世之中的永远延续”言“永续”。另外,法国学者朱利安的观点也颇具参考价值。他区分了“永恒”与“恒常”,“恒常”即我们所谓的“永续”。他说:“我们须要从根本上区分出‘永恒’和‘恒常’。……两者皆表明持久性,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永恒的持久性依附于存有而成为沉思(theoria)的对象,而恒常的持久性则涉及了事物的运行,或者说,涉及了中国人所说的事物的‘运作’(用的观念)。永恒指向本质的‘同一性’;而恒常则属于‘〔自然的〕能力’的范畴(德的观念)……简言之,永恒存在于时间之外,恒常则是永不间断者。”参见朱利安《论“时间”:生活哲学的要素》,张君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17页。朱利安以“永恒”言西方文化,以“永续”(恒常)言中国文化,亦失于笼统,因为西方文化中亦有“永续”观念,中国文化中亦有“永恒”观念。我们在此只取其“永恒”“永续”观念,不取其笼统的地域性区分之说。朱利安虽然只言时间之内外,但从其言中可以推论空间亦有内外。总之,所谓“永恒”,若就时空来讲,它意指超越时空;若就天地万物之“万有”来讲,它可谓“万无”。“永续”何指呢?《说文解字》释为:“续,连也。……古文续从庚贝。”[19](P.272)“永”与“续”合在一起为“永续”,其义为永远、永久,特征为时空之内的永远、永久,而非超越时空的永远、永久。“永续”即余志民所言的“在现世之中的永远延续”,亦即朱利安所言的时空之内的“永不间断”。“永续”所标示的不是超越时空的“永恒”,而只是在时空之内的不间断。时间的不间断相对于人生来讲已足够久,空间的不间断相对于人来讲已足够大,故而产生了时空之内“永恒”的观念。但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并不是无限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个相对者和条件即作为天地万物之总体的“万有”,它未包含之外的“万无”;它只包含宇宙全部外延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基于上述所言,通常所谓的时空永恒只是“相对”的,即相对于人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而言;就这个世界而言,时空具有永恒性,一旦超出这个世界,它们便不具有永恒性。质言之,“相对”的时空不是真正的“永恒”,而只是时空之内的“永续”,其理论预设是所谓的“有”。
关于“恒”,《易经》专有“恒”卦,卦辞曰:“恒:亨,无咎,利贞。”[6](P.142)孔颖达正义曰:“恒,久也。”[6](P.142)关于“恒”之内涵,《彖传》以“四事”具体说明:其一,“刚上而柔下”;其二,“雷风相与”;其三,“巽而动”;其四,“刚柔皆应”。王弼注第一事为“刚尊柔卑,得其序也”;注第二事为“长阳长阴,能相成也”;注第三事为“动无违也”;注第四事为“不孤媲也”。[6](P.143)关于“恒”之呈显,《彖传》以三方面具体说明:其一,“日月久照”;其二,“四时久成”;其三,“圣人久于其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6](P.144)“四事”与三方面乃不可分之体用关系,它们的实质是“恒”。质言之,“恒”乃“天地万物之情”,而天地万物即“万有”处于时空之中,故,“恒”或“永恒”为时空意义中的永恒。
由此来讲,无论是《说文解字》对“永恒”词义的解释,还是《易经》“恒”卦的卦辞、孔颖达的正义、《彖传》的说明,均非超越时空的“永恒”,而乃时空之内的“永续”。质言之,其所谓“永恒”实指“永续”,即时空意义下的永远、永久。关于“永续”,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周易》第六十三卦“既济”与第六十四卦“未济”之序——“既济”指事物某一发展阶段已经完成,“未济”指事物之新一轮发展又开始了。《周易·序卦》云:“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6](P.339)很显然,“既济”与“未济”连在一起,意在强调具体事物发展变化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载体是具体事物,而具体事物以时空为存在条件,故这种周而复始必在时空之内。
四、天地无始说与儒家的宇宙观
依上述关于“永恒”“永续”的厘定而言,宇宙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永恒”的宇宙观;另一种是“永续”的宇宙观。相应地来看,前述老子、《易纬》、邵雍为代表的“天地有始说”属于前者,其以超越时空为特征,其宇宙包括“有”亦包括“无”,既包括“万有”,亦包括“万无”,为周全的宇宙。王船山所主张的“天地无始说”属于后者,它以时空之内为特征,其宇宙只包括“有”而不包括“无”,即只包括“万有”,不包括“万无”,为不周全的宇宙。关于王船山之为“永续”的宇宙观,除了前述内容为证外,还可以做进一步说明。
第一,王船山的“天地无始说”具有明显的时空性质。其言:“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让天地之大,则终不及天地之久。有‘初’有‘终’,有‘吉’有‘乱’,功成一曲,日月无穷。方其既而不能保,亦不足以配天地之终始循环,无与测其垠鄂者焉。”[9](P.973)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天地“可大”“可久”。“可大”指空间无限,“可久”指时间无限。其二,天地之内有“始”(“初”)有“终”。其三,“始”“终”乃无限循环者。经分析不难发现,这三层意思均以时空之内为预设:第一层,“可大”“可久”虽意为无限,但均为时空之性质,而没有超越时空;第二层,“始”“终”仅就具体事物而言,即就时空之内来讲,非就超越时空讲,因为具体事物存在于时空之内,以时空为存在条件;第三层,具体事物无限循环,由其构成的“天地”亦无限循环;既然具体事物在时空之内,作为“万有”之总体的“天地”亦在时空之内,无有超越时空之性质。由这样三层分析可知,王船山的宇宙观乃时空之内的“永续”,而非超越时空的“永恒”。
第二,王船山的“天地无始说”之“天地”(宇宙、世界)只为“万有”,即万事万物之总体,未包含“万无”即事物之外的部分,故其宇宙为不周全者。或者说,王船山只承认与人相关的经验世界,拒斥与人无关的超验世界,故其“世界”亦不周全。例如,他说:“以我为子而乃有父,以我为臣而乃有君,以我为己而乃有人,以我为人而乃有物,则亦以我为人而乃有天地。器道相须而大成焉。未生以前,既死以后,则其未成而已不成者也。故形色与道,互相为体,而未有离矣。”[9](P.905)因为有“子”方可称“父”,因为有“我”方可称“他人”,因为有“人”方可称“物”,因为有“人”方可称“天地”,故“道器相须而大成焉”,宇宙乃“道”“器”不离的总体;这个总体既无“未生以前”,亦无“既死之后”,它是一个纯粹的“形色世界”,乃拒斥了“超验世界”的“经验世界”。正因如此,他主张儒家应只探讨和追求“尽生理”,而不应计较死亡问题,更不能“惜死以枉生”,否则会“害生理”。“仁人只是尽生理,却不计较到死上去。即当杀身之时,一刻未死,则此一刻固生也,生须便有生理在。于此有求生之心,便害此刻之生理。故圣人原只言生,不言死;但不惜死以枉生,非以处置夫死也。”[12](P.830)
如王船山所言,“只言生,不言死”乃圣人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圈定了儒家宇宙观的规模:具体来讲,孔子如下两段话即圈定了儒家的关注对象为经验世界。其一,“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0](P.79)“知”同“智”。鬼神当属“超验世界”,孔子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而且称其为“智”;此为对“超验世界”的拒斥,对“经验世界”的肯认。其二,“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20](P.146)此段话再次拒斥了“超验世界”,主张将目光圈定在“经验世界”。不过,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孔子亦有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0](P.36)“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0](P.93)这些话似乎指孔子肯认超越的“天”,肯认超越时空的“超验世界”。其实,孔子之为孔子,他之所以为儒家奠立者,其贡献在于由“神文”向“人文”的转变——他努力淡化商周及以前的“上帝”观念,淡化“超验世界”的观念,努力将目光集中投射于“经验世界”。故,其思想中虽有“超验世界”之论,但绝非其关注的重点。因此,他亦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0](P.241)子贡亦有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20](P.61)总之,由孔子对“经验世界”的肯认不难推知,他对世界的理解是在时空之内的,而非超越时空。
虽然儒家宇宙观的源头在孔子,但孔子并非四无依傍之创造,而是“会通”了鸿古时期古圣先贤的思想。熊十力说:“孔子之学,殆为鸿古时期两派思想之会通。两派者:一、尧、舜至文、武之政教等载籍足以垂范后世者,可称为实用派。二、伏羲初画八卦,是为穷神知化,与辩证法之导源,可称为哲理派。”[21](P.333)“实用派”对“经验世界”的关注毋庸置疑,“哲理派”其实亦对“经验世界”关注,可从《易经》的主旨“易”来看。关于“易”之含义,《易纬·乾凿度》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籥。”[7](P.77)“籥”为“要”。“易”之含义有三:一是简易;二是变化;三是不变。郑玄注这段话说:“言易道统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包道之要籥也。”[7](P.77)理解“易”对“经验世界”之关注,关键在于“道德”一词。“道德”固属于“经验世界”,故《易》对“经验世界”的关注无疑。《易纬·乾凿度》言:“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万物之宝。”[7](P.78)“道”属“天地”,“德”属“乾坤”;无论是“天地”,还是“乾坤”,均属经验世界无疑。《易经》的主旨“易”是通过六十四卦体现的,而六十四卦皆为对自然现象之概括、抽象,进而引申为吉凶、祸福预测。既然如此,《易经》属对“经验世界”而非“超验世界”的关注毫无疑问。
既然孔子通过“会通”古圣先贤思想奠定了儒家宇宙观,便可言儒家的宇宙观为“永续”的宇宙观。这样一种宇宙观,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尽管这种继承或自觉抑或不自觉,它都形成了儒家的重要传统,也成为与“永恒”的宇宙观相异的一种宇宙观。时至现代,儒家依然在这种宇宙观下思考。如,熊十力认为,所谓“宇宙论”,不过是“解释现象界之学”。他说:“宇宙论一词,以广义言,即通本体与现象俱摄之;以狭义言,即专目现象界所谓宇宙万象。此中是狭义。”[21](PP.19-20)宇宙论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以宇宙全体为研究对象;其二,以宇宙人生为“浑然同体”;其三,超越了纯知识之学,是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根据。[21](PP.546-547)“现象界”自是经验世界,故熊十力的宇宙论属于经验世界,其宇宙观则为“永续”的宇宙观。由于儒学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主干地位,故其宇宙观还影响了其他中国哲学派别。如,张岱年作为“新唯物论”的奠立者,他对“宇宙”的理解便具有代表性。他说:“宇宙是一个总括一切的名词。万事万物,所有种种,总合为一,谓之宇宙。宇宙是至大无外的。……宇是整个空间,宙是整个时间。合而言之,宇宙即整个的时空及其所包含的一切。”[5](PP.1-2)这里,“总括一切”和“整个的时空”是两个关键词,它们虽然有“宇宙是至大外”之义,但其所指向的是时空之内而非超越时空,即为“永续”的宇宙观,而非“永恒”的宇宙观。
总而言之,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大儒,他以反思和重构宋明儒学为自我期许,而其反思和重构的基础和宗旨是原始儒学。由此来讲,他的思想包括宇宙观可被视为儒家宇宙观的代表,至少为儒家宇宙观的传承者。基于此,可由王船山的宇宙观推及整个儒家的宇宙观——“永续”而非“永恒”的宇宙观。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言王船山为“永续”的宇宙观,并无损其宇宙观的价值;进而推及于整个儒家,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尸佼著、汪继培辑:《尸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3] 程志华:《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
[4]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6]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7]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8] 邵雍:《邵雍全集》叁,郭彧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9]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
[10]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
[11] 王弼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
[13]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14]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册,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
[15] 约翰·格里宾:《BBC宇宙的本质:夜晚的天空为什么是黑的》,周宇恒译,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
[16] 周掌柜:《元宇宙大爆炸:产业元宇宙的全球洞察与战略落地》,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
[17]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Chinese-English Bible.Berkeley, CA:Hymnody and Bible House,1990.
[18] 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9] 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0]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 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