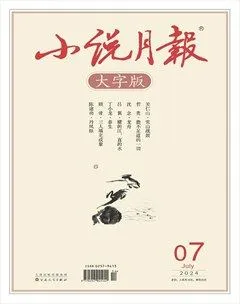丹凤眼
都说北京女的比男的多,可京西不少的小伙子就是搞不着对象。
怎么,他们都没个模样儿,歪瓜裂枣似的?要不,就是不争气,都是吃饱混天黑的主儿?错啦。不信你就去看看。出了三家店,漂亮小伙儿有的是!身高膀圆的,眉清目秀的,拨拉脑袋就是一个!这里面,有劳动模范,有革新能手,也有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要是在北京城里,也能把姑娘们迷得魂飞神散呢。可他们是在京西,他们是井下挖煤的,是矿工。这就糟啦!姑娘们一听说干的是这一行,十有八九皱眉头,哪怕面前站的是十全十美的小伙子,回答也是两个字:“不成!”
就因为这个,矿区的小伙子们搞对象不知碰了多少钉子。一来二去的,有的小伙子开始恨上身上这身工作服了,变着法儿也得把上面印着的“?菖?菖矿”这几个字给抹了——走大街上怕人笑话,寒碜呀。有的小伙子还总结出一条“恋爱经验”:“先不能让她知道你是矿工,等把她‘俘虏’了,再亮‘番号’!”于是就有那么一位,在城里的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姑娘。人家问他在哪儿工作,你猜他回答什么?他说:“在黑色冶金粉末研究所工作。”多妙!这笑话多啦。我可不敢再说了,京西的小伙子得向我提抗议:“别净糟践我们!京西净是这号自轻自贱的人?有血气的小伙子也有的是!”
没错儿!有血气的小伙子有的是。“人家看不起咱,咱自己还看不起自己?挖煤怎么了?比别人矮半截儿?就欠给他们来次‘能源危机’,到时就都把咱矿工当宝贝了!”说这话的,是燕南煤矿的采煤工辛小亮。他最容不得别人说他干的这一行不好。据说有一回有几个姑娘下井参观,领她们下来的工会干事一边走,一边抱歉似的说井下条件如何如何不好,让她们留神。辛小亮听不入耳了,说:“这儿又不是万寿山,不怕崴了西太后的脚!”把那位伙计憋了个大红脸。工友们笑他说:“你呀,甭想得人家姑娘的欢心,就抱着井下这些风锤电钻过一辈子吧!”可不,别人给他介绍了四五回对象,全是第一面就吹了。至于人家一听说是矿工,连面都不见的,那就没数啦。辛小亮呢,挺挺儿地戳在那儿,还是个一米八的大汉!甚至比从前越发骄傲,越发牛气起来了!特别是见了姑娘们,眼皮抬都不抬。食堂里卖饭的姑娘们、矿灯房里发灯的姑娘们,没有不怕他的。他太损呀。到开饭时间了,你窗口晚开了一步,他就在外面敲开盆儿了:“卖饭呗!卖饭呗……真他妈白吃饱儿!矿上养着你们干什么!干不了趁早回家抱孩子去……”从井下出来,矿灯房的姑娘收他的灯,常来常往的,有时冲他笑笑。他反倒瞪人家:“谁跟你笑,瞅你漂亮?!”一句话能把小姑娘噎出眼泪……这还不算什么。最气人的是,他给矿上的姑娘们起了不少“雅号”。这家伙聪明,外号一起就准。食堂卖炒菜的姑娘老板着脸,斜着眼睛翻人,他背后管人家叫“憎恨”。卖馒头的姑娘新近把头发烫成了“大花”,他就管人家叫“花卷儿”。四号卖饭窗口的姑娘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位,特别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眼角微微向额上翘着,标准、美丽的丹凤眼。这位辛小亮倒好,偷偷叫人家“吊眼儿”……食堂的姑娘们早有耳闻,气得咒他“找一个丑八怪”!这可咒不着他,反正他是决心打一辈子光棍儿啦。其实小伙子挺帅,乱蓬蓬的刺儿头下面一副白净的方脸庞,老爱眨巴着眼睛高声说笑,潇洒又粗犷。他干活儿不惜力不说,拿起什么活计都有点机灵劲儿。要是不犯“嘎”,怎么也能交上女朋友的。谁知别人介绍了好几个,他死活不肯去见面了。这可把他妈急坏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眼瞅着连孙子也抱不上了。每次介绍人登门,总让辛小亮给噎走。他妈不知为这跟他抹过多少回眼泪,生过多少回气。有一回,他烦了:“妈,您别说啦,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我去见一面还不行!”他妈说:“你早明白一点,我给你准备八抬大轿!”他说:“那我可跟人家来实在的。”他妈说:“我让你拐骗人去了?”得,他这“实在的”可真够“实在”啦。一见面,女方说:“听说你在矿上工作?”他说:“是啊。”女方又问:“下井吗?”他说:“当然下井。”女方下一句话还遮遮掩掩的哪:“那……现在井下安全搞得不错了吧?”这位辛小亮倒好,嘎劲儿上来啦:“不安全。净死人!我们矿上,净是寡妇!”这不是胡说八道嘛!可他这招儿真灵,不但对象吹了,打这以后,介绍人也不大上门儿了。他妈不更抓耳挠腮了?有什么办法!整天找碴儿跟那个退休的老伴儿生气:“就知道喝茶喝茶,找那些糟老头子‘敲三家儿’‘拱猪’……儿子的事你就屁也不放一个!哪还像个当爹的……”辛师傅过去也是个老走窑的,少不了那份幽默劲儿:“那你说咋办吧?我这就准备绳子。你指点着,相中哪一位了,后半晌我给你捆一个回来……”
辛大妈心急火燎,见了家属区里“他婶”“他姨”的,少不了唠叨儿子的“对象问题”。这嘴皮子是不会白磨的。这不,这天傍晚,热心肠的乔奶奶又上门儿啦。
乔奶奶住柳花台家属区,离工人新村好几里地远,一双“白薯脚”(俗称“解放脚”)一颠一颠地赶来也真不易。辛大妈见乔奶奶一身新,心里就明白了几分,高高兴兴地招呼她进里屋喝茶。两个老太太在里面嘀咕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辛小亮叫进来了。
“小亮,乔奶奶特意为你的事跑来一趟。我听着,那姑娘挺不错……”
“哪儿的呀?”辛小亮举起双手,按住两边的眼窝,使劲儿揉着,又上上下下在脸上搓了好几把,撇嘴笑着,那样子活像开始犯困了。
乔奶奶说:“那姑娘过去在‘京棉’三厂。这不,家里只剩一个老母亲了。调回矿上上班,照顾她妈。现今在食堂卖饭哪……”
“哦。倒近。”辛小亮还是一副睡眼眯瞪的样子。辛大妈恨不得过去给他一条帚疙瘩。
乔奶奶笑了:“近还不说。那姑娘真不赖呢。听说在食堂得算顶漂亮的。双眼皮儿,细皮嫩肉……”
“得,得,谢谢您了!”辛小亮耷下眼皮,摆手把乔奶奶的话截住了。“乔奶奶,您快别说了。大老远的,您跑这一趟也不易……真对不起您,我得扫您的兴了。我呀,您就找那些猪不吃、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介绍给我得嘞。您说的这位,咱消受不起。那是给矿上的小科长们啊,写材料的小白脸儿们啊,头头脑脑的儿子们啊预备的。咱可没那个福分……”
“你还不知道是谁,就……就把人家回啦?!”辛大妈火了。
“甭问,问也白搭。人家肯定看不起咱们,咱也不高攀人家,一见面准崩。让乔奶奶再白受累,咱也不落忍……”说着,他站起来,冲乔奶奶笑笑,走了。
“瞧我这孩子!瞧我这孩子!……”辛大妈气得直哆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没啥!没啥!搞对象嘛,还不得由着他们?谁不得挑个可心的!强扭的瓜不甜……”乔奶奶是个开通人,咯咯笑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话是这么说,她这一路可犯愁啦,回去怎么回女方的话呀。姑娘是她老邻居孟家的闺女孟蓓,二十四岁了。前儿个,孟家老太太托她给闺女张罗,她一口应承下来了:“行,行啊大妹子。别人家的闺女咱不敢说,您这姑娘还愁找不着婆家?我包你得个满意的姑爷!”谁承想,第一个就撞上了辛家那么一个嘎小子!怎么跟孟老太太说呢?说辛小亮连名儿也不打听,就一口回绝了?那可太伤面子了。人家闺女那么漂亮,漂亮姑娘脸皮子都薄啊……乔奶奶到底是乔奶奶,来到孟家,倒也没什么为难的了。她告诉孟老太太那小伙子并不合适,个头儿不高,脸庞儿也不精神,和孟蓓站一块儿不般配!“赶明儿我给您找个合适的!把咱家小蓓介绍给那个辛小亮,太亏!闹不好,见第一面下来,咱小蓓就得气得背过气去!”三言两语,把孟老太太说得乐散了架,既开心,又熨帖。等闺女下班回来还当笑话唠叨个没完。没想到闺女听了,却撇了嘴,气哼哼地把手里的茶杯往桌上一蹾,说:“都是您都是您!多管闲事!”闹得孟老太太忽然摸不着头脑了。以前,她也给闺女张罗过,虽说闺女也不乐意让她管,可从来也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呀。
孟蓓回到自己屋里,也奇怪刚才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慢慢地,她明白了,自己是在生辛小亮的气。俗话说,吊眼儿的姑娘难斗。这话不好听,可有点儿道理——丹凤眼的孟蓓确实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听妈妈一讲,她就明白乔奶奶在瞎说。辛小亮,她太认识啦!个头儿绝不低,脸庞儿绝不难看。哼,那家伙肯定说出了什么难听的话,乔奶奶回来不好一五一十地转达,找个话茬儿搪塞罢啦。她哪想到,孟蓓还没调回来时,就见过这位辛小亮了。岂止见过,他肚子里憋什么坏水,对姑娘们抱什么态度,她都知道!
那是去年春节前,她从城里坐火车回矿,陪妈妈过节。车还没从永定门站开出的时候,她就听见靠背那边的座位上,两个小伙子在聊天。和自己一板之隔坐着的,是个高声大嗓的“大块头”,坐在椅子上很不老实。聊得高兴了,索性用膀子一下一下地撞靠背,好像浑身有劲儿没处使。有时,他仰面大笑,把那支棱着又粗又硬头发的后脑勺倒过来,头发触到孟蓓的头上,气得她躲了好几回。他对面坐着的一位,是个“活宝”,岁数小,声音细,不断和自己的朋友开玩笑。开始,孟蓓倒没注意他们聊些什么,只听他们讲什么“到北京钓鱼”啦,“鱼没钓着,惹一肚子气”啦。孟蓓心里奇怪,大冬天的,到北京钓什么鱼!听着听着,她捂着嘴偷偷笑了:什么“钓鱼”啊!敢情这是矿工的行话,说的是交女朋友!孟蓓倒是从小在矿区长大的,还没听过这么个讲法儿哪!再听下去,那粗声大嗓的小伙子在讲“钓鱼”的经过。那个“活宝”呢,不时地插科打诨,逗他。他们的话,惹得孟蓓好几次险些笑出声儿来。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装作取开水,跑到车厢间的过道儿里,笑了好一会儿!
“瞧瞧,为这么一趟,我妈忙活得骨头都酥啦!逼我穿上这么一身不说,还教我哪:到了北京,别露怯,显出咱没见过世面。记着,人家爸爸是煤炭部的干部,你可别叫人家‘大爷’,得按城里的规矩,叫‘伯父’……”
“嘻嘻……”大概是“大块头”学他妈的口气学得太像了,“活宝”笑起来:“结果怎么样?一进人家门,舌头就转筋了吧?”
“瞧你,咱窑工让人瞧不起,可并不是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到了她家,咱也不卑不亢,人模狗样的哪!”
“得得得,牛气不小,怎么灰溜溜回来了?”
“灰溜溜?告诉你,别说她长那模样儿咱不待见,就是天仙似的,我也不要!”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
“烂葡萄!哼,见一面不要紧,得做几天噩梦,折我十年寿……八成是城里找不着人家了,处理给我啦。可她家老头儿老太太还觉着便宜了我这个傻小子哪!亏那老头子还是煤炭部的,把咱窑哥们儿挤对得够呛。说什么‘过了三家店,家雀儿都是黑的’。还说‘你样样都好,就是工种不好’。又吹!说马上要想法子把我调出井下……把我气得鼓鼓儿的,心说,你们倒样样都好,就是心眼儿不好!良心大大地坏了!要不碍着介绍人的面子,不损他两句才怪……”
“对!”“活宝”也不禁义愤填膺了,“老弟上刀山下火海,也得给你奔个大嫂子来。明儿还给他们送喜糖去,气他!”
“算啦,别气我了!我打一辈子光棍儿也不找啦……那些女的,没几个不势利的!”
“你还是认熊了!熊!熊!”
“熊?我出气了!临走,趁屋里没人,我顺手把身边的暖气给他关了!把旋钮摘下来,出门又扔回他家报箱了!别看你是煤炭部的,冻一宿吧……”
“哈哈……”
两个人又笑起来。座位的靠背又让那个“大块头”撞得“砰砰”响。
就这么着,两个小伙子简直像在说相声,你一言,我一语,聊了一路。孟蓓呢,也偷偷听了一路。她挺爱听,常常忍不住想笑。可有时却又气不过——他们也太伤众了,常把那些轻蔑的话推而广之,对女同志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偏见。要是在自己工厂里,熟人中间,孟蓓肯定要站起来,唇枪舌剑地回击了。哼,你们男的就那么好?她也可以举出好几例,证明有不少趾高气扬的小伙子,瞧不起她们纺织姑娘呀!想是这么想,她还是蔫蔫儿地靠在那儿听着——甚至靠背被撞得最厉害的时候,她也没有什么抗议的表示。
车到燕南煤矿,孟蓓下车了。没想到他们也在这儿下车。听到有人和他们打招呼,孟蓓一下子就记住啦。那个一肚子坏水的“大块头”,叫辛小亮。那“活宝”呢,叫赵涛。
这以后没多久,孟蓓就从城里调到矿上了。辛小亮在矿上是个人人瞩目的人物。他的大名经常在矿上的广播喇叭里被喊出来,超什么纪录呀,战什么险情呀,这就不必说了,就是在工会组织的摔跤比赛场地上,他也是观众崇拜的勇士。更何况他净在卖饭窗口外喊“白吃饱儿”,孟蓓能不一下子认出他来?
孟蓓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姑娘。一瞧见辛小亮,她就想起火车上那一段,心里一直气不过——他太狂了!太看不起女同志了!可她还是原谅了他。谁让姑娘们中间,确实有那种势利眼呢。在矿上时间长了,从女伴儿们那里听说了好多矿工搞对象的“趣闻”,其中当然也有辛小亮的事,心里对他倒有几分敬畏了。以至听说自己也被起了外号,她还是微微一笑,只是心里说:哼,你这就算男子汉啦?也就给人起个外号,出出气。连个知心的人都找不到……可这一次,孟蓓是大大生气了。她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猜想着乔奶奶怎样去辛家,辛小亮怎样冷言冷语。哼,他那一翻一翻的眼皮子怎么动,孟蓓都猜得出来……
这天晚上,辛小亮躺在床上,倒还和往常一样,鼾声如雷。他根本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自己一口回绝的,是食堂的哪一位姑娘。“真是那么漂亮?她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念头他闪都没闪,高高兴兴地去看了一晚上电视,十点钟回来,宽衣上床,进入梦乡。他更不可能想到,几里地以外,柳花台家属区,有个姑娘为了他直到半夜还没睡着。别看她眼角向上翘翘着,嘴角也向上翘翘着,笑模笑样儿的。她在咬嘴唇,小酒窝一跳一跳的——气得够呛呢!
孟蓓这姑娘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别瞧他辛小亮气粗如牛,买饭之前还是敲盆敲碗,没心没肺地捣蛋,孟蓓反正盯上他啦。结果怎么样?没过几天,孟蓓站在窗口里就把辛小亮给治了,治得服服帖帖!你说邪不邪?
第一次,就是辛小亮害得孟蓓半宿没睡着觉的第二天,中午开饭的时候,辛小亮排在四号窗口买米粥和炸糕,巧巧儿赶上卖饭的是孟蓓。
“二两粥,四个炸糕。”辛小亮把大搪瓷碗递进了窗口。
“当——当——”铁勺碰得碗底脆响。二两米粥盛上了。“砰”,放在窗口台儿上,热腾腾的米粥一涌,险些溢出来。
“拿着!”四个炸糕捏在孟蓓手里,伸了过来。
辛小亮只拿来一个碗,已经盛上了粥。如果接过炸糕,又怎么腾出手来交饭票?“搁这儿!”他把两根筷子架在粥碗上。
孟蓓眼帘一挑,瞪了他一眼,把炸糕往两根筷子中间重重一搁。筷子“锒铛”滚下粥碗,四个炸糕一下掉进了粥里。
“啧啧啧,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辛小亮急得把脑袋伸进了窗口,用嘴吮着稀粥漫出的碗沿儿,烫得他不时吸嘘着。
“你干什么吃的……我不要了!不吃了……这叫炸糕吗?成元宵了……”辛小亮气得喊起来,“退你吧,我不要了!”
看着他那狼狈样儿,孟蓓扑哧一声笑了。又抿起嘴,丹凤眼里闪着开心的光:“得啦得啦,凑合吃吧,下次多拿个碗来……”
“真是白吃饱儿!连个炸糕都不会放!我不要了……”辛小亮还是怒气冲冲地喊着。
孟蓓呢,眼角也像在笑,嘴角也像在笑,还是轻轻的声音:“谁让你用的是圆筷子。要用方筷子,也接住啦……吃吧,去吃吧,吃到肚子里还不一样了?”
唉,再发火,有什么意思呢。辛小亮气得咽下一口唾沫,端着“粥泡炸糕”,走了。
食堂就那么几个窗口,卖饭的也就那么几个姑娘。想买饭,又不想碰上哪一位,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辛小亮根本没想到孟蓓会成心治他。这么着,在窗口遇见,可不止这一次啦,孟蓓对辛小亮的怨气,这一次还没出够哪。得,这以后,辛小亮只要买饭撞上孟蓓,不是豆腐脑里多搁了卤,咸得没法儿下嘴,就是要吃白菜,她给盛了西红柿,进了饭碗,不端走还不行。有时候,辛小亮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有时候呢,站在窗口,七窍生烟地嚷嚷一通。可气的是,孟蓓还是第一次那个劲儿,不跟你发火,反倒挺得意,笑模笑样儿,细声细气的。辛小亮还是只好一走了事。
辛小亮哪受过这个呀!三次两次,他坐到饭桌前嘀咕开啦:“我怎么她了?她干吗净跟我过不去……”
“你净喊人家‘白吃饱儿’,又叫人家‘吊眼儿’,不治你才怪!”赵涛——就是孟蓓在火车上也见过的那个“活宝”,眨巴眨巴眼搭话了。
“可前几天还挺顺的哪,怎么……”辛小亮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行啦行啦,包在我身上。‘情报局长’给你调查调查去。”别看赵涛人不大,猴精猴精的,几十里矿区,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人,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自封“情报局长”,是当之无愧的。
果不其然,两天以后,赵涛的“情报”回来啦。
“你得罪人家了。”他绷着脸,神色严肃地说。
“狗屁!我看都没多看她一眼!”
“嘿嘿,就为这个……是俱乐部老杨头儿告诉我的,你把人家晾啦……”
天哪!辛小亮一下子明白了。俱乐部老杨头儿就是乔奶奶的老伴儿。敢情乔奶奶那次要给他说合的,“食堂最漂亮的姑娘”,就是孟蓓!哈哈,自己当初连个名字都没问,现在才知道!他拍拍脑门儿,“嘿嘿”笑起来,捶了赵涛一拳,把座椅晃得“吱吱”响。可慢慢地,他不笑了,心里总有点疙疙瘩瘩的,一肚子心事。说实在的,这也是个聪明小伙儿。他寻思着,我那就得罪她了?至于吗?我当时说啥来着?说啥了?哦——我说她“是给小科长、写材料的小白脸儿、头头脑脑儿的儿子预备的”。是为了这句话?不,乔奶奶不会把这话传给她呀!哦,是因为说了“人家看不起咱,咱也不高攀人家”?总之,辛小亮心乱啦。“敢情是为了这,得罪她了?那怎么才算不得罪她?”他想这些的时候,眼前闪出一个卖饭窗口,里面有孟蓓那含嗔带怪的眼梢嘴角,又有孟蓓“治”了他以后那得意的笑……这里面,好像都包含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深意啊!
小伙子们哪,你们谁也别夸口自己有“坐怀不乱”之勇,看看你们的血性男子汉辛小亮吧,当他从疑惑中恍然大悟,又渐渐品出一点味儿来的时候,竟也忘了自己所固守的对女同志的偏见,从吃“粥泡炸糕”开始,回味起每一次被“整治”的细节来了。虽说只有那么三两次,却被他反复咀嚼。他骂了自己多少遍“没出息”也没用……
这天,他又去四号窗口买馄饨。看见孟蓓在窗口里面,隔着五六个人,他的心就开始怦怦跳了。他要了二两馄饨。虽然还是装出平常那种不经意的样子,眼睛却偷偷瞟着窗口里那颀长的身影。雪白的工作服很合体,衬出那圆圆的肩头。松润的鬓发被身边电扇的风吹得飘飘忽忽,有一绺搭在她上翘的眼角上,她抬起右臂弯,灵巧地向上一抹,然后把手里的铁勺一挥,“当”,馄饨盛在左手的搪瓷碗里。
“两毛五。二两。”她和以往一样,重重地把碗放在窗口台儿上,眼睛毫不躲藏地盯着辛小亮,紧抿着小嘴,下唇轻轻地一努一努。
辛小亮慌慌张张地找出三毛钱饭票。她接过来,找回五张“一分”,往窗台上一扔。“呼”,电扇吹来一股风,把三张饭票吹进了辛小亮的馄饨碗里。“哎呀!”她肩膀一耸,眼睛一闪,做了个怪样,又扑哧一声笑了。脸红红的,伸手把饭票捏出来。“不脏,不脏……”她的眼睛还是大胆地朝辛小亮望着,“你骂我吧!”那眼睛好像在祈求。“你才不会骂呢!”那眼睛又有几分得意。
要是以往,辛小亮不又得暴跳如雷才怪!可现在……
“唉,也就是赶上你了!”辛小亮瞪着她,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苦笑着接过换给他的干净饭票,端起了饭盆。
身后,传来那姑娘的笑声,这是从心里冲出来的笑。吃馄饨的时候,他几次把勺子送到鼻尖上,心里又暗骂起自己没出息来啦!
这往后,辛小亮真的没出息啦。排队买饭,不喊了,不闹了,老实得像根木桩子。赶上孟蓓卖饭,一站进队,脸就红。这些,瞒谁也瞒不过赵涛——他老跟在他后面呀。得,这小家伙故意用话撩拨他啦:“小亮,怎么如今老实了?不喊‘白吃饱儿’了?”“你没喝酒啊,脸红什么?”到了饭桌上,赵涛更少不了拿他开心了。辛小亮端起了粥盆,赵涛问“香不香”;小亮摘下帽子,赵涛问“热了吧”;小亮吃完了,赵涛指着盆底儿说:“还不刮干净点儿,多香甜的棒子面儿呀!”辛小亮把他推一边去了:“滚滚滚。”赵涛还有“撒手锏”哪:“怎么,过河拆桥啦?你还有用得着我‘情报局长’的时候!”
可不是!这天上早班,汽笛快响的时候,赵涛来了,兴冲冲地跳进辛小亮坐的人行车里,得意扬扬地说有“最新情报”,然后,忍不住举起手里的镐把儿,往辛小亮的玻璃钢帽盔上敲:“太开心啦!太开心啦……‘吊眼儿’……哈哈,真妙……”往常,赵涛有了那么一点点关于孟蓓的“情报”,且卖关子呢,非憋得辛小亮心痒难熬才说出来。可今天,他根本没心思卖关子啦:“这是第一号‘情报’,第一号!”
“得得得,今晚夜宵店不开门啊。”——赵涛平常净拿孟蓓的一颦一笑当“情报”,拉辛小亮去夜宵店敲竹杠。
“我请客!”赵涛举手打了个响指。“孟蓓给胡连国来了个大窝脖儿!……你当只是你的胜利?这是咱窑哥们儿的胜利!”
胡连国是劳资科科长胡玉通的儿子。本来和辛小亮他们一样,是燕南矿的井下工人。可他爸爸让他“支援”了燕北矿。一换了单位,就成了科室干部,不再下井啦。兄弟矿嘛,劳资科也互相协作得不赖。
胡连国追孟蓓了?辛小亮还是第一次听说。
“他托膳食科的一位副科长去说合。还说矿长办公室的打字员考上大学走了,正要补一个。透出那口风不说你也明白啦……你猜孟蓓怎么回答?你猜不着!”
“还不美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辛小亮说。
“去去去!”赵涛一挥手,“人家孟蓓问了一句:‘他爸爸今儿晚上要是咽气了呢?我靠谁去?!’哈哈……”
“呜——”汽笛响了,人行车“咣当咣当”启动了。赵涛凑到辛小亮耳边,在轰隆隆的巨响里高声喊道:“她还说啦,科长的儿子,又是科室干部,咱可攀不起,要是个井下工人嘛,差不多……这可是重要信号,重要信号啊!”说完,他又向后一躺,双腿掀起老高,开心地笑着。
“真是笨蛋!放着打字员不干,还挺爱卖豆腐脑儿……放着白脸儿不爱,爱黑脸儿!”辛小亮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冷冷地笑着。
其实,赵涛早把他琢磨透了:“别猪鼻子插葱——装象了啊!”他捶了辛小亮一拳,放开喉咙,反复唱着《解放军进行曲》的第一句“向前向前向前”,在奔驰行进的人行车里晃着。
平常下班以后,辛小亮的眼窝里、鼻翼边,总带着黑印儿,这是他在浴室里用十几分钟“结束战斗”的标志。可今天,他足足在喷头下面耗了半个小时。下午回到家,按惯例,晚饭应该在家吃的。可今天呢,他没魂儿了似的,跑到邻居家,给妈妈留下话,说矿上有事,走了。什么事啊?就是到矿上食堂吃晚饭——孟蓓在四号窗口卖饭哪。吃完了晚饭,他心神不定地在山谷里转悠了好久,十点多钟,又进食堂吃了一顿夜宵——也就是说,这一天,他吃了四顿饭。食堂要是不关门,恐怕他还得去吃第五顿!害得他妈白白往商店转悠了一下午,买回来那么多好菜,预备着给他过生日!
用赵涛的话来说,自从辛小亮接到了“重要信号”,就有了十大变化。第一,绝口不提“吊眼儿”这个外号了。第二,晚饭也在食堂吃了。第三,专爱买四号窗口的饭。第四,吃饭愣神儿。第五,也不提什么“打一辈子光棍儿”了。第六……赵涛真不愧是“情报局长”,算是把辛小亮的心思摸透了。“伙计,咱平常挺冲的啊,这会儿还等什么呢!没胆儿就说一声,老弟撕破脸皮,帮你上门问她愿意不愿意!”这话不假。辛小亮平常对女同志耍横犯嘎,真到了这节骨眼儿上,什么招儿也没啦。赵涛看着费劲儿,倒比辛小亮还急三分:“咱矿工搞对象,是‘集体’搞哪!找着一个有眼力的姑娘,不易!”他捋胳膊挽袖子,“反正我是完啦。倒八字的眉毛,绿豆眼儿,又摊上干的这行当,一辈子没人跟!可我小亮哥该有个好爱人啊,多精神的小伙儿,谁看不上他谁瞎了眼!……”这小伙子在井下干了几年,讲起话来总是充大,学老窑工的口气,未免粗俗,可他确有一种为了他小亮哥两肋插刀的侠气。
几天以后,辛小亮休假。这天赵涛也歇了。午饭时,他来得很晚,卖饭窗口前,已经没什么人了。赵涛到四号窗口买了饭,靠在一边,歪着脑袋,对里面的孟蓓说:“给你们食堂提个意见,行不?”
孟蓓一看是他,心想,你也是提意见的人?憋什么坏哪!她说:“有意见找科长提去。”
赵涛说:“我专给你提的!听说你还得头等奖金呢,我们班的辛小亮病了好几天,想吃点可口的东西都没有!你没见他一天往食堂跑好几趟!”
孟蓓的脸红了:“去去去!谁病了都管,就他病了活该!”
“当真?”
“当真当真当真!”孟蓓的声音又甜又脆,“告诉他去吧,活该!”
赵涛端起饭碗,咳了一声,装出一副丧气样儿,心里却偷偷发笑。三口两口扒完了饭,他又到了辛小亮家。
“辛小亮,今儿下午别出门啊!在家等着,有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党委书记找你谈话。”
“我?我怎么了?”
“你好哇!一会儿就知道啦!”
他穿着白背心,手里摇着脱下的衬衫,风车一样地转着,跑了。他跑进家属区的小酒铺,买了一升啤酒、一碟香肠:“哼,今儿要不是他得在那儿等着,非逼他请客不可!”
且说孟蓓轰走了赵涛,站在卖饭窗口里愣神儿。你可不知道,姑娘们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从小伙子的一缕眼神里,也能看出此中的深意。更何况孟蓓这样的,从纺织厂的姑娘堆儿里出来,又精明得不饶人的姑娘!辛小亮心里哪怕打起一个浪花,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开始,她多开心哪,降伏了这个狂气的小伙子,出了一口气,真是太棒了!到现在,她忽然明白:天哪,到底谁降伏了谁啊!你为什么老希望他站到你四号窗口的前面?你为什么在“治”了他以后,总后悔自己太泼辣,总在想,人家不讨厌你?”爱情这东西,真是太神秘了。我敢说,不管是诗人还是心理学家,他们给爱情下的定义远没有真正的生活来得微妙。孟蓓当然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大块头”辛小亮,可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她也说不上。也许,是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听了他那些让人笑破肚皮的谈话之后?可是刚才,听了赵涛一番话,孟蓓的心里又“骂”上辛小亮啦!她知道赵涛是辛小亮的哥们儿。哼,鬼知道是真病假病!真病,找我干什么?想吃可心的东西,回家去呀……一天往食堂跑好几次,不是心病才怪……想着想着,她的脸一直红到眉梢,抿嘴儿想乐:这会儿就不充好汉了,还得派个传话的来。我非去给你治治这个“病”不可!
这天下午,辛小亮真听了赵涛的话,老老实实地在家等党委书记。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孟蓓,这才明白赵涛那家伙把自己骗了。当然,这比门口站着党委书记可招人高兴多了。可这……这也太突然了。他心慌意乱,舌头打不过卷儿来。
“哦,是你……你,干什么来了?”问完这句话,辛小亮心里一个劲儿后悔。这样问,太失礼啦。
孟蓓呢,望着他,一笑,不答,坐到椅子上,眼睛往四处打量:“听说你病啦,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是真的吗?”
“胡说!”虽说辛小亮这两天真的茶饭不思,不过他才不会嘴软呢。“我睡得香着哪。一天吃一斤六两,活得舒坦着哪!”
孟蓓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亮晶晶的眸子往他身上一闪:“可是你哥们儿赵涛说的,还把责任推我们食堂的人身上,说是吃得不可心儿啦什么的……说你一天进五六回食堂,还是不可心儿……”孟蓓忍不住从嘴里啧出笑来。
“你听他的?听他的……”他说了半句,把后半句咽下去了。他本想说“听他的两口子都得分家”,又觉得这么说好像有点儿那个,他“呃呃”了两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真的没病?”孟蓓就差过去捶他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得自在,过得滋润!”
该死的!孟蓓气得哭笑不得!过去在纺织厂里听姑娘们议论,到这个份儿上,再硬的小伙子也得露点儿声气儿了,说自己“睡不着觉”啦,“吃不下饭”啦。可他……有什么办法!孟蓓几乎拔腿要走了!哼,过得滋润、自在,一个人过去吧!过一辈子!姑娘的心还是硬不过小伙子,你信不?这不,孟蓓没走。坐在那儿,挺尴尬,她还是红着脸,东问一句,西扯一句。她心里想,哼,再坐十分钟,你要是还装傻,我就走,再也不理你,看你怎么办……十分钟到了,她又想,再给你五分钟,该死!
辛小亮和孟蓓在屋里坐冷板凳。这屋子对面,辛家的小厨房里,可紧张着哪。孟蓓刚进屋没多一会儿,辛大妈就买菜回来了,还从菜市场拽回来一位,就是上回要把孟蓓介绍给辛小亮的乔奶奶。一路上,辛大妈搀着老太太,千般感谢,万般道歉,骂自己的“犟头”儿子,最后无非还是那句话:请乔奶奶别见怪,再给小亮张罗一个。两位老太太你搀我扶地到了辛家,正待进门,听见里面有姑娘的声音,隔玻璃窗一看,乔奶奶忙把辛大妈拉一边去啦。
“可了不得啦,大妹子……咱们操的哪门子闲心呀,你们家小亮这不都搞上啦……”
“搞上了?谁呀?”
“就是上次我要说给他的孟家闺女呀……啧啧,人家敢情是秘密接头……”乔奶奶咯咯笑着,用手捂着腰,生怕笑岔了气儿。
辛大妈还想凑窗户上看个仔细,让乔奶奶拽到小厨房去了:“别添乱!咱们七老八十的,一边待着去!”
这么着,两位老太太在小厨房里躲了老半天啦。
小厨房里还生着火炉,又赶上夏天,闷在这里可不是个事儿。这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辛大妈着急呀,开始还听见那姑娘在笑,怎么一会儿没什么声儿了?辛大妈一个劲儿催乔奶奶一块儿看看去:“您可不知道,我那嘎小子动不动就犯犟,咱们在旁边待着,别让他把人家姑娘给欺负了……”三说两磨的,等到乔奶奶经不住厨房的热劲儿,也就跟她一块儿去了。
两位老太太进了门,算是把屋里的别扭劲儿冲开了。可乔奶奶三句闲话没扯完,就点上正题啦,这可把两个小年轻的臊个大红脸!
“好小亮!我看你上次扬脖儿挺胸的,也是个发誓打一辈子光棍儿的好汉,敢情瞒着你乔奶奶哪!你不是要那猪不吃、狗不啃的主儿吗?我们孟家的姑娘可金贵哪,人家跟你?!”
“乔奶奶,您……您扯哪儿去啦!”辛小亮一个劲儿挤眼睛。
“甭做鬼脸儿!那我也得揭发你!”乔奶奶又转脸对孟蓓说:“话又说回来。这个小亮呀,除了犟,样样都好。你看看,我跟你妈说得不差吧,个头儿又高,脸庞儿又精神……你们站一块儿,真是好好的一对儿呢!”
孟蓓气得直瞪对面的辛小亮。谁让她天生一副笑模样儿呢,像生气,又像笑。
这么着,这层窗户纸让乔奶奶给捅破啦!辛大妈根本没听见乔奶奶唠叨啥,只是上上下下起劲儿地端详眼前的姑娘,乐得拢不住嘴。
“搞对象有闷在屋里搞的?这么好的天儿,俱乐部又有电影……”乔奶奶俨然是权威的介绍人的口气了,“去!到俱乐部去。跟我们家老头子说,是我让你们去的,给找两个座儿,看电影!”
不知是乔奶奶的命令有威力,还是人家两个年轻人各自有心。他们红着脸,一人撑一把伞,走啦。乔奶奶真会说话:“多好的天儿——凉丝丝的雨点儿漫天飘着哪……”
看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乔奶奶的得意劲儿还没过去:“昨儿矿上李书记见了我啦,问我:‘乔老太,听说你净忙活着给青年人拴对儿啦?’可把我吓坏了。我说:‘李书记,这没啥错误吧?’李书记乐了:‘怎么是错误!那么多安心为‘四化’挖煤的好小伙儿没人认,你给引荐引荐,让那些姑娘们知道,小伙子们心里都有宝啊!’嘿嘿,我这个人呀,越说我胖,我越鼓腮帮子。这不,昨儿晚上就跟我那老头子说了:‘你那俱乐部得给我配合!凡是我介绍去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你得保证人家两个人看上电影!’谁想到,小亮他们成第一对儿啦……”
乔奶奶一边说一边乐,转脸一看,辛大妈竟笑着抹上眼泪儿了。“哟,大妹子,这是怎么啦?”
辛大妈说:“我先寻思着,小亮这行当真干错了,得打一辈子光棍儿啦,谁承想找着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两位老太太闲扯这当儿,孟蓓和辛小亮已经走上永定河畔的马路了。
“这个乔老太太,真没治!”辛小亮“嘿嘿”笑着,又偷偷斜眼瞟孟蓓。
孟蓓瞪他:“你才没治呢!”
“哟,我怎么啦?”
“你干的坏事还少?”
“我干什么坏事啦?”
“自己想想!”
辛小亮挠挠后脑勺儿,好像想不起来。
孟蓓站定,把自己举的伞收了,说:“过来。”
辛小亮乖乖儿地举着伞站过去了:“你今儿成心给我摆什么谱啊。瞎折腾!”
孟蓓说:“不让你请罪就美了你!”
“我到底怎么啦?”
“你都说了我什么坏话?老实交代!”
“没有哇。”
“装得多像!”
“我说什么来着QXa/GDzJKvA+EW9fnTsrGQXSXLxcSqNpYAmK0RAzsuc=?你倒给我提个头儿。”
“你说我眼睛来着……”
“眼睛?眼睛……”辛小亮脖子一缩,眼睛一眯,鼻子一耸,坏笑起来。他瞟着孟蓓那俊俏的微翘的眼角,“我说你是丹凤眼啊……要不,要不怎么我看着那么……顺眼呢。”
“鬼!谁看着你顺眼!鹰鼻鹞眼,长脖鹿的个头儿……”孟蓓好像不把难听的话全发泄出来不足以平“吊眼儿”之恨。终于,她也忍不住笑了,“也就是啊,有一点还像个人!”
“哪一点?”
孟蓓挨他近近的,轻声说:“你呀,也还算个男子汉。”
…………
【作者简介】陈建功,一九四九年生,广西北海人,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曾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一九五七年随父母迁至北京,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后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找乐》,散文集《嬉笑歌哭》《北京滋味》《默默且当歌》《我和父亲之间》《岁月拾荒》等。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重要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捷克、韩、日、法、英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