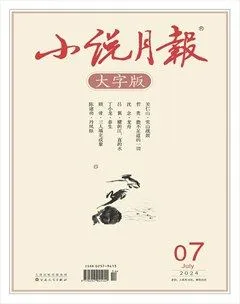横的江,直的水
一
酒是最有性的水,三两碗下肚,血就活了,腰就梆硬起来。脖子一伸,碗里的酒全入了喉。抹抹嘴,乌爷就要上船了。这次出行,不是一般的重要,船上的东西,说有多贵重就有多贵重。乌爷从方桌前站起,开始念咒,声音低沉,却字字都有分量。这段时间以来,他老是觉得诸事不顺,刚才喝酒,还被呛了一口,脖嗓眼儿寡辣。昨天出门,又被门槛绊了一跤。老伴责备他:“喝两口猫尿,腿脚都会划船了。”经常走夜路的人,难免会有失蹋的时候。经常下河的人,不湿身也是不可能的。“喝口酒咋啦!没有酒,能和这江扳腰?”老乌一发脾气,老伴就不吭气了。不吭气的妇道人家聪明。乌爷只要遇到咯噔绊脑的事,就念念咒,内容多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一类。江上行船者,皆师从鲁班先师。他们善木匠活,会鲁班尺,还能熟背鲁班经。此咒一念,啥乌龟王八、恶鬼䝚貀都会逃之夭夭。这咒不是骂谁,也不是让人下十八层地狱、断子绝孙那种。乌爷心善,他不念绝咒,不指桑骂槐,不挖根断苗,不刀来剑往。他这咒,更多是祈祷,是对好结果的臆想,是善咒,可以当着青天念的。乌爷有个说法,心怀善念,哪怕误跌暗洞,前边也会有盏灯。小骡子接话说:“乌爷,你那光是自带的。”
乌爷行船的地方,叫老鹰滩。金沙江到了这里,突然拐了个弯,积了两滩好沙,左岸一滩,右岸一滩,阳光下,亮晃晃地灼眼。那闪烁着金光的水,就只能突然地横了一下,转过身,再直直地劈下去。从无人机拍的照片上看,这两片滩沙,就像两只巨大的翅膀,平添了江岸的灵动。这里水面宽阔,流势缓和,但知水性者,都晓得这里面依然有着很多变化。再往下,就是浩荡的长江了。这里一直是人们过江的必经。乌爷打小就在这船上东岸西岸两边跑。有时也跑上下游,给要家送送货。最近,有些麻烦,上游不远处,一家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入驻,各种机械鬼喊乱叫,弄得山摇地动,黄汤直淌。看那样子,像给山谷掏心摘肺。据说,要不了多久,双向通行的大桥即将完工;据说,大桥还连接了两岸的高速路;据说,到了那时,开车到北京、上海,轻轻松松两三天就可以到达。果真如此的话,乌爷这船,注定就要寿终正寝了。乌爷六十岁挂零,经风历雨,死死生生多少次还能活下来,也算是功德圆满,应该含饴弄孙了。但他闲不住,坐下来就老想事。心动,脚就停不下来。他专程跑到县里,找到交通部门,找了一家酒店请客。乌爷几次要说话,坐首席的人只是笑,举起杯子说:“喝酒喝酒,不谈公务。”跑那么远,没得到一句实话,不踏实,但他又不敢多问。人家能接受邀请,也就是愿意沟通。人家说了这话,其实也是知道他的意思了的。知道了他的意思,却不明说,这就是官场中人的高明之处。末了,人家说:“回去等消息。”等来等去没有动静,春节前,乌爷提了两条活鱼再去,保安不让进了。打电话,那边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乌爷在大门边徘徊,看忙忙碌碌的车出车进,纳闷呢!再回头,却见大门边有巡视组入驻、有让大家提供线索的通告。乌爷按住怦怦跳的心,连忙走开。
越往后,越是觉得行船的时光不多了。乌爷做事,从来不会坐吃山空,该干啥还得干啥。念完咒,老乌抬脚刚要出门,不料有人趔趔趄趄冲过来,和他撞了个满怀。是小骡子。小骡子一脸惶恐:“师父,怪事!怪事!”乌爷皱皱眉。他不喜欢这种大惊小怪,只有没见过世面的人,才一点芝麻大的事就像裤裆着火。这小骡子,嫩。“啥子嘛?”老乌黑风丧脸。小骡子按住似乎要蹦出的心,上气不接下气:“乌爷,老……老鼠,一大帮呢,我刚到江边,看到它们在船上翻窝,不晓得咋个了!”
老鼠下船!乌爷大惊失色。这下跌跌撞撞的变成乌爷了。眼下当务之急,是把老鼠留住。他跳过门槛,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歪歪扭扭的石板路和沙滩,跨上码头,来到船边。一看,他傻眼了,那些老鼠,大约有七八只吧,有大有小,有胖有瘦,牵成一条线,已经从船板上下来。它们四只脚像雨点般密集,越过沙滩,便消失在芦苇丛中。最后一只,回过头来,朝他看了一眼,目光里有些怨,也有些挑衅的意味,它朝乌爷挤挤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乌爷喘着气,后脚挤着前脚,趔趄上船。船有些沉,已经到了船帮的水位线。举目四望,货物没有问题。乌爷回头,有几个人跟在后面,不知所措。乌爷挥挥手:“都是老天安排的,这活暂停。”小骡子问:“那,啥时可走?”“等通知!”乌爷说。“船上的东西要送,咋办?”小骡子又问。“听天由命!”乌爷发呲。
人人喊打的老鼠,在掌舵人心里,分量却重得不得了。金沙江上行船有个老规矩,船上得有动物,最好的是老鼠。老鼠机灵,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一,居老大位置。老鼠下船,是行船人的大忌。船上没有老鼠,就没有活力,就没有生气,这船就等于是死船。一直以来,老鼠在船上活得好好的,要吃有吃,要窝有窝,就是它们牙齿痒,啃坏了船帮,咬破了船帆,嚼碎了绳索,都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老鼠突然下船,是大麻烦。这事蹊跷,乌爷得弄清楚。人多,办不成事,看西洋景还差不多,乌爷让众人先回,自个儿往船上走。上了船,乌爷突然发现有个黑影,在船舱里蠕动,怪吓人的。昨夜清了仓,应该不会有人的,那是啥?是盗贼吗?水怪吗?是恶鬼䝚貀吗?乌爷擦了擦眼睛,那黑影还在。乌爷呸了一口,问:“谁?”没有回应,那黑物好像还在蠕动。“不吭气?我可不客气啦!”乌爷不怕邪,抓起一根铁棒,步步逼近,举起要打。那黑物突然站起,头一露,原来是青眼膛。青眼膛是个人,两只眼眶不同程度青了一圈,船上的人都这样叫他。乌爷松懈下来,扔掉铁棒,啐了一口:“青眼膛,你吓死我了。”青眼膛望着他笑,憨憨的。乌爷心疼,拍拍他敦厚的肩:“青眼膛,你整啥子,鬼鬼祟祟的?”青眼膛侧了侧耳朵,眼睛里有些迷惑。乌爷又重复了一遍,他好像是才听清。青眼膛说:“老鼠牙齿尖利,把油桶咬漏了。我收拾它们。”乌爷睁大眼睛:“你整的?”“我整的。我先用闹药,放在鱼肚里,它们不吃。我用铁夹和粘胶,放在角落,但它们也会绕开。它们脑壳够用,我一个也干不倒。”青眼膛举了举手里的高压水枪,“人还干不过它,不是丢丑吗?怎么弄它们都不走,还在船上躲来躲去,就用这,装上消毒液,直射。这不,它们全都逃了。跑慢的,只能去那里了。”乌爷回头,浑浊的水面上,几只老鼠漂浮在上面,随波蠕动,显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乌爷大惊失色:“青眼膛,你干的好事!”青眼膛有些惶惑:“师父,咋个了?”乌爷捶胸顿足,牙齿都差点咬碎:“老大不在,还开啥船!还找啥钱!憨脑壳!”青眼膛嘟囔着,难以回应。乌爷每次上船,第一件事就是给老鼠投食。乌爷看它们活蹦乱跳的样子,就会很开心,开起船来,内心踏实。乌爷发这么大的火,是他对命理的尊崇,是对这次开船的焦虑。
二
认识青眼膛,也是命里有。那年,乌爷往下游送货。主人当大事,要得急,棺木搬上船,天上就乌云堆叠。风来潮急,瞬间大雨如瀑。乌爷裹上雨衣,顶风把舵,久经风雨,他倒也不当回事。正要开船,一大一小两人被风雨卷来。大的是个女人,面目憔悴;小的是个男孩,一脸懵懂,憨乎乎的。两人紧紧拽住船帮,死活要搭上一程。原来,煤矿瓦斯爆炸,女人丈夫被煤块深埋,尸渣渣都没找到。煤矿公司通知她去谈话,签字,领抚恤金。要是去晚了,那边的负责人出差,财务就不再受理。母苦儿弱,可怜。乌爷心一软,拉拉扯扯,将两人拽上船来。乌爷见娘儿可怜,便将身上的雨衣脱下,顶在他们头上。自己嘛,湿了也就湿了,他也不是湿过一回两回了。既然上了船,他就都会竭力去护佑他们。
船在摇摇晃晃中启动。那儿子举着个憨脑壳四处观望。突然,他看见黑漆漆的棺材,脸唬得寡白。女人也看到了棺材,吓得全身哆嗦,将儿子紧紧搂住,不知如何是好。不想,更麻烦的事发生了。那棺材盖慢慢翕开,一只水淋淋的手伸了出来。接着,又一只水淋淋的手伸了出来,鸡爪子般抖动。再接着,是蓬头垢面的脑袋钻出来。女人大惊失色,大叫一声,站起来就跑,不料一失足,扑通一声跌进江里。江水湍急,漩涡翻滚,若不施救,肯定要葬身鱼腹了。乌爷好身手,一个鱼跃钻入江中。那个从棺材里钻出来的,是小骡子。来不及多想,他也跃入波涛。师徒两人费了半天力,将那女人拽上船来。
原来,当时小骡子正感冒,难受得很。乌爷一人行船,肯定不行,他就带病陪他。刚才在大雨中,他躲东躲西躲不住,便掀开棺木盖子钻了进去。迷迷糊糊中,他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呜里哇啦,呜里哇啦。他不知道发生了啥,又想着自己躺的是别人家的寿木,怕要惹祸,便挣扎着出来,不想就出事了。女人当时命还在,但半年后就死了。她不是因为这次被吓,而是被民间借贷公司骗了。民间借贷公司以每月六万元的高额利息,将她的六十万元赔偿金都哄走了。那公司做得露骨,第二个月就不再给利息。那是她男人的命换来的钱,要不回,她肯定不饶,就去公司找人。不料那原本富丽堂皇、人来人往的地方,已经关门闭户,一把铁链子锁,冷冰冰地将她拒之门外。她要踢门,旁边有人来说,原来的租房户早走了,这房子是别人的,劝她冷静处理,不要犯法。她找到派出所,掏出合同请民警看,才发现那名字、身份证号、公章、手印,全都是假的。气不过,她脚一抻,脖子一硬,“咕噜”一声咽口气,丢下儿子找男人去了。那儿子十四五岁,有人养,无人教,像条流浪狗。哪家有红白喜事,他就去踩煤、生火、守大夜,混口饭吃。村主任老母过世,他负责搬运,不想手酸,装碗的筐子落在水泥地上,碗烂了一摞。吃饭时,总管将饭菜倒在地上,让他去吃:“没有碗啦,将就点。”他趴在地上,像一条狗。吃了几口,四周有人哈哈笑。他觉得不对劲,站起来,看他的人围了一圈。他举起袖子,擦擦泪,“呜呜”哀号两声,走了。他半个月没在镇上出现,乌爷以为他死了,让小孩子们沿江跑两转,要是看到什么不明物体,赶紧回来说。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后,孩子们都没有带回半点有价值的信息。乌爷只好给派出所报告。左查右查,才知道他没有死,是下矿洞了。这家伙知道一坨煤就值一坨钱。在黑暗的煤洞里,他赤身裸体,四脚抠地,进去的时候拖撑木,出来时拖煤块,这样可以挣双份工钱。这天,他拖进去的撑木还没有撑好,“轰隆轰隆”几声闷响,无YjHYpyL3h/uxJmNro8smsQ==数黑暗落下,构成了他的全部世界。他的眼眶被一块煤打了个正着,伸手摸摸,除了湿漉漉的血外,其他似乎还好。退路阻断,他缩在撑木的空隙里,捂着伤眼哭泣。光亮没有,声音没有,四周只有乌黑的煤。他成了乌黑的一部分。看不见,他就使劲揉眼,眼眶都给揉肿了。他不敢伸手,不敢伸脚,仿佛恶鬼䝚貀就在左右。他想得最多的是,啥时候能有人将自己和这帮被埋的人当作煤块刨出去。这样,自己也许会值点钱。三天后,突然又是无数的响声和震动,他知道有人来救他了,便大声喊叫,用煤块不断地敲打撑木。半天后,一缕光刺得他眼睛一红一绿。有人将煤块铲开,将他拖出。有人立即用黑布遮住他的眼睛,但还是受伤了。他的眼伤好后,眼眶周围又青又紫。从那时起,人们不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青眼膛。那煤窑是私人开采的,出事后,据说老板蹲了监狱,连根毛都没有赔他。
青眼膛视力恢复差,三米外的东西都分不清,感觉到处是雾。耳朵呢,长时间嗡嗡响,像是江水涨潮。小煤窑被查封,青眼膛失业了,整天在江边逛。看到大江,他以为是柏油路,一脚踩进去,落在漩涡里。正巧乌爷船过,看见有人落水,乌爷跳入江中,将他救起,青眼膛又得了个活命。救下青眼膛后,乌爷继续行船,却在下游遇上大风,几次船差点撞在礁石上。虽然硬生生扳了过来,绕开了,但乌爷魂丢了一半。乌爷从船上下来,朝供桌上方的竹篓鞠了三个躬,那里面供有先祖和保护神的灵牌。乌爷从阎王爷门槛边逃回来,命大,他叫老伴炒盘猪肝,他得喝两口缓缓劲。爆炒的猪肝味重,满屋子热闹起来。刚端起酒碗,却见一个黑影在外面晃动,恍若熊罴。乌爷把酒碗扔了出去:“谁?”黑影过来,见他就擦眼抹鼻:“师父,请收留我!”仔细一看,不是青眼膛是谁?这小杂种就是怪,在哪出场,都是黑黑的一坨。青眼膛扑通一声跪下:“师父,在船上给我留个位,你指东我就打东,你指西我就打西,有口饭吃就行。”乌爷推开:“腰杆断了能成啥事?男子汉要顶天,更要立地!”青眼膛嗫嚅站起,努力将腰挺直。乌爷挥挥手说:“你回去,我想想哈。”
船是几个人合伙的,乌爷个人说了不算。晚上来了几个人,一说这事,都立即分头电话,四处打听青眼膛的情况。归结起来,意见不一,大多是反对。有的说这个青眼膛,一脸苦相,唯唯诺诺,背地里偷奸耍滑整不成事。有人说,他没得教养,行为没有规矩,怕会坏事。也有人说,他体力好,下得烂,用人所长。乌爷综合大伙的意见,最后还是决定留下他。两次救他,乌爷觉得这是上天安排,命里和他有裹搅。这些年,他在江里救人无数,但两次救过的同一个人,只有这个青眼膛。救人救到底,这是乌爷的原则。乌爷也是穷人出身,早年要不是有人出手相救,他早就喂了滩上的野狗、河里的鱼虾。青眼膛总算梦想成真,来到船上,倒也听话,只要是乌爷安排的事,没有一件他会落下。但没过多久,有人反映,乌爷不在时,他就不干活,一个人躲在船尾,噘着嘴,看着天,呜里哇啦吹口哨,像是饿疯的野狗在哭,让人心惊肉跳。乌爷在江湖上吃饭,对狗哭是忌讳的。这船是大伙的家,小骡子让青眼膛别这样,他不听,鼓起眼睛看他一眼,调过头,依然吹。乌爷听那哨声凄凉,知道他内心苦,就找他来问话。果然还有大事:他爷爷早年被疯狗咬,发癫疯,不死不活几十年,掉进猪厩被猪咬死,差点没有将肠肚弄出来,被好心的村民裹了床凉席,软埋了。爷爷死不甘心,偶尔托梦给青眼膛,弄得他心神不宁。乌爷掏出两百块钱,让他去买些纸人纸马、香蜡纸烛,到爷爷坟上祭拜。再回船上,青眼膛安静了。有人还是不放心,说:“最好让青眼膛走,不然,迟早还要出事。”乌爷没有理会,人活着,谁能离开事?谁不是在做事中成长的?既然上了船,就是自家人,手拐子哪能往外掰?风里雨里,淘来淘去好些年。
现在,老鼠弃船而去,有的还连命都丢在青眼膛手里,乌爷气不打一处来。“为啥要这样?”乌爷把青眼膛揪到一边问。这对于青眼膛来说,并不难回答。老鼠走到哪吃到哪,破坏到哪,人人皆知。青眼膛碗里的食物,一不小心,就会让老鼠吃掉,偶尔还在里面拉屎撒尿。船帮、麻绳、米袋,经常都给它们尖利的牙齿啃烂。青眼膛清楚地记得,自己被埋在矿洞里的头天夜里,衣服给老鼠咬坏了,咬了衣袖还咬衣领,咬了后襟还咬前胸。早上起床,提起要穿,全是筋筋绺绺。衣服给老鼠咬得如此,这是不祥之兆。矿难发生后,有人透露,矿洞里的撑木出问题,就是老鼠和类似老鼠的人干的。矿山的办事员贪财,收了不少的贿赂,得到的撑木是便宜货,加之老鼠的啃咬,撑力显然就不够了。撑木折断,死伤了一些矿工,撂倒了一大串活人。青眼膛他恨老鼠,有错吗?
青眼膛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不劳而获的家伙,显然是无可挑剔。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别说是弄死几只,就是把全世界的老鼠都剥皮掏心、斩草除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金沙江船上的老鼠,与其他人理解的老鼠不一样,它是船的生命,是他乌爷和合伙人的保护神。青眼膛干得这等好事,乌爷深浅不得,心口辣疼,一气之下,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思路还没有厘清,麻烦事就纷至沓来。先是收货方说如果货物不及时送到,不仅不给运费,还要求赔偿损失。再接着,又有人来电话说,这不是赔不赔的问题,他老乌根本赔不起,更重要的是,货不按时送到,带来的后果谁也扛不住。再后来,村主任也急匆匆赶来:“在上级的安排面前,有的事,可以不叫事。老鼠要下船,就让下吧!过几天让它再回来,不就行了吗?”
三
乌爷其实是生病了。别说开船,就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全身发热,流鼻涕,浑身无力,一咳就扯心扯肺。他天天在船上,接触的都是南来北往的人,他不先着,谁着?紧接着,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打摆子、拉肚子、发高烧、流鼻涕,吃啥药都不管用。活了大半辈子的乌爷,居然不清楚这病的来龙去脉,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村主任找人问了,都说不出个所以然。这种急毛病,来路不明,来无踪,去无影,难防难治。乌爷对老伴说:“啥怪病,不就是恶鬼䝚貀吗?”就硬撑起身,翻开老书,照着呜里哇啦地念,说是驱瘟经。早上念,晚上念,夜半三更还念。念了半月,并无大用。船上生了病的,都好不起来。原本还好好的,却冷不丁又趴下。大家互相戒备,歇了船,都不往来了。非得有事要做,就将脑袋套进大口罩,只是露了两个眼洞看路。小骡子年轻,抵抗力强,居然安然无恙。他戴上摩托头盔,弄得像个宇航员。他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偷偷来了两次。第一次背来一大筐中草药,金银花、板蓝根、鱼腥草、柴胡,糊着新泥,一看就是刚从山里挖来的。“连根带叶,炖了吃。”小骡子交代说。第二次送来的是两盒胶囊,说是药店买的。这药紧缺,村主任托过好几个人,也没有拿到,也不知道小骡子用的是啥办法。药刚入口,乌爷突然想起青眼膛,担心他也生病,可是,电话打了几十个,也没人接。乌爷吓坏了,担心他又出意外,让小骡子找找。小骡子就按师父的要求,船上船下看了一遍,江岸偷偷跑了两趟,结果也是徒劳。小骡子打电话给派出所报了案。乌爷随时提心吊胆,手机一响就一脸惊恐,生怕派出所打电话叫去认尸。
乌爷在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三个月里,小骡子没少来,但就是没有青眼膛的任何消息。檐后的杏树,遇到春天就控制不住,将粉嫩的花瓣撒得满院都是。乌爷熬完最后一锅中草药,站起来,试咳了两声,嗓子居然不痒不疼了。活动了两下,腰也不是太酸麻。老天没让自己死掉,就不应该等死。他趁着黑夜,钻过栅栏,摸摸索索到船上。船上一片狼藉,久未打扫,到处尘土,潮湿的气息糊了一层,伸手摸去,腻腻的。黑暗里,夜风汹涌,一阵紧过一阵,久违的感觉像猫在抓心。粗糙的手在机舵上捏了两把,乌爷双眼潮湿,想哭。沙滩上好像有人影晃动。乌爷大叫:“青眼膛!”一阵噼噼啪啪的脚步声,那人瞬间跑掉,成了黑暗的一部分。乌爷的电筒照去,只有沙砾上错乱的脚步。
乌爷没困时就开始睡觉,天没有亮时,又已经醒来。老伴给他竖筷子、烧鸡蛋、泼水饭,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预测乌爷的凶吉,将恶鬼䝚貀驱走。乌爷少了风里雨里的奔波,少了寒冷饥饿,天天有老伴做的好饭菜,乌爷摸摸脸,肉厚了一层,甩甩手,踢踢腿,捶捶腰,朗硬呢。这病居然一下子没了。乌爷盘算着要开船,约了合伙人商量了几次,货物的准备、启程的时间、简单的仪式都做了安排。想着船行江面,养眼的绿色和掠人的江风,想着又有钱可挣了,乌爷心痒痒的。
不料,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人,戴着口罩,提着公文包,说话和颜悦色,神情却异常严肃。说是纪检部门的,他们奉命而来,原因是有人举报了乌爷——说他收留人在船上住宿,说他借货运之机找企业拉赞助,说他船上载有违禁物品,说他打着治病的幌子破坏山上的林草,说他开船不按时走让客人老等,说他用了工却不给员工待遇,说他在船上养老鼠致使瘟病传染……乌爷脑袋发木,真真假假的事,屎尿一样往他头上泼。他还没有说话,小骡子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放屁,是左眼瞎,还是右眼瞎?我家乌爷,从不偷鸡摸狗!”两位同志算有耐心,好言好语,找了相关人员,一一核实,知道乌爷并无差错,让乌爷写了个说明了事。小骡子说:“不写不写,我家乌爷又没有干坏事。”乌爷接过笔,喝道:“别牛厩头伸出马嘴来!”
提公文包的人离开后,乌爷想来想去不得其解。小骡子说:“想想,青眼膛……”乌爷气粗:“给我理由!”小骡子说,青眼膛行为怪异,不仅将船上的船老大赶走,瘟病来临期间还在船上生火做饭。小骡子担心他将船烧坏,让他下船。他不走,小骡子再说,他就一拳打来。小骡子将他的东西扔下船,要他好好想想再说,底线是别忘恩负义。但青眼膛并不买账,他说人间太黑暗,所有人都在整他。“乌爷,船上的东西,除了你我,其他人是不晓得的。他在船上待这么久,不翻个底朝天才怪。”
乌爷得上船去看看。这段时间,青眼膛在船上生活,是他安排的,其他人包括小骡子,并不知晓。乌爷刚上船,便发现有个黑脑壳在晃动。他多了个心眼儿,手操铁棒,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那黑脑壳,不是青眼膛是谁?青眼膛举着一副望远镜,看看下游的江流,又看看高处的天空,见乌爷来,脸梗住了。“以为你走了。”乌爷说。青眼膛说:“师父你收留了我,这里就是我的家……”“有人找我问话,在你看来,我有啥不对的吗?”青眼膛听不清,看着他傻笑。乌爷凑近他的耳朵说:“有人举报我,你知道是谁吗?”青眼膛好像是听到了,表情很复杂:“师父,我要是干坏事,天杀雷打,断子绝孙。”青眼膛发的是毒誓,倒把乌爷僵住了,一脸尴尬。这样,倒是自己多心了,小了。
想不明白,乌爷认为是恶鬼䝚貀还没有走开。恶鬼䝚貀的恐怖在于,先折磨人的肉体,再折磨人的灵魂。刚到村口,乌爷就见老伴坐在那里,面前的案板上堆了几根萝卜。老伴手提菜刀,把萝卜剁碎,堆成小人的形状,一边砍,一边骂:“剁小人,剁小人,剁断你的骨头,剁断你的筋!剁小人,剁小人,剁碎你的骨头,还有你的魂……”仿佛背后使坏的小人,会在她的菜刀下碎尸万段。乌爷将老伴拖回:“嚼啥筋!炒盘猪肝,倒碗酒来。”乌爷叫来村主任,两人边喝边商量。村主任认为事情不大,谁告也没用,更何况,有他在,啥乌龟王八也翻不了天。不过,如果身边真有恶鬼䝚貀,别迁就,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会骑在你脖子上撒尿。酒一入口,身体舒泰了些,愁肠却又在心头扭结。小骡子找了对岸的画师,画了钟馗右手举剑、左手捉鬼的画像。乌爷看到,高兴得不行,立即就挂在堂屋,像是有了保护神。小骡子又买来护肝片,他吃了几片,感觉神清气爽。
夜里,小骡子跑来:“乌爷,师母剁的小人,放在村口,给人破坏了。”乌爷站起来:“真的?”小骡子给他看手机:“我守了几个小时,这是我刚拍到的。”里面一个黑脑壳,摸摸索索走来,一脚将那剁小人的菜板踢翻,又摸摸索索地走了。乌爷脸色寡白,双腿一软,颓然坐下。
四
江上的大桥说通就通了。政府部门和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来了不少车,桥头红红绿绿挂了布标,悬了彩球。领导讲完话,路口的栅栏拆开,长长的车队有序而过。这一天,也就宣告渡船再也没有大用。乌爷和合伙人商量,预备把船卖了,再放下去,也只剩下腐朽的份。大伙没有太多意见,都分别在朋友圈、视频号、抖音里发了卖船的消息。眼下,生意萧条,很多人都懒心无肠,谁还在乎这无用的破船。几天过去,乌爷没有接到任何一个询价的电话。乌爷通知大家,再去船上看看,把自己的东西都拎走,预备把船拆掉,当废品卖掉。这样一说,个个儿心下难过,有人居然揉眼抹泪。乌爷硬着心说:“船拆了,你们的空间更大,也不能靠一只破船养老。”
正在这时,村主任骑辆摩托兴冲冲地赶来。乌爷说:“这船就要四分五裂了,你正好来,这样,当中你有一份,看上哪些,你先拿。”村主任摆摆手,让乌爷把船留下:“别泄气,老路堵了,新的机遇又来了。船不能拆,要留下来。我们用来搞旅游嘛!这老鹰滩,可是方圆几十公里最好的景区。到时,你的收入怕是现在的好几倍。”乌爷问:“那我干啥?”村主任说:“开船啊,拉着那些游客顺江下去,晃几下,再逆水上来,再晃几下,钱就像这江水,“哗哗哗”淌来了。黄浦江上,夜夜灯红酒绿,天天财源滚滚,靠的就是这个。”船失去了本来的功能,成了摆设,没多大用,还钱不钱的,乌爷没有兴趣。乌爷不看他,喃喃自语着,大约又是在念啥祈福的咒。末了,乌爷说:“各位,带上工具,船上见!”
到了沙滩边,小骡子从船上跳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乌爷,快看,船上……”乌爷不明白他在说啥,一脸茫然。小骡子伸手来拉他:“乌爷,你仔细看,老鼠上船了!”船老大回来是喜事,是大喜事!乌爷在小骡子的搀扶下,三步并作两步奔过去。一群老鼠争先恐后,正往船上爬。跳板上,好像有不少诱饵。
“是谁干的?老鼠……”乌爷问。没有人回答他。乌爷四下里看了看,合伙的人都在,唯独没有青眼膛。前几天,青眼膛曾来乌爷家门槛外跪哭:“乌爷,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乌爷心冷如灰,无心再搭理他。第二天早上,老伴开门,院子里一个潮湿的跪痕。后来,小骡子曾到处找他。在矿山上,有人说见到过他。一个很黑的夜,青眼膛头顶萤火虫一样的矿灯,拖着一车撑木,钻进比黑夜更黑的煤洞,就再也没见出来。
村主任的摩托追了过来,一个急刹,跳下车来。村主任没有生气,相反,脸上露着笑,有些意味深长。他拍了拍乌爷敦厚的肩膀说:“听我的,没有错。”乌爷不想笑,也没有承诺。虽然作为老大的老鼠已经上船,这是让人高兴的事,但江水烈过酒,横来竖去,漩涡纠结,深不见底,其间暗礁令人防不胜防,且船事复杂,若真要开船,也还得认真琢磨。
原刊责编 段爱松
【作者简介】吕翼,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云南省“云岭文化名家”;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边疆文学》《大家》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部);有小说入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和多种选本;出版有《寒门》《肝胆记》《比天空更远》《马嘶》《生为兄弟》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第十一届湄公河文学奖、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首届青稞文学奖、第二十九届梁斌文学奖、云南文艺精品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