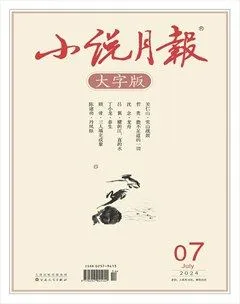三人填充成象
前书
早年,水墨这只小奶牛猫尚在家中嗲声嗲气时,朱琺先生埋头于四方墙壁以书砌成的斗室中,做关于安南志怪的种种研究。他俯首时,水墨总盘绕在书桌前嗅探他诞下的墨水。那些墨水更多是注解,是缭绕于正统文字四周的种种小文字。朱先生将此命名为“琺案”,后来索性拎出来单独成篇,以作互文。偶尔,不甘于嗅探的水墨会以猫爪充当朱先生的钤印,朱先生便在旁呆笑。这段记忆太过紊繁,如今朱先生也要通过好一番抽丝,才能把它从书房往事中标新出来。这一同位素标识法首先点亮的节点是水墨的褪色。大概是因为在梅雨季,一连多日的潮湿闷热煨炙着水墨,让小家伙不安于待在书桌上嗅探墨水的气味,又或者是因为雨中的顿悟,让水墨通过嗅觉识别了琺案上的墨水:安南,不安于南。总之,不安于斗室中的水墨离开了朱先生,去往四通八达的野土地,遍寻不见。
寻找的过程是艰难的,寻找水墨不成之后,朱先生接到编辑《安南汉文小说集成》的任务,那是笼盖着包括越南与粤地在内的庞大体系,他从此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往墨线所指的南方寻找另一种水墨。巨著告成时,他带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白咖啡、越南砧板和装进肚子里的屈头蛋,也带回来许多幅画。那些画用更小的图案作线条画成,比如拿小兔子拼出的大骆驼,或者用小乌龟凑作的千里马。朱先生称之为细密画或画里有画。他钟爱这样的画像,也请画师给妻子画了一幅素描,素描的线条是妻子的名字,这种根茎促成花果的植物性浪漫,深得妻子青睐。
在安南,最让朱先生忘不了的,是作为画家的巫师阮氏慧女士。在越南的日子里,朱先生常跑去请阮氏慧作画,以至于临走前,如古铜铸成的阮文强伸出五根手指,善解人意地暗示朱先生,越南媳妇的彩礼统一以五千元为准,换算成越南盾,是皇皇一千五百万元。阮氏慧在手势旁脸红,朱先生大窘,解释自己只是为了买画,几乎到了要走遍每一个安南当地祠堂赌咒发誓的地步。回来后,他常想起这段往事,不是回忆人,而是试图在脑海中打捞那只孤象。
朱先生记得是在取回给妻子的画的下午,阮氏慧找到他,告诉他有一只迁徙中离群的孤象在往他们的村落走,她的哥哥阮文强带着刀叉将孤象制服。孤象被捅出许多伤来,血流汩汩,阮氏慧请朱先生一同前往救治。
朱先生对象的兴趣是绝伦的。他手头正在做的安南志怪研究里,便有关于飞象的神话——阿Q在一只象形的气球里填充满飞鸟,从而生成一只飞象。这与阮氏慧擅长的“画中有画”若合一契。他请阮氏慧画一只以小鸟图案为线条,编织成的大象。阮氏慧却很着急,没有理他。他边同阮氏慧走,边向阮氏慧科普象的怪谈。事后想起,他之所以那么不解人意地对阮氏慧喋喋不休,是因为在陌生的越南,阮氏慧是为数不多的懂汉语者。由此,他又想起大象并不常见于中原的志怪之中。在历史的囹圄里,大象逃狱成功,退出了主流的话语藩篱,像自己的水墨一样,来到了野土地。
典籍中的越南大象是刚硬的,据传甚至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用鼻子卷起负心人,而后抛掷在空中,用牙齿将其戳死。这得益于其嗅觉,自家的猫咪水墨曾经也爱嗅探,可现在它却迷失在了高楼里,把着钢筋不应朱先生的呼唤。朱先生很想念它。
眼前的孤象更可怜,鼻子软塌地垂在土里,呼出的气吹在三叶草上,间或喷出些许血沫。朱先生抚摸那些皮肤的褶皱,他研究过象,却更多是针对象的延伸。如今象的眼睛湿润,对准朱先生,像两道处死哥斯拉用的射线,使他浑身发烫。后来他查阅更多关于象本身的资料,从而得知,象鼻更多时候是鼻而似非鼻。它如舌如手,灵动自由。长鼻由四千块以上的肌肉性静水骨骼组成,这样富足的肌肉,使得它能够单纯以肌肉来完成骨骼与关节的功能——抛、拾、甩、掷。朱先生又得知象的鼻子拥有两千多个嗅觉受体基因,是狗的三倍以上,便在书桌上遐想起来:那只象没准当时也能闻到我身上残留的水墨的气息。如果孤象如今在我身边,那它一定会替我嗅出水墨的踪迹。这些后来知道的知识无法穿越回去,朱先生在那一刻,只知晓象鼻如人鼻,是呼吸管道,并由着《动物世界》种下的记忆明白象鼻还可以充当花洒。朱先生半蹲着抚摸象的头颅,象感激地用象鼻去轻轻反触朱先生的脸颊,血沫呼在朱先生的圆框眼镜上,朱先生先天的满头鬈毛被吹得飘逸。
阮氏慧请朱先生帮忙用手扶住被刺伤的象鼻,竭力上药。阮氏慧说,孤象离群的十三天里,村民的芭蕉林和蔗田被大面积毁坏。阮兄是英雄,替村庄保住了许多人命,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他注定是村庄的好人。
朱先生看着象的眼睛,实在不忍附和这句话。他问阮氏慧村民打算如何处置这只象,阮氏慧说,它会由我处置,我会骗大家说它是神灵附体来传话给我的灵物,我会救它。
朱先生与阮氏慧合力在阮家村郊的瓦房旁搭建了象棚。那些日子里他日夜砍伐,牛奶被高温惹得馊臭,原本白净的皮肤因此渐转古铜,而古铜般的阮兄在旁讥嘲地看着他们,像看待那只象时一样冷漠。朱先生寒栗,想起阮氏慧是村中德高望重的巫师,医人医兽不过是通灵的附带,便自欺式地信任她的话语权。他害怕阮氏慧不够格,又不自信地以学者的身份向阮文强强调,那只象,奇妙的,奇妙的,杀不得。朱先生并不太会说越南语,他按着英式越语的拼法,将译作奇妙的K?伥diêu念作key due,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服阮文强。
在越南搜集汉文小说集成的最后日子里,他频频前往象棚注视那只孤象,自觉已成为那只象的一部分,这种关联似乎是脐带式的,他像舍不得水墨一样舍不得那只大象,如同婴儿依偎乳房。
左象
阮文强从阮氏慧那里接手孤象时,和阮氏慧大吵了一架。阮氏慧那套巫蛊的把戏,他是不信的。两个巴掌扇过去,和吃草药后发蒙的样子也大差不差。通灵通灵,一巴掌把天灵盖扇到通风就灵了。什么神啊鬼啊的,村里人信,自家人还信吗?他连夜动炉子,做了象钩,钩在象身上反复试了几次,象按喇叭般吼。痛吗?痛就对了,糟蹋那么多芭蕉甘蔗,总该遭罪。象吃痛,异常驯良,他也依旧用赶制的锁链锁住它不放。这只象是亚成体,他自觉够格做老师开始上课。青少年的人也好,象也好,都是最宜在教育中学习的。阮文强教育这只象搭载人,教育这只象搂住游客,时不时佐以象钩伺候,象学得很快。某天,阮氏慧回来喂象芭蕉,象用鼻子搂住阮氏慧,阮氏慧霎时软下来,阮文强便知道,自己的教育是如此有成效。他拥有独有的会讨好人的象。这在以前很常见,如今却是怪谈。他跑去市镇,和办戏团的中国人陈隆大喝酒,陈隆大最喜欢看戏,他用鼻子喝酒给陈隆大看,陈隆大开心得像个孩子。有一瞬间,阮文强有像教育象一样教育陈隆大的冲动,他自觉是喝酒喝昏了头,强忍住了。他觍着脸,和陈隆大签了协议,定期把象弄到市镇的戏团表演,由此赚了一大笔钱。陈隆大不知从哪儿搬出的古老词典,不许他自称驯象师,而要叫作驯象卫,他觉得没差别,就听了陈隆大的。这帮人和之前来的那个朱先生一个样,爱装神弄鬼。
演出进行了几次,最初的表演项目是搭载乘客和泼水游戏,比较初级,后来,他怂恿陈隆大架设相机供大家和象合影,合影只收两万越南盾,加象鼻搂抱服务的,收四万越南盾,戏团每天爆满。陈隆大说:“你不要天天来,一周来一次,观众的新鲜劲就一直在。”他很相信陈隆大的判断,也趁机清闲,用赚的钱装修了祖宅,打理了象棚,还说了门亲,每天在家做新房的监工。
他富起来了,孤象也乖,并不忤逆,几乎用不着打便很听话。阮文强吹嘘是自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功劳,这让阮氏慧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阮氏慧是最看不得他打象的,为了摆出一副好人样子来,阮文强把象钩扔到地上,摊手念:“象,好象,听话的象,不用打。”阮氏慧笑,他还拿芭蕉和阮氏慧一起喂给象吃,象尽数吃了,也分一瓣给他。
平时,阮氏慧也会像朱先生想起她一样想起朱先生。这样的想念是无关风月的,全都赖在一只象上。朱先生告诉她,象就像中原文化一样,一路南迁到安南来,变成了新鲜事。就像朱先生手头的工作。朱先生说六千万字的书,好像到头来也只用得到十几万字而已,但毕竟是安南人用汉字写的,所以很难得。这她懂,几千的越南盾,到头来不也只值朱先生手里的一块钱,在安南却是最基本的东西。
朱先生还给阮氏慧讲汉诗,讲六八体,她就学下来,写祭祀词,想着显得更专业一点。朱先生说他在广西边境的村里遇到一个越南媳妇,写了一首让他很是忘不掉的六八体,他常念诵。
无家欲说喑哑,思家望尽天涯路呀。
寒鸦笑我囚枷,谁怜我体留痂与疤?
阮氏慧想着朱先生朗诵那首拗口诗的样子,用手掌掩住唇舌发笑。朱先生还和她说:“汉话里想象、幻象、意象这些词,和大象是脱不了干系的。”大象的边缘化,让他难过。
她听不懂这些,但自有另一番理论来体察。村人不再信奉她的通灵了,经常她开始舞蹈时,孩子们就在台下捣乱,阮文强也带头嘲弄她。她知道自己正在成为孤象。她一直陷在这样的思考里,心不在焉地喂食孤象,也喂食自己。阮文强为了赚钱,和孤象外出的频率越来越高,她越来越孤独,想起还没有画朱先生不经意提起的小鸟作为线条的大象,便不厌其烦地画起来。阮文强回来见了,也不耻笑她。偶尔站在她背后观摩,看得她头皮发麻,擦擦改改,总觉得自己画不好。有一天,她看见阮文强在拿牛角刀削木枝,刻成两个十字架的模样。她问阮文强在做什么。阮文强说,让象画画试试。她不同意,挨了巴掌,眼睁睁看着阮文强把那东西插在象鼻上,流出血来。象从未发出如此凄绝的长鸣,如同抛锚的轿车引发高速路上大堵车时才能听到的喇叭合唱,震耳欲聋。那些车子卡在路上,耗到汽油燃尽,也成为抛锚的一员。她眼睁睁看着大象驯良地绘画,阮文强让她教它,她不愿,阮文强就自己教,无非是画根香蕉或树或笑脸,但水墨都刺在了她的眼睛里,烙下印,再忘不掉。
阮文强找到了赚钱的新途径,陈隆大大喜。他是最会出主意的,问阮文强:“让象给人画像可以吗?”阮文强说:“人都画不出来的东西,象也难画。”陈隆大说:“难才有钱赚。让它写名字也行,先拿我的名字来练,‘陈隆大’。”
“我自己都不会写自己名字,叫象来写个卵。”阮文强不屑,“要不然叫象画自己,得钱吗?”
“象的自画像,得得得。”陈隆大两眼放光,“就练这个,就练这个,你教它画。”阮文强便应允下来。他回到象棚,还没到阮氏慧来送晚饭的点,便想着马上教象画画试试。他想阮氏慧每次来象棚看见他教象画画,象没出声,她就先像条狗一样呜呜起来,烦得很。这样想着,他在纸上用笔画了一只简笔的象,又把画挂在画板上,往象鼻插画笔,示意象画。象却石化般不动了。他觉得奇怪,抓起象钩往皮里扎,象前膝跪下,扬起尘来,没有叫。他又来了一下,象鼻便动了,他放下心来,却见象鼻挥动,如一道灰蒙的鞭子抽在他脸上,他眼睛一黑,随巨力飞出。即将晕过去时,阮文强听见妹妹的尖叫。
右盲
成为盲瞽后,阮文强的世界弥漫起雾来。他向妹妹精确地形容这雾的森罗。他说:“雾和我眼前的暗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世间的雾都是在阮文强被巨力甩出那一刻造访的。那一天,还有许多大事发生,比如远在千里之外的朱先生的编纂工作被校方否定为无用的废纸,又或者那只孤象在甩晕阮文强后真的画下一幅自画像来,阮氏慧发现那幅画里没有长鼻。然而相比这折磨人余生如一日的雾,这些色彩斑斓的事物都黯淡下来。
那年的中秋节,一群孩子在泥路上互相甩着炮,吵得阮文强半梦半醒,阮氏慧忙着在无数庙宇间穿梭,她请神上身的技法得到了瞩目。祈福舞跳到一半时,瞥见台下孩童的脸,阮氏慧就想起自己第一次随阮文强去戏团子看那只孤象演出,自觉羞耻。扮演女神的妩媚能力消失了,她一下子成了僵硬的机器人。可即便如此,这舞姿却仍成为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是无人在意的背景,又是许多人在意的伴奏,有她的舞,狂欢才有理由进行,有就好了,跳得怎么样,并不重要。她想起朱先生在安南时,亲历过这场盛会。那么多年,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认真地看阮氏慧跳祈福舞,还录下视频来,说要写考据文章。朱先生告诉阮氏慧,他给这场盛会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安南女巫代表大会”。阮氏慧想起他,为他祈福。
阮文强是看不见这些事情的。整个中秋节里,炮仗声隆隆地轰着他的耳朵,但这不影响他睡过去。视网膜脱落后,他便无比嗜睡。村民将他的嗜睡归咎于眼瞎,虽然歪打正着,却没有人究其物理,只惊讶于他竟然一反常态地温驯下来,没再叫嚷杀象。刚失明的日子里,他反复地发高烧,清醒时总尽力如呕吐般喷出文字,请妹妹杀掉那只象。成年后,他第一次在妹妹面前落泪,哭着醒来又睡去,又在睡梦中哭着复醒。他总告诉妹妹,自己没瞎,自己还能看见。阮氏慧却并不相信。好几次他的怒气想从双瞳里面射出,让妹妹别吵醒他睡觉,自己却被一片雾牢牢笼住,无从发泄。他感到痛苦。
彻底清醒过来时,阮文强才意识到他真的失明了。那些昏迷时自以为没瞎的呼喊却不是自欺,而是后天失明者必临的宿命。他通过实践知晓,后天全盲者是能够做复明的梦的。在梦里,他如冯虚御风般飞奔,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村落。他肆意地吃喝放纵,闲下来时就仔细地打量起自己的手。他伸出五指在面前挥舞,拉长又放近,几抹朦胧的肉色在满世界的雾里忽隐忽现,世界多彩,他傻笑着醒过来,喊阮氏慧杀了他。
他说:“你杀了我,我能看见。”
阮氏慧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我能看见。”
阮氏慧说:“我请神时,没请过瞎子,因为瞎子看不见路,附不到我身上。”
他说:“你把草药捣碎了,每天给我点,让我睡过去。”
阮氏慧没有说话,阮文强感到恐慌,他大叫:“阿妹。求你了,阿妹。”现在,他不再叫妹妹阮氏慧了,他叫她阿妹。阿妹没有回应他,过了一段时间,他闻到一股草药香味,便笑起来,“阿妹”二字成了呓语,他又做起梦来。
最后得知阮文强眼瞎的是陈隆大。他从市镇赶来,陪在阮文强床前半个小时,阮文强一直不醒。他就出门打了通电话。下午,来了一批人,嚷嚷着把象弄走,阮氏慧拦在象前面不许。这些人吵醒了阮文强,阮文强叫妹妹过来,妹妹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摸索着取下墙上挂着的刀叉,让阮氏慧扶他出去,对陈隆大说:“我明天就要杀象,它害我瞎了眼。”
陈隆大嘲笑他:“你是盲佬吹蜡烛,不如把它留给我,我替你杀。”阮文强循声,听见孤象的喘息,他踱着步挪到孤象旁边,摸着象腿说:“这只象只听我的,你们不滚,我让它也把你们弄成瞎子。”陈隆大挥手让手下上来抢,阮文强咳一声,象果然灵动地挥起鼻子来,阮氏慧把锁链从桩子上拔开,孤象冲出去,吓走一批人。陈隆大说:“你还我象。”阮文强拍象背作回应,孤象从水桶里吸水,把陈隆大冲在泥地上。阮文强说:“你再来,我死给你看。”
他真的动手,用的是象钩指住胸膛。陈隆大不信邪,说:“那你死。”阮文强便挥钩。仍是那只象,把象钩甩出去了,用鼻子卷起水桶,往陈隆大身上夯。陈隆大走前,阮文强的胸前已经是一片血迹。这次他又昏了过去。阮氏慧照顾阮文强,又是五六年了。她时常持续性地发呆,呆立着想念朱先生。现在,她和阮文强都废了,阮文强赚钱时说好的亲跑掉了,她自己带着一个废人,又做灵婆这种活计,也是没人要的。两个人连同象一起住在村郊,像是在坐牢。
中梦
偶尔醒来时,阮文强便在象棚里摸象,陷入长久的呆滞之中。他常把攥在手里的蒲扇大的象耳当作念珠来盘搓,靠触感数清楚每一道褶皱;或示意孤象蹲下,让他爬上象背的座椅。总之,阮氏慧在外采草药时,阮文强都陪着象。偶尔采完药回来早,她能听见阮文强在和象说话,那些话她听不到。她赤着脚过去想偷听时,阮文强就说:“阿妹,你回来了。”然后便不再说话。
她不知道是象在报信还是阮文强能听见她来的声音,总之这些话语成了盲人的秘密,让她想窥探而不得。阮文强成了气球,既不炸开又不泄气,眼看着一天天胀了起来,藏了一肚子心事。要像朱先生口中那只飞象一样飞起来。她在饭桌上问阮文强:“梦还好吧?”
阮文强说:“不好。”
她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低着头替兄长难过。又过了很久,大概是把嘴里的米嚼烂了,阮文强说:“越来越瞎了。”
阮氏慧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只他自己懂。他被蛰伏已久的浓雾彻底吞食了,失明日久,梦中雾越来越浓,让他在梦里也看不清楚东西了。梦渐趋于恐怖,他日复一日地被象鼻抛起,被象脚踩死,被象身撞开,却连象也看不真切了,象如同一团黑色的球,压过来让他体验上天入地。他早料到了这一点,每每安定地醒过来,并不闹,只是试着练习不再睡觉,一困就掐痛自己。有生以来,他觉得自己成了那只被驯的象,孤零零。从此,阮文强醒着的日子比以前多了许多。他不再嗜睡,阮氏慧说:“你不能连觉都不睡了。”他说:“我每秒钟都在睡。”阮氏慧说:“我搞点草药回来,让你做舒服的梦。”他说:“从来没有舒服的梦。”后来,阮氏慧问过久别重逢的朱先生才知道,后天全盲者的梦多数是噩梦,一开始贪恋做梦不过是为了没瞎时记得的色彩,越往后梦却越歹毒,全是灰蒙与恐怖。朱先生说,无论梦里梦外,阮文强都注定是一个只有体感在的盲人了。
阮文强不告诉阮氏慧的是,他偶尔也会梦到朱先生,梦到那个白牛奶般的书生,披着一头鬈发,笑吟吟地骑在象背上追他。在逼仄的黑暗巷子里,朱先生与象拼命蹍他,叫他崩溃。
阮文强便也试着骑在象背上,那是他失明后第一次登临,他和象说了许多话,求它放过他,别再在梦里追杀他,几乎跪下来磕头,而后自己爬上了象背,对象说:“我们一起走,我们都是象。”如果这些话被阮氏慧听到,阮氏慧大概会觉得兄长彻底疯了,又或者告诉兄长,我也是一只象。
阮文强第一次骑象出走时,阮氏慧正在给他采草药。她怕劣药让阮文强陷进噩梦里,就往深山走,采药的时间便越来越久。就是在这样久远的冒险里,阮文强一个人骑上了象,引导孤象走出象棚,去山上找她。一人一象出门,邻家捡垃圾的阿奶喊他说:“强,久不见你了。”阮文强回他:“阿奶,你以后天天能见我,我天天出来。”他说着,用脚踩孤象的左背,孤象受启发,在泥路上左转,往山里去。好在那天阮氏慧回家早,才不至于让一人一象远行迷失。阿奶却自以为象真识路了。她进村里,去市镇,把垃圾捡到袋里,把这事四处说出去。说阮文强成了象人。大家信奉赞叹,只陈隆大立刻赶到村里,请阮文强带象出山。
“不让画,不让骑,搂搂人也是好的。”他劝道。
阮文强犹豫许久,同意了,于是陈隆大每天派人接他和象进城。象的复出典礼是盛大的,市镇万人空巷,人人挤着要和一人一象合影。阮氏慧跟在旁边守着阮文强,她放心不下这一人一象。一连待了三个月,戏团人少了些,陈隆大却坚持让阮文强每天都来。有次表演,陈隆大邀阮氏慧去吃饭,她去了,便把阮文强和象留在戏团里。陈隆大请阮氏慧喝酒,问她会不会像阮文强一样用鼻子喝酒的戏法,她也能用鼻子喝,但不想演给钱眼看,就不说话。她估摸着时间,不顾陈隆大拦她,匆匆吃完就一路赶回戏团去。到戏团时,她才发现陈隆大的马仔摆着一幅画在孤象和盲兄面前,请象作画。盲兄在象背,自以为是地命令孤象搂抱观众,还时不时拍一下象背,说:“下一个。”
阮文强幻想着象鼻挥开后,会有下一个游客进入怀抱中,却不知道自己成了指挥作画的家伙。直到阮氏慧哭着冲上来喊,他才反应过来,也哭着喊:“陈隆大,你恶!你恶!”
他踹象背,示意冲刺,阮氏慧冲上前去解锁,象鼻轰鸣,蓄水池里的水被它吸上来,尽数往人群喷去。人群一哄而散,阮氏慧和象在劈开的道路中赶回村里。陈隆大没敢再来找他。
阮氏慧不去采草药了,她每天在家里守着这一人一象,闲着没事干,就画朱先生请她画的那幅画。画纸攒了好几炉火,始终没画好。阮文强问:“你这是在给我烧纸钱吗?”
阮氏慧不答。
后离
五六年来,朱先生总忘不了自家的水墨。每每在中山公园之类的路上遇到流浪猫,都会试着唤水墨的名字。他听信喂食流浪猫后请流浪猫找猫的传说,经常带着罐头与照片外出,却永远只带着照片回来。他继续写书,赖于那两年在越南的经历,他写了一部注解安南志怪神话的书。有几篇故事就配几篇琺案,编辑请他参与自家书的设计,他附上几张有水墨爪印的琺案手稿在扉页;又请求封面画师画只飞象,画师换了四五个,总画不好,出书便耽搁下来。朱先生知道自己想要哪种画,他常看阮氏慧送给他的几幅细密画,想着把飞鸟填充成象。
他常常向周围的人讲安南救象的往事,他说话太慢,大家怕了他,往往他一开口就扯开话题,并不愿听。他便把这事讲给妻子,妻子听进去了,也说:“有机会该去看看那只象的。”他说:“是该去看看,是该去看看。”
他着手准备安南汉文小说补遗的新项目,但几次申报都被驳回,便不得不放弃了,连带着放弃的,似乎还有手中的教职。在非升即走的体系里,他似乎注定要走一趟。实在不得已,就往越南去吧,他想去,但又迟迟未成行。某天他在课上给学生讲课,不得不援引想象、幻象、意象等词汇时,又牵动了对那只孤象的思念。他顿了顿,学生却没有反应,多是埋头看着手机,他走下讲台,看见一个学生在看象照镜子的短视频。学生惊慌地关掉软件,他示意学生点回去,他说:“我想看看那只象。”
课堂俱寂,学生打开软件,视频里,一只象不断在镜子前搔首弄鼻,解说词讲,象的自恋,是在鼻子上的,因为鼻子是象身上的万能器官。
朱先生发着愣,想起那只象的鼻子如舌如手,对学生说了声“谢谢”,又回到讲台上接着上课,他讲自己救那只象的事。没讲完,下课时间到了,几个学生让他拖堂,他看到后排不耐烦的脸,笑道:“下回分解吧。”
朱先生回到家,犹疑着和妻子说:“国庆快到了,我想回越南一趟。”妻子立刻知音,她说:“你这个爱玩文字游戏的家伙,你这一趟,明明是‘去’不是‘回’的。”妻子看出了他的魂不守舍,他觉得妻子的鼻子,也如象般灵敏。
他买了当天的机票,飞去南宁,又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入境。一路来到阮家祖宅,象棚依旧,祖宅却空无一人。他立在象棚前,发了很久的呆才远远看见一个疲惫的女人拎着一背篓草药回来。朱先生用蹩脚的越南话说:“好久不见。”阮氏慧用汉语说:“欢迎回来。”他步入正题,问:“象呢?”阮氏慧说:“走了。”
他怅然,说:“走了是好事,总该自由的。”
阮氏慧低下头说:“和我哥哥一起走的。”
朱先生这才记起来如古铜般的阮文强,说:“他怎么样?”
阮氏慧说:“好多事,慢慢说。”
她请朱先生进瓦房,朱先生进去,看见地上铺满被踩脏的纸,他低头看,发现就是他请阮氏慧画的充满鸟的象。他问阮氏慧:“你画了好多遍?”
阮氏慧说:“我画好了的,晚点给你带回去。”
朱先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又转头去看那象棚,想起自己的水墨来,长叹一口气。他坐在板凳上,听阮氏慧讲这五六年里发生的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天彻底黑下来,两个人才意识到没有吃饭,阮氏慧说:“我先做饭。”
阮氏慧去做饭,朱先生便低头看那些画,一幅幅画铺满世界,炉里也装满纸灰,他觉得自己闯了祸,自责让阮氏慧画了那么多幅画,却想不明白阮氏慧为什么画得差了许多。他看那些画时,发觉阮氏慧的象鼻总画不好,或短或长,或粗或细,似乎总不得其神韵。朱先生想,那是象身上最重要的地方,他长叹一口气,想着阮氏慧到底画了多少幅,才会如此有底气地告诉他,她画好了。他发着呆,想着阮氏慧说的事情,觉得自己此前实在应该每年回来看一次孤象,偏偏在孤象离开的这一年才回来,有什么用呢?
阮氏慧做好了饭,安南的饭菜好酸甜口的,他向来吃不惯,现在却很怀念地吃起来。阮氏慧问他:“我说到哪里了?”朱先生答:“说到一年前你哥哥带着象从戏团回家。”
阮氏慧笑着说:“阿哥回家后,我就像一个人在家养两只象一样,每天画完画就去给他俩送吃送喝,但也没送几天,阿哥和象就走了。说起来,阿哥走还是因为朱先生呢。”
朱先生觉得奇怪,他没有追问,搛了菜,等阮氏慧自己解答。阮氏慧说:“阿哥总梦到朱先生骑着象追他上山,那几天改口了,说朱先生原来不是追他上山,而是追着他请他一起坐在大象的背上。”
朱先生自嘲道:“我竟然还会骑象了。”
阮氏慧说:“嗯,骑象上山。阿哥说,你请他爬上去以后,他做梦就彻底成了一团雾,什么都看不见了。挺好的,至少最后一个能看见的梦不是噩梦。”阮氏慧说着,流出了眼泪。她说:“阿哥就是做完那个梦想走的,那天我趴在桌上给你画那幅画,阿哥突然说:‘阿妹,扶我去找象。’”
“我拿着笔过去扶他,他从我手里接过画笔来,被我扶着到象棚去,跟我说:‘阿妹,你让孤象画它自己’。”
“阿哥从没有那么吓人过,像好几次我请神时请到的恶神一样,用最缓的吐字挥砍大刀扎在人心口,我被吓得不敢拦他,他蹲下来摸索那个用来卡住象鼻的十字架。象不反抗,很听阿哥话。它用鼻子画它自己。”
朱先生彻底停杯投箸了,他抬头看着正在哭泣的女人,女人从烧香的神台上取下一幅画来,递给他。
他去看,阮氏慧在旁边说:“象画完,阿哥趴在它背上,说:‘阿妹,我走了!’就一路往北边的群山上去了,那是这只象离群前原本要去的地方。”
朱先生低头看那幅画,是一幅没有鼻子的自画像。紧接着,他透过昏黄的灯光,看到纸正面渗着墨水,他犹疑着给纸面翻身,听见阮氏慧的话洒在他耳廓里,流进四肢百骸。阮氏慧说:“这是我答应你画的填充成象。”
朱先生俯身去看,线条却并不是鸟,组成象身的是密密麻麻的阮氏慧、阮文强以及朱先生。显眼的鬈发和眼镜让朱先生一瞬间认出了自己,他不知该说些什么。阮氏慧说:“你来晚了,你该看看那只象的,它长大了。”
朱先生捧着那幅画走出瓦房,对着象棚,象棚空空荡荡,背景是夜色与遥远的群山,恰好向着北方,他听见几声幽远的象鸣,似乎还夹杂着自家水墨的欢叫。他想起水墨丢失的那一夜,他一直在家楼下的小区里搜寻它到凌晨四点,小区的路灯坏了,没有光,四处是水泥,也听不见野猫的叫春声。他用嗓子模拟出猫叫,仍没有获得回应。现在,他有些想尝试发出象鸣,但他没有。他拈住画的几根手指停止隔着膜的亲吻,那幅画从他松散开的手指中飞出去,消失在了黑暗里。
原刊责编 王 棘
【作者简介】顾骨,本名黄鼎雄,壮族,生于二○○一年。现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写诗词,写小说。有小说见于《广西文学》《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