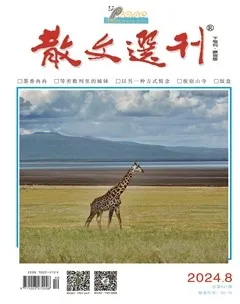渐渐深起来的苍凉
暮色从村口涌进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站在村口,好似一个迷路的孩子打量一座突然出现在眼里的村庄。那棵虬枝虬干的老槐树荡然无存,时间改变了一切,可时间不能救赎一切。
老槐树曾经葱茏遮日,从茂密的枝叶里打下来的日光斑驳在我曾经少年的脸上,风从远方来,带来眺望的风情。老槐树不只是一棵树,对于村庄来说,它是游子回到故乡看到的第一个亲人。
远远地,看到老槐树那高耸入云的树冠,那份回到家乡的温暖宛如树下的那湾涌泉汩汩而出,荡漾心湖。旅途上的风尘和疲惫抖落一地,离乡背井的凄苦和无助烟消云散。在老槐树的眼里,多大都是它的孩子,多好都是它的孩子,多不好也还是它的孩子。众生平等,是老槐树恪守的神性。老槐树是神树,在村庄里是不宣而知的秘密。很多驱魔辟邪的民间祭祀都在它的身下一一发生,红丝巾系满它低垂的枝干。隔三岔五还有一堆堆的纸钱灰烬,遇到调皮的风,灰烬一飞冲天。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父亲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让我认下老槐树为义父,祈望老槐树庇佑我。自此,我顺风顺水地长大成人,负笈求学,直至工作。无论是一脸得意还是一身落魄,我总不会忘记我还有一个义父和父母亲一样在乡下望我归来。我常常回去,回去的第一时间就是放下所有的行囊,在义父庞大的树荫里享受清凉或安抚,听它在风里给我的声声叮咛。可现在是谁谋杀了我的义父,也抹杀了我关于村庄的第一印象?
后来细细询问母亲,才知道老槐树是自己倒下了,一开始没谁敢动它,是村里通灵的那位巫婆建议用来修建土地庙。于是,老槐树被锯成木板,撑起了整整一座土地庙。无数次我都不敢靠近土地庙,我生怕听见义父支离破碎的呻吟。如同枝叶,各自有枯荣。时间的长廊里,大地上的万物都是一阵急促的穿堂风。
经不起时光,一棵千年古树尚且如此,那生育我的村庄呢?青草归来,除了村主干道是水泥打成的,灰着脸,其余的小路都被青草覆盖,通向一栋栋旧房子的几乎挪不开脚步。田园将芜,而现在我置身的村庄已经荒芜,那空空荡荡的田野没有稻禾簇立的身影,板结的一片,咧开干涸的嘴。良田数年不种,好比无人居住的房屋自动开裂。良田其实也不多了,只要靠近马路的都被一栋栋五光十色的楼房占据。这些年,房子是村庄里长得最为茂盛的作物,可再茂盛的作物也结不出果腹的稻子了。可这么疯长的作物只是大地上的装饰。所有的新房子都雕梁画栋,瓷砖折射最后的夕光刺痛我的眼睛。一座座新房子如这个时代一样无限的荣光。
村庄里的乡亲一生最热衷两件事。一是送书,一度乡亲们以送孩子读书为荣,谁家的孩子考学出去,哪怕再不济也是光宗耀祖。有孩子在外工作,父母走在田埂路上都有劲儿,好像泥土不沾脚。二是建房。一生为人就要修建一栋好房子,房子好,儿子能娶得好,女儿能嫁得好。可这些年乡亲们已然丧失了送书的热情,农家子弟即使读大学出来还得打工。慢慢地,有很多父母不主张孩子多读书,而宁愿把钱省下来建房,房子看得见、摸得着,还能指望娶个好媳妇。一窝蜂,房子如蜂,叮在一丘丘好田上。
富丽堂皇的房子一扇扇大门紧闭,好似暮年失语的老人,一言不发地呆立在夕照里,暮色是唯一的衣衫。偶尔吱呀一声,走出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或跳出一个欢呼雀跃的孩子,见不到一个青壮年。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之路。可对于村庄来说,离乡谋生是唯一之路。他们把低人一等的凄苦抛撒在异乡的土地上,把思乡之苦、思亲之痛遗落在熟稔的村庄里。离开的和留下的都是苦,这些苦酿成深沉的静默在村里贮存。还不是很黑的天色,一家家都关门闭户了,只有微弱的灯光告诉世界,这里还依稀有人烟。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繁华,村里的风景也越来越繁华,可人影儿越来越稀少,人气越来越淡薄。没有狗叫之声,偶尔传来的是电视声。因为青壮年不在家,一户户人家早早关门,孩子自然也被关在了家里。一个个心灵都变得孤寂。
而我那时候的童年和少年是何等的欢悦,没有星星的夜晚,我们齐聚在石拱桥上听老爷爷讲《三国演义》《聊斋》和《杨家将》,那些说书人滋养了我的年少时光。有星星的夜晚,我们那一大群孩子或玩儿丢手绢或捉迷藏,有时候成群结队地去草地里捉萤火虫。那些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我们手上的瓶子里,点亮我们深深浅浅的梦境。
而现在,提前进入寂夜的村庄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生疏。我好比一个不安的游魂,在宫殿里游走,到处是触目的光彩,唯独找不到出口的光亮。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不光鲜,但一定要光亮。我在我挚爱的这片土地上找不到内心的光亮了。
新房子都坐落在过去先人挥汗种植的良田上,而诸多的土墙老房子依旧在原地,岁月的风里,它们先后倾身弯腰,相继露出沧桑的眼神,相继显出不堪的负荷,相继吐出深沉的寂寥。曾经这些老房子里人丁兴旺、五畜繁衍,白天欢声笑语,夜晚热闹喧腾,而今,没有人烟,没有人气,一切都是残败的。老房子里神龛上的先人还在否?他们愿意迁居到新房子去吗?先人在每年的中元节还能沿着那些老路回到老房子吗?他们可会在这个变幻无常的村庄里迷路?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世界还是当初的模样,是他们熟悉和喜欢的那个村庄。老房子随风送来陈腐的气息,不时有瓦片坠落的回响。
我踌躇不前,离开了就回不去了,只能在可怜的记忆里寻找陆离的光影。头顶的星星迷离清浅,似祖先深邃幽远的眼神。夜不深,村庄的睡眠已经很深了。行走的脚步惹不来一声熟悉的犬吠,无奈的叹息惊不走一只小小的青蛙,深深厚厚的寂静包裹我。
一点儿夜露打在我的额头上,我不禁一愣,旋即明白那不是清凉,是苍凉,是渐渐深起来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