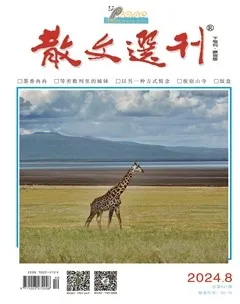彭见明散文小辑

墨香冉冉
一个人持久的兴趣,可能与他生命最初形成的兴趣有关,当然,这种兴趣应该是有意思、不低俗,能够成长和持续的。在我的兴趣库存中,保留得最好最久的是写字。
我的写字兴趣始于上世纪60 年代初,那时我有七八岁了。其时有一位姓汤的私塾先生入驻我家,他的老家离我家不远,只有十几里地。他在国民党政府某县当过几年县长。解放时,因为任内既没有血债也没有引起民愤,抓起来,又释放了。尽管没有民愤,因为你毕竟当过伪政府的县长,批斗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批斗时被人打断了一条腿。
他既然能当到县长,书是没少读的,而要读到很多书,没有丰厚的家产是供不了的。他成才之前就有了妻儿。那个时代的男婚女嫁,大都会在二十岁之前完成,尤其是不愁结不起婚的富家子弟,大都是早婚,娶童养媳的较多,童养媳的义务就是来服侍小她一截的夫君的。
汤先生要通过读书走上仕途且统领一方,也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自山民到达官,一个在地,一个在天,十有八九的糟糠之妻会被离弃或搁置,汤先生也难避潮流,他在长沙再度择偶成了家。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县长夫人要与被打断腿的落魄流民共患难的可能等于零。被后妻抛弃的汤先生无路可走,只能是拖着残腿回到故乡。这时他的发妻已离尘世,仅剩一个眼睛高度近视的儿子在家,地方上的人早就称他汤瞎子了。
因为你成了陈世美,因为你当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县长,因为你当县长大权在握时没有帮过故乡一根稻草的忙,其时的故乡人很难同情接受他。
但是我那七十岁的老祖父和五十多岁的祖父把汤先生接到了我家。那时我家四代已有十几口人过日子,仅有四间房可以开铺。我祖母腾出一间靠近堂屋的大房给汤先生住。我们这些孩子以及嫁出去的姑妈和他们的孩子回娘家来做客,就只能上楼在木板上打地铺了。
我的老祖父和祖父是接汤先生来教私塾的,私塾是场面上普遍且久远的称谓,而我们山里的说法变成了“读老书”。新中国有了新的教材,读的是白话文,是新学。《三字经》《五字鉴》《千字文》《增广贤文》《论语》等等就是老书了。汤先生是读老书成才的,拿手的应是教老书。
教室就设在堂屋里。这堂屋是我老祖父和他弟弟的共同资产,堂屋的前后门都是日夜不关的。我们这个屋场住着六户人家,出进都要经过这里,堂屋就成了往前往后耕田种地的农人以及牛羊猪狗的必经之地。
来这里读老书的学子,有七八岁的,也有十几二十岁的,都是附近的。也有个别住得远的,就寄读在附近的亲戚家。学生可以出出进进,多的时候有十来个,少的时候只有五六个。来这里读老书的,是两类人:一是家境不好,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供孩子去上新学的;二是错过了上学年龄而来补课的青年人。家长们的期望很低很低,只求孩子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出外买货晓得找钱回来。
来这里读老书不必交学费,根据家庭情况,给先生送点儿不花钱买的蔬菜、瓜果、大米、豆子、柴火等等以代报酬。于汤先生而言,在他儿子已无能供养他时,这些贫寒学子微不足道的馈赠,成了他唯一依仗的最后一根活命稻草。
从天上跌到地下的汤先生不让大家叫他先生,也不让叫老师,顶多叫他一声“师傅”。师傅是各个行当手艺人的专用称呼,在我们乡人的认知中,师傅可以没文化,但被称作先生和老师的一定是文化人,两个行当是大不同的。但见汤先生的寒碜境地,低着头弯着腰做人,哪还有半点儿先生和老师的气度。送孩子来上学的家长见此惨状,无不同情,坚持要叫他先生或者老师,但汤先生还是不认。当一个县长的凛凛威风被打成零后,就只有弯腰低头的活份儿了,怎能享受先生和老师的高贵?
寒暑假,我在汤师傅膝下读老书。课程还是保留着古私塾的模式:上午讲课文,下午写毛笔字。我是最小的学生,已经在读新学,再来阅读文言文的积极性不高,却是喜欢写毛笔字。上写字课我比大哥们都用心,汤师傅对我的教导也特别用心,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得到过他手把手同时握笔书写的训练。在他面临生存绝望的时候,我家给予了他什么他是明白的,他唯一能给我家的回报,是要培养和提升我的写字兴趣。
不到半年工夫,汤师傅的弟子们有了不同寻常的进步,而这种不同寻常,也只有方圆几十里幸存的有过私塾学习的老人才明白。很快,汤师傅以他的教学成果获得了乡党的认可,伪县长的反动身份和弃妻恶举不再成为他们的愤怒。学生家长开始轮流让女人们给他煮点儿好吃的,帮他洗洗晒晒被帐衣衫,早晚有空儿就来帮着搞搞卫生,这也给我祖母减轻了负担。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四年时光,“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破旧立新”的行动顷刻席卷大地,复旧私塾成为首当其冲的铲除对象。我父亲见势不妙,忙领着几个年级大些的学子,抬的抬轿,挑的挑担,翻山越岭,过溪蹚水,将汤师傅送回老家。他的儿子近视到只看到人影儿在晃,不知谁是他爸。不久,有红卫兵进山准备将伪县长抓出来批斗,但在爬满荆棘柴刺、虫蚊横行的羊肠小道上没走上一里路,便打了退堂鼓。
我父亲领着我进山去看过汤师傅两次。初来时,我无法形容他家房子破烂不堪到什么程度,大有鼓足劲儿吹一口就会坍塌的可能。看这破败场面,就可以联想到汤先生走出山林读书后就没有再回来过;可以看出来他当上伪县长后,既没能给家乡修过一座踏水桥,也没给生养过他的老屋添一片瓦。第二次来,他就卧床不起了,但还是强打精神和我谈了一会儿写字的话题。离开我家那也可以叫作课堂的堂屋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是光着身子来我家设堂教书的,没有课本、笔墨、纸张。我记得最初的课文《三字经》《五字鉴》《增广贤文》都装在他的脑袋里,他是一边背一边讲解的。笔墨和纸学生自带。纸是山里农家土法自制的敬菩萨用的纸,叫作“毛边纸”。教我们书写的字帖也没有,他在毛边纸上挥笔示范,说先教我们写颜体(颜真卿)楷书。他说,真正写字是写在宣纸上的,你们今后有钱了去买宣纸写字,用宣纸写字笔就走得顺畅,会好看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宣纸是什么样子,别说是宣纸,我们还没有去供销社买纸练字的本钱。毛边纸用鸡蛋和菜干都可以换到,以最低成本培育的这门功课在我们这个地方生根发芽开花。汤师傅带出来的这批弟子,成为我们这方圆几十里地几十年来无人超越的写手,凡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公共场所必需的书写,必请他们出山,普遍浸透着颜体楷书韵味的笔法,引起了过往书家的关注,问这个地方过去是否有书法高手带过一批门徒。于是关于汤先生的故事就传开了,同时,还传开了没有我老祖父和祖父就没有这位先生和他的弟子业绩的故事。
汤先生一无所有,是光着身子走的,连用毛边纸写的字都没给他儿子留下一个。他临终时交代儿子,他走时要悄悄地走,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下葬在什么地方。有人分析他是担心有激进分子会掘他的墓,毕竟他当过伪县长。生不安宁,但死后想图个清静。
我的写字兴趣爆发于我走进中学门槛的这年。我发现下课时在任何一个教室的讲台上都可以捡到老师没写完的粉笔,我们叫它粉笔屁股。粉笔即笔,用不花钱的笔在早晚空着的黑板上写字,成为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不久,我的课余爱好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便叫我去办学校的室外黑板报。学校的黑板报很大,相当于教室里的七八块,嵌在一个长廊里,进校门可见,非常醒目。这时我不必去捡粉笔屁股了,可以一盒盒地领。这时,校园内也受到各种运动的干扰,教室是可去可不去了。检验一所学校的运动搞得好不好,第一眼就是看黑板报了。黑板报的内容一个星期要换一次,雷打不动。一个星期有三天我扑在黑板报上,我在这个平台上尽兴摆弄着各色粉笔,其乐无穷。
很快,黑板报不能满足运动快速发展的要求了,“大字报”的时尚迅速遍地开花。大字报是将运动中流行的话和个人发泄的话用毛笔写到整张的纸上,然后用糨糊贴到墙上,让过往行人阅读。我的同学中几乎没有练过毛笔字的,于是我就成了大字报战场上的劳动力了,教室里的课桌拼成了写字台,堆满了成捆的白纸和红纸,需要抄写的文章和标语口号一叠又一叠堆着等待书写,厨房里用面粉煮成的糨糊一桶桶送来等着把大字报张贴上墙。我们几个有一点儿书写基础的老师和同学,从早写到晚也不能完成抄写任务。
后来运动越运越动,动到去山上写字。我们这个地方的田头、地边、行人路侧,裸露着不少没长柴草的石壁,正好写上几个响亮的标语,如“农业学大寨”“为人民服务”“抓革命促生产”“打倒走资派”……在参差不齐的石壁上写字,毛笔是完成不了的,一上去就会将毛给撕了。我们便用棕叶扎成的扫帚替代毛笔,一个扫把有几十支毛笔宽。替代墨汁的是石灰调成的浆汁,用木桶拎上山来,用脸盆作砚台。字要写成两米左右高,远处才看得清。这类书写,大多是黑体或宋体,汤师傅教我们的颜字在这种地方达不到效果。
在我十七岁时,我已经有了五年书写多种字体的尝试,我的五年从初中到高中的学习,除了入学时按照原有的教学规范读了一年书外,其他的时光基本上耗于服务运动的写字,过足了写瘾。
我在十七岁这年,高中尚未毕业就被招工入县剧团工作,一步登天从农家子弟成为公职人员,直接跳过了时下的高考、上大学、考研或再考博、报考公务员、面试,还有失败了再考等等千辛万苦、风雨飘摇的门槛。
相比之下,我是何等的幸运。我之幸运,兴趣与爱好应该是帮助了我。
十七岁那年,我有三个同学被招入县剧团工作。因种种原因我未能获得公社和大队的推荐,那时入职,考试是走过场,唱几句歌嗓子没问题就行了。政治推荐才是关键。我非常羡慕我同学的幸运。为了安慰我,他们也邀我去县上走动。其时老剧团早已解散,新招收的与我年龄相仿的演职员,没有能动手写粉笔字和毛笔字的。一日,上面来了重要精神,要求各个单位紧急行动办黑板报、写标语、做宣传。这时团长急了,埋怨说新招来的都是些孩子,没有一个会写字的,怎么办?便叫手下去外单位找人来帮忙。
这天正好我在场,我同学便接下了这活儿。这活儿于我是小菜一碟,几个孩子赶紧出去买笔墨纸张粉笔,煮糨糊。我只花了半夜工夫就完成了任务,应付好了来日的大检查。
也许就是这事,我得到了剧团领导的看好,不久就帮助我盖到了管辖我的公社、大队的红色公章。又安排我同学带着我,去找团里一位根红苗正的资深老演员考我。我只唱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师就挥挥手,说可以可以,是个男中音。
于是,喜从天降,鲤鱼跳龙门,一个农村孩子一步登天就吃上了国家粮,成了公职人员。
这时我想起了引我写字上路的汤先生。他手把手教我用笔的情景如在眼前。
我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书法家,真正的“家”,不是靠写就能够写成的。以后我也没有以此为业,只是对书法之爱从未间断。以后的光阴,无论我走到哪里,当看到街巷店铺门头有好字,必是要止步品味欣赏的。古今书法名家的帖子,少不了是要经常翻翻的,就像抽烟上瘾的人一样,不抽也要去兜里摸一摸。我没有过依赖临帖取得进展的奢望,我更趋向欣赏与研究。字是少不了要常写写的,也只有常写才能真正领悟到其趣味于精神生活有多么重要。
赶考
很多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赶考”是一个很神圣的字眼。这是科举时代有本钱进京考试的书生才能体验到的神圣。很多很多年后,科举废了,叫作高考,“高考”成了新时代的神圣,不管你的考试结果如何,你毕竟神圣过。
我无缘高考,未能体验过考试神圣,但也有过值得回味的“赶考”。
我母亲在二十岁这一年生下我,也在生我的这一年拿到了小学毕业文凭。我母亲十八岁出嫁前,读过四年初小。那时候的小学分为四年初小阶段和两年的高小阶段,婚后我母亲坚持要回娘家去读完高小,那时她的伟大理想是要拿到小学毕业文凭。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陪着她取得了小学毕业证。在这一年中,她收获了理想,还生下一个男孩儿,双喜临门,一时成为方圆几十里的佳话。那时候在我们老家湘北山区,小学毕业生已是很高的学历了,不亚于现在的本科生,而女性上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我母亲一毕业就当上了人民公社(现在叫乡、镇)的干部,几年后成了小学老师,母亲是我们这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拥有最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我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在她膝下读完初小,四年学业换了三个学校,从一个山洼子换到另一个山洼子。这样频频换校,估计是每一个学校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条件差异不小,好一点儿差一点儿的味道大家轮流尝尝,就没有什么不公平了。
那时候我们这个公社,有七八所初小学校,只有一所高小学校。大多数农家认为自家孩子读了四年初小,能够认点儿字,打打算盘就够了,不再向往读高小,所以一个公社有一所高小学校也就够了。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起步,百废待兴,一时还拿不出钱来全面开花广建乡村学校,只能是自力更生,寻找能够坐二三十个学生的可以勉强叫作“教室”的地方。找来找去,最合适的地方是庙堂。庙堂除了进门的正面墙上有个神龛,神龛下面有个放香炉的台子,其余就是空处,可以摆上二三十张课桌,一个公社有七八个大队(现在叫村),巧合的是,在那个没有“大队”行政划分的时代就有了七八座小庙……当然,我无须知道,这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一个村一座庙,就读初小的也差不多是二三十个学生。于是所有乡间小庙,大都挂上了某某学校的牌子。也有庙堂盖在陡坡或山尖上的,因不利小孩子往来,便去找堂屋相对大点儿的农户给予支持,这一招儿有求必应,在那知识极度贫乏的时期,能把学校办到家里来,是这户人家极其荣耀的事情。
我的四年初小,跟着母亲在两所小庙和一户农家堂屋里完成学业。庙堂小,大门不小,拜菩萨的香客有时候来得多,门就不能小。进门的正面墙上安放着木雕或泥塑的菩萨,教室的黑板就挂在进门的左边或右边墙,这样老师和学生就不面对菩萨了。民间祭事,有两件是比较重要的:一是敬神,二是敬坟。敬神和敬坟是不能同时进行的,分开为“上午敬神,下午敬坟”。上午敬神的乡民来了,学校又要上课,怎么办?好在香客们都通情达理,既要敬重神明,更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学校和香客就想出个办法来:上午有三节课,三个下课时间,老师叫学生出门玩儿,把教室留给香客。这时我们不在乎玩儿什么,我们在等待香客点燃拜神的鞭炮,我们专注于寻找没有爆炸的小鞭炮。那时,在我们的快乐追寻中,小鞭炮的爆炸声和刺鼻的硝烟味,是最刺激的娱乐,而对娱乐的渴望,一年中只有在大年三十才能实现——长辈们会给我们分发一角钱的压岁钱——那时候一角钱可以去做爆竹的作坊里,买到五十个散爆竹(买成型的鞭炮划不来),这50 个散爆竹小心地躺在口袋里,为了延续快乐,我们练就了可以将点燃的小爆竹扔到水里不被水浸灭而是炸起浪花,还可以精准地扔到猫和狗的身上且烧出毛的气味,那是具有成就感的香味。
庙堂没有窗户,关上大门就一团漆黑。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电灯,我们依仗从大门进来的光照着看黑板上的字和写作业。凡上课大门必打开,就是寒冬腊月也照开不误。我母亲一到寒冬便将能穿的衣裤都捆到身上,结果还是日积月累染上寒病折磨她一生。那时候我们这些农家子弟,都还没有本钱穿上棉衣棉裤,幼时的锻炼,导致我40 岁以前没有穿过棉衣棉裤。我至今留恋敞开大门读初小的时光。我们的课堂是向香客敞开的,还有猫儿啊、鸟雀啊、蝴蝶啊、蜻蜓啊、青蛙啊、蚂蚁啊、苍蝇啊……可以大摇大摆闯进门来同我们一起听课,那时的农家是家家户户要养狗养猫的,养狗是看家,养猫是抓老鼠,有一部分家狗每天跟着主家孩子来上学,我母亲要求凡带狗来上学的,要守纪律,纪律是不能进教室,那些狗都守纪律,趴在外面等着小主人放学一同回家。这些动物自小与我等为伍,除了狗外,我们不认为它们进教室有什么不妥。这扇大门是谁都可以出进的,我母亲也这样认为。
人民公社附近有一个祠堂,建国以后就空了,整出来七八间教室,有可以站百把人的礼堂,都被天井的光照亮着,可以关上门上课了。读初小时,我母亲同时当着校长和语文、算术、音乐、体育老师。四个年级的学生同坐一室,给这个年级讲课,另外三个年级的学生就看书写作业,久而久之,也就练就了互不干扰的本领。读高小了,规格就高了,每一门功课由不同的老师来讲,教室里就不能有动物了,一个教室单独坐一个年级的同学,上课下课有专人敲钟。小庙里是没有厕所的,女学生都到附近农户家上厕所,男学生就在庙后面的菜地里贡献最好的肥料,那里的菜从来就长得好。祠堂的后面盖了很大的厕所,分男女两条路,拾级而上体面如厕。
这个祠堂叫作“敬祖堂”,我非常幸运地在这里读完高小,幸运的是我家离敬祖堂不到两里路,家人可以放心地让我独来独去。与我一同读完初小的七个同学,除了我同另一个同学去敬祖堂读高小,另外五位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们要越过一个有十里路长的大水库和一个山包、两个山坡才能到达敬祖堂。学校是没有饭吃的,我们可以回家吃,他们不行。既不能保障在水库边上的崎岖小道上行走的安全,又不能解决吃的,这个书就很难读下去了。我母亲二十岁那年肚子里怀着我,是带着中餐去读完高小的,她是个大人了,她能够在上学的路上捡点儿柴草,在学校外的某个墙角,捡几块石头搭个小灶,将冷饭冷菜搅在一起热一热。长大后我喜欢端着饭碗到室外吃饭,看眼前的花草、猫狗、鸟雀等等鲜活的动态伴随着吞食一并下肚的感受,其乐无法形容。我再长大些,参加工作了,每年有两百多天在乡下跑,除了天下雨,我们的餐桌都摆在农户的院落里。我母亲以十月怀胎的胎教,使我能够体验到“秀色可餐”的美好。
我有个姨妈比我大两岁,她在家里附近读完初小后,铁了心要向我母亲看齐读高小。但她既没有独自在村野行走十几里的勇气和体能,又做不到在学校周边架个小灶做饭吃,这事僵住了。好在我父亲出了个主意:让我姨住到我家来,同我一起上学。这是我最乐意的事。我的初小四年,寒暑假几乎在外婆家度过,同我姨一起长大。很小的时候我姨要求我叫她“姨”,我不从,说,你这个姨只比我大两岁,太小,我不能叫你。她说随便随便,叫什么都行。她性格开朗,像一个男孩子一样同我上山砍柴,下水捉鱼,踢皮球,把门板取下来搭台子打乒乓球。那时候寒暑假作业不多,但我大多数是赖着她给我做了,我的理由是:谁叫你是我的姨呢!
我和我姨朝夕相处在敬祖堂完成了两年的高小学业,取得了小学毕业证。我姨成绩好,两年学习语文算术考试始终名列全班第一,无人可敌。我母亲在外面教书,父亲天亮出门摸黑回家,被农活儿累得摸不到床,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学业,毕业成绩通知单都懒得看,他们叫我姨管我,姨也管不了,顶多是我问她的她才作回答。
我老祖母十九岁生我祖父,我祖父二十岁做父亲,我父亲二十二岁育我,我老祖母六十一岁便享受四代同堂的美誉,我父亲是她的长孙,我是她的长曾孙。我们乡下有言“公疼头孙,父疼晚崽”,头孙是荣誉,一出生就代表了这户人家又添一代。那时候普遍结婚早,十几二十岁都做父母了。父母老了,大点儿的儿子也跟着老了。父母养老一般就寄托在晚崽(最小的儿子)身上,这个利益很现实,所以父母是普遍疼爱晚崽的。
所以我老祖母就一直跟着我父亲过。我的初小四年,我老祖母一直跟着陪读,我母亲到哪儿,她就到哪儿。她是封建社会留下的小脚,凡寒暑假和周末我们回家,都是我的叔父们抬着轿子接送的。
我读高小了,老祖母就回家陪读,做家里几口人的饭菜,搞卫生,还能喂猪(只是提不起猪潲桶)。老祖母跟随我母亲教书四年,她知道学校上午是什么时候上课,晚上学生该什么时候睡觉,我母亲不在我身边了,这个任务得老祖母来完成。她的闹钟是鸡叫,她知道哪一遍鸡叫过后多久,该叫我和我姨起床了。每天早晨她不愿影响我们的最后一段睡眠,摸着黑悄无声息地给我们做好吃的。我不愿使用“早餐”这个诱人的词汇。我们一成不变每天早晨吃的都是头天晚上留下来的剩饭剩菜。依我老祖母的力气和家庭状况,实在是做不出可以称作“早餐”的花样来。
我和我姨高小毕业了,马上要去参加神圣的初中考试了,它的神圣在于:我那高小毕业的母亲都可以当上人民教师,那么高于小学的中学,在普通百姓看来,其前途就不可想象了。我老祖母在左邻右舍的谈论中,也明白了这场考试是如何重要和神圣,她在我们即将赴考的这几天,将家里预备候客的储存鸡蛋全都煮给我和我姨吃光了。我老祖母从来不说那种什么你们好好学习之类的大话,顶多说到要睡好觉,养好精神。她认为“响鼓不用重敲”。
老师交代了,赶考的这天,要求我们早点儿赶到学校集合,然后统一步行前往考场。考场在中学,其时县辖下役区,区下面是公社。全县有九个区,每个区设一个初级中学。中学要容纳几百名学生,找不到这么大的庙宇和祠堂,是国家出钱建造的。我们小学到中学有十五里路远,快点儿走也要走一个半小时,我老祖母打听到了路上要走多久,然后叫我们早点儿睡,睡好了才有好精神考试。她会叫我们起床吃饭。其实这一晚我和我姨是无法睡好的,这一场赶考,可是超越我母亲的考试,据说我们这个有一两千人的大队,还没有出过一个中学生,那么这场考试,还是超越全大队人的考试,如果考好了,就叫作是神圣的赶考。如果没考好,也没有什么惭愧,所以在兴奋和自我安慰的状态中,我们一直处于半醒半睡中,待二遍鸡叫过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我老祖母也做好了罕见的可以称作是早餐的早餐:煮的是新鲜饭,煎了鸡蛋,还特地让我叔叔头一天去河里钓了鱼,煮了一大碗鱼汤——为了我们这个家族里程碑式的赶考,我估计我老祖母一夜没睡。
天还是黑的,老祖母很平静地送我们出门,从她的表情中我可以看出来叫我们考试不要慌张。她没有文化,但她以她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总结:慌慌张张是做不好事的。老祖母给我和我姨每人一角钱,说是考试完了买点儿吃的,中午饭是赶不到了。我自以为很神圣的赶考,就只有老祖母一人送行。我母亲在学校里,昨天傍晚我父亲给她送油和柴去了。我的祖父祖母、叔叔姑姑们不知道我今天去赶考,就是知道了,也不觉得这事有什么了不起。我六个叔叔姑姑们只有两个读过初小。
我和我姨上路时,鸡还没叫第三遍,天还是黑的,路也是黑的,我点燃着一根草香边晃边走。走进教室时,比我们早到的同学有三四个。老师说,你们兴奋了吧,没睡好吧?快补补,快补补。我就伏在课桌上倒头便睡——有老师在,不必担心迟到误了考试。
这天的阳光特别明媚。自人民公社通往区政府的可以行走一辆板车而在我们看来很宽阔的道路,也被艳阳洗得特别干净。我们一行三十多位考生绝大多数没到过十五里外的区政府所在地,更没有进去过本地的最高学府,其时的小学生是没有胆量也不打算去见识见识中学学堂的。当我们列队唱着歌,走进被高大的围墙围圈起来的十几栋教学楼、宿舍、食堂、四个篮球场、两口池塘和菜地,才明白了学校应该是这样的。
我的考试位在进校门的第一栋第一室,屋顶上挂着一口大钟,钟锤下的绳子吊在讲台一侧,一位老师进来拉响开考的钟声时,来自全区八所完全小学考生的考场顿时鸦雀无声。
考的是语文和算术。
我做完卷子,就交给了监考的老师。我发现我是第一个交卷的,交完卷了,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摸到老祖母给我的那一角钱,我的心马上飞到了离学校半里路的镇上,接下来是要去品尝大地方做的包子了。这时已有考生开始交卷,交卷后都回到座位。一直到那位打钟的老师拉响钟声,宣布考试结束,我们才陆续走出考场。我是考生中第一个冲出学校大门奔向镇街的,一到镇街,就闻到了面粉被蒸烤的气味,顺着气味的指引,很快就看到了一面墙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仅有“面铺”两个字。我看了看面铺仅有四样吃的:面条、油条、包子、馒头。我这一角钱吃不起面条和油条,我爱吃甜食,一眼就看中了糖包子。一角钱可以买四个糖包子,这买卖令我称心如意,欣喜若狂。做包子和卖包子的都是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他从蒸笼里给我拿出的包子又白又胖、又软又甜,一口下去,就让我觉得以往在端午节吃过的包子无可比拟。自此以后我吃包子只吃糖包子,而且每吃糖包子都要与十二岁赶考时吃的包子相比较,比了很多年,竟无一超越。这个做包子的师傅叫李四,开课后才知道李四的女儿和我是同学,很多年后,每每同学聚会我都要对她讲,你爸做的糖包子至少也是全县第一。她就埋怨我:“现话讲百遍,猪嚼狗也厌。”后来有些朋友谈到他们的子女读了大学不知道干什么好,我说早晓得要是跟李四学做包子,早就发大财了。
初中考试录取通知下来,我们学校三十多个赴考的同学,录取了七个,其中有两个交不起学费的没去报名。那时候考个初中比现在考大学还难。
全班成绩始终第一的我姨没有被录取,而我这个不上不下经常抄我姨作业的却考上了。我怎么能考上呢?想来想去,可能是班主任老师在赶考前反复说过的话,上了考场要“胆大心细”。我的成功可能就得益于胆大,同时还没考完就想着吃包子。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姨没有收到,她躲在她的外婆家哭了几天。后来我母亲找人了解:因我外婆家是富裕中农成分,比地主差不了多少,由于政治原因,我姨考得再好,也要把名额让给贫下中农子弟。幸好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这个下中农子弟,不然,凭她这个学历,也当不到人民教师。
1965 年9 月1 日,我走进了中学的大门,开始了标准化的学习。1966 年5 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固有的学习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体表现是老师大部分下乡当农民去了。学生上课可来可不来。初中三年,我取得了初中毕业证,尽管这个证件,仅有不到一年的知识含金量,我还是很珍惜我的最高学历。在我的记忆中,我从初小到初中一年的学习生活经历,仍旧是最难忘却的部分。他们未能帮助我取得体面的学历,却是从未间断我对学习的敬重和渴望,渴望是因为没有得到而渴望。
我姨虽说没有读到中学,后来还是被聘请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又考上了公办教师。她终于和我母亲平起平坐了。凡她们姐妹教过的学生家长,都说她们的课讲得好,学生也带得好。
处女作记
我的文学阅读兴趣,始于就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的乡村中学是有图书馆的,但很小,隔了半间教室,书架子摆得很密,中间只能侧着身子过一个人。借书只能在外面排队,进馆选书的余地是没有的,管理员能找到就找,找不到就轮到下一个。那时我十三岁,读初一,身微力小,排队排了半年也没有借到过一本书。
初中一年还没读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上课读书已经不重要了,图书馆的门也就砸烂了,图书撒满一地。这时我看到学校围墙外的老奶奶们背着篓子进来捡书,捡回去将书页撕开来当引火柴。那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煤,烧火做吃的都是柴草,用纸来点燃柴草是无与伦比的好办法。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校方怎么不来制止这种拿书行径?不久前排队借书的学生们,怎么突然看不上书了?眼见来捡书当引火柴的农民开始多起来,我就顾不上去问为什么了,也赶紧去捡书,想想再不动手就迟了,那么好的东西就都要化成灰了。我很庆幸我作为一个懵懂少年的并不懵懂的决策,因没有错过时机,很快就抢出来几个书包的书,那时候喜欢故事书,便选厚本的长篇小说拿,先藏在宿舍楼后面的草丛里,然后分几个周末背回家,我的这批书成为一个中学图书馆的幸存者。但没过几年,又被乡亲们和同学们借走了,在一个没有书看的时期,轮流着借看的书,怎能指望有借有还。
自1978 年起,我被卷入一个光彩照人、席卷全国的文学阅读时代,这时我特别注重文学期刊的阅读,加上过街即到图书馆、新华书店、邮政所的便利,其时县上能有的文学杂志,被我翻了个遍,有的甚至是从头读到尾,一篇不漏。
读来读去,我渐渐地能够读出来哪些写得好,哪些一般般。
读来读去,就能够说出来好的好在哪里,不足处在哪里。
读来读去,就有了好的多读几遍,一般般的就前后翻翻点到为止的习惯。
其时我很想找几个读友交流一下阅读心得,讨论一下我这种阅读心态是否正确。可惜县上有几个能写的前辈,都调到市里省里去了,本地已是知音难求。
1979 年,市里组织各县剧团的舞台美术工作人员去武汉看一场汉剧,学习舞台美术,一位资深美工在聊天时说了个成语“见多识广”。这是一个众所周知、普遍使用的成语,怎么就被我忽略呢?这时我就联想到了一些很小儿科的日常存在:当你到过很多地方吃过很多菜肴时,你就知道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一般般。当你游览过很多风景名胜,你就知道哪里风光如画,哪里一般般。当你看过不同层级的表演,你就明白什么是艺术,什么还是唱戏。总而言之,见多方能识广,识贵贱,识高低,识好歹。
以我自十三岁开始十几年来的没有间断过的阅读兴趣垫底,又有了一点儿不一般与一般般的阅读审美判断,就想写一个小说试试笔。其时滚滚向前的文学热浪令多少文青在做文学梦,有一些我这个年龄的写手都已获得全国奖了,这种诱惑力、推动力太大了。
1980 年,我写了一篇9000 多字的小说。
我很想找一个行家看看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不是有了点儿模样,但未能如愿。
后来我那在市文联工作的舅舅回来了,他会写戏,也写小说,我想请他看看我这个初试锋芒的小说,然后请他带给市文联办的文学刊物找编辑看看。
结果是音信全无。
后来我有一位在省里一家杂志做编辑的同学回老家了,我委托他把我这个稿子带到编辑部看看。
结果也是杳无音讯。
那时没有电脑和复印机,一份手写稿可以用一种叫作“复写纸”的复制成两三份来。这时我手头仅剩一份原稿。也正好在这时,我在上海的《文学报》上读到了上海《萌芽》杂志复刊的报道。报道还注明,这是一份青年文学杂志,该杂志的创始人是鲁迅先生。我没听说过这份杂志,但读过鲁迅的作品,“文革”十年期间,还是能读到鲁迅作品的。这个报道令人鼓舞,我便把手头的最后一份手稿,按地址寄往上海。那时候寄信要贴八分钱的邮票,而寄新闻稿和文学稿是免费的,就是超重了,也不收费。但有一个要求,要在信封上标明“稿件”字样,并需剪掉一只信封的角,让邮政工作人员看到内面是一叠稿件,而不是几页信纸。那个政府职能部门以实实际际的行动支持和厚待文学及新闻写作的时代,让人难以忘怀。
大约是两个月后,我在午睡,楼下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院子里高喊,叫我去接长途电话。电话是《萌芽》杂志社的编辑打来的,说他们准备刊载我这个稿子,并要求我不要再寄给其他刊物。
1981 年5 月,我的处女作刊出。7 月,被当时全国唯一的选刊《小说月报》转载。该作获本年度的《萌芽》文学奖,因领奖,我第一次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上海。颁完奖后参加文学笔会,一支由8 位获奖作者组成的队伍开往安徽黄山,再去浙江千岛湖,在岛上听名家讲创作课,并要求在地创作,每人交稿一篇。前后历时一月。我首次体验到了什么叫作笔会,领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温暖。从上海回来不久,湖南省搞了个三十年文艺评奖活动,又给我的处女作颁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奖。这是我首次光顾省作家协会,立马就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处女作荣誉的推动,约稿的也多,我进入了疯狂的写作状态,但当我再往前行走,接触到更多的作家和作品,试了试文学圈的深浅后,再仔细看看我自以为开了个好头的文字,顿觉陌生,毛病不少,后悔不该匆匆出手……但木已成舟,就如一个人曾经稚嫩过,成了一个无法修正的生命过程。
因内疚,我以后不大愿意说出这个处女作的篇名,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初出茅庐时的稚嫩。
我一直还愿意谈的是,我有幸在一个最好的文学时期开始了文学创作的起步,可谓生正逢时。我一点儿也不埋怨我的舅舅和我的同学没能帮上我。
尊重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和风格选择,这恰恰是对文学生态的最好保护和培育。一旦发稿和评奖开始有了“关系”二字的侵入,也就是文学衰败的开始。
我非常景仰《萌芽》的文学编辑,能够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剪角信封中,抽出一篇第一次试写的稿子来阅读。
我很欣赏“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佳句。我在尝试着写小说时,已经是一个有点儿资历的舞台美工了,尽管文学尝试初见成效,但我还是不敢轻易放弃本业,以美工为正业,写作为副业。后来写得顺了一点儿,稿约在增加,我还是坚守在熟练的工作岗位上,并不以为我就能当成一个作家,不要以为理想就是未来,我得小心。此处之无心,即无欲,无狂,无累,潜心爱着所爱,小心经营,方有可能水到渠成。
后来换岗,那就是后面的事情了。当然,这也是我那时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