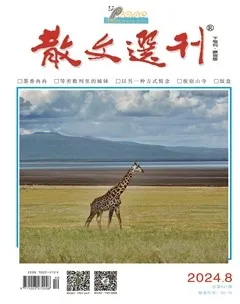等差数列里的姊妹

我有一个姐姐,大我三岁;我有一个弟弟,小我三岁;姐姐叫英,我叫镑(后来,身份证名字改为“磅”),弟弟叫法。身处社会最底层的父母,他们以农民最朴实的本能,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设计,终于把我们弄成一个等差数列带进了人间。
其实,我还有一个妹妹老四,她比弟弟还小三岁。她的降生,似乎是上天要赋予这个等差数列一个更加完美的定义域,姐姐是首项,是不变的;妹妹是末项,是上苍的魔法变进来的;弟弟在妹妹的拥挤下,跟我一起挤成了中间项,我们就这样拥挤于山间一处悬挂着34 号门牌的小屋,那是一间二层的木瓦房,小屋边还紧挨着一个修葺得更加矮小的小屋,那是爷爷的住处。小屋与小屋相连,我们姊妹于34 号会聚,像流水相聚的浮萍,像觅巢归来的春燕。
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那时的老四尚未来到人间。我们母女四人围在竹篾、箩筐前,挑拣一堆的茶叶。我们分工明确,妈妈拣最精致的小芽尖儿;姐姐拣两片叶儿的小芽苞儿;我拣三到四片叶儿的;弟弟一把一把抓最粗的老茶。如果我是质检员,三弟的作品肯定是过不得关的。可妈妈从不坏了弟弟的兴致,还尽夸他挑得快,挑得好。三弟对于妈妈的夸奖,一向很会享用,他像充了气的气球,又蹦又跳、轻飘飘的。我一向分不清、道不明这是三弟的天真,还是无知,但苦于妈妈在旁,只能偷偷用鄙夷的眼神扫射他,撞击他。他竟更得意了,还用扮鬼脸还击于我。
此时,只有姐姐是永远中立、安静的样子,像是海洋中的一座孤岛,又像是围裹孤岛的一片大海,她既深沉又孤寂,智慧又善良。我问过姐姐,是不是虚长几岁的年华,是不是一声声“姐姐”的叫唤,让她变成了独特的样子,她一时嗫嚅,我没问出答案。
在我们挑拣完所有茶叶的时候,夕阳还在山头露出半个笑脸。妈妈对我们宣布:“明年,你们就要多一个姊妹了。”“多一个弟弟吧。”她又补充作了说明。当时我和弟弟都把妈妈的话当耳旁风,我向来对未卜先知的言论持有狐疑的执念,因为我见了太多大人们关于明天和未来信誓旦旦的承诺皆是在时间里扑了空;而弟弟更愿意在言论里捕捉关于吃和玩儿的信息,对于其他信息一律毫无兴趣。三弟痴迷于扮鬼脸与我隔空较量,并为自成一派的“变脸”技艺而沾沾自喜、扬扬自得。
或许是“哥哥”二字压制了我的胆量,束缚了我的手脚,我不敢同三弟一样肆无忌惮,心有不甘的我谨慎地以比枪手势予以回击,再借余光偷偷瞥过母亲和姐姐的脸庞。妈妈的面容平静祥和,只有姐姐愣神于须臾之间。这种瞬间的愣神旁人极难用理智去分辨,唯有那时的我洞察到。我确信,恍惚间愣神涟漪起始于她仰起的侧脸,转瞬,又隐没于那深邃的眼眸。她用很自然的低头动作掩饰,再抬头时,她的脸庞清澈动人,静如止水。
或许,真就姐姐听进了妈妈的话,或许真就因她虚长了几岁,就因她被屡屡叫唤为“姐姐”,她就在本不该懂的年纪里懂得了他人不懂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斜阳照在姐姐绯红的脸庞上,这抹动人绯红是阳光赐予她的色彩,是青春赋予她的气息,是父母期盼她长大的急切呼唤。斜阳又轻轻擦过妈妈和三弟的衣袖,在地坪上留下浅浅的影子,再又缓缓地走进了那间小屋。
一年后,看似一模一样的春末夏初的午后,总要有一些故事要发生。
那个静谧安睡的午后,被母亲一声腹痛的哀号唤醒。女人们按部就班,开始忙活,她们有说有笑,从屋子进进出出。男人们则是站在地坪里讲一些无关于女人生产的话,说说土地庄稼、鸡鸭牛羊,扯扯风水宝地与天上人间。他们好像对女人生产漠不关心,无心帮忙,或者说该帮的忙、该出的力皆早已倾情奉献。屋里,一个女人说剪刀在哪里,就有另一个女人四处去找寻;一个女人说水热好了没,就有另一个女人使劲儿地往土灶里塞柴火;又有一个女人说毛巾、毯子准备好了吗,房间里就传来另一个女人翻箱倒柜的响动……这时必有一个女人大声地呐喊:“再用点儿力,用尽你所有的力,就跟吃坏肚子使劲儿往外拉一样,再也不要保留……我就要看到小脑壳了。”
“痛死了。”唯这是我母亲在整个下午uMfN7HZm/ssDOL8YDJ+6Zw==里叫喊得最清晰的一句,其他尽是她的吼叫。“痛死,你也得再顶一顶。”“你都生仨了,咋还这么费劲儿,我生第一个崽都跟鸡下蛋似的……”又有一个女人在旁附和。
“痛死了。”我又听见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嘶吼。渐渐地,母亲的嘶吼哀号渐而微弱细渺,女人的加油呐喊也不那么沉重有力。我以为是母亲不那么疼痛了。接生婆张阿婆神色凝重地从昏暗的屋里走出来,父亲三步并两步迎了过去。张阿婆在父亲耳旁嘀咕了几句,又踅足折了回去。我似乎隐隐听见了关于“死”的细小字眼却又无从查证,可我清晰看见了父亲一脸从容转瞬成了愁眉紧锁。我开始多心并担心起来,我的母亲是不是要死去了。
父亲开始在院子里踱步,来来回回,一刻都不消停。祖父坐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只有姐姐、我、弟弟三人静静地,并排着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待大人们的指令,苦等那一声破空而来的哭响。我甚至于幻想以姊妹仨悲恸哀歌来化解“小四”沉寂无声所带来的空前灾难,我懵懵懂懂,坚信只有母亲的孩子的真切痛哭才能拯救她的性命,才能结束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慌乱。
阳光在我们的头顶走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我们的影子也从西边倒向了东边。不知等了多久,夕阳要彻底落山了,再也留不住;父亲的额头冒着汗,他杵在院子里;祖父的手指在烟袋疙瘩里不停摸索着,不知在找寻什么;楼上几乎也没了什么动静。我料想,屋子里的女人们铁定是把所有古老的接生仪式走了一遍又一遍,她们实在是黔驴技穷了;而房外的男人呢,我是亲耳听着他们对三界神灵苦苦哀求并虔诚念诵了一遍遍,他们也只能是希冀于神明庇佑了。可这个小家伙呢,还是迟迟不来人间。它是有多么厌恶这个人世间呢!
寂静,有的时候比死亡更可怕。就在所有人都在无计可施、面如死灰的时候,就在所有人认定这将是由一个喜剧沦为一个悲剧甚至是一尸两命的惨痛事实的时候,这个小家伙竟以一声带着哭腔的嘶吼撕破一片死寂,老四与哭吼声几乎同时来到人间。可谁还有那个闲心管它是哪个先来哪个后到呢,他们都来不及从惊魂未定里逃出,来不及躲进一片喜悦与祥和。总之,它来了,母女平安,这就足够了。
“生了,是个女孩儿。”这喊声和哭声也几乎是同时发出的,父亲从站着变成了坐着,爷爷从坐着变成了站着,他们姿势的变化也几乎是同频进行的。
我们也一起抬头向二楼的楼廊看去,企图从两扇玻璃窗里睥睨出个究竟与未来。我们还只是看到了两扇小窗,还有窗沿儿上摆着的一盆尚未开花的剑兰。姐姐扭过头,靠近我耳朵说:“生了,是个妹妹。”我也扭过头,靠近弟弟的耳朵说:“生了,是个妹妹。”弟弟也扭过头,发现没有耳朵可诉说,就跑去拽着祖父裤腿上的一个破洞,跟破洞说:“生了,是个妹妹。”
慌乱的午后在小四起起落落的哭啼声里,在女人们逐渐恢复理智而又温柔有力的驱赶下,终是消失于浅浅的夏夜里。“劫后余生”,母亲用自己的亲身劫难来演绎这个古老成语的真谛,它将比任何课堂、任何辞典的说文解字都清晰透明、生动形象。这也必将是一个令我永生不忘的幸福词语。
我和姐姐的欢乐在小四带来的哭声与笑声中变得松软、扩展而蔓延,我和姐姐学大人的样子,捏捏她的小脸,勾勾她的小鼻,管她叫“细细妞”,轻轻地叫她“小四”。小四哭与笑像轻柔白云包裹整个山顶、整个34 号。三弟也学我们,学我们欢快的样子。我和姐姐的欢快随着时光的脚印一路前行,而三弟的快乐是潮涨潮落的。他玩儿疯了依然忘乎所以地笑,他静下来时,就又闷闷不乐,他时而快乐、时而悲伤。他似乎觉察到小四将给他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他时不时在空气里挥舞着小拳头,他以比小四更猛烈的哭声与笑声来表达他的悲伤与欢乐,他甚至一度妄想以这种疯癫手段来重新夺回继续被母乳喂养的权利。他的危机感是敏锐的,也是极其准确的。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三弟的眼里,那肯定是一个遭罪的午后。他被迫从带着两扇玻璃窗和配有一段木楼廊的前屋搬出,离开那个踮脚倚栏杆就恰好瞧见山前潺潺燕子沟和天空白云飘荡的“ 上等房间”,他从此就要跟入睡前形影不离的父母和那一张温暖柔软的床分离。那是一个足以体现身份高人一等的住所。他从此就要住进一个狭小而昏暗的房间,跟我们分摊难过与黑暗。后屋,只有一个小木窗,即使打开木窗也只能看到后山那株风烛残年的老枫树和稀稀拉拉的枯黄竹林子,关上窗就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悲惨世界。
确实,我对后屋的印象与评价也的确是如此。我们毕竟是亲兄弟,我与他皆有着一样敏锐的感知和一样正确的审美,在他的眼里是那样,在我的眼里也是那样。
紧紧一墙之隔的距离,三弟近乎使完了全部气力才把自己从“前”挪到“后”,他没带什么行李,也没什么行李可带,仅是带着两眼汪汪的泪水和一个小小梅花枕头,迎接他的是姐姐的安静与柔软的微笑,还有一个哥哥的幸灾乐祸的鄙夷之情。从此,他的活动空间从光明透亮的前屋退出;从此,他的睡眠再也无法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轻抚与告慰。三弟苦苦喊了一声“姐”就摔入姐姐的怀里。至此,他正式与“前屋”的过去告别,即使他万般不舍、万般哀求,可无论怎样,前屋的两位主人,眼下是仨人,他们皆是“哑巴吃秤砣——铁了心”。
而最早走完这一段艰辛路程的是我的姐姐,那时迎接她的只有一张小床与无边的黑暗。我猜想她曾无数次战栗于我与父母安睡的房门前的那条狭窄的过道,战栗于那一小方平坦的楼板却又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可她终是选择了向“退”妥协,她一度踌躇,一步步退缩,她无助地退向黑色无声的世界,或许是黑暗世界主动侵袭了她,也或许是她压根儿就没得选择。我猜想她度过了无数个无声的暗夜,我猜想她无数次等待我的到来,或者说在等待三弟的降生,她为此等待了将近三年。
在小四快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已经七岁,在她快乐成长的日子里,在长辈们都习惯喊她老四的时候,在我和姐姐沉溺于喊她小四的时候,弟弟也跟着期期艾艾、含糊不清地叫她小四的时候,在我们都认为她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降落人间的小精灵的时候,一个困扰我们姊妹整个青春乃至一生的谜团毫无征兆地笼罩上我们。
那又是一个夏日,只是从午后推延到了翌日清晨。我们仨都还沉浸于后屋不再黑暗的睡梦,我的父母竟藏匿于天色未亮的黑暗谜团里,他们将土灶里的草灰涂抹于脸上,如敌特一般做了乔装打扮,他们鬼鬼祟祟地摸出了村庄,他们应该没有经过爷爷的同意,他们瞒过了村庄所有人,将小四从暗夜的34 号裹挟进小镇的另一个黑暗里。襁褓里,小四的心口间,仅是戴了一只写着生辰八字的平安符。
父母是再一次吃了秤砣铁了心,他们把小四与襁褓一起托付给了一张还未开张的猪肉铺案板,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时的小四早已清醒、早已号啕大哭。一年前,她有多么不想降生那个人世间,此时就有多么不想离开这个人世间,这个34 号。
清晨的天色还是暗的,暗得像一团迷雾,没人看得清,就像缠绕在小四身上的谜团一样,唯生辰八字,成了一条可有可无的线索和一个不清不楚的答案。
这些可恶的细节是在我们逐渐成长岁月的旁敲侧击与追溯过往的合理推演下得出的,父母一直是不置可否的样子。
后来,祖父走了。无比衰老、了无生机的祖父从矮小的小屋里搬出,在祖厅的一张门板上留恋了两天,就头也不回彻底地离开人间,离开34 号。他跟祖母一起住进了燕子沟旁高高的向阳坡上。从此阳光无须半点儿辗转即可寻到在一起的他们。后来,我的父亲又从庄稼汉转行当了矿工,母亲也跟着他到处流浪。
时光无声逝去。父母带着一身无可逆转的伤害从矿井爬出,爬上地面再次成了农民,此时的我们皆已成了家。
再后来,几经行政区划归并与村规模优化调整,老家的地理范畴从大变小,又从小变大。34 号门牌更写成更为吉利的66号和8 号,可我们终是觉得任何一个吉祥的数字都没有原来的34 号好,于是我又故意把那张已坠入历史长河的34 号打捞出来,并明目张胆地悬挂于老屋门前。或许34 号,才是数列里我们姊妹四人关于家的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坐标。
我不想换。我怕有人寻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