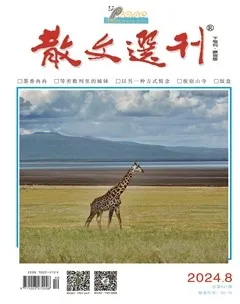外婆的金子
我和外婆终是分开了。
外婆在哪里呢?她住在县城里呀。外婆住在县城里做什么呢?要赚钱呀。
我知道外婆在城里租住的房子,那是老建家正房后面的拖背小屋,走过一条落满淡紫泡桐花的小巷,绕过主人的正门,就来到一扇破旧的木门前。木闩上套着一根生锈的铁链子,底下悬着一只银色的小锁。外婆从腰间拎出一片单薄的钥匙,像变魔术一样把它摸索着塞到小锁的牙缝里,木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一股霉味从看不见的地方扑过来,直往我的鼻孔里钻。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我看清了,靠墙有一只油漆剥落的五斗柜,房间中央有一张雕着复杂梅花喜鹊图案的枣黑色大床,床沿儿已磨得油光发亮。听说老建的老母亲在这张雕花木床上咽气后,这间屋子就再没人住过了。那大床上铺着的稻草也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气,但是外婆不怕。拖背屋的房梁上牵着一根绵绵长线,那根历尽艰辛的线绕了很长的路,爬上了墙壁,又穿过了一大片屋顶,最后才在一根梁柱上垂下来。长线的尽头,悬着一个电灯泡,就像南瓜藤上结下了一只个头儿矮小营养不良的瓜。它苦着个脸,勉强把昏黄的光抖出来,照亮了房间中央一个圈儿。
屋檐边有一个煤炉,上面有一口小黑锅。每天夜里,它就蹲在屋角默不作声,好像一个人劳累了一天,正在睡觉。早上,外婆就把它提到外面,用火柴点燃一截旧报纸或者一撮刨木屑,塞进它空荡荡的大嘴里。不一会儿,压在它头顶上黑乎乎的蜂窝煤就被点燃,锅被烧得吱吱冒出热气。这个时候,外婆就拎起油瓶一倒,金黄色的菜籽油在锅里炸响,满屋子飘起了秋天田野里那种晚熟的香味。我知道,外婆又要开始变魔术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锅,外婆也能给我变出各种各样好吃的,有时候是香喷喷的蛋炒饭,有时是油炸花生米、金黄的糯米丸子。有时又是炒起来蹦蹦跳跳的豆子芝麻,这两样炒好后,外婆又烧一壶滚水,摸出一只黄油陶罐、一只茶碗,要给我筛姜盐豆子芝麻茶。每次过去,把我喂得饱饱的时候,外婆把我搂在怀里问我想不想她。
我嘟着嘴不说话,其实我已经不想外婆了,我变成了乡下的野孩子。
野孩子的快乐是无边的,野孩子的恐惧也是无边的。
那个叫露水坡的地方,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是茶树,到春天的时候,开满了白色的茶花。新绿的茶片托着莹白的花,一阵微风吹过,它们把自己当成了舞台上翩翩起舞的白衣仙子。每一朵茶花花托里都藏着蜜,摘下花朵嘟嘴轻轻一吸就是满满的香甜,等于满山都是一窝窝甜蜜,想想都让人心花怒放。当新茶尖冒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满山都像被绿油浇过了一遍,老师好像也等不及了,会停半天课安排学生摘茶叶。我们都很喜欢摘茶叶,一个下午也不用上课,就在一望无际的绿色波涛里奔跑翻滚,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老师蹲在一棵茶树前,教我们只能摘芽尖顶端那几片新生的嫩叶子,嗡嗡叫的蜜蜂围着她转圈儿,好像在争着说“我听懂了”。可是我哪有心思放在采茶上呢?那茶树底下红扑扑的覆盆子,熟得眼看就要掉下来了,还没人发现呢!茶树底下的草丛,一踏上去就会飞腾出几只绿蚱蜢,我急着想把它逮回来。还有在茶树枝间飞来飞去有飘带的花蝴蝶、愣头愣脑的白蛾子,每一样都把我的心牵走。在玩耍的间隙,我才揪几片绿叶子丢进篮子里。到了收工的时候,我篮子里的绿茶尖总是蓬松松稀拉拉的一点儿,不像别人都是绿油油的一座小山。
我很快就熟练了爬树,简直比有四个足垫的猫爬得还轻还快。我像猫一样在枝叶间梭来梭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树杈高处藏着鸟的家,刚出生不久的小鸟在巢里张着鹅黄色的嘴,等着爸爸妈妈飞回来,给它带回好吃的小虫子。看着小鸟幸福满足的样子,我羡慕极了。我从树上朝底下看,我的家就在不远的地方,可是我感觉和他们总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我站在高高的树顶俯视着走来走去的人们:像蚂蚁一样东奔西忙的母亲,像八爪鱼那样悠闲踱着八字步的继父。长廊远处又走来左肩膀高右肩膀低斜得好厉害的李老师,远远看去好像驮着一袋子重东西的歪车。教室里关着满屋子麻雀一样乌压压叽叽喳喳的学生,他们躲在书本后面、背着讲台上的老师探头探脑的样子真是好玩儿啊。放学的铃声响起,学生们陆续都回家了,天快黑了,母亲还没有找到我。看到她急忙窜进窜出寻找的样子,我差点儿笑出了声。我捡起一粒苦楝籽往母亲身后砸过去,她茫然地回转身,一抬头望见了树杈上的我。母亲想拿竹竿扑我,那也扑不到。竹竿尖快触到我的时候,哧溜一下,我越过一个枝杈,爬上了更高一层的枝杈。再不能高了,风一吹树就摆,我也跟着摆。其实我也想有翅膀可以随时飞走,可惜我并没有翅膀。我得在树顶上玩儿腻了才会下来,或者要母亲在树下承诺不再打我,也可以下来。我在高高的树梢顶上,像一片树叶一样随风飘摇,直到暮色将天地缩得越来越小。远远地,我看到外婆苍老的身影爬过了土坡,像一只黑蚂蚁一样慢慢挪近。
母亲和继父刚开始的新婚生活,就不可避免地拖上了我这个大油瓶。一到晚上,学校的学生散去,校园变得又大又空旷。前房对着操坪,这还好一点儿,草坪上虽然很空,但时不时还有人走动。可是安排给我的后房正对着山坡,一到晚上,山坡上都是黑魅魅可疑的树影儿,学生们告诉我,这里以前是乱坟岗。我时常赖在母亲房里睡,挨着母亲和七仰八叉的继父旁边挤着,到夜里便被抱了出来,放到隔壁漆黑的大房中去。到深夜醒来,我便盯着漆黑的山坳,时时提防着从窗外要飘过来一个黑黑的、哀怨哭着的鬼影儿,再也不敢安心入睡。乡下的同学教我,红布或者是铁器都是可以避邪的,我便悄悄地在床底下藏了火钳子,这至少能让我稍稍安心。而我在半夜醒来,还是时常会听到床底下真切地传来扑扑的新鲜的跳动声,我感觉自己的心在胸腔里快要蹦出来了。在惊吓中,我半睡半醒地度过一个个可怕的夜晚。愁云惨淡的我,被无法摆脱的恐惧完全压倒了。我很想外婆能过来陪着我,可她每次来,待不了一两天又得走。
有一次,外婆在路上遇到一只流浪的黄色小野猫,便给我带了回来。用小鲫鱼做了汤拌着米饭,拿一只缺口瓷碗盛着放在墙角,它勉强吃了一点儿,站在水泥地板上瑟瑟发抖,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渐渐长得肥大,到冬天的时候,外婆用旧棉衣给它改了一件背心,套了四只猫脚穿在身上,于是,穿着花背心的猫在房间里窜进窜出的时候,如杂技团的小丑一般,引得我们所有人都哈哈大笑。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小猫就乖乖钻进我的被子,靠着我打呼噜,那一起一伏有节奏的呼噜声像轻拍海岸的潮水,渐渐地将睡意蒙眬的我淹没。
我的新生活里不再常有外婆的影子,当一个拖油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拖油瓶的时候,还是挺快乐的。外婆大约每隔一个月来看我。从县城到乡下露水坡到底有多远的路呢?我也不知道。我所在的露水坡中学,应该就像是嵌在连绵起伏的茶树丘陵中央的一滴露水,要翻山越岭才能看到。
外婆可以搭火车来,从无穷远处驶来的火车,经过县城,也经过这个范家园小镇,它像一阵新鲜的穿堂风,吹过那迟缓而重复的小镇日常。那个时候的慢火车,像一个行动迟缓的老头儿,很有耐心一个站一个站地缓缓停靠,每到一个站,惊起站台的麻雀四处飞散。火车肚子里装满了人,到一个站放下一批,又上来一批。挑着担子背着麻袋的乡亲们,在孤独的月台上聚成一小撮。火车在镇上停留几分钟,从巨兽的大肚子里吐出来几个人,再喘一口粗气,消失在绿荫深处。这个时候,外婆已经跨过月台走上山坡,再顺着蜿蜒的山路走过来。
外婆应该还可以搭汽车过来。搭汽车过来要穿过村庄,还要路过一个代销店,店门口有一个厚重的大木案,早上有屠夫在那里挥着屠刀卖猪肉,五花肉切成长长的一条,用一根草绳系着啪的一声甩过来。村庄里有各种性情的狗,还有猫鸡鸭鹅。有的狗叫得很凶,但不过是虚张声势,并不会冲过来咬人。有的狗叫得又凶又追人,以为你要侵犯它主人的小院,非要把你赶出一里地不可。有时候狗群也会拉帮结派,对路过的人围攻,这个时候要捡一块石头,蹲下来,不能跑,假装做出威胁的样子,与狗的目光对峙,它就会心生退意。尽管积累了诸多经验,外婆有一次还是被一条恶狗咬了。被狗咬了的外婆对我说不疼,但我看到她手上的血牙印子很深,青筋仿佛要透过薄薄的皮肤暴出来,让人感觉很害怕。外婆沏了一壶酽茶,她说茶叶水是解毒的,用茶水洗洗就没事了。我听说过疯狗的事,担心外婆会死,但是到了第二天,外婆的伤口开始渐渐愈合了。
每次外婆都要想方设法给我带一点儿小礼物,很多时候是苹果或者香蕉、橘子。我也不知道外婆从哪里变来那些水果,听说外婆已经在城里摆摊儿卖水果了,那个时候敢做生意的都是胆大的人。各种花花绿绿的票子被外婆悄悄攒起来,藏在枕头底下,积多了就存进了银行里。她说,攒到明年冬天的时候,就可以买一块地。到时候,要在地上建一座漂亮的花瓷砖小洋房,要想办法给我一个家,细妹子得要有自己的房子才有底气,吃饭睡觉都不用看别人脸色。那个时候,乡里有一个水果是多么金贵呀! 小伙伴们除了家里吃的饭菜,其他的零嘴就是春天的甜茅根、刚抽出条的野蔷薇杆、茶树泡儿。还有秋天山上的野果,比如树上落下的苦栗、还带着刺儿的蔷薇花的梨形果子。乡下谁家有闲钱买水果给小孩儿吃呢。一个苹果是可以分成很多份儿的,用削铅笔的那种小刀切成薄片,争先恐后的一双双小手伸过来,把我包围。
除了礼物,外婆说的一路上的趣事更让我神往:无论坐火车还是汽车,都要跨过一条汨罗江。涨水的时候,江面上漂过从上游、平江山谷里冲下来的巨大的木头根和青竹子,比一个人还高大。枯水季节,能看到有人在沙滩上捡到跳出水面透气的鱼,还能捡到带花纹的石头、在江底沉了几千年黝黑发亮的乌木。汨罗江好像一个神奇的大口袋,时不时掏出一点儿新鲜的东西来炫耀一下。外婆说江边上有人不停地在找金子,但最难找到的是金子,它是捡不到的,要靠淘金船不断地往河床底下掏,挖出一筐筐的沙子,再经过机器的大手细细地筛过一轮又一轮,最后才能筛出那藏在沙砾中的碎金石,一点点儿就很值钱。河里的金矿石收集多了,就能送去淬炼提纯,再打成各种花样的金链子、金镯子、金耳环,摆在城里商店的柜台里,用暗红的细绒布托着,整个屋子都会被金灿灿的光照亮,好看得不得了。我被外婆说的金子迷住了。
在寂静的夜里,我好像隐约能听到江上传来淘金船吱吱呀呀的怪叫声,那声音在空荡的黑暗里张牙舞爪,只要闭上眼睛,我似乎感觉到它要把热乎乎的嘴巴凑近我,把长长的獠牙碰到我的脸上来。那江面上日日夜夜挖呀挖的船,像一只钢铁怪兽蹲守在江河的心脏上,好像把汨罗江的心肝肺都要掏出来。我怀疑他们要趁夜色把江底掏空翻个面,到底还要挖多久呢?那有成千上万的沙粒呀,金子会躲在什么地方呢?既然是那么珍贵的东西,又是谁把它藏在河底呢?
金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关于金子的幻想把我孤单的日子也点亮了,想想世界上还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夜也变得不再恐怖而漫长。我央求外婆下次来看我的时候,一定要带点儿金子来给我看看。外婆支吾着面露难色,架不住我扑在她的怀里反反复复地央求,终于答应了。
外婆先给我带来了一条晶莹剔透的塑料珠项链,也是金灿灿的,一下子套在脖子上,不长也不短,特别好看。一个乡下小姑娘怎么配拥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呢?它衬得我脸蛋儿都发烧,心里觉得怪难为情的。我假装问外婆,给我买这个干什么用呀?外婆一眼看穿我的小心思,她笑眯眯地对我说:隔汗的,隔汗的。我的心里好像来了一只小鹿,来来回回跳得可欢了。我戴着这条项链,白天把它藏在衫衣内里,晚上睡觉也舍不得摘下。开心过后,我又忍不住想,外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带金子来呢?
这次外婆好久没来看我了,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难道她是去河里找金子去了吗?这一天放学,太阳洒满斑驳的林间小道,我一边蹦蹦跳跳独自穿越山林,一边唱着新学会的歌:“竹子开花啰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远远地,我突然看到外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另一头,细碎的阳光穿过翠绿的树枝,落在她的身上,好像给她披上了一件镶满珠宝的花衣裳。
我欢快地叫起来,朝外婆飞奔过去,耳边只听到呼呼的风声。
外婆张开双臂把我搂进了怀里,又慢慢地放下来。接着,她解开两粒衣扣,把手伸进夹衣的内袋,从怀里郑重而神秘地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布包,托在手掌心里一层一层慢慢打开。外婆的手微微地颤抖着,每揭开一层,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终于等到最后一层揭开,我屏住呼吸,看到那雪白的粗布中央,躺着一些形状像碎土粒又像瓜子壳的东西,但是它们有着美丽的颜色,在太阳底下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好像是阳光点燃的一堆火,这是一把细碎的金子。我的嘴巴张得圆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原来金子就是这样子的呀!
那是外婆从淘金人那里借来的一把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