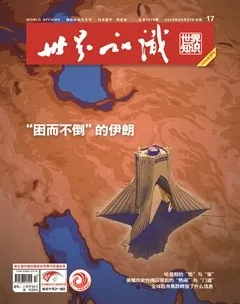美俄历史性换囚背后的“热闹”与“门道”
8月1日,美国和俄罗斯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换囚行动,涉及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七个国家的26人。俄罗斯向美西方移交16人,其中包括被俄以“间谍罪”定罪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美西方则向俄移交10人,包括此前被关押在德国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瓦季姆·克拉西科夫。
换囚是美俄(苏)博弈的重要手段
纵览美苏交往史,换囚从来都不是罕见事件。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复杂微妙,两国既是领导两个对立阵营的“敌国”,又不得不采取必要手段,防范局势在紧张对峙过程中失控。囚犯交换作为兼具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地缘政治博弈工具,曾多次在美苏之间进行。
美苏换囚史上最著名的当属1962年美苏首次交换被扣押的间谍。1957年,苏联王牌间谍鲁道夫·阿贝尔被叛徒出卖,遭到美中央情报局抓捕。被捕后,阿贝尔拒绝与美情报部门合作,被判处30多年监禁。1960年,美国U-2侦察机在对苏联进行间谍侦查时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抓获,并承认为美情报部门服务,这使苏联掌握了用于交换阿贝尔的最大筹码。1962年,美苏最终达成换囚交易。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间谍之桥》正是根据该事件改编。在电影末尾,鲍尔斯和阿贝尔在夜雾笼罩中,以同样的时间穿过连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格里尼克大桥重获自由。在此之后,换囚成为美苏两国营救在外被捕间谍的重要方式。1985年6月,美苏在“间谍之桥”——格里尼克大桥上进行了两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美国释放了四名社会主义国家情报人员,包括著名波兰间谍扎哈尔斯基,其通过收买美飞机制造公司工程师获得大量美军机雷达和武器资料。苏联则释放了23名被控在东德和波兰从事间谍活动的美情报人员,相关人员信息至今未被公开披露。
除交换情报人员外,美西方也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异见人士”作为重点交换对象,以持续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工作。1976年,美苏首次进行非情报人员交换。苏联释放因反苏宣传被捕的布科夫斯基,以交换智利共产党领袖科瓦兰。对苏联而言,布科夫斯基只是耍弄政治的“流氓分子”,能换回被授予“列宁和平奖”的社会主义斗士科瓦兰是一笔“划算交易”。对美国而言,布科夫斯基却是炒作苏联人权问题的重要工具。因此,两国都将此次换囚视为本国外交成功的标志,布科夫斯基和科瓦兰在分别抵达美、苏后都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1979年,苏联再次用五名“政治犯”从美西方换回两名被扣的克格勃情报人员。1986年,苏联又通过“异见人士”夏兰斯基换回来自苏联、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五名情报人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俄罗斯仍然保持换囚传统。2008年,被视为“更具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梅德韦杰夫当选俄总统。次年,奥巴马政府上台执政。双方都希望改善俄格冲突后的紧张关系,美俄关系更趋务实。2010年7月,美俄进行大规模囚犯交换。美方移交了十名俄罗斯间谍,俄方则向美西方移交四人,其中包括投靠英国情报机构的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2018年,斯克里帕尔在英国被投毒,一度引发俄与美西方国家的外交危机。在这次换囚中,还有一对夫妇被释放回俄罗斯——埃琳娜·瓦维洛娃和安德烈·别兹鲁科夫。有报道称,过去20多年来这对夫妇一直以化名在加拿大和美国过着“潜伏”生活,其间安德烈曾在一家战略咨询公司就职,因此获得了很多对俄方有价值的情报。2010年6月,他们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判终身监禁。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美俄换囚行动仍在继续。2022年12月双方进行了“一对一”换囚。俄方释放了因持有和走私毒品罪名而获刑的美国女子篮球明星布兰妮·格里纳,美国则释放了俄军火商维克多·布特。

单赢还是双赢?
8月1日夜间,俄总统普京和新任防长别洛乌索夫等俄高官亲自为获释人员接机。普京称:“感谢你们所有人忠于誓言、职责以及没有忘记祖国。”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也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俄方释放的四名美国公民。拜登将此次换囚行动评价为“外交和友谊的壮举”,赞扬参与换囚的西方盟国所作出的“大胆且勇敢的决定”,尤其感谢德国总理朔尔茨。美国媒体也争相炒作称,这是拜登距离卸任还剩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取得的“重大外交胜利”。
美俄此番看似“双赢”局面背后,暗藏着各方复杂的利益考量和内部分歧。在美国大选正酣之际,拜登政府力促达成换囚协议,更多是为了彰显民主党政府与盟友协商的能力,争取更多政治和外交遗产。近期,民主党大力宣传哈里斯为推动达成换囚协议的种种努力,意图为其增加竞选筹码。共和党似乎对此并不买账,特朗普及其团队批评此次换囚是“一笔糟糕的交易”,质疑民主党政府为了促成换囚“付出了不必要的沉重代价,将侧面助长俄罗斯政府的错误做法”,担忧“人质交易”会放大敌对国家对美国公民的威胁等。
相较美西方,俄各届舆论对此次换囚评价整体较为积极。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的背景下,俄需要藉此加强内部凝聚力。俄释放人数总数虽多于美西方,但最有价值的只有《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几人。惠兰于2018年12月在莫斯科参加前海军陆战队同事与一名俄女子的婚礼时被俄联邦安全局抓获。2020年6月,俄法院判处惠兰间谍罪成立,其获刑16年。现年32岁的格尔什科维奇是《华尔街日报》驻莫斯科分社编辑,因涉嫌“试图获取军事机密”,于2023年3月在叶卡捷琳堡被拘捕。俄此次释放的其余人士大多是反俄的“异见人士”,因此俄总体上并不“吃亏”。还需考虑到,普京早年在情报系统工作,对营救在外执行任务并被逮捕的俄情报人员“感情特殊”。在这次换囚中,俄情报机构人员瓦季姆·克拉西科夫被释放回俄。2019年,他在德国柏林一所公园枪杀了一名格鲁吉亚公民。有报道称,后者是一名打入极端组织的间谍,为格鲁吉亚政府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随后,克拉西科夫因被判谋杀罪在德国服刑。
俄与西方关系难言缓和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美西方经历过数次关系紧张和缓和。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与美西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此轮换囚更多是双方在紧张关系下,基于本国利益的“机会性交易”,而俄与美西方关系真正的缓和绝非易事。
一方面,大规模换囚表明美俄间仍保留必要沟通渠道。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关系虽彻底跌入低谷,但在涉及两国核心安全关切,以及换囚等复杂棘手问题上仍存在畅通的长效沟通渠道,涉及国家安全决策、专门特使、情报、外交和国防等各层级各部门。比如,2022年11月,俄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就曾与美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通话,就核风险问题进行讨论。2023年6月“瓦格纳事件”后,两人再次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2024年6月,俄新政府重组伊始,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和俄新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通话,讨论了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可见,虽然美俄立场严重对立,但双方仍尽力避免发生直接对抗,导致局势失控,并能在有限的共同利益议题上达成共识。据悉,美俄自2022年初就开启了此次换囚谈判,美国务院发言人、美驻俄大使、俄副外长等高官多次在不同场合“对外吹风”,美俄正在利用“有效渠道”沟通换囚。
另一方面,换囚难以对美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换囚往往被视为关系缓和的象征,但美俄就欧洲安全框架、乌克兰危机、国际秩序等问题存在根本分歧,双方关系很难因本次换囚而出现实质性变化。此次美俄实现换囚的主要目标也并非“改善关系”,更多是出于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美白宫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也在换囚后表示,“美俄关系仍非常困难”,并强调“这种关系中并不存在充分信任”。事实上,仅在换囚一周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就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再次加剧俄与美西方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上述这些沟通渠道难以弥合美俄间长久以来积累的矛盾,也难以改变两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作者分别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