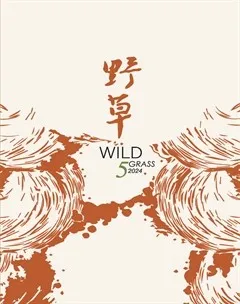蝴蝶的诗学
读这本诗集的时候是夏至前后,一个新的季度翩然而来,带来闷热与潮湿的气候。
诗集的名字奠定了宁静淡远的气质,既是树皮与苔藓,那必然是幽暗的、古朴的,接着,便引发出种种疑云:是何人何物从树皮和苔藓中诞生?而那诞生的,又如何成长与消亡?然而事实上,读者看完便知,其中蕴含的题材类型与情感质地要远远超出预想,常识与尝试、新与旧的诗学,同时在南方的山水中搏斗。
最后,它变幻为一只翩翩而来的旧蝴蝶,有着春水的肉身和钢铁的骨骼。
就这样,又翩翩而逝。
Ⅰ画蝶:现实之轻与抒情之重
叙事在骆艳英的诗歌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于现实的感知和描摹是诗人的必备生存技能。如何描绘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这对每个诗歌写作者来说都是一个终身命题。首先,我关注到《世相往复》这首诗,其中写道:
我值守的卡点
位于南坑西路出入口
它的西边,是一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居民小区
见证过无数日出日落
云雀似落叶——
那无辜的秧苗,麦地,蚯蚓与蛙鸣……
车,马,邮件,淡淡炊烟……
之所以特别提到这首诗,是因为它提供了富有画面感的鲜明镜头:身处于南坑西路出入口的卡点,由这一固定狭小的视角来进行种种观察。这个画面给我的感受近似于某种隽永的寓言,不仅仅是对于具体事件的描述,而且是诗人对现实进行洞悉和描绘的出发点与中心点。由此,“往来车辆的呼啸声”“一位父亲把年幼的儿子举了起来”“测温仪,文件夹,圆珠笔与健康码”……才逐渐登场,成为骆艳英所构建的一种新江南,在梅雨声中交织起暧昧的现实主义的阴云。古典的生活方式已经退场,仅留下空荡荡的布景,等待着一种时代的诗歌语言去填充。
从这里,我们可以感知到骆艳英诗中独特的运镜和时空感。譬如从一扇童年的窗中向外眺望。诗人以敏感多情的心灵将所见所感生发在笔端。“从房间里面出来/然后,天空看到了我/黑色裤子,上衣停满了白鹤”(《10月13日,与天空的片刻凝视》),“我在母亲的地里剥蚕豆/疾控中心的消杀车开过人民路”(《剥蚕豆》),“奶奶的躯体像一块巨大的砖/被殡仪馆的人扔进炉子”(《夜聊》)。在这些叙事类型的诗歌中,总是洋溢着静谧的美感,与其中淡而鲜明的讽喻口吻形成微妙的对比。这种批判的基本立场尤为关键,它是诗歌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明证。尽管,诗歌从不向人证明它自身。尤其是在隐蔽的写作中,它并不期待列入某种诗歌史的叙述中,也不需要汇入诗歌运动或团体的河流中。
与此相对的是,诗歌抒情的传统在本书中随处可见,它们代表着骆艳英写作的另一层面的特质,就像“两片互求印证的上弦月与下弦月”。或许,这个特质是更为深重与坚固的。骆艳英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似乎对于每个主题,每样事物,她都有话可说。比如《麻将诗学》《树叶》《雨》等作品,它们都是将一个具体的东西抽象化,从而产生诗的内涵。在《婚礼》一诗中,婚礼被提炼为:“花冠,烟火,蜜的深思,克重/名字的缩写……/让它看起来像一座小型的宇宙:/转动着婚纱,礼服,花童,进行曲,牧师……”我们无从猜测诗人对于婚礼的态度,它似乎仅仅是如此多要素的集合,这背后的秘密则令人遐想。而在《八字桥访友不遇》中,诗人选择了一种拟古的语调,“八字桥像一首小令”,当历史与现实互为印证,我们自然能感受到古今相同的旷达与失落。
骆艳英的抒情具有明显的怀旧气质,它是属于夜风、白鸥和乌篷船的,属于此生此世的幸福与不幸,属于美丽而孤单的月亮,它们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如此洗刷着我们沉浸于世俗的心。当你翻开月亮的背面,自然可以寻找到通往记忆与观念的传送门,回到一所被屋檐包围的旧日房屋中。
II放蝶:野柿子,第五艘船,江南迷宫
吟咏山水风物和人文民俗,是骆艳英诗歌的一大主题和一大亮点,如《西湖半日》《与群山同行》《11月26日:会饮西白山》等诗作,触摸浙江山水的脉搏,富有生活乐趣,充满了对自然界的熟悉和深厚情感,如同一场雨后的行吟,惬意而美妙。
这其中有大量清新自然的小品式佳作:“山塘水泛起的薄雾里,看到一枚果实/像惊喜的隐喻,分泌出一层甜霜”(《一棵柿子树》),“梅树的脊椎上/蜜蜂用一只脚支起春天的耳朵/另外一只挂着黄金”(《钟声与船桨》),“这一管一管从根茎中抽出的秘密的线条/管弦乐队无人演奏的白色竖琴”(《芦花》)。写景状物、借景抒怀是重要的诗歌源头,只是如今,新的情感内涵不断涌现,山水和行吟正在逐渐衰落,在这本诗集中,我们仍然能找到一些工笔画般刻画风景的遗风。
在山水中遗存的诗句,至今仍能为失意的人们提供永恒的文学遗产和心灵安慰。在剡溪,我们见到的是散发弄扁舟的李白(《低飞的剡溪》)。而在湖莲潭,我们见到“杜甫,杜牧,杜秋娘的诗句/装点着一座灯杆的三个面/谢谢他们把空出来的一面留给了湖/告诉我里面装着茅屋,草木,金缕衣/还有好大一个长安”(《湖莲潭即景》)。是否前辈诗人留下的馈赠太多,都像碎珠玉,随意散落在溪水边、山头上,俯拾即是,只要有人愿意去捡拾,如同诗人揣摩一只偶遇的野柿子:“在淡青色的雾霭之下/将自身缩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火焰/每年秋天,它们都将焚烧一次”(《与群山同行》)。
《第五艘船与大佛寺》一诗糅合了风景、历史与现实,非常值得一读。寺庙,这个风景诗的常客,以往它出现时,或寂静超尘,或萧疏荒凉。此时,当它同样被放置在时代的布景中,则呈现出奇异的荒诞感。
首先是口罩的登场,“每个人都会讨厌它,通过反复调整角度/来主张鼻子有畅快呼吸的权利”。然后是游人对于蜥蜴断尾的漠然,接着,停泊于人工湖的第五艘船,已经失去了船桨,诗人关注到这个残缺和矛盾,正如失去绳索的山洞,人们对于周遭的冷漠是一以贯之并愈演愈烈的。香枫的树荫仍然在保护我们,九岁的男孩仍然无忧无虑,窗洞里的一声“平安”,这些景象与漠然的社会氛围形成某种残酷的对比,揭开了这场游览内在的错位感。
此诗丰富了风景诗的内涵和情感类型,不拘一格,足以证明骆艳英写作此类诗歌时贴近生活的特点,有着真切的肌理,十分动人。
《西湖半日》中写到“它无限扩张下的江南迷宫/需要一支振金手臂在江水里掘开春衫的地图”。不妨将骆艳英所创造的山水宫殿称之为一所江南迷宫,所有幽静和绮丽的意象是建筑材料,将青萝裙和白沙堤引进同一片枯山水中,夜雪和雨水都来临了,而文学的无用性则是最后的辩词。
将心灵放归与山水自然,是对于永恒不变的核心的向往,对于自由的终极追求,如同蝴蝶飞回风中,从此褪去旧梦,真正变幻为万事万物。
III梦蝶:隐喻的蝴蝶,抽象与野性
李白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到“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神仙诸人纷纷降落凡间。李贺则有“天上几回葬神仙”之句。关于宇宙和时空的奇诡想象从未断绝,近年来不乏以科幻、技术革命、电子游戏等为题材的现代诗,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媒介、新的汉语,同样的迹象也出现在骆艳英的诗中。
首先是,我们熟悉的自然景物类的意象被取代了,转而变为3D 巨幕、VR 直播、VR 游戏、暗物质、黑洞……在亭台楼阁之上,数字世界的元素正在侵蚀与修补原有的空洞。
紧接着,便重新组合成另类的传奇和野史。在《白色的庄周》中,诗人写道:“白色的庄周,驾驶着飞船/在银河流汗”。庄周的形象在这里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特征,或许这正是“庄生晓梦迷蝴蝶”式的梦幻,能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的庄生,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每个宇宙,进而演化为一种太空奥德赛版本的《逍遥游》。这首诗延续了骆艳英一贯疏朗清澈的笔调,如同运行在平静的云层之上,又发展出浪漫的隐喻与诘问,可以说是“抽象与野性”的风格体现。
而《移动研究》一诗,则更集中反映出骆艳英诗歌的理性、沉思与精密。“移动”意为改变原来的位置,凭借科技发展的羽翼,移动对于我们来说更为便捷,不论是肉身的迁移,或是信息的传递。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曾互为时空伴随者。骆艳英敏锐地捕捉到“移动”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我们在截然不同的事物的两面之间往返,通过坐标与编码互相复制与传送,直到逐渐混淆彼此的区别。
这既是空间之间点对点的移动:“是我随身携带的一体机/宇宙的发送器”,是地球(家乡/传统)到外星(异地/现代)的移动:“是我在星际迷航,为你和她,你和故乡/荒草与稻谷,米沃什与里尔克”,又是生与死之间的移动:“甚至是为死者与生者之间/建立一种虚拟与现实的链接”。
这首诗是对于马克·斯特兰德的“我移动,是为了保持事物的完整”的一种再诠释。科幻美剧《西部世界》第三季也曾引用这首诗作为标题《田野中的空白》。马克·斯特兰德以精妙的诗句展现了对于自我存在的质问,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辨认关系。“我”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空白、一个缺口,唯有“我”不断移动,才能使这个世界被充满,重新合拢,变成完整的事物。而如今,漫天飞舞的信息流是否以一种更虚无的方式充满了世界?我们不仅在田野的这一处,也在田野的那一处,然而我们自身的空洞究竟是否仍有人孜孜不倦地去观察与思考呢?
到了《边界的意义》中,骆艳英对于自我认知又提出了新的问题。“直至时间的暗物质,被明天扔进今天的黑洞/光明只剩下一个尾巴,但是/如何解释尾巴,又成了新的问题”,在宏大时间的辩证与矛盾之下,在一个被新概念填满的宇宙中,我们如何维持着生老病死、忧伤快乐的日常生活?或许我们最终无法逃脱肉体的牢笼,只有“当人类变成另一个物种时/才能解释我与本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诗人仍然留给我们一个光明温暖的结尾:“可以将桃子,手,书,筷子等同桌子解释/但是道德,诗歌,气味与爱不可以”。
这种坚持,正是诗歌的勇气与自尊所在。
为何说到蝴蝶呢。
或许在骆艳英的诗歌故土上纷繁降临的意象中,蝴蝶原本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那不曾到达的地方,眼窝深处的蓝蝴蝶”(《白果树下(三)》),“我想象自己正在变成一只蝴蝶”(《十九峰,在天空的锯齿里彻夜不眠》)。无论是梁祝哀史的结局中飞出的转世蝴蝶,还是庄周的故事中永远醒不来的蝴蝶之梦,它们都共同代表着一种自由与转化的启示。正如事物的两面,既是脆弱的,又是轻盈的。到了终结之日,它将提供给我们顿悟和出路:“这世间的爱,与逻辑学建立起来的永久叙述/是一种疾病,需要蝴蝶的治疗”(《边界的意义》)。
在秩序森严、久有沉疴的世界上,情感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负担。请让我们暂且相信,诗歌与真正的爱和美德一样,具有久远的价值。愿这本诗集在增加我们的困惑的同时,亦增加我们的信心。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