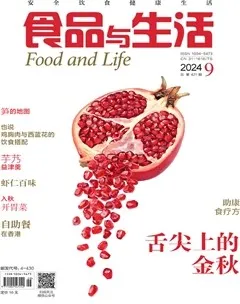论“浇头”
之前聊过阳春面,这一期便来讲讲阳春面的好搭档。
笔者初到上海,与友人约吃面时,便从中感受到南北饮食文化的差异——北方人吃面,吃的是不同粮食的滋味,不同技法的口感,吃时配些简单的韭菜花、芝麻酱、辣椒糊等,丰富入口时的味觉层次即可,再奢侈点,配些“汆儿”、卤与臊子,那便是面餐的顶配了;南方人吃面,几乎是雷打不动地以阳春面做底,好吃与否全凭面上用来调味的菜肴,其花样之多,滋味之丰富,与其说是吃面,不如说是吃菜时配了碗顶饱用的主食。而这些令食客魂牵梦萦的菜肴,便是今天的主角——“浇头”。
所谓“浇头”,就是加在面条上的各式菜肴,或提升面的卖相,或丰富面的口味。浇头在清朝的诗作与小说中偶有出现,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便有“面有浇头……以长鱼、鸡、猪为三鲜”的表述;《红楼梦》第六十一回,莲花儿与柳家因鸡蛋起争执时,柳家也以制作“预备菜上的浇头”为由回击“偷主子分例”的指责。虽然由来已久,但浇头具体出处如今已难以考证,只留下几种说法,一说是“加头”的谐音,如在1924年东陆图书公司发行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切口”指古时各行各业的行话)中,便用“加头不在面上,另用盘盛也”解释“过桥”一词,此处的“加头”便是如今的浇头;另一说则是苏州话中“桥头”的变音,当煮熟的面条入碗后,厨子要用长筷给面条定型,使其端上餐桌时如水上拱桥,淋在上面的菜肴自然成了“桥头”,久而久之便演变为“浇头”;此外,还有人认为其出自民国时期风靡上海滩的“盖浇”技法,由盖浇饭延伸而来……各种说法皆有其道理,任由各位看官评说。
作为阳春面的灵魂,浇头的食材包罗万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田里种的,无一不足;至于技法,红烧、清炖、油炸、卤制,也是花样百出——卤鸭、熏鱼、焖肉、三虾、大排、肥肠、鸡丝等等,各个都有其庞大的受众。上海的老字号面馆不算少,比如“德兴馆”的招牌焖蹄面,蹄子在老汤中经过长时间卤制,早已软烂松散,入口一抿即化,咸中带甜、甜中蕴鲜,香味久久萦绕于舌尖,令人食欲大开;又比如源自苏州的“朱鸿兴”面馆,新出锅的爆鱼与爆鳝口感脆爽,不仅鲜、香、甜、咸兼备,且滋味越嚼越浓,单拿来下酒也是绝佳的佐品;此外还有“心乐面馆”的肥肠面、“明呈黄鱼面馆”的黄鱼面、“长脚汤面”的肉丝面、“春和面馆”的大排面等等,也是各类美食排行榜与探店节目的常客。
随着阳春面的盛行与面馆的扩张,久而久之,以浇头为中心的各类隐语也悄然流行开来。比如在古时苏州一带,猪肉制作的浇头被称作“带面”,肉质从肥腻到精瘦,又细分为“硬膘”“五花”“小肉”“去皮”四个档次;鱼肉制作的浇头被称作“本色”,鱼身从好位置到边角料,则可分为“肚档”“头尾”“头爿”“甩水”“卷菜”五个部分;倘若食客想一次性品尝几款浇头,也无需多费口舌,想要双拼,就说“鸳鸯”;想要三拼,便说“三鲜”;如果再复杂些,对双拼、三拼的浇头有具体的要求也无妨,“红鸳鸯”是鱼肉双拼,“白鸳鸯”是鸡肉双拼,此外还有“大鸳鸯”“小鸳鸯”等等,各有对应。此外,面里加不加葱、浇头放在哪里也有相应的叫法,比如多葱叫“重青”,不要葱则叫“免青”;浇头单独盛盘叫“免浇”,埋在碗底则叫“底浇”……如此一来,进到面馆,老饕只要简单吐露寥寥数语,店家便能心领神会,准备对应的浇头,既便捷又高效。只是难为了初来乍到的食客,面对这间谍接头般的情景,反倒不知该如何点单了。
从词义到种类,从隐语到文化,在江南地区,浇头与阳春面的关系与故事绝非一篇文章可以说清的。总之,当上海人说“吃碗面就好”时,最好不要只把它当成一碗面,他们真正想吃的,可能是面上千变万化的浇头。至于具体是什么,恐怕只有面对菜单时才会揭晓谜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