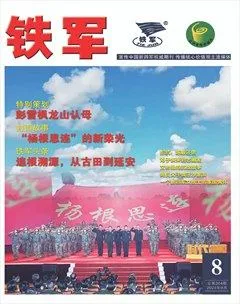青山一道同云雨

同学,同事,同伴。朋友,亲友,战友。人在社会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学是一起学习,同事是共同做事,同伴则是携手为伴。朋友因投缘为友,亲友为亲情相依,然而战友却是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并肩战斗而结成的一种高于一切的关系,是那种可以为你堵枪眼、挡子弹、蹚地雷的情谊。干渴了,一壶水全连喝;饥饿了,一个馒头掰碎了吃;未婚妻的照片大家抢着看;家庭有难常收到不署名的钱。这就是战友,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情。这种情越是在艰难困苦危急时刻体现得越是分明。
在岛上战士每月6元钱的津贴,外加2元的驻岛补助,就这点钱也没处花。“烟枪们”开心和愁闷时想过把瘾,烟没有。酒友们逢年过节想刺激一下,酒不见。哪个小馋猫过生日想打打牙祭,除了白菜萝卜煮黄豆,还是啥也没有。因此,凡是探亲回乡,出岛训练,看病归来,吃的喝的用的,大家都把大包小袋塞得满满的,甚至父母和未婚妻来队也要叮嘱他们多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来,因为战友们在这小岛上日子过得太清苦了。所以每当船进岛,码头上就成了欢乐的海洋,战士们开心得像过年一样,你抢我夺,你推我让,共同分享着甜蜜。
记得1980年春节前,教导员谢宝君随送年货的登陆艇来连队蹲点,这位老红军的后代,是师球队的中锋,一米九的个头站在小艇上就像挺拔的船桅,可海上的风浪却把他折腾得半死,下了船还蹲在码头边呕吐。谁知晚上他却来到我宿舍,从挎包里掏出几个罐头和一瓶红酒,往小桌上一摆,把倒满酒的茶缸递到满脸惊讶的我手中:“来,祝你生日快乐!”一句话,让我差点泪奔,我早就忘了今天是啥日子,可教导员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还不顾颠簸晕船,特意赶来为我庆生,酒还没喝我先醉了,面对这浓浓的战友兄弟情谊,谁能不醉?!
1979年1月20日,大海碧波不兴。平山岛上新兵连手榴弹实弹投掷正在进行中。副连长李雪半蹲在掩体内,仔细地为每一位新兵讲要领,提要求,做示范。引弹,拉火,投掷,卧倒。李副连长瞪大眼睛跟着那条冒烟的抛物线飞行,直到远远传来爆炸声才长吁一口气。轮到浙江籍新战士姚良发投弹了,李副连长脑中的弦没有丝毫松弛,引弹,拉火,投掷,意外的是手榴弹落在了两人的脚下,“吱吱”地冒着白烟,千钧一发之际,李副连长肩膀一挺把发呆的小姚撞下了掩体,自己顺手抓起手榴弹向外扔去。巨大的爆炸声响过后,李副连长看到掩体内发抖的小姚安然无恙,此时才感到自己左腿沉重地挪不动了,殷红的鲜血早已浸透了棉裤。他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救战友的行为,是新战士受到的最震撼心灵的天花板级别的教育课。
1979年12月9日,是准备做新郎的我难忘的日子。
下午3点,观察哨电话:“连长,海里有人!”来不及细问,大家立即中断了正在召开的支委会。手枪一拎,就冲到了哨位上,那时候,虽然听不到西南边陲急骤的枪声,但小岛上许多战友早已奔向了那片血与火的国土。那一封封来自遥远边疆的信笺,无不带着浓浓的硝烟味,此时半点情况都不敢马虎。
在距岛500米的海面上,一只用几块泡沫包装板扎起来的小筏子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吃力地划着桨向小岛接近。这样的小筏子居然敢在这深海中与6级大风搏斗,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越南难民?还是化装特务?我边用望远镜观察,边命令三班长用上膛的冲锋枪瞄准了他。我想一旦有诈,迅即将其击毙在海里是绝对有把握的,因为三班长是全师数得着的神枪手。小筏子越来越近,我看清上面只有一个人,而且用绳子捆在小筏子上。
“靠过来,接受检查!”半导体喇叭在海浪的喧嚣声中没有多大作用。但那人还是听到了,看得出,他正竭力地向小码头靠拢。但是海浪撞击岩石后回冲的力量,使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岸边。怎么办?炊事班长韩复胜拿出了他钓鱼的绝招,线一甩,钓钩准准地钩住了小筏子,岸上的人齐声大喊,让他把鱼钩钩在锚绳上。那人哆哆嗦嗦了许久,总算钩好了,绳子慢慢地拖过来了,小筏子也揺摇晃晃向岸边靠近,巨大的回浪几次差点把筏子掀翻。官兵们都禁不住发出一声声惊呼。为了安全,我让大家把小筏子小心地牵引到码头的一侧,那里有一排台阶直伸到水里,趁一个很大的回浪退去之际,我迅速沿台阶下去,伸手抓住了那人冰冷的手。此时只要他站起来,随我的牵拉,向前一跨就等于挣脱了死神的拥抱。不料,他却一动也不动,我又迅速抓住他的衣领,想拖他上来,还是不行。来不及了,一个大浪呼啸着当头压下来,我就像被人轻轻地一举,接着眼前一片黑暗……
当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我已离码头十几米远了,只听得码头上一片“连长,连长”的呼喊,有十几个战士已准备跳到大海里来,我一边借着又一个大浪的推拥乘势向码头靠近,一边竭力大喊:“谁也不许下来!”我深知,此时若再有人落水,结果是统统完蛋。
驻连的教导员张志林一边拦着要下海的战士,一边宣布纪律:“谁不听指挥处分谁。”
幸亏我穿着一身新棉衣,此时还没浸透,就像穿了一件救生衣。当我胳膊挎住了台阶的瞬间,也下了台阶的四班长张广忠双手拉住了我。我也顺手抓住了已经落水但仍抓着绳子的那个人。一个更大的海浪,铺天盖地当头压下来,我想这下真完了,但海水退去后我们几个人从水里露出来,就像小时候课本上《猴子捞月亮》的插图一样,一个拽着一个的胳膊,全连都挎在了一起。
现在每想起那个最珍贵的镜头总是要定格,总是让我激动不已,面对死神的挑战,大家挽起手,心连心,分一分危险给自己,送一分安全给战友。平时生活中你高我低,他强我弱,似有解不完的小疙瘩,而此时心胸却像蓝天大海般广阔无际,晶莹剔透,里面装满了浓浓的战友情谊。
人都上岸了,大家欢呼着把我围住,却几乎忘了那个躺在码头上一动不动的落水者。等安排把人送到卫生所去抢救,组织把小筏子拉上岸,叮嘱哨兵在没弄清其身份之前不能放松警惕,并及时向师报告后,我才感到周身麻木,双腿都冻僵了。
那人挂了两瓶水,第二天才缓过来,他吃力地告诉我们,他是山东胶南县灵山岛人,叫薛友林,56岁,在海上干了40年的渔民。五六天前,侄子结婚,求他在近海钓点鳗鱼,正当他全神贯注沉醉在丰收喜悦之时,突起的大风使他来不及反应,就被无情的风浪刮到了茫茫的深海中。在这死神随时都会降临的四天五夜里,强烈的求生本能,使他随波漂流,手虎口被小桨磨得露出了骨头,双腿肿得比腰还粗,他靠生吃鳗鱼、喝尿来维持生命。当看到我们小岛时已产生了幻觉,以为到了他们的灵山岛,甚至仿佛看到自己的老婆孩子,然而被拖上岸时,心中那股支撑的力量,一下子全都没有了。问他是怎么上岛的,他只记得是被解放军抬上来的。他在千恩万谢的同时,求我们给他家发一封电报。
薛友林获救的消息使胶南县灵山岛震动了,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这之前公社先后出动了130多条船去寻找他,在感到毫无希望的时候,家里人只好面对茫茫大海,哭天喊地给他办了丧事。这突降的喜讯,把他一家都召到了连云港。10天后,家人随补给船赶到岛上,当看到薛友林穿着连队赠送的一身军装,已基本恢复时,全家人都哭了。
十几年间,仅自己参加和组织抢救沉船落水的渔民就达23人。每次官兵们都是不顾个人安危,顶风斗浪,从海龙王口中把遇难的渔民抢了出来,帮他们修好船,补足食物和饮水,送返回家。此外我们还多次救治了患急病的和被毒鱼咬伤生命垂危的渔民。每次台风,渔船靠岛避风,官兵们总是嘘寒问暖,送水送粮送燃料。因此,渔民们总是不无感激地说:“无论有啥困难,只要一看到小岛,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在岛上,人与人之间就像这碧水蓝天,通透晶莹。在物质利益、名利地位,甚至生死面前,总是坦荡磊落,先人后己,奋不顾身。新兵站哨紧张,老兵陪了一班又一班。施工排险掏哑炮,连长和营长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一起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本来一家人,何分你我他。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老先生说的就是这意思。
(责任编辑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