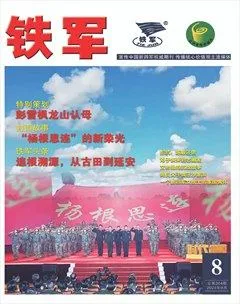爷爷的“花生情结”

自我记事起,爷爷的餐桌上,常有一碟花生,有时是煮着吃,有时是炒着吃,也有时是生吃。我知道,那小小一碟花生承载的是爷爷对那段烽火岁月、那些难忘往事的深切回忆。
爷爷名叫吕凤翔,是一名新四军老兵。1937年“七七事变”后,爷爷作为进步青年,毅然舍弃家中的千顷良田、数十家商行,怀着满腔热血,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940年,爷爷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敌工班毕业,又经过半年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特殊训练,奉命奔赴淮北,任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一团政治部敌工股股长兼团直属机关指导员,负责分析情报、处理战俘、思想宣传等对敌工作。
那年秋天,根据地发生了“耿吴刘事件”,六旅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叛变投敌。支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急调爷爷到萧县,任二连指导员,争取可能投敌但尚未行动的耿蕴斋和吴信容部。临危受命,爷爷却十分冷静,他很快确定了以争取底层士兵为突破口的方针,与士兵同吃同住,为他们念家书,和他们一起唱歌、拉家常、交朋友,打下了稳固的群众基础。下了一番工夫后,爷爷终于成功化解了一场濒临爆发的哗变,为部队保存了一个整编连的有生力量,受到首长的肯定和赞许。
1942年,爷爷升任十一旅敌工部负责人,随着部队转战,出任驻泗五灵凤县敌军工作站站长。豫皖苏边区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日、伪、顽、匪四股力量交织,据点林立,形成日伪合流、顽伪合流、顽匪合流、伪匪合流的局面,地下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爷爷凭借在延安学习的一口流利日语和帮家中打理过商行的经历,乔装成旅日归国的富商少爷,与日本军官攀交情,巧妙应付盘问试探,套取情报。为团结各派力量,他只身深入敌区,与伪警察所所长交朋友,在伪军内部发展线人、安插卧底,策反敌伪副旅长陈香圃率部起义;与土匪头子促膝谈心,使土匪为我军通风报信,将匪势力范围变为敌我冲突的缓冲过渡带;与安青帮会结交,考察可靠的帮众发展为特别党员,在市井各行当遍布岗哨。他广交望族乡贤、官员名流,以救亡图存共识争取支持,也访贫问苦,常常步行百里山路探望敌占区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军民感情。
淮上的沙土地,适合种花生,不管到哪家,热情的农民一边让孩子到门外玩耍放哨,一边捧出花生招待他,有水煮花生、炒花生,若来不及煮、炒,就吃生花生。“老百姓愿意拿自家的花生招待新四军,代表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爷爷说,“那时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能吃上花生,是我的福气,只是为遵守军纪,却无法将花生带回去,与战友共享美味,很是遗憾。”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站在淮北设置了诸多交通站,织就了一张密集的情报网,为粉碎日、伪多次“扫荡”“围剿”与对敌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支持。
爷爷的其他一些战友,却没有如此幸运,在对敌特战线的残酷斗争中,没有等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就和同志们永别了。
我理解了爷爷的“花生情结”。它源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源于那片浴血奋战的热土,源于那些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的往事。它纪念淮上军民的鱼水深情,也寄托着他对同袍战友的难以忘怀、对同志牺牲的不愿释怀,以及对捐躯烈士的无限缅怀。
我想起许地山的名篇《落花生》,花生最宝贵的地方,在于“果实埋在地里”。在我的心中,深藏在地下低调生长、默默结出硕果的花生,就像爷爷和他的战友们,在地下对敌隐蔽战线上,默默工作、默默奉献。
(责任编辑李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