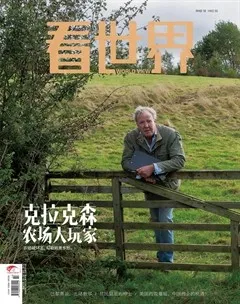人造子宫,能否拯救人口危机?

今年6月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韩国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表示将启动全力应对体系,努力解决当前生育率过低的严峻形势。
韩国是世界上人口预期寿命最长、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自2020年开始,人口已连续数年负增长。如果低生育率问题得不到解决,韩国或将成为世界上首个自然消亡的国家—实际上,不仅仅是韩国,低生育率问题也是其他不少国家正在面临的重大挑战。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2022年全球平均生育率已经跌至2.3%,有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低于2.1%—这是维持自然人口数量的红线。
如此前景下,近年来“人造子宫”正在为越来越多人所关注,并被寄予厚望。它能否成为一剂良药,为解决生育难题带来些许曙光?
持续提供血氧支持是关键
1923年,在剑桥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首次提出“人造子宫”这一概念。他提出了一个畅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所有婴儿都将通过人造子宫出生,人类将停止本能式的繁育方式,催生出更为理性和先进的繁育过程,即从怀孕到分娩,全都在人体外完成“体外孕育”。
以此为伊始,人造子宫被纳入研究人员的视野。
1954年,美国科学家伊曼纽尔·M. 格林伯格设计了一个模拟母体子宫的装置,并为此申请了专利。该装置包括一个充满羊水的育儿箱、一个连接到脐带的机器、血泵、一个人造肾脏和一个热水器。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该装置显得有些简陋。
1960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提出人造子宫的研究计划,探究在无重力情况下胎儿如何才能正常发育,但计划最终不了了之;196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研究团队首次开展人造子宫领域的动物实验。
此后数十年间,不少国家陆续用猪、狗、羊等哺乳动物的胚胎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羊的心率、血压、体温等与人类最为接近,成为了首选。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相关研究进展都十分缓慢。
直到1993年,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才成功让两只4个月的山羊胚胎(山羊孕期全长约为6个月)在体外孕育系统中存活了约500小时,被视为重大突破。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成果都难以被复制。
实验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为胚胎持续提供血氧支持?这是保证胚胎存活最重要的一环。直到21世纪后,ECMO(体外膜肺氧合器)技术的发展,才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可靠的路径。
到了201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团队将脐动脉、脐静脉与ECMO机器相连,让山羊胚胎在“人造子宫”中健康发育了19到28天。这些山羊还睁开了眼睛,长出了羊毛。
这一成果通过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也掀起了已沉寂多年的人造子宫研究领域的研究热潮。
关于人类的子宫自洁系统,目前尚为研究盲区。


2020年,中国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研究团队成功复现了上述山羊胚胎实验。团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难题。
胎体血液在ECMO机器中循环时,细胞反复受到剪切力的破坏,容易形成血栓,要使用抗凝药物抗血栓,又会造成胚胎出血尤其是脑出血。同时,人造子宫的自清洁能力低于人类子宫,如不慎有细菌混入,胚胎就容易受到感染,引发致命疾病—而关于人类的子宫自洁系统,目前尚为研究盲区。
该团队还表示,对胎盘的研究与培育,也是人造子宫实验团队所面临的另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其中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技术,更在于伦理的限制。
绕不开的伦理争议
2023年9月,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团队研发了“新生儿发育子宫外环境”(EXTEND)设备,申请批准以该设备进行的首次人体临床试验。随后,《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示人造子宫的人体实验可能很快就会开始,由此引发了一场广泛的社会讨论。
面对可能的伦理争议,该团队谨慎地强调,“绝不会将该技术运用于人类胚胎的孕育”,只是希望以此模拟人类自然子宫环境,寻找提升早产儿存活概率、改善其预后发展的方法。
在此前2017年的实验中,由于让山羊胚胎从人造子宫中“出生”,可能涉及违反动物保护相关条例,因此研究团队对山羊胚胎实行了“安乐死”。而在人类胚胎的研究领域,更是涉及政治正确的敏感话题。
1978年,全球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也衍生了一系列伦理问题。经过各方激烈的讨论,“14天伦理准则”逐渐成为了学界的共识,即“自受精之日起,人类胚胎体外培养的时间不得超过14天”。此后,各国对人类胚胎的研究都严格遵循了这一不可逾越的界线。
现有的人造子宫技术,和大众所理解的“人造子宫”也有着显著的区别,研究方向基本是将已经在母体子宫内发育至一定月龄的胚胎,移入人造子宫继续生长。
受限于“14天伦理准则”,现有人造子宫技术的研究,很难涉及胎盘和胎儿的具体发育过程。在这一方向,科学家只能小心翼翼地前进。
2003年,旅美华裔科学家刘鸿清的研究曾引起关注。她用胶原质和软骨素制成子宫形状的培养床,在上面“播种”人类子宫内膜细胞,形成一个由生物组织构成的“人造子宫”,再把老鼠受精卵放入人造子宫,证实了受精卵可以顺利着床,并形成胎盘和羊膜囊—但随后,出于伦理方面的考量,实验被中止。
2021年3月,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发表论文称,他们首次使用人造子宫培养了小鼠胚胎6天时间:实验中,研究人员提取了卵细胞受精之后几天的小鼠胚胎,在特殊生长培养基上,复制了胚胎发育的第一阶段后,再将其放入“人造子宫”,在没有脐带连接母体获取营养的情况下,胚胎发育出了明显的身体结构和器官。
到了9月,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又发布公报宣称,研究人员在此前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用干细胞创建出了人类早期胚胎模型。“该人工模型虽然在结构上与人类胚胎非常接近,但并不等同胚胎。”尽管如此,研究人员成功将其在子宫外培养到14天的发育阶段后,就中止了实验。
近些年来,科学界关于放宽“14天伦理准则”的呼声逐渐提高。该限制的存在,事实上让人类胚胎早期的发育过程,变成了一个“黑匣子”。而在彻底弄清楚这一过程之前,人造子宫没有可能完全取代女性子宫的生育功能。


“自受精之日起,人类胚胎体外培养的时间不得超过14天。”
2023年9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5天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召开会议,驳回了费城儿童医院关于人造子宫人体临床实验的申请,理由是“根据当前的动物数据,还未做好人类实验的准备”。
未来的“美丽新世界”?
由此来看,让人造子宫拯救韩国或别的国家的人口危机,还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人造子宫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仅是韩国,对于部分欧洲国家而言,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同样是其面临的现实问题。2019年,欧盟在其公布的“地平线2020计划”中,拨出了290万欧元研发人造子宫,计划用5年时间,实现人造子宫的临床运用—荷兰的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目前已建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人造子宫研究基地。
正如大多数“人造子宫”领域的研究一样,该计划强调研究旨在提高极早产儿存活率,而非推动体外妊娠技术发展。
这种谨慎的态度,也在侧面反映,倘若真正意义上的“人造子宫”到来了,势必将对社会形态造成巨大的冲击。
2022年12月,分子生物学家Hashem Al-Ghaili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8分钟的科幻短片。视频中,“人造子宫”装置不仅可以完美取代女性子宫的生育功能,实现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到出生全过程的子宫环境模拟,还可以通过人为筛选或基因编辑技术选择最优秀的胎儿,实现优生优育。视频中还表示,这项技术可以解放女性,并帮助那些生育率过低的国家恢复人口增长。
这个短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而其中“基因编辑”“优生优育”等概念,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诚然,人造子宫能够实现安全无痛妊娠,让众多女性免受生育之苦,但这一深刻的变革,是否会对“女性”甚至“母亲”这一社会身份产生冲击,从而逐渐瓦解传统的家庭观念?
另一方面,人造子宫技术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倘若说人类自身都可以被廉价量产,那么“人”本身的价值是否就会被消解,成为“商品”一般的存在?
早在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就在其反乌托邦名作《美丽新世界》的开篇中,设想了人类在“人造子宫工厂”被批量生产的过程。
作品中,基因的优劣成为了阶层筛选的标准,被量产的人类千篇一律,缺少独特的个性,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先进的科技作用于人类自身时,反而让文明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
回归现实,无论是生育率因素,还是造福女性,推动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都有着强烈的需求。而在一项技术真正到来之前,审慎地考量其可能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有价值的,更是必不可少的。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