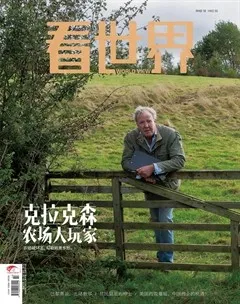反思现代化的印度人

在上个世纪末,印度后殖民政治学家帕沙·查特吉曾在文章中论及:印度的现代性是一种“国族的现代性”,里头有一种深深对现代的不满与对过去的依恋。例如,19世纪末的印度孟加拉知识分子,总是在感叹过去时光的美好,抱怨现代化带来的弊端—自私、虚弱、短命。这样的感叹或许来自主观感受,不一定符合客观现实。现代医疗确实大幅减少死亡率,平均寿命也增加了,尽管如此,这些印度人依然会觉得过去的人比较健康。他们会说:“在以前,如果生病,喝点豆汤咖喱休息几天就好了,过去也没有那么多慢性病、传染病。”“那时哪有什么糖尿病,大家常常一口气吃三四十颗芒果当点心!”
这样的态度,在今日印度的老年人身上依然看得见。我在加尔各答的朋友家,朋友的爸爸看到电视新闻上出现强暴案件,说道:“真是世风日下啊,我们以前哪有强暴这种事,街上可安全了。”“这个恶风就是从西方传到了德里,现在传到我们这边了。”仿佛西风东渐,带来的不是进步,反而是灾难与后退。
这样的态度在当今年轻一代却已经消失了,年轻人抱怨上一代人食古不化,并且大力拥抱进步与现代,认为现在的一切都比过去好。在印度生活十几年的我,与这些年轻人相比,倒像是那些依恋过去的老一代印度人,总觉得过去的才是比较好的。
在卧铺火车上,我常常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即使火车摇摇晃晃,即使自己行动不便,他们也能成功地将自己的位置保持一尘不染。吃饭的时候安安静静,不会有一滴咖喱汁滴在座椅上或衣服上,吃完后将餐盘端正地放在自己的座椅下方。最让我惊奇的是,他们睡觉时平整地将火车提供的雪白床单铺在卧铺上,起床时床单依然平整。我努力想要以他们为榜样,但在摇晃的车厢内铺床单,我就是铺不平,而整晚翻来覆去,床单早就因为翻身皱成一团,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这些爷爷奶奶睡觉时都不翻身的吗?我纳闷。这些老人在印度独立前后的时期出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受甘地主义启发,是甘地主义者。像我朋友的父亲,退休后依然维持着素食与规律生活,80多岁依然保持着健康的身体,每天清晨做瑜伽,倒立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反观中年人与年轻人,他们总是大声喧哗。有一次我只身与一家印度人同一车厢,爸爸张腿坐姿不甚雅观,小孩子甚至当着我的面说一些不友善的话,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全。许多年轻人吃完点心纸屑直接往地上扔,火车餐点的餐盘吃完后不放在自己座椅的下方,反而塞进别人座椅下。我时常同情负责打扫车厢的火车小弟,扫过一节车厢的地板总会清出一大袋垃圾,偶尔会有咖喱汤汁倒在地上需要擦拭。
查特吉在文章中提到,印度人“对过往的依恋之情”,在印度文化中对照的概念是Maya(摩耶),幻觉或错觉之意。佛教中也有这样的概念,也就是一种对现实的感知,但本身亦是一种幻觉。他精辟地提出,印度上一代人这种对过去的依恋之情,或许也是一种不真的幻觉,但它并不是保守的,这样的感情不是拒绝改变。相反,这是追求改变的。他们认为被西方现代性侵蚀的“现在”是一个需要被改变的疾病,过去虽然不一定提供“解答”,但“现在”肯定是个问题。当这样一代人逐渐消逝,印度这一台火车,将会开往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