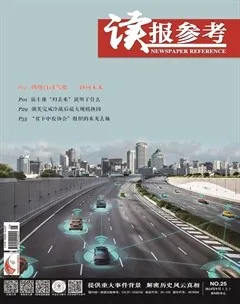铜雀春深锁往
邺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都城之一,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在此建都,是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建筑、手工业、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影响深远。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580年,邺城被焚毁,随着漳河改道冲刷,逐渐没入黄土流沙之中。40多年来,几代考古人持之不懈地穿越流沙,苦寻真相,邺城容颜逐渐浮现……
曹操的终极舞台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739年,唐代诗人岑参作《登古邺城》,那时尚有废墙堪登,旧城可见,断壁残垣空惹姹紫嫣红。他追怀的武帝是曹操。曹操向来引人注目,邺城是他的终极舞台。
邺城见证了曹操的人生巅峰,印记着他的功业,也是他的归葬之处。204年,曹操攻占邺城,将此地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尽力经营。之后,除在外征战,曹操多数时间住在邺城,处理军国大事,遥控在许昌的汉室,直至220年去世,遗令葬在邺城。
在邺城期间,曹操着力增加其领域面积和人口,使之成为号令天下的王畿之地;组织开渠修河,使之成为纵横四方的交通枢纽;修缮建设灌溉工程,使之成为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汇聚起邺下文人集团,使之成为建安文学发祥地。
邺城最早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西门豹治邺就发生在此。东汉末年,邺城是冀州的治所。曹操是从袁绍势力手中夺取的邺城。袁绍占据冀州,曹操攻取邺城。
赤壁之战发生在208年,建铜雀台是210年。《三国演义》将建铜雀台移到赤壁之战前,于是诸葛亮能背《铜雀台赋》智激周瑜。曹植确有《铜雀台赋》,当然是作于赤壁之战后,赋中也没有“揽‘二乔’于东南兮”等语句。这样写或是剧情需要,但书中写曹操在邺城命建铜雀台后就“班师回许都”,在许都谋划南征,建玄武池教练水军,就显得弱化邺城了。曹操当时并未“班师回许都”,而是在邺城筹划南征和建玄武池。类似手法不止一处,或是因为小说产生时,邺城泯灭已久,对曹操在邺城的经营,对邺城的历史地位,《三国演义》的表现都算不上充分。
西晋左思《三都赋》,对邺城的规划建设和面貌有较多描述。三都指蜀都成都、吴都建业(南京)、魏都邺城。如今,成都和南京仍是名城,邺城只是个小镇,但《三都赋》中,是以成都和建业衬托邺城的壮丽。
文章以华美古奥的文辞,对邺城进行了精彩描绘。其中讲到邺城处在中心位置,有依山傍水的优越条件,“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山林幽岟,川泽回缭”;又说到邺城吸取了前人都城建设经验,按先贤和典籍的思想进行规划设计,精益求精建起宏大都市,“修其郛郭,缮其城隍。经始之制,牢笼百田。画雍豫之居,写八都之宇”。
建造这座壮丽城市的关键先生是曹操,他是邺北城总设计师(东魏、北齐时在曹魏邺城之南建新城称邺南城,曹操建的邺城被称邺北城)。《三国志》裴松之注说,曹操主导建设,亲自规划,“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曹操对邺北城的城市建设历时14年。他不是邺城的初创者,但他将邺城由一个普通的州城,打造成天下名都。
穿越流沙证前尘
现代考古学兴起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地面上走访和文字中追寻,开始努力从地下探掘文明曾经的真实印迹。
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来邺城调查,限于条件,只采集到部分汉代到南北朝的砖瓦。
1957年12月,考古学者俞伟超到邺城进行了5天调查,作《邺城调查记》写道:“邺城旧垣,地面荡然无存。我们曾于传铜爵台(铜雀台别名)台基正南与东部偏北两处,用洛阳铲略加钻探,2米以内,尽为淤土,不见墙基夯土……地面毫无古迹可求,但在井边渠旁则可看到翻上的古代砖瓦,古城遗迹或有很多已深埋地下而保存尚好。”
1976年8月至1977年12月,临漳县文化馆组织古邺城考古训练班,对古邺城进行调查和钻探。曾任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所长的张子欣参与了那次考古调查报告的整理。他后来写道:“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技术不专业,同时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虽然有近一年半的时间,但真正工作时间并不多。”“真正对邺都遗址作认真细致地勘探发掘、研究的,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以考古学家徐光冀教授为领导的邺城考古队。”
考古队人员有徐光冀、蒋忠义、屈如忠等。张子欣记得,快开工时,徐光冀安排蒋忠义带人在邺北城进行初步钻探调查,选定了10多处进行钻探,忙了一整天,有一处遇到碎石,探不下去,其他均取出的是沙,无一处夯土。蒋忠义感叹:“完了,邺城没什么希望了。”这句话张子欣印象很深。
1983年10月15日,邺城考古队的钻探工作正式开始。目标是找寻邺北城城垣,连续几天,都只见沙土。半个月后,探得夯土踪迹,一路探寻,进入漳河河床,探铲遇水带不上样本,一提铲,探孔就被流沙吞没,城墙基址又断了线。
考古队偶然从村民打轧水井得到启发,将两根木杆呈十字横绑在探杆,按下、提升,还可推转,得以使探铲穿越流沙,寻找夯土。经过艰苦努力,又在田野中找到了城墙基址。邺北城轮廓图终于能够依据考古实证画出来了。
成果来之不易,据张子欣回忆,夏天“钻进玉米地里钻探,如在蒸笼里一样……豆大的汗珠密密地顺着身子滚落,脚底板下都湿湿的”。冬天“扬起的河沙和横飞的雪糁掺和在一起,如投枪匕首般犀利,打在脸上刀割一样的疼痛……休息时,大家把干树枝拢来烤火,脸被火苗烤得热乎乎的,衣服前面冒着白色蒸汽,而背部和身体两侧依然结着薄冰”。
1989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发掘出湮灭千年的古都邺城》,消息称:“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座古代都城——邺城,在湮没千年之后,正逐渐显露出真相。”消息写道:“由于历史湮没,再加上地下水位高,邺城的勘探发掘极为困难。据介绍,经过艰苦努力,目前已基本确定了邺北城的城墙、城门、街道的位置,勘探出近20座宫殿基址,发掘工作虽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已证明邺北城的总体规划在曹魏时期即已形成。”以中轴线为中心、建筑对称均匀、呈棋盘格形状的封闭式城市规划与布局,标志着中国当时都城规划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重要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规划建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2012年3月,一则新华社消息再次引起外界对邺城的关注,题为《考古队在河北邺城发现近3000件佛教造像,为当代同类考古之最》。据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利群介绍,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发掘出土编号佛教造像2895件(块),造像碎片数千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何利群说,佛造像绝大多数是汉白玉造像,根据造像特征、题记年代等初步认为,这批佛教造像时代主要是东魏北齐时期。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这一发现被评为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