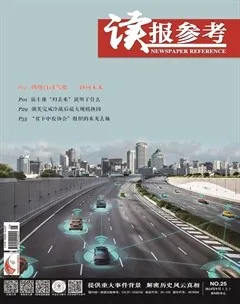甲骨文学者许进雄:回望三千年
65年前,因为清代训诂学著作《广雅疏证》,许进雄的命运发生改变。书中多种形态的汉字,引导他投身甲骨文研究。这条幽僻的学术道路,他一走一甲子;3000多年前的汉字刻在殷商甲骨上,也深深刻在他的心头。
“钻凿人生”
高三读到《广雅疏证》时,许进雄对训诂学一无所知,只觉得原本熟悉的汉字充满奇妙之处。为满足好奇心,他又读了《经义述闻》《古书疑义举例》等清代学者著作,还读了书中所引典籍。“我终于发现自己兴趣所在。”考入台湾大学中文系后,他为厘清文字、声韵与训诂的关系,旁听高年级文字学和音韵学课程,自学《说文解字注》等。
许进雄不盲从古人说法,反而发现《说文解字》不少错误。“《说文解字》被奉为文字学圭臬,但汉代学者看不到甲骨文和金文,难免望文生义。”他意识到,正确理解汉字创字本义,要从甲骨文下手。他由此确立毕生志业。
1968年,他远赴加拿大,受聘于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负责整理馆藏商代甲骨文实物。通过对大量文物仔细拓印、观摩,他系统论证“周祭”特征,重排祭谱。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以甲骨钻凿形态为依据的断代法。
为了让占卜烧灼后兆纹容易显现,殷墟甲骨背面都挖有凹洞,学界称为“钻凿”。许进雄发现不同时期钻凿形态有不同特点。为验证自己的结论,他走访各地的博物馆、研究机构,绘制大量钻凿形态图样,最终发表博士论文《卜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许进雄来过后,所有甲骨就翻身了”,一度成为学界流传的趣闻。
许进雄说,前辈学者从刻辞现象归纳出甲骨断代的十个标准,但对其中部分刻辞年代存在争论。“我的钻凿断代法提供了不同切入点,有利于解决争论。”如今,钻凿断代法已成为他的标志性成就,他的回忆录就取名为《钻凿人生》。
“新说文解字派”
说到具体的甲骨文,许进雄拿起笔在纸上描画出要解释的汉字的甲骨文、金文形态,解释笔画和演变。比如“吉”字,他解释说,从甲骨文看,这个字代表放在深坑中已浇铸的型范。上古工匠已知道,要把铸造型范放进空气不流通的深坑慢慢冷却,有利于铸件形状符合要求。此后,浇筑顺利并得到良好铸件,才引申到顺利、美好的抽象意义。他说,要理解该字本义,须结合上古冶金技术背景。
“解读甲骨文,要知道笔画含义,还要理解古人为何如此造字。解读创义的过程给我莫大喜悦。有时,睡梦中我也在解字。”说到解字,许进雄滔滔不绝,从一个汉字联系到另一个,脑海中仿佛有个完整的数据库。
长期在博物馆工作,让许进雄积累了大量考古、文物、农业、冶金、民俗等多领域知识,使他能跳出一般学者的训诂框架,开辟出对甲骨文本义探索的新路径,发表诸多创见和新说,出版有《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字字有来头(六卷)》等专著。
“汉字的图画特性,包含造字时代的丰富信息。一旦了解汉字创义,就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验。”许进雄说,1980年代初,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他就萌发了深入解读甲骨文、阐发中国文化的想法。于是,他选择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汉字,配合文献与考古材料、人类学知识,说明创字本义。比如,围绕“酒”字,结合半坡遗址小口尖底红陶瓶,谈陶器运输酒的特点;用甲骨文“姬”字谈发饰与贵族身份的关系;说到“郭”,谈考古遗址中城市的不同建造形态……开课一年后,选课学生从最初12人增加到上百人。
“剑客和游子”
甲骨文研究从来是冷门学科,但百余年来中国学者传承不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以“文章不写半句空”自勉,其中包括董作宾、石璋如、屈万里、严一萍等学者。
在这些学者指导提携下,许进雄继承志业,练就破解甲骨文的“独门功夫”。朋友称他为“殷墟剑客”,形容他是“右手持剑,左手捧着古文物,口衔甲骨文的游子”。
1970年代,身在加拿大的许进雄就关注中国大陆的发展。陆续有朋友赴大陆旅游,其中一位回来对媒体表示,登上长城后,“每一块砖头都对着我说,这就是你的祖国”。这让他对大陆、对典籍中的文化中国更加向往。
1975年,许进雄第一次随团到访大陆。在北京,他见到了长期保持书信交流的同行学者。“后来才知道,我无意中为大陆学者和海外交流做了破冰的工作。”此后,他多次访问大陆,在高校、博物馆发表研究成果和心得,与胡厚宣、于省吾、商承祚等学者相互切磋,结下友谊。“希望大陆读者能检验我对甲骨文的解释,共同透过甲骨文回溯中国历史和文化。”
如今,尽管受到疾病折磨,许进雄仍坚持给古文字爱好者免费授课,并规划着新作——把甲骨文按年代排列,把每个字形整理清楚,让人可以看出甲骨文整体演变过程。
《说文解字》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为探究3000年前的社会原貌,许进雄用一甲子时间,随甲骨文溯流而上,这位“剑客”和“游子”终于回到历史和文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