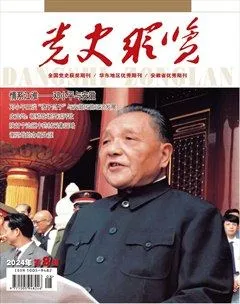陕甘宁边区中药材采集记略
陕甘宁边区中药材蕴藏丰富,药用价值可观,当地民众素有利用天然植物保健治病的传统,并积累了丰富的辨识、采挖和炮制使用经验。1944年6月24日,《解放日报》载文:“我们认为,药材的调查采挖运动,是应该加以提倡的……药材在边区经济上的价值,至少应列为第三位。就目前情形看来,如能很好地加以采挖,产量一定是很多的……如能很好地采挖起来,对于边区内部的制药厂、民间中药铺的原料问题,也可做到全部自给,不致有时还须要向边区外购买。”边区军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的号召,广泛开展中药材采集活动,实行自给自足计划。仅1945年,边区就出口甘草193.38万公斤,金额1424.17万元;当归2.52万公斤,金额87.67万元;大黄0.64万公斤,金额10.65万元。中药材产业在边区生产和贸易中占有一定地位,在边区卫生保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积极倡导
陕甘宁边区各级医疗机构将药材采集作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备条件和基础工作。早在1939年1月,边区政府就开办了保健药社,并于8月颁布暂行章程,明确保健药社以“采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以利保健工作”为宗旨。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中医团体——国医研究会成立,决定“总会制定各种产药式样名称,发布药材,供大家开采参考”。
1944年夏,关中分区党委《关中报》号召群众利用农闲挖药,提出“认得药的人要教大家认药,和大家一搭去挖,发扬有饭大家吃的精神。药挖多了,使边区群众看病方便,卖出去还能赚大钱”。淳耀县召开区长区书记联席会,详细讨论采集山货、发展农村副业问题,指出本县出产的较为贵重的药材有党参、甘草、秦艽、天花粉等。柳林区则于1944年8月邀请中医、药铺掌柜举行座谈会,商讨药材采集、炮制法研究等事宜,随之发动群众挖药,使挖药与副业生产、发展医药卫生工作结合起来。三边分区还组织成立了边区第一个分区级中西医药研究会,把采集中药材作为其重要职能。
1944年11月,经边区第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指出,必须有计划地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药。1945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各专署县(市)政府推动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的通知》要求,边区各级中西医药研究会要“协助卫生行政机关,指导及组织采挖制造土产药材,种植药物及研究制造药品等”。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有利的副产,其中专门指出要发展药材生产,以活跃农村经济。
边区民众采集的中药材在历次陕甘宁边区生产成果展览会上都有一席之地。1939年,边区农展会陈列药材数十种。1940年,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陈列有甘草、独角莲、红花等中药材。1943年11月,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队生产展览会开幕,展出中西药60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生产展览会展出边区药材76种;边区政府机关系统生产展览会、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三届生产展览会也都展出多种药材。
各界热情高涨
中央军委原卫生部政委兼中国医科大学政委饶正锡曾回忆:“延安时期,药材供应十分紧张……组织力量上山采集。陕甘宁边区盛产麻黄、甘草、当归、桔梗、柴胡等中草药,把这些中草药采回来,经过加工,可以制成许多成药。”部队和政府各级卫生系统都派医务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如延安中央医院把中草药配制成各种粉剂、水剂使用,兵站医院司药入山采到了价值三四千元的中草药。独立第一旅卫生部医务员李逢琪说:“及时给各团发通知,要求在开荒种地的同时采集中草药上交卫生部门。我们门诊部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除留值班人员外,其他人上山爬沟,寻采药材。不长时间,卫生部就收到了大批中草药。”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也加入采药队伍。边区保安处直属队动员各单位到甘泉采挖中药材,一天采药1500多公斤,价值7000余元;关中分区直属中心区采挖党参等中药材348公斤。1945年初,关中马栏等地疫病流行,当地中医采集黄芩、柴胡、白芍等药,加上元参、苦参等熬汤,或将松圪垛配绿豆熬汤,单独用薄荷水、灯草等熬汤,并推广加味藿香正气散,取得了较好的防疫效果。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采集中药材也成为重要的生产项目,并涌现出一些生动事例,受到宣传表彰。1944年6月14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志丹县三区合作药社中医周岐山采集药材的事迹:他带领药社人员到山中采药七八十种,其中有党参、生地、五味子等30多公斤,为药社节省7万余元。8月9日,《解放日报》报道,华池县保健药社发动群众采集药材,仅药社王天喜一人,就采集了柴胡、远志、百合、车前子、山楂等30余个品种75公斤药材;药社还发动群众及放羊娃在山中采药,并出钱托各区民办社代购,将药名改用群众熟悉的土名,如山楂叫“木豪黎”,以此方便群众辨识。曲子保健药社是陕甘宁边区有名的模范卫生合作组织,该社三分之一的药材靠自采,因其药价较低、真心服务群众,赢得了群众的信赖,营业利润也因此增加。
资源考察与科普宣传
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对植物资源的科学考察和利用,先后组成多个考察团,进行一系列考察调查活动,写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陕甘宁边区林产初步调查》《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等相关考察材料。这些材料对于人们掌握了解边区中药材资源、促进边区医药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林务局技术科科长江心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森林里的药材很多,除树木本身的根、皮、花、叶、果实、种子等而(之)外,还有森林里生长着的许多药用草本植物。”著名农林生物学家乐天宇也说:“本边区药材生产丰富,单就珍贵实用的主要药材来说,已在百种5rz6eT7ssIz4XL9nXhBc65oF3AsMIp7sPVGHTlhhXLE=以上,其余兼药用植物数量更是广大……例如龙胆、薄荷等在制药厂附近遍地都是。”据调查,边区中草药资源主要有甘草、枸杞、远志、黄芩、车前、大黄、当归、党参、贝母、黄连、黄芪、防风、柴胡、马兜铃等。1940年1月13日,《新华日报》报道:“边区出产药材甚多,且品质优良,如甘草、麻黄精、黄芩、苦参、党参、益母草等数十种。”
中草药分布的广泛性和其价值的独特性,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关注,并就此开展了一些科普宣传工作。1942年,《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分4次在《解放日报》刊发地方药草23科49种。1944年,《关中报》载:“人常说‘秦地无闲草’,咱们关中出的药,就有一百多种。出名的‘宜党’(宜君的党参)、‘耀芩’(耀县的黄芩),就算咱们马栏、双龙镇一带的最好。其他如甘草、白芍、赤芍、桔梗、柴胡、防风、沙参、知母等都是道地药。除过自己采用,还可大量销售。”“有经验的人挖药,是在发芽以前,白露以后;那时地气下降,水汁都在药根上,药性就好。”1944年6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边区药材介绍》一文,介绍了麻黄、柴胡、甘草等药材33种。1946年6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丁香治疟》一文,介绍丁香形状、功用、采集方法,并指出:“边区的丁香很多,农村疟疾亦到处发生,如能采用以上方法,实在方便,希中西医生,再多加以研究,以便推广。”“在夏秋之间采集最有效,制成煎剂及丸剂均可。”
陕甘宁边区有三宝:咸盐、药材和羊毛。三边地区为甘草的主要产地,在历次陕甘宁边区生产成果展览会上,甘草都备受瞩目。1939年边区农展会上展出三边著名的铁心甘草。1940年3月,《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参观记》一文记载:“药材在边区出产近百余种,如麻黄、铁心甘草、大黄、党参、关参、秦椒、知母、车前子等,只甘草一种每年产量千万斤以上,为边区输出品之第二位。现边区当局正由专家从事研究炮制成药,以补西药之不足。药材展览室内陈列着两棵特大的甘草,一名甘草王,一名甘草龙,重约数斤形如树,据群众谈:‘这种甘草必经多年生长,颇不易得。’在这两棵甘草上,一标价300元,一标价500元。”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期间,部队劳动英雄在会上报告生产情况,三边驻军某团生产模范工作者贺振清说,该部5个连当年33天挖甘草15万公斤,创造了当地前所未有的纪录。1944年7月,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边区自产甘草等亦现身医疗成果展示会。
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边区军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计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