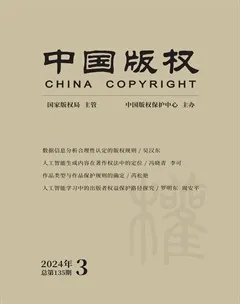从《方舆胜览》所载告示看宋代版权保护
摘要:“宋代是否出现版权”问题向来为学界讨论之焦点,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安守廉与郑成思之争。安守廉认为“20世纪以前中国所有现存的表明国家努力为智力成果提供保护的事例都完全是为了维护皇权”,郑成思则列举一些宋代刻印出版者向官府提交版权保护的努力进行反驳,其中就有《方舆胜览》中登载的版权保护告示。笔者认为,仅从这一告示来看,版权保护在宋代就已出现,其维护的是商品经济秩序,而非皇权。遗憾的是,该萌芽在此后数百年间未能破土而出,未发育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本文将围绕《方舆胜览》所载告示探究东西方版权保护在特许阶段的不同及中国古代未能发展出专门的版权立法的原因。
关键词:版权史;版权保护告示;特许令状
一、宋代版权保护的历史背景
版权观念的产生与出版业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在隋唐应用雕版印刷之前,魏文帝曹丕就将著述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著述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但此观念是十分朦胧的,与版权保护相差甚远。直至宋代,由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书籍生产等因素的进步发展,版权保护方才成型。具体而言,政治上,宋太祖赵匡胤在建立政权后,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了武将的权力,奠定了宋朝崇儒礼士、文臣治国的基调。据史料记载:乾德四年(966年)二月,“权知贡举王祜言进士合格者六人,诸科合格者九人。上恐其遗才,复令于不中选人内取其优长者,第而升之。”宋朝统治者不仅加强科举取士,还对多次科考而久不中试者表示了莫大的关心,这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参加科举、入仕为官的热情,读书蔚然成风,社会对书籍刊物的需求量激增,形成规模化的图书交易市场。
出于“文德致治”的方针,统治者极其重视官方典籍的保护,对民间图书出版管制也较为宽松,宋太宗就曾向群臣表明自己的态度:“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同时,宋代十分重视法制,所修法典有名可考的就有242部,梁启超赞叹称:“宋代法典之多,实前古所未闻,每易一帝,必编一次。甚者每改一元,必编一次。盖终宋之世,殆靡岁不从事于编纂法典之业。”宋朝法典的大量刊行提高了民众的法律意识,也为出版者积极寻求版权的政策保护提供了前提。
经济上,宋代土地无限制自由买卖导致官僚地主、权贵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均田制遭到破坏,与之配合的部曲制也被地主购置田产和对佃客进行租佃剥削的租佃制所替代。这种变化使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解放和生产自由,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手工业制造、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城市的繁荣意味着宋朝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市民阶层,他们存在着巨大的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需求,推动了各种书籍的刊印出版。
元代理学家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镘板成市,布满天下。”书籍生产的进步离不开雕版印刷、造纸、制墨、雕镂等技艺的发展。雕版印刷术经过唐代的发展,至宋代已获得广泛应用,除却国子监主持的官方出版,方兴未艾的民间出版也借此技术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精细化为家刻、书院刻书及书坊刻书。其中最能代表图书出版商品化运作的大方向无疑是坊刻,《书林清话》就对“宋坊刻书之盛”做了一番描绘:“此五代时有书肆也。至宋则建阳、麻沙之书林、书堂,南宋临安之书棚、书铺,风行一时。”
在以江浙、四川、福建、汴京为中心的坊刻业蓬勃兴起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宋人的义利观亦发生重大变化,李之彦在《东谷随笔》中指出的“钱之为钱,人所共爱”成为宋人金钱崇拜观念的写照。在书籍成为一种可社会性生产的商品后,它所可能创造的利润及财富强烈吸引着一批嗜利之徒,或未经作者同意将其原稿付诸梨枣,或取已有刻本翻刻内容,或将已有之书改易名目,刻作新书以射利,使得著作者和刻印出版者的“数载辛勤”变为“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刻印出版者凭借自身能力往往难以解决纠纷,只能向官方提出利益诉求,要求禁止盗版,保护与自己相关的精神和财产权利,版权保护应运而生。
一、以《方舆胜览》所载告示为代表的宋代版权保护
宋代的版权保护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对官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对民间出版物的版权保护以及著作者的自我保护。官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存在,其核心是维护官方的“正统”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保护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对思想传播的严格控制,既禁止和销毁含有异己思想的图书,又保护官方编纂出版的图书,严禁民间书坊翻刻。这类保护就如安守廉所认为的,属于“帝国控制观念传播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思想统一的需求。与此同时,著作者的版权保护意识随着宋代文人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加强。例如,理学家范浚在得知建阳有书坊假冒其姓名出版了《和元祐赋》后,就采取了一定行动:“甚者至有盗窃姓名,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今伪赋自为一集,不以仆文参之,则无杂乱间厕之患。其为盗窃姓名,甚易见也。然传闻失真,翻转名实,古人所叹。近亦尝白官司,移文建阳,破板多矣。前散鬻者,人得之。尝即以供瓿覆药楮,有不得其详者,足下以是告之。”范浚的案例并非个例,许多有名的作家都遭受了类似的侵权行为,但大多无可奈何,彼时尚无针对作者的政策保护,政策保护仅针对民间出版商存在,具体表现为民间刻印出版者在发现盗印行为后,向官方提出“申禁”报告,官府机构通过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榜文、公牒等,向书业界表明打击盗版、保护申告者版权的态度。
这种保护告示以1238年两浙转运司为保护祝穆自编自刻的《方舆胜览》《四六宝苑》《事文类聚》等书的版权所发布的榜文为代表,其所透露的信息已显现出现代版权的特征:
两浙转运司录白。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日《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板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客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嘉熙贰年十二月口日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转运副使曾口台押。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其一,该告示登载于浙本《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上,内容基本符合1952年签订的《世界版权公约》中规定的版权标记:“只要经作者或版权所有者授权出版的作品的所有各册,自首次出版之日起,标有符号,并注明版权所有者之姓名、首次出版年份等。”由此可见,宋代的版权标记已较为完备。其二,该告示不仅保护了刻印者的权利,而且肯定了作者的创作:“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即扩大了版权保护主体的范围。其三,该告示列举了几种当时常见的盗印翻刻形式:“辄将上件书板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与现代版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有类似之处;其四,阐明了告示保护程序:“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一旦发现盗印行为,刻印者向地方政府进行申请令状,出具后的公文下发给“榜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还会进行“毁板”处罚。其五,表明告示保护具有跨地域效力:“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两浙转运司公告会转发给福建转运司,地区间的沟通协作在更大范围上保护了出版商的权益。其六,告示保护具有一定的保护时限。这则榜文初登于嘉熙二年(1238年),在时隔28年(1266年)后书籍再版时,福建当局重新颁布了禁止翻刻该书的文告,并且原公文仍有效力,竟巧妙地契合了现代版权法的保护期限要求。此外,现代版权法中,“财产权利可以像普通财产权利那样通过转让、继承或遗赠而被他人取得。”而新榜文则提到:“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称:本宅先隐士私编《事文类聚》《方舆胜览》《四六妙语》,本官思院续编《朱子四书附录》进呈御览。”“祝太傅”“本官思院”即指祝穆之子祝洙,祝穆去世后,这种权利即像物质财产一样被其子祝洙继承下来。
宋代还有一种公据保护,也会以告示形式出现,与地方转运司所提供的保护有所区别,公据的发布机构是国子监,即中央政府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宋朝国子监在淳祐八年(1248年)向罗氏颁发的出版权执照:
旧钞本宋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三十卷,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板公据,曰: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成宗之。印山罗史君瀛尝遗其子侄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漕贡樾镘梓,以广其传。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TPZprjVbftp3QDTYYODHuw==为先叔明经之玷。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口日给。
这份公据特殊的地方在于,申请人并非出版家罗氏,而是著作者(已故)段昌武的侄子段维清,他因其身份地位(迪功郎和新赣州会昌县丞),受出版家罗氏委托,向国子监陈述了其先叔段昌武在《诗经》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罗氏所持有的缮本经过精心校对,被认为是最精准的版本,段维清担心其他书肆为了利益而翻刻此书,可能会导致内容的篡改和失真,这不仅违背了罗贡士的初衷,也损害了段昌武的学术声誉。因此,他请求国子监发出公据,以保护作品的版权。
公据中还提到了对翻刻者的惩罚措施,包括追回翻刻的印板并销毁,以及对违规者的处罚。此外,公据还涉及了版权继承的问题,继承权的转移似乎是默认的,并不要求作者在生前进行明确指定或授权,这表明在当时著作被视为一种可传承的财产。
从公据的行文来看,它实质上是一种官方的文牒,文中也会出现“备牒”“判牒”等词汇。在宋代,这种文牒相当于中央政权授予的专印许可证,与现代的行业营业执照在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官方对特定活动或权利的认可和保护。
版权保护告示无疑是现代版权保护的雏形,它主要针对的是民间的翻板书,这些翻板书虽然可能会带来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但它们的内容并不必然对时政构成威胁,也不会动摇皇权的统治基础。因此,这些告示的目的并不在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控制,而更多地是维护商品经济秩序,类似于今天盗版行为对图书出版市场的影响。
然而,尽管宋代的版权保护在当时是领先的,版权专门立法的整体发展在中国随后的数百年中却遭遇了停滞。反而是在印刷术仅传入一两百年的英国,通过颁布《安娜女王法令》开启了专门的立法保护。这一法令的实施,标志着版权保护理念的重大转变,强调了作者对其作品的所有权。那么,在出版特许时期,东西方版权保护究竟存在何种不同,竞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三、宋代版权保护告示与西方特许令状之比较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起源在中国,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无争议。法国学者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在其著作《书籍的历史》中强调:“如果思想的新载体,即来自中国的纸张,没有于两个世纪前就通过阿拉伯人出现在欧洲,并于14世纪末广泛流行使用,那么印刷术的发明也没有什么意义。”纸张的出现,不仅为书写材料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更为印刷书的生产工业化奠定了基础。12世纪,纸张通过与阿拉伯人有接触的商人传人意大利,这一事件标志着欧洲书写材料的一次重大变革。
北宋时期,中国的毕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之后,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在西夏等地得到了应用,并逐渐向西传播。印刷技术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图书的成本,使得书籍变得更加普及。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书籍,这打破了以往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接触到书写文化的局面。知识的广泛传播,不仅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交流,也为文艺复兴等文化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特许令状在宋代如同保护告示一般,是随着盗版现象的出现应运而生的。随着书籍市场的不断扩张,图书的数量急剧增加,出版商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重印已出品的著作成为一些追求便利的盗印者眼中最大的诱惑。这些盗印者无需支付任何出版费用或作者报酬,便能以低于原版许多的价格售卖图书,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到了15世纪下半叶,出版商们已经无法忍受愈加频繁的盗印行为,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保护机制。因此,他们开始求助于公权力,希望获得一种特权,以在一段时间内独享印刷和销售作品的权利。这一需求最终催生了在欧洲流行长达300年之久的出版特权制度。在法国,国王于1507年颁布了出版特许令,这一举措为出版业提供了专制王权的强有力庇护。然而,这一制度却将作者排斥在外,使得巴黎书商行会的成员成为实际上的出版特权垄断者。他们利用这一特权,对图书的印刷和销售进行了严格地控制,从而确保了自己的利益。而在16世纪的英国,印刷术的传人助推出版业的兴盛。玛丽一世于1577年授予伦敦书商公会皇家特许状,允许其成立,并规定所有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在书商公会注册。这一政策使得出版商们取得了出版独占权,他们可以对图书的印刷和销售进行独家控制。作为对国王恩惠的回报,出版商们也承担起了管制非法出版物的责任。
事实上,宋代版权保护告示与西方特许令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保护主体都集中在出版者。除却《方舆胜览》因编著者与刻书者同为一人,告示中注意到了作者的辛勤劳动,正常情况下,面对翻刻盗印,著作者是无法通过有效的法律路径进行维权的。如宋代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大文豪苏轼的诗文在无授权的情况下被出版成册,导致政敌抓住诗中内容大做文章,苏轼由此遭受政治迫害,却毫无办法,只能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发发牢骚,以写心中不忿:“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在西方,出版特权是王权赋予书商的,作者并不是书商公会的一员,并不拥有阻止他人再印刷出版的权利,故作者也无法就侵权提出诉求,与宋代的著作者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在东西方版权保护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走向和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宋代,尽管版权保护的概念已经萌芽,但正式的法令中并没有皇帝对国家所有的印刷、出版部门给予的特别保护。告示作为一种政府的应急措施,在没有专门法律可以运用的情况下被实施,但它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主要保护的是那些向政府机关提出“申禁”的书籍。在当时,普通人由于缺乏门路,要向官方申请禁止翻刻并非易事。《书林清话》中提到:“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板,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因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官方的渠道,可以得行其志。”这里的“有力之家”,指的是那些有权势或门路的刻书人,例如上文提到的祝穆、祝洙、段维清,他们因有官方的身份和渠道,故能顺利取得告示。与此相对照的是,英国在颁布特许令状之初,星室法庭颁布的《关于管理印刷秩序的新法令》(1586年)就要求所有的印刷商必须在书商公会登记,同时任何材料的印刷必须获得事先的许可。这一措施证明了出版许可对印刷商是普遍适用的,体现了一种更为系统和规范的版权保护机制。此外,唐宋时期皇室除对钦定作品进行出版控制外,对无碍皇室统治的作品一般既不授予专有出版权也不进行控制,不存在独占的出版特权。而欧洲书商公会为皇权所用,帮助其控制思想的目的就是获得具有排他性、独占性的出版特权。这种中国传统与权利观念之间的沟壑导致了宋代民间的版权观念与利益主张无法向版权专门立法转化。
四、中国古代未发展出版权专门立法的原因
虽然世界上最早的版权保护例证出现在中国宋代,但这一发展势头并没有持续下去。在清末受到西方列强的外力冲击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专门的版权立法。相比之下,西方的版权保护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轨迹。15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出版业随着封建王权的衰落,出版商开始寻求摆脱王权的束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出版所有权”,而是成功地将作者引入法律体系,作为版权的主体。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英国于1709年通过了《安娜女王法令》,确认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所有权。在这个进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从保护告示向专门立法的转变?这需要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思想基础中去探求。
其一,中国古代社会始终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并未充分发展,而版权制度的建设需要一个广阔的文化产品市场作为支撑。在“士农工商”的阶层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商人在积累财富后,往往选择将财富储存起来,而非投入市场流通,这限制了大型图书交易市场的形成,版权制度难以在这样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与此同时,在欧洲早期,商人虽然也会受到歧视,需要缴纳更重的税负,但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1558-1603年),重商主义成为潮流。女王要求积极发展海军和船商队,努力突破西班牙海军的限制以扩大英格兰国内的金银货币累积,出版业也乘此东风完成资本积累。
其二,中国古人的创作观念与版权保护的理念与西方社会存在差异。在他们看来,创作是修身、齐家、治天下的个人修养过程,而非换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即使在宋代,义利观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文人士大夫不再像过去那样耻于言利,但这毕竟是少数现象,不能成为普遍风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使得古人即使重视作品权益,也多集中在精神层次上,道家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思想更是使人们淡化了对权利的要求,重视义务而忽视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版权观念的形成。相比之下,英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从海上贸易到发展海军,其社会骨髓里浸透着一种冒险性、扩张性。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面对高压的王权,这种特性随着重商主义的渗透到达了顶峰,孕育出了张扬个性、倡导私权神圣的观念,出版商和作者的版权意识相继觉醒,最终在《安娜女王法令》中确立了版权归属作者的制度。
五、结语
版权制度如今已成为全球性的权利保护体系,随着《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系列版权国际公约的相继缔结,版权保护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范畴,而是扩展到了国际层面。此时回望宋代的版权保护告示,不禁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在那样一个商品经济尚在起步的时代,拥有了保护作品出版权利的超前意识。尽管在随后的数百年中,中国未能实现从保护告示向专门立法的转型,但无论如何,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成为指引西方走出黑暗世界的文明之光,之后又将一些养料反哺回中国,为后来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任何忽视这一贡献,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人类的文明进步依靠的是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智慧的结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亦是。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