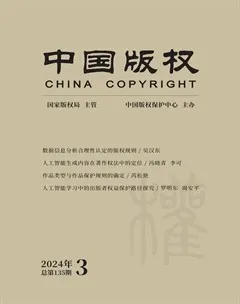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认定研究
摘要:月光舞蹈案作为我国首例“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案”,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再审法院将服装、化妆和道具等舞台元素纳入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进行侵权对比,并认定了单个舞蹈动作的可版权性,但解释力仍显不足。本文首先审视舞蹈作品的内涵与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分析服装、化妆和道具等舞台元素,本质上是服务于舞蹈表演的辅助元素,而非舞蹈作品的“动作”范畴,将它们单独视为作品,显然与著作权法保护“最低限度的智力创造”的原则相悖。其次,单个舞蹈动作难以全面体现编舞者的艺术追求,其实质更多是对身体动作的“发现”,而非“创作”,不属于合格的外在表达,若给予过度保护,不仅难以用于侵权判断,还可能抑制舞蹈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最后,在评估静态作品与动态作品之间的相似程度时,应当将同一作品类型进行对比,以避免主观感受的不确定性,从而出现类似案件中判决不一致的结果。
关键词:舞蹈作品;静态手段;舞台元素;单一动作
一、问题的提出
舞蹈作为一种将时间性与空间性紧密结合的综合艺术,往往融合音乐、诗歌、戏剧、绘画、杂技等艺术元素,成为独立的作品门类。近年来,网络传播的便利性助力了各类优秀舞蹈作品的宣传,如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亮相央视春晚,引发了很高关注度。然而,在这股蓬勃发展的热潮背后,舞蹈作品却频繁遭遇日益复杂的版权问题的困扰。其中尤以杨丽萍公司诉云海肴公司等侵害著作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下简称月光舞蹈案)最为典型,此案是我国首例因将单一舞蹈动作制作为静态图案而被判侵权的案件。2023年11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相关诉讼作出了再审裁定,此次再审认定云海肴餐厅将杨丽萍部分经典舞蹈动作复制成剪影墙画、隔断等作为餐厅主体装潢的一部分,置于餐厅显眼位置进行展览以及在网络上进行宣传的行为侵犯了杨丽萍《月光》舞蹈作品的版权,不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规制,即确认了原系列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否定了原系列二审判决的认定。
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一是舞蹈作品的定义是否包含其他舞台元素。有观点认为舞蹈作品作为一类综合性作品,其中使用的音乐、服装、情节表情等可能不具有原创性或者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应当作为舞蹈作品的组成部分纳入版权保护范围,否则舞蹈作品的内涵就只剩下动作及其描述。另有学者反对将动作之外其他创造性元素纳入著作权法语境下的舞蹈作品保护中,不应混淆舞蹈作品与其他作品类型各自的保护范围。国外有学者同样提出,在比对舞蹈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要排除服装、灯光效果、舞台布景等无关因素。二是单个舞蹈动作是否具备可版权性。一般来说,由于舞蹈作品是由“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构成的,是这些因素相互组合和连接的方式体现了独创性,因此否定观点认为静止的、单独的动作几乎不可能有独创性。然而司法实践上多次出现了将具体动作进行比对的判决,如月光舞蹈案中一审及再审法院即认定单个静态舞蹈动作也是舞蹈作品独创性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祖国你好》秧歌舞侵权案中也持相同审理思路,认为舞蹈动作本身具有独创性,并对“单腿跳”“8字绕”“转圈开扇”等具体动作进行细分比对。
上述关于舞蹈作品版权问题的观点分歧,反映了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舞蹈作品定义认识上的困惑,根源主要在于对舞蹈作品创作机理的认识不足以及在对作品侵权认定规则上存在分歧。现存争议直接影响了舞蹈作品相关版权纠纷的法律适用,因此有必要对舞蹈作品的法律内涵以及版权侵权认定规则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求更加合理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舞蹈作品的定义是否包含其他舞台元素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其中,道具、灯光等舞台元素是否属于第四条中舞蹈作品定义中“等”字的解释范围,我国立法层面未作详细解释。而在月光舞蹈案中,再审法院认为“舞蹈表演中的服装、妆容、道具等元素的存在和丰富使得舞蹈作品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其运用对于舞蹈作品思想情感的表达亦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从而与舞蹈作品中的动作、姿势和表情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亦应作为舞蹈作品的一部分予以保护。”可见,在再审法院看来,单一舞蹈动作与月光背景、灯光等元素相结合所构成的“独特表达”,作为舞蹈作品的组成部分,应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针对舞蹈作品的定义是否包含其他舞台元素这一问题,本文与再审法院持相反意见。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服装、化妆和道具等元素不应纳入著作权法语境下舞蹈作品的定义范围。
(一)著作权法中的舞蹈作品属于“动作作品”
诚然,在舞蹈作品的表演过程中,除了细致的动作表现外,精心设计的道具、服装妆造、舞台布置、灯光以及音乐等元素,共同营造了独特的环境氛围,丰富舞蹈艺术形象。正如《月光》舞蹈中利用全场漆黑的灯光效果和只有一轮道具所做的圆月,营造静谧、朦胧的文化意象。但从舞蹈作品侵权角度来看,即使完整复制了某个舞蹈作品中的表情、音乐设计、舞台布景设计、服化道设计等,只要没有复制其中的舞蹈动作和姿势,便不会侵犯该舞蹈作品的版权。相反,只要动作、姿势实质性相似,即使使用完全不同的舞台布景设计、服化道设计等,也会侵犯舞蹈作品版权。这说明,舞台布景设计、服化道设计等元素并不是舞蹈作品的独创性构成要素,而只是为了增加舞蹈表演效果、可欣赏性所做的设计。上述结论在国际版权条约及其解读文件中同样能够得到有力的支持。《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版权公约,仅在第二条规定舞蹈作品属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范围,虽没有对舞蹈作品的内涵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编写的《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一书中,将舞蹈作品定义为“动作的组合”。此外从权威学者山姆·里基森(Sam Ricketson)教授对《伯尔尼公约》的解读中,可知“舞蹈作品是动作作品,在作品中通过动作传递故事,塑造形象或表达感情”。
从比较法层面来看,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迈尔斯与哈罗案(Myers v.Harold)中,法院明确指出,单纯的服装改换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或“转化”舞蹈作品本身,因此构成了对原告版权的侵犯。这一判决强调了舞蹈作品版权的核心在于其动作和编排的独创性,而非其他装饰或道具。再如,从我国以往判例来看,目前我国关于舞蹈作品侵权的判断处于“混乱”状态。早在月光舞蹈案之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知名舞蹈作品《千手观音》侵权案时的判决指出,“鉴于舞蹈作品《千手观音》系在音乐的伴奏下由聋哑演员表演并由四位手语老师分别站在四个方向进行辅助性指导,因此确认该作品的作者不能仅凭舞蹈的音乐、服装、灯光、舞美等元素的设计,而在于动作与音乐的结合,能够使特定的演员表演特定的动作形成特定的组合达到可确定的艺术效果。”而在月光舞蹈案中同一法院在一审中将舞蹈动作同灯光、道具等其他元素结合与被诉图案进行对比,再审裁定采取相同的审理思路,此做法不仅与国际上关于舞蹈作品属于动作作品的共识相悖,也违背了本案法院一贯秉持的裁判规则。
(二)不符合著作权法立法目的
关于舞蹈表演中使用的服装、道具、灯光等元素保护问题,若该部分达到版权的独创性要求,即可依据其具体作品类型获得著作权法保护,如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等。然而当舞蹈表演中的辅助性元素未能达到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标准,此时将其纳入舞蹈作品的组成部分,以另一种形式使其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做法未免有欠妥当。回到月光舞蹈案来看,《月光》舞蹈以一轮明月作为突出背景,通过灯光的明暗对比所营造出人体剪影效果,其中道具、灯光的设计更多的是对现实中月亮形态的真实还原,此时难言其是“符合作品特征的智力成果”。既然这类简单的舞台辅助元素无法被单独视为作品从而获得版权保护,那么这一结论自然也不会因为其与舞蹈动作的简单结合而发生转变。从比较法角度而言,世界上鲜有国家对舞蹈表演中服化道等元素进行版权保护,已知的只有意大利《著作权法》第86条规定的“对舞台布景设计的权利”,但其并未赋予舞台设计复制权等专有权利,而仅仅为权利人设置了获酬权。由于国际条约和大部分国家均不承认舞台元素的可版权性,倘若将舞台布景设计、服化道设计等作为舞蹈作品的组成部分通过狭义版权保护,将过度扩大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此举非但不能使我国舞蹈作品的上述内容获得域外保护,反而基于《伯尔尼公约》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使外国舞蹈作品的上述内容在中国获得了保护,这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
因此,尽管一整套舞蹈的呈现凝聚了灯光师、动作设计师、舞者等多元专业人才的共同努力与智慧,但并非每个个体的劳动成果都能单独被视为作品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有其特定的界定和限制。正如电话号码簿不能受到版权保护一样,“最低限度的智力创造性”才是劳动成果具有独创性和受到版权保护的条件。针对这类劳动成果,可以按照合同支付报酬,相关纠纷的解决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民法典》。
综上所述,在月光舞蹈案的再审裁定中,法庭将“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明暗对比等元素”认定为《月光》舞蹈作品具有独创性表达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对于舞蹈作品内涵的误解。舞蹈作品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独创性体现在动态的舞蹈编排、动作设计。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保护的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智力成果,即作品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应当是基于作者个人的创作思维和表达方式,而非简单地依赖于一些外在的、容易模仿的元素。因此,将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明暗对比等元素视为舞蹈作品的独创性表达,显然忽略了舞蹈艺术本身的核心价值,也违背了著作权法保护原创作品的基本原理。在评估舞蹈作品的独创性时,应当深入探究作品所传达的艺术情感、思想内涵以及舞蹈编排的创新性,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容易模仿的元素上。
三、单个舞蹈动作是否具备可版权性
除了上述舞台元素是否属于舞蹈作品定义范围这一争议外,单个舞蹈动作是否具备可版权性是本案的另一个判决重点。月光舞蹈案的再审法院认为,“《月光》舞蹈中结合了人物造型、月光背景、灯光明暗对比等元素的特定舞蹈姿态并非进入公有领域的舞蹈表达,属于《月光》舞蹈作品具有独创性表达的组成部分”。该判决实质上是对单个舞蹈动作具备可版权性的确认。然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六)项规定,“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该案判决无疑是对我国现行立法中“连续”一词的否认,本文认为,就单个舞蹈动作而言,哪怕其属于很高难度的动作,也难言其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单个舞蹈动作不属于合格的外在表达
《著作权法》第三条的核心要义在于,作品被定义为“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这一界定着重强调了作品的外在表达性,即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创作者通过一定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情感,而非单纯停留在脑海中的内在思想。例如,在美国Bikram’s Yoga College of India v.Evolation Yoga案中,原告声称其创造的瑜伽动作有“避免、纠正、治愈或至少减轻几乎任何疾病或伤害的症状”的功能,并且“非常漂亮和优美”。事实上,任何具有实用功能的因素,如作品思想、表达或者可为人们所利用的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功能性部分,作者都无权谋求独占。该案法院认为瑜伽动作不论其美学价值如何,都与美国版权法相抵触,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对作品的版权保护都不会延伸到任何思想、程序、过程、系统、操作方法、概念、原则或发现,而不论其在作品中被描述、解释、说明或体现的形式如何”。而瑜伽动作属于“一种想法或过程”,因此不具备获得版权保护的资格。虽然该案并非直接针对舞蹈作品,但其在涉及身体动作表达方面的判断逻辑,对于舞蹈作品的版权保护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在舞蹈作品中,单个舞蹈动作与瑜伽动作有着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简单的身体动作。注意这里所说的“简单”并非指动作的难度低,而是指与完整的舞蹈作品相比,单个舞蹈动作所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是相对有限的,尚未达到“外在表达”的充分标准。
正如在文字作品中,单独的字符或短语虽然构成了作品的基础,但只有当它们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句子或段落时,才能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在著名的“娃哈哈版权侵权案”中,法院认定“娃哈哈”三字“作为歌曲中的副歌短句、歌词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表现的内涵并不是作者思想的独特表现,也无法认定其反映了作者的全部思想或思想的实质部分”,因此不属于合格的外在表达。同样,在舞蹈作品中,单一舞蹈动作虽然构成了舞蹈的基础元素,但只有多个舞蹈动作组合衔接,形成完整的舞蹈作品时,才能充分展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在评价舞蹈作品的版权保护范围时,应当将单个舞蹈动作置于完整的舞蹈作品中进行考量,而不是将其单独抽离出来作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否则,这将无异于对思想的垄断,违背了著作权法保护创作者智力成果、鼓励创新创作的初衷。
(二)判断版权侵权往往需要多个片段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判断被诉行为是否构成版权侵权,往往需要达到一定的“量”,即存在实质性相似。例如,判断两种文字作品中的相似情节是否达到侵权标准,需要将两者的多个情节进行对比,若只有个别情节构成相似则无法认定构成实质性相似从而确认侵权。原因在于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许多叙事情节和手法早已被前人使用过,此时很难判断某个单一的情节是由谁首先原创。因此实践中往往需要将多个情节综合联系,使其足以构成一种整体“表达”,从而进行对比判断相似程度,否则将两个细微情节的对比实质上是思想的对比,不符合版权侵权的基本原理。正如琼瑶诉于正案中法院即将涉案作品中的二十余处情节所衔接而成的表达进行对比,从而认定剧本《宫锁连城》与小说《梅花烙》构成实质性相似。同样,舞蹈作品、杂技作品等动作类作品也需遵守著作权法的侵权认定规则。在杂技作品《俏花旦》案中,法院认定“《俏花旦》在开场部分的走位、动作衔接安排,以及多次出现的标志性集体动作等动作的编排设计,与《俏花旦一集体空竹》法国版相应内容构成实质性相似”,在判决中遵循了将多个动作构成的具体表达进行对比的审理思路。
回到本文的重点舞蹈作品,由于人类的舞蹈创作历史悠久,许多舞蹈作品都是基于传统风格,并融入了相似的动作,例如,自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建立国家学院以来,古典芭蕾的教学方式几乎完全相同。而单个舞蹈动作虽基础、常见,但通过多个舞蹈动作的结合,就可能形成独创性的舞蹈作品,例如,2020年,贾奎尔-克尼(JaQuel Knigh)成功地为美国著名歌手碧昂丝的《单身女郎》音乐录影带中的舞蹈编排申请了版权,而《单身女郎》的舞步实际上是由鲍勃-福斯(Bob Foss)创作的一套舞步中汲取灵感,并融入了其他著名舞步以及芭蕾舞、爵士舞、嘻哈舞和现代舞的元素,但由于贾奎尔一克尼的作品具有新的元素和创造性的表达,最终美国版权局确认了该作品具有独创性,为其进行版权登记。可见,评价舞蹈作品的独创性,应看舞步的整体编排,而并非特定的单个动作,因此赋予单个舞蹈动作版权,于司法中通过整体表达判断实质性相似的实践做法并无实际意义,且仅由单个舞步这一“思想”判断相似程度,也与版权侵权的通行原理不符。
(三)单个舞蹈动作缺乏足够独创性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六)项规定,“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根据上文,《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解读文件和权威著作也明确了舞蹈作品是“动作的组合”。在美国,美国版权局多次拒绝为舞蹈动作登记版权,并表示由舞蹈步骤组成的简单或常规舞蹈动作不构成可受版权保护的舞蹈作品,如华尔兹的基本步、古典芭蕾舞步,原因在于“这些动作或步骤仅具有微小的空间变化”。舞蹈作品的创作不仅仅是选择、协调和安排身体动作。事实上,舞蹈作品其实可以认定为许多个单独舞蹈动作的汇编作品,如果舞蹈作品创作者在选择、协调或安排舞蹈步骤或动作中没有构成独创性的整体表达,则该汇编不构成著作权法中的舞蹈作品。正因如此,美国版权局曾驳回一个由足球迷创作的舞蹈套路“Ode to the Endzone”的版权请求,该套路融合了多个著名的终结区舞步(职业足球运动员在成功触地后表演的庆典舞)。最终版权局认为该舞蹈动作缺乏原创性,因为从整体上看,“Ode to the Endzone”是一个相当随意的套路和舞步集合而不是一系列连贯的整体舞蹈作品。由此可见,在国内外,单个舞蹈动作并不符合法律层面的明确规定,其中独创性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独创性是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实质性要件,也是区分思想与表达的关键性要素。
即便身体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移动,但实际上身体所能做的动作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单一舞蹈动作不存在各种动作组合的可能性,这就支持了舞蹈动作不符合独创性要求的说法。因此,与其说舞者创造了某个舞蹈动作,不如说其发现了人的肢体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动作。一个人只享有对自己身体“最初”创造的东西的权利,而不享有对从其他身体模仿或挪用的东西的权利,即使挪用的行为可能是通过身体进行的。正如19世纪的舞者富勒(Fuller)所创作的“蛇形舞”动作未能获得版权保护一样,富勒将舞蹈与精致的丝绸服装和多色的戏剧灯光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她的标志性舞蹈——蛇形舞,然而该舞蹈实际上衍生于印度传统舞蹈,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富勒的“身体权利”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她把别人的身体动作“占为己有”。事实的发现并不受版权保护,同样,身体动作的发现并非创作,因此不属于作品。美国学者埃维-怀廷(Evie Whiting)曾指出,“动作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因此,版权法应该将其视为一个等待发现的既存事实”。由此可知,将单个舞蹈动作认定为作品,实则是不适宜地降低版权保护的门槛,使原本的事实“发现”行为等同为“创作”行为。
此外,允许单一舞蹈动作获得版权保护,理论上将会激励创作者花时间和精力去创造更为独特的舞蹈动作。然而,事实上鉴于单一舞蹈动作的短暂性,创作者将更缺乏创作动力,因为创作单个动作本身花费更少的精力和时间,长此以往也许会导致优秀的完整舞蹈作品的减少。
(四)平衡司法负担与创作成本
如果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符合版权法的基本独创性要求,并且能够呈现出连贯的艺术视觉,此时该作品应当享有版权。但如若将这种保护范围扩展至完整作品中的单一要素时,则有可能导致过度垄断公共权利的情况。版权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创作,而完全不借助他人思想所创作的作品几乎不存在,因为每个作者都会不自觉受到他人启发,为了平衡这种影响与创作自由,思想被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由此可见,如果赋予单一舞蹈作品版权,将会出现“舞蹈作品过多”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舞蹈作品的侵权案件将会急剧增长,法院将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去界定每个舞蹈动作的原创性和实质性相似度。这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判决压力,也使得舞蹈界人士在创作和维权过程中承受沉重的负担。如果单一舞蹈动作得到版权保护,那么对于新的艺术家来说,要创作出原创作品而不陷入版权侵权的问题将是十分困难的,就像建造楼房必须要用到一砖一瓦一样。例如,芭蕾舞蹈作品中的许多跳跃动作基本相似,如果这些经典、基础的芭蕾舞姿势可以获得版权,那么编舞家将很难创作新的舞蹈。因此,应当审慎对待单一舞蹈动作的版权保护问题。在鼓励创作和推动舞蹈艺术发展的同时,也要确保公共权利的合理使用和创作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综合来看,单一舞蹈动作无论是从思想表达的形式,抑或是独创性程度,均未达到版权作品的标准。强行赋予单一舞蹈动作版权,不仅不符合著作权法基本原理,还可能引起舞蹈作品过多导致判决压力陡增的情况,而从鼓励创作的目的来说,以版权保护单一舞蹈动作于创作也无甚助力。
四、“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具体认定标准
在月光舞蹈案中,被告云海肴餐厅并非在其实体店内完整地演绎了原告精心编排的舞蹈作品。实际上,被告仅是在其餐厅环境中运用了与原告舞蹈作品中若干舞蹈动作相仿的剪影元素。因此“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判断关键在于,被告所涉及的被控侵权作品实质上是美术作品(或归类为摄影作品),这与原告所创作的舞蹈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存在显著区别。在此情况下,是否能够将两类不同的作品直接进行对比判断版权侵权?
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暂未确立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认定标准,从国外相关案例来看,美国霍根诉麦克米伦公司案(Horgan v.Macmillan)与月光舞蹈案相似,均涉及以静态手段侵权。1954年,著名编舞家巴兰钦(Balanchine)编排了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这部芭蕾舞剧改编自霍夫曼(E.T.A.Hoffman)的19世纪民间故事《胡桃夹子与老鼠王》,以及俄罗斯编舞家伊万诺夫之前对该寓言的编舞版本。纽约芭蕾舞团每年圣诞节都会演出《胡桃夹子》,并已成为经典之作,是美国最成功的芭蕾舞剧之一。1981年12月,巴兰钦向美国版权局登记了他对《胡桃夹子》编舞的版权,并向版权局交存了一盘纽约芭蕾舞团彩排的录像带。在他去世后,1985年4月,巴兰钦的遗产继承人霍根(Horgan)获悉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计划出版一本关于纽约市芭蕾舞团巴兰钦版《胡桃夹子》的书籍,该书中包含多张纽约芭蕾舞团制作的《胡桃夹子》场景的彩色照片。霍根认为被告出版《胡桃夹子》的表演照片应获得舞蹈作品的使用授权,双方数番协商未果后,霍根便以舞蹈作品版权人的身份,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寻求救济。该案的最终争议焦点是“芭蕾舞剧的照片是否可以侵犯该芭蕾舞蹈作品的版权”,与月光舞蹈案类似。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法官欧文(Owen)认为,麦克米伦公司并未侵犯编舞版权,因为“编舞与芭蕾舞中的舞步流动有关”。静止的照片在特定的时间瞬间,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捕捉到舞者姿态,因此读者无法从照片中感受到完整、流畅的舞蹈表演。而上诉法院认为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断照片是否侵犯舞蹈作品版权时,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标准。主审法官费恩伯格(Feinberg)认为静止的照片同样能够构成对舞蹈作品的侵权,因为照片可以传达给读者大量的信息,符合“实质性相似”原则。该案最终达成庭外调解,因此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判断标准在美国亦未有定论,各个判断标准合理性有待深入探究。
本文认为,月光舞蹈案的再审法院将被控侵权的平面作品与舞蹈作品进行比对判断实质性相似的做法有待商榷。正如霍根诉麦克米伦公司案初审法院的判决,舞蹈作品的本质在于“流动性”,各个动作的流畅组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舞蹈作品,单一静止的图片无法展示舞蹈作品的流畅表演。一般来说,作品类型不同,在进行侵权判断时,难以进行实质性相似比对,原因在于不同的作品类型呈现重点并不相同。例如,美术作品的独创性在于艺术家在创作平面或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时,对线条的勾勒、色彩的调配以及其他细节上的独特诠释。这种独创性不仅体现在对艺术元素的独特运用上,更体现在艺术家个人风格的独特展现中,使得每一幅作品都独一无二。而摄影作品的独创性,则源自摄影师对景物的敏锐捕捉、对构图的精心布局、对拍摄角度的独到选择,以及对曝光时间和明暗度的精细控制。此外,摄影师还可能通过对底片的修改和后期处理,进一步彰显其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艺术视角,因此不同的摄影作品有不同的风格。回到本案,舞蹈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创作者对连续动作、姿势的设计和编排,《月光》舞蹈利用月亮背景和动作剪影,表达舞者对月光的虔诚和对生命的热爱。由此可见,由于各个作品的独创角度不同,强行将其放在一起对比,实质上是将主观感觉作为决定性的判断因素而非客观角度的对比,该做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免有失公平。因此,判断本案中被告的摄影作品或美术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同样应将舞蹈作品的摄影或美术作品进行实质性相似的比对。正如“判定电影画面是否侵犯电影作品版权时,应当比对两个电影画面是否一样,并不是比对两个电影故事情节是否一样。”而本案中被诉侵权装饰图案与该舞蹈作品画面相比,两者在月亮大小的比例、舞者动作等方面均存在差别,也不能够完整或实质性还原舞蹈作品动作之间所呈现的流畅表演,因此再审认定装饰图案侵犯《月光》舞蹈作品版权,未从作品的相同独创角度进行客观比对,确定其相似程度,实则不当。
综合来看,对于“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应坚持以下三方面。
第一,需明确在著作权法的语境下,舞蹈作品的定义并不包含诸如服装、化妆、道具等舞台元素。当判断两部舞蹈作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时,应将焦点集中在舞蹈动作本身,而非其他辅助舞台元素的相似性。这些舞台元素虽为舞蹈表演增色,但在法律层面上,其并不构成舞蹈作品的核心内容。因此,如果两部作品的舞蹈动作在比较后并未构成实质性相似,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基于其他舞台元素的相似性来认定存在版权侵权。
第二,对于单个舞蹈动作是否可版权性,无论是其难度还是新颖度,都未达到成为独立作品所要求的外在表达程度,从创作角度来看,这些动作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事实的发现”,而非“作品创作”。因此,不能仅仅因为一个舞蹈动作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或技术难度,就将其纳入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如此可避免过度单一动作导致的权利滥用。
第三,在涉及“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案件中,审视静态作品与动态作品的相似程度时应当遵循科学、客观的比较方法。具体来说,应当将对应的作品类型进行对比,而非根据主观感受将毫不相干的作品种类混为一谈。例如,在判断一幅装饰画是否侵犯了某部舞蹈作品的版权时,应当尽可能地将该装饰画与舞蹈作品的其他平面作品如录像等进行对比,而非将其与动态舞蹈作品进行直接比较。遵循该对比方法有助于保持法律判断中的公正性和准确性,避免主观臆断导致的误判。
五、结语
月光舞蹈案作为我国首例“以静态手段侵犯舞蹈作品版权”的案件,自2019年一审伊始即引发了广泛关注,针对保护舞台整体、保护动作设计等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同的看法。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首先深入探讨了舞蹈作品的法律定义以及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认为诸如服装、化妆和道具等辅助舞台元素,实际上并不属于“动作作品”的范畴,这些元素主要是为舞蹈作品的表演服务,而不构成舞蹈作品本身的核心内容。此外,将这些辅助元素单独视为作品,也与著作权法所强调的“最低限度的智力创造”原则相悖。其次,单个舞蹈动作无法全面展现编舞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不属于合格的外在表达;并且单个动作受限于身体的物理特性和空间的变化,缺乏足够的创作空间,其实质上属于对身体动作的“发现”而非“创作”;即使单个舞蹈动作得到版权保护,也无法实际运用于版权侵权的判断,还可能增加法院判决压力和阻碍舞蹈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最后,判断静态作品与动态作品的相似程度时应当将对应的作品类型进行对比,以避免主观感受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情形。
针对云海肴公司利用《月光》舞蹈中的动作元素制作装饰画进行商业宣传的行为,本文认为,这一行为虽然涉及对杨丽萍舞蹈作品的某种程度的使用,但更核心的是构成了对杨丽萍舞蹈形象及其知名度的商业利用。在此情境下,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似乎更为贴切和有效。杨丽萍的《月光》舞蹈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辨识度,而云海肴公司作为一个以云南菜为特色的餐厅,其使用《月光》舞蹈元素进行商业宣传,无疑是在借助杨丽萍的舞蹈形象进行商业推广,对杨丽萍的舞蹈作品和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对云海肴公司的这一行为进行规制,不仅是对杨丽萍舞蹈作品及其形象的有效保护,也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
(作者袁锋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院研究员;许冰冰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