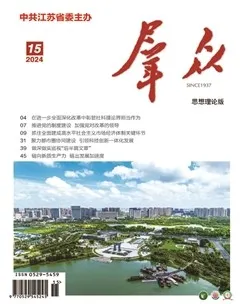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一战略任务鲜明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某些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不少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和堵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健全的体制机制保障,要先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条件?二是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和堵点是什么?三是如何打通现存的卡点和堵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组成,这同样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三要素。但是,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既有“新”的起点,又有“质”的变化,还有“力”的升级。其中“新”的起点主要体现为作为生产力载体和表现形式的产业,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起点;“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变换”范畴,将从以往主要以有形的物质消耗为主,逐步向以无形的知识(数据)消耗为主转变;而“力”的升级主要表现为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热力、电力、网力,到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算力的升级。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三要素”有新需求。就对劳动者需求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新”劳动者队伍的需求,显然不同于传统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技术工人,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就对劳动工具需求而言,正如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明确了划分时代的标志正是人们的生产工具或劳动资料。与发展传统生产力相比,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工具需求的最大变化在于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进而从实体经济生成数字经济。就对劳动对象的需求而言,新时代最大的变化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即可以使用的加工对象,其基本特征是,数据的使用不仅不会被消耗,反而可以不断增值,即越是使用就积累越多,价值越高。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卡点堵点
目前,在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三要素”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卡点和堵点。
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尚未形成。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人”无疑发挥着最为积极、最为关键的作用,因为从本质上看,这一要素是决定科技进步以及技术运用的根本因素。但目前,我国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短板,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型劳动者队伍支撑不够,尤其是高端创新型人才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在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人才供需比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人才供给不足不仅凸显了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和卡点,也凸显了人才流动和科技创新体制等方面的障碍。
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工具尚未出现颠覆性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融合应用,孕育出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最终表现为产业升级。当前,我国已形成了规模大、门类全、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然而,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庞大,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制造业总体上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仍然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仍然较为缓慢,即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过程中存在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中面临投入大、难度高、要素适配性低等问题。
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对象仍面临诸多问题。数据成为可以使用的加工对象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根本特征。信息和数据等要素不仅因为成为劳动对象而直接创造价值,而且能够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进一步放大价值创造效应,并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扩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未来产业领域。遗憾的是,当前我们不仅面临着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不足,在某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存在“卡脖子”问题,而且还面临着由于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不开放、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等“数据孤岛”问题。诸如类似问题的存在,不仅使得数据资产潜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也限制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扩展。
以体制改革为牵引打通卡点堵点
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卡点和堵点形成的原因固然众多,但体制机制障碍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卡点注入强大动力。
深化教育模式改革和人才激励机制改革。伴随科技创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岗位缺人”和“人缺岗位”并存现象,因为新的就业岗位不断出现和增加,并且往往超过人力资源培育的通常周期。以“干中学”“自成才”为特征的适应性就业岗位和工作方式,会成为许多新创就业岗位的人才成长路径。这就需要对当前教育模式进行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还要不断强化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在人才激励机制上,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性强和技术迭代快的趋势特征,人才政策取向应更具重在责任担当的特征,需要有创新担当和允许试错的制度安排,以此激励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人才成长。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升级不仅包括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更重要的是加快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完善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公平竞争、优化价格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不仅要确保政府在市场失灵时能够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而且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产业数字化提供物质基础,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
在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激发数据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数据发挥着极为关键乃至主导作用,但目前数据要素市场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不仅包括前述指出的“数据孤岛”问题,还包括数据权属界定不清晰、数据交易机制不完善、供需匹配难、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推动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加快破除阻碍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应成为未来数据要素市场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和方向。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江苏新时代自贸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