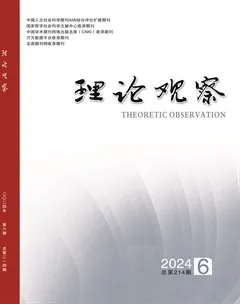分析美学视域中的想象话语研究
摘 要:想象话语作为艺术想象的定型与最终呈现,是对私密又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心灵意指的具体描述。想象话语的成型主要存在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想象话语的塑造会受到内在审美判断与外在语言游戏规则的制约;二是在艺术想象虚构与现实世界之关联中,想象话语作为非实存的虚拟指称能否找到存在的意义与合法性,三是在不同文字世界中想象个体的唯一性识别与超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分析美学视域中想象话语的发生与呈现、合法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想象话语;虚拟指称;可能世界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6 — 0124 — 06
一、引言
分析美学是分析哲学向美学领域拓展的结果,或者说,是美学研究对于分析哲学的一种回应。它延续了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放弃传统美学所追寻的“本质”,直面对象本身进行多层面的美学问题探讨。想象作为普遍意义上认知主体的心理过程,一直是哲学、艺术学等领域中的热点话题,因此它在分析美学中的定位同样值得关注。在美与艺术中,审美主体借由想象开辟无数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幻想世界,作品使得独属于个人的想象变为可以为他人认知、理解的形象,这也为研究想象话语提供了可能性。语言是文学表达的灵魂和出口,因此对想象话语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文学语言。相对于现实世界,文学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想象话语的本质是虚构与非存在。通过溯源想象话语的发生逻辑,可以基本确定这样的联系:审美主体将审美经验与情感变形重塑为虚拟对象,并且参考审美判断和语言游戏规则确定想象话语。在迈农的认知主体的意向性理论和意义指称论中,想象的虚构在话语层面可以体现为“非存在”问题,通过分析想象个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原始联系以及想象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多维统一可以还原其深层逻辑。追溯幻想物与想象话语的原初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向了克里普克指称理论下的本质主义,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现实却又实现了超脱。本文对想象话语的讨论主要基于维特根斯坦与克里普克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以此为起点发现更多的空白与问题。
二、想象话语的呈现前提:语言塑形的限制与突破
(一)想象的心灵意指:私人内心的封闭与不可认知
沿着想象话语的发生逻辑探寻,创造者如何以语言塑造想象?这关乎到认知与心灵,主体面对同一对象的感觉、经验各有不同,思维在语言表达一环节已经存在缺失与异化。维特根斯坦认为私人语言源于认知主体的内在心灵,他人无法进入。假如个体之间以私人语言为主要交流方式,不仅无法沟通,也不符合日常生活语言实践。吉尔伯特·赖尔认为个体之间顺畅交流的关键就在于答者已经掌握了相关问题的知识,“一个人决不能目睹另一个人的意志活动;他只能从观察到的公开行动推出产生它的意志活动”[2]。而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实践的角度出发,针对个体心灵的私有特质与日常交流的现实必然性提出了反私人语言。从认知与想象双重角度出发,如果个体之间没有作为桥梁的公共语言,想象只存在于主体的内在心灵,便是在与他心的交流中建立了双重壁垒。鉴于交流沟通的需要,克里普克认为存在一种公共语言使得理解这套话语的人组成交流共同体。想象是私有经验、情感倾向等复杂心理因素的创造性结合,与日常语言相比,想象话语的描述对象是虚拟事物,更具有不确定性与陌生感。假设个体A与B各有存在于其内心的私人体验,并结合情感等因素创造了想象新事物a,如果能以交流共同体承认的公共语言B将a表述出来,就会得到公共语言通行的想象话语a'。在心灵想象a转译到能被外界理解的想象话语a'的过程中,某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私有经验与情感倾向就已经消失了。
而对于交流共同体的其他接受者而言,想象话语成型之前的改变与流动都属于无法接触的他人心灵,那么想象话语究竟有什么标准参照呢?描述想象的心灵意指如果以接收者的心灵历史、实践经验为准,那么语言的出现即可被认可作为交流共同体内部规则的新参照?这是否形成了一个以交流共同体为圈子的语言游戏?
(二)想象话语的内外限制与突破:审美判断与语言游戏规则
虽然想象话语建构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的虚拟世界,但审美主体需要从文明语料库提取素材。首先,审美判断从创作者内在的维度限制了想象话语。语言能够较为准确地表达心灵,而选择用什么语言、什么称谓来表达想象事物,则涉及到审美判断。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指的是对象的形式是否能引起主体愉悦的情绪体验,并且这样的体验是先于理性判断而合目的性的,情感是联结审美主体与对象的桥梁。维特根斯坦则关注审美判断的日常语言实践。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判断的同时夸赞对象“美丽”,这是简略粗糙的感叹取代了真正的审美判断。只有当审美主体认识对象并具有相关知识储备时,其表达会更加精确。
第一,鉴赏能力与艺术素养影响主体的审美判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32节讨论过这个问题,人无法充分发挥他们先天拥有的鉴赏能力,只有不断练习才能让他们变得更加敏锐。学习绘画便要学习色彩的搭配与光影的透视。因此创造者在判断之前需要掌握相应的规则,而规则掌握的深浅与否直接影响审美主体的判断。对于想象,对象的分类、性质、状态等方面都在于创造者的判断,而更精微的判断并不仅仅只是掌握规则,就像刚刚认识声乐规则的人并不能浑然天成地谱曲,初习绘画的人作不出《星月夜》,浅显掌握与技艺娴熟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与练习补足,创造者的艺术实践能够显示其鉴赏与创作能力。第二,审美判断主要蕴含着审美情感,这贯穿于想象创造的整个过程,而且关乎规则与语境。想象基于审美主体内心中强大的动力与激情,强烈的表达欲促使他们将脑海里的奇思化为文字。从创作动力而言,审美情感的触动与推进是不可忽视的。情感作为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仅影响创作的即时状态,它同样影响创作前期素材的选取与后期的语言表达。不过,相较于情感,语境与规则的存在对于想象事物的表达影响更大。虚拟对象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完整的场域,后者即文字世界中的语境,而完善背景、特征、目标等一系列描述有助于丰富语境位,为虚拟对象提供可参考的背景。虚拟世界的合理性建立在客观现实的规律之上,虽然虚拟对象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但公共话语可以参考近似的现实事物,尽可能展现虚拟对象的特质。因此,想象话语不仅受到语境的影响,也会受到历时与共时交叉范围内规则的制约,这也是想象话语表达的外部制约的表现。
其次,语言游戏规则在范围与深度上限制了主体的个性表达,想象话语在遵行规则的基础上超越现实。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为了解决语言实践问题提出了“语言游戏”、“规则”等概念,“我还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3]8,“语言游戏”只是一种对日常语言实践的描述与类比。艺术想象源于审美主体改造日常经验而来的奇思妙想,想象话语会给接受者带来更多的惊奇与陌生感,这需要接受者调动知识与经验去理解和感悟。因此想象话语同样会受到语言游戏规则的限制。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与游戏作类比,他认为重点就在于遵行规则。“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23]178,规则并非不可怀疑,提前划定边界会带来神秘与未知。遵守规则的要求就是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语法,规则与我们的生活形式相关,它不仅在历时维度受到传统的制约,也在共时维度受到社会群体生活实践的影响。《哲学研究》第83节:“我们不是也有‘边玩边制订规则’这样的情况吗?而且也有我们边玩边修改规则的情况。”[3]59音乐、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都是它们作为特殊的语言游戏同样会受到相关艺术规则的制约,那么想象创新对于艺术规则的遵循与突破则成为了首要问题。
第一,艺术创作会自发遵行规则。维特根斯坦说“我遵守规则时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3]130。以文学为例,情节、人物、话语模式等等都属于写作范式。作家在创造想象世界时不自觉地利用范式建构人物和情节,这是一种自然遵循。当言说者做出与规则相符合的行为和反应时,交流共同体中的其他人才认可他已经掌握了规则。审美主体从语料库提取素材进行拆合加工,由此,想象话语是主体在艺术实践中自然遵循语言游戏规则的结果。第二,规则并非一成不变,维特根斯坦同样承认“修改”与“制订”规则的存在。艺术家们可以借由想象突破一般规则。克里普克认为只要言说者被交流共同体承认,违反规则也可以被后者认同并承认,想象创作亦同,“修改”并不意味着规则完全变了,创作者因为时代环境的限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规则,想象话语一并归入语言游戏规则中。虽然表现范式有所变化,但规则的重新制订并不意味着它否定了过往的历史与传统。所以,想象话语带来的“修改”与“制订”虽然打破了此前的规则,但随着生活形式与日常语言实践的改变,规则亦发生了更迭。每次遵行规则都是新与旧的交互,但却不是新值覆盖旧值,传统与历史的必然存在着,但新修订的规则同样在内。只要语言实践存在,更迭就不会中止。掌握规则的方式并不都是有意遵循,遵守或违反都属于认识和掌握规则。
艺术游戏规则同样如此,想象话语带来的是对已有规则的突破,这种突破是能指与所指对想象话语内外限制的双重突破,而新的规则纳入之后又会面对更新的变动。而想象作为诗人原有感觉、经验的异化更显示了创作者在话语表达上对规则的自然掌握。富于想象力的描写显然是不符合日常语言规则的,但是对艺术而言,它虽然违反了语言游戏规则,但也是一种新的更迭。创作既先于规则,又受制于规则,规则终究是深深扎根于生活形式与语言实践的。
三、想象话语表述的虚拟本质:虚构事物的存在前提与唯一性
(一)想象话语作为虚拟指称的本质非实存
想象话语“本质非实存”是指作为文学话语表达的一部分,想象话语是审美主体表述虚构性心灵意指的语言表达,而读者们并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相应的对象,因此其本质并非现实存在,是为非实存。话语构成的文字世界承载着文学作品的内涵与外延,与日常话语实践不同的是,文学想象带来的是虚拟世界,想象话语要比日常陈述多出了幻想与不确定性。陈述所指向的事物能在现实找到原型并一一对应,但想象话语所指涉的幻想物并不能实现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依据想象话语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因而想象事物在现实世界非实存或将实存。
参考日常语言的表达习惯,话语交流的合理与流畅建立在对象是真实存在这一基础上,而想象创造的对象无法在现实中得到验证,这意味着想象事物是一个非实存的对象,对它的称呼则属于虚拟指称,因此日常语言逻辑并不能汇通想象话语。非实存的幻想无法在现实世界的物理事实方面得到肯定判断,它既是一种否定判断,亦是关于该事物的非存在判断,即非肯定判断。意义指称论要求指称事物的前提是该事物存在于现实,而异于现实与虚构就是想象话语的本质特征,我们无法在现实世界为所有想象物找到联系与根基。因此想象话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认话语指涉的存在前提,如果想象话语的本质特征与现实世界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就需要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地方确认他们之间的联系,进而确认想象话语作为一种本质超时空语言表达的存在前提。探寻想象话语的现实依凭,也即确定世界上不存在圆的方,首先要作出一个关于圆的方不存在的判断。然而这个判断的提出本身就使得非存在的判断存在了,因此非存在物的存在判断这一表述是矛盾的,这亦是“金山悖论”的含义。对于想像话语而言,讨论想象话语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孰真孰假,而在于如何确定虚拟指称与涵义的本质关系,心灵哲学中关于虚拟指称的“非存在”讨论就与此有关。
想象诞生于审美主体内心幻想的刻画与呈现,因而塑造虚拟对象的语言极为重要,由于想象话语的本质非实存,关于幻想物的指称可以称为“虚拟指称”。虚拟指称与被指代的幻想物则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强指称关系,指称联系着幻想物的本质,或是想象话语仅仅作为指代的专名存在?因此,虚拟事物作为非实存能否在可能世界中找到存在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独一无二的联系也就成了关键问题。
(二)想象话语专有意义的承载与指称内涵的丰盈
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就开启了指称问题中存在与非存在的哲学思考,柏拉图也在《巴门尼德篇》与《智者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关于非存在的讨论主要基于形而上学的纯粹概念世界,不仅与后来分析哲学基于经验与现象世界的讨论相异,也与上文所讨论的问题有较大区别。迈农基于意义指称论研究非实存问题,提出了“金山悖论”。金山悖论是这样的一句话:“金山不存在”,即“The golden mountain does not exist”。其矛盾之处就在于虽然话语包含金山,但金山作为非实存的事物,我们无法在现实世界找到一座真正存在的金山。其次,依据意义指称论,语词具有存在论意义,只有当对象真正于现实世界中存在,才会有一个专门的语词用来命名与指称。即“金山不存在”一句指现实世界应当有金山与之对应,这个判断本身也是具有存在意义的。因此,从句义看来,“金山”一词的出现已经代表着金山的存在,但又说“金山不存在”,否定了其实存,这也就形成了悖论。金山悖论的症结是研究想象话语无法避开的,其关键就在于虚拟指称作为主词被赋予的存在论意义,文学虚拟世界必然需要想象话语的建构,那么指称与描述则要率先面对想象事物的存在合法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表述的困难,罗素在《论指示》中提出了摹状词理论,否定迈农关于非实在理想对象“虚存”的观点,认为“在命题的分析中,不能承认‘不实在’的东西”[4]。但是可以通过改写摹状词的方法改变空指称的主词地位,同时在逻辑上将“存在”理解为存在量词,即“有一个”,可作真假判定。“金山不存在”变为存在x,x由金子构成且X是山,且x的全部取值都能使命题为假。从艺术语言实践的角度看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虽然能够较好地解决意义指称论下虚拟指称的矛盾问题,但不适合应对艺术创作存在的无限可能性。
面对特殊的虚拟世界,接受者并不需要通过现实判定孰真孰假,只要能依据语言描述找到相应的指代意义,构建一个虚拟形象即可,摹状词理论可以为此提供更加精确的描述。然而想象的随机性与多样性让可能世界的存在跃然纸上,想象的可能性使得个体常元与个体变元在诸多可能世界的指称相异,而摹状词理论无力应对虚拟指称的指称问题,众多想象世界中的不同趋向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想象话语的出现就是对此前语言游戏规则的突破,在未来时间线上,想象话语的每一次运用都是意义被填充的机会,想象话语的多变会导致不同状态下的摹状词描述不同,进而出现不同的名称。而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可以清晰地区分摹状词理论下分界逐渐模糊的专名与摹状词,鉴于文学想象中虚拟对象的存在带来的阐释模糊,专名比摹状词具有更严格的指示效用。专名作为严格指示词可以在任一可能世界指称同一对象,而专名与指称对象之间的联系本质来源于专名相关的事件,这也有利于确定虚拟对象的基本内涵。虚拟指称虽然是审美主体创造性思维的具体展现,但由于审美主体的时代局限,想象世界以现实世界的客观事实为基底,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虚构与想象。因此,虚拟指称所指代的对象必然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语言哲学中的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指称问题则与之相关。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支持的摹状词理论不同,克里普克与普特南等人认为摹状词可能只描述了对象的偶然性特征,在专名与对象之间建立指称关系需要依靠历史因果指称论。由于社会历史活动的存在,专名与其所指的关系逐渐稳固,名词与指称的联系是语言使用者之间共同协调的结果,在特定场合与运用者的见证下,对象与语词永久地联系起来。
在可能世界中,指称与幻想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不仅受到审美主体的影响,外在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影响着创造者的审美判断。专名与对象、指称与想象的心灵意指之间的勾连是偶然的,但社会历史的链条会将专名与事件这最初不稳定的联结变为较为稳定的约定俗成关系。偶然的借代转变为必然的联系,专名有历史因果链条的支撑可以作为跨世界不同个体的同一指称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虚拟指称约定俗成的历时性展现了稳固与强化联系的效用,而不断延申的历史长河中想象亦会丰富虚拟指称的内涵与意义。譬如“望舒”作为月的一种创造性想象表达,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神话譬喻,指代月亮驾车之神望舒,屈原《离骚》亦有“前望舒使先驱兮”,而张衡《归田赋》中亦有“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盘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专名的指代与意义都源于故事的发生,而这样的联系会在漫长的语言实践中因为约定俗成稳固下来,其内涵也逐渐丰盈。审美主体需要参照艺术规律与经验创造一个专有指称,而专名的抉择与描述则要依靠创造者的审美判断。虚拟指称的诞生并没有违背语言游戏规则,而是自然遵循,专名作为跨世界个体在诸多可能世界中共同使用的严格指示词,承担着跨世界个体的同一识别功能,而虚拟指称所蕴含的意义会随着诸多可能世界的诞生而展现更丰富的可能性。
四、想象话语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关系
(一)想象话语是虚拟世界联系现实世界的桥梁
艺术创作的语言实践代表着对规则的自然遵守,创作的关键就在于以可能性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异的世界,构造虚拟世界需要艺术语言,而可能性便蕴含其中,这与逻辑学上的“模态”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为了更好地解释模态逻辑表达式的意义,证明模态推理的有效性,确定模态命题的真值,逻辑学家们提出了“可能世界”的概念。莱布尼茨认为事物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只要不存在逻辑矛盾,事物A就会有A1、A2……An共同存在的可能事态,An是现实世界A在无数可能世界中的不同存在方式,由可能事物组成的多个可能世界也同时存在着。这里说的可能世界不仅指向了物理意义,也包含物理意义上不可能但逻辑上可能,过去与将来的可能世界。
在艺术想象中,虚拟世界的构造得益于审美主体对想象话语的运用,想象话语对现实世界的偏离造就了可能世界,文学想象话语与现实的不同就在于虚构,因此想象话语就是在美学中汇通可能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桥梁。《山海经》《聊斋志异》中的神鬼精怪虽然不具有物理上存在的可能性,但它们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艺术家的想象本身就是多个创造过程叠加的可能性推演:事物可能是杂糅现实中多个事物特征而创造出的全新形象;人物或许取材于现实但走向却恰恰相反;审美主体以现实世界为蓝本改写亲身经历……想象天马行空,但并不是空中楼阁,审美主体很难超越其时空限制,因此想象的虚拟世界并不是全然的虚拟,必然存在着源于现实生活的因素。艺术想象不仅仅指向了虚妄的幻想,在某种方面,艺术的虚拟世界或许也可以被称作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可能世界,在这里,哲学与艺术发生了跨学科交流。可能世界理论为人们观照世界提供了新的路径,人们对理性的追寻与非理性的探索,都能在可能与现实的双重对照中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可能世界理论能够进一步解释现实与虚拟的关系,个体的跨世界识别与同一性问题对于审美想象而言极其重要。由于想象的存在,实在世界的元素被移用到虚拟世界,两个世界的走向却不尽相同,跨世界个体能否在想象话语的作用下被清晰识别?如果虚拟世界中的形象与现实世界中的众多个体存在同一性,我们如何确认虚拟世界中的形象就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特定个体呢?假设现实世界中A实有,在可能世界中只有同一于A的个体具备A的唯一性特征,而历史因果指称论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本质特征。
(二)想象话语是唯一性与超时空性并存的物质载体
以上几个问题都与语言哲学上的指称问题关联密切,指称理论认为,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依赖于由适当名称和描述而实现的强指称,使得个体常元与个体变元在众多可能世界中的所指同一,从而引发可能世界理论中个体跨世界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假设个体跨世界存在,有什么标准能用来辨认它在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中是同一个体呢?创造者通过想象话语建构虚拟世界,接受者理解想象话语不仅需要依靠虚拟世界的语境,也需要现实世界的语言。因此,确定想象话语关于幻想物的特有描述是在根本上确立并加深虚拟指称与发生事件之间的联系,在“严格指示词”与其对象建立本质联系之后,借助虚拟指称与对象之间的强指称关联确认跨世界个体的同一性。
在可能世界理论的讨论中,克里普克并不是唯一提及本质主义问题的学者,齐硕姆假设了一个极端环境下跨世界同一理论面临的“空同一”的困境,悖论的关键就在于个体的关系与性质可以无限制、无穷尽地变换,随后仍可以保持同一关系,因为对象的性质不断更迭,齐硕姆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出对象的本质属性,这便与前文的虚拟指称问题紧密关联。依据历史因果指称论,幻想物与虚拟指称之间的本质关系在于历史发展进程中想象话语日渐丰富、层累的含义,这不仅联结了想象话语与指称对象,其指称关系也由偶然转为稳定。同时,这也可作为跨世界个体的同一性识别标准,区分虚拟与现实。克里普克以投掷骰子为例,可能世界便是每一个数字正面出现的六分之一概率的微型世界扩充,因此,可能世界是世界可能会采取的众多方式方法下状态或者历史的不同呈现。对虚拟指称而言,历史与社会发展下的信息传递链条稳固了语言符号与幻想对象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这一链条不仅能够成为跨世界个体同一性的判断标准,可能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亦造就了虚拟指称含义之多样。由此,从幻想物到虚拟世界,从虚拟指称到想象的可能世界的逻辑进程中,确认虚拟指称与对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更需要历史发展进程中想象话语那不断丰富、变换的所指,而随着能指对象内涵的日益充盈,严格指示词所代表的语言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虚拟指称不仅仅是符号化的想象话语,想象话语与幻想物之间形成了强指称关系。同时,也为验证个体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同一性提供参考。因此,虚构世界的艺术想象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是广泛存在的,与现实世界个体有同一关系的物理实体对象,我们可以通过其自然构造和所属类别进行辨别与分析。但艺术的可能世界既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刻,也不是没有基点的虚拟世界。不具备思想特质的个体能够依据本质构造在两个世界中找到同一关系,那么存在于复杂社会关系中,拥有生命与思想的个体呢?历史因果链条便成为判断与度量跨世界个体同一性的标准与尺度。
想象世界随着幻想物一同诞生,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想象世界总是对时空的超越。而想象话语作为艺术创作的结晶则成为幻想世界的永恒载体,它作为文字承载着创作者的幻想。历史因果链条的存在使得未来时间线上将有更多的文字世界丰富这个原初的可能世界,而他人的解读与幻想会带来更加丰富的内涵,虚拟指称之含义亦愈发充盈。以衍生于历史的想象世界为例,在这样的想象世界中,虚拟形象衍生于过去的可能世界,历史人物传奇的续写与创作本身就依赖史书对该人物和某段特定历史的记载,相对于现实世界,史书里的世界属于过去的可能世界。时间无法回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衍生于历史的想象世界却并不需要依照历史的轨迹。对于这类世界,以多个文本作为参照的标准,从人物经历、命运之中寻找可以重合的锚点,人物命运轨迹必然不会完全相同,因为历史人物在虚拟世界出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再次上演过去的命运,写实并不是艺术家创造这类人物的首要目的。而想象的多样性、可能性与凝结则可以在作品的表达中得到充分展现,譬如历代以唐明皇杨贵妃为题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长恨歌》、《马嵬》、《长生殿》还有许多民间话本。虽然作品的主旨、思想与情感各有不同,但都衍生于唐代君王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所建构的虚幻世界,作者寄寓的情感与意义都借由文字流传下来,而且其中意义不断丰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文本与创作者交流,在自觉填补空白的同时进行二次创作,无数可能世界随着读者们的再创作展开,跨世界个体的无限可能性与生命力随之显现,想象世界建构的魅力就在于此,而这恰恰展现了艺术创造者想象的生命力。并且这样的生命力不会随着作品的完结而结束。
五、小结
想象话语作为审美主体艺术创造的最后呈现,既遵循了语言游戏规则,又展现了丰富的可能性。从想象话语的发生逻辑来看,想象话语的表达不仅仅在于个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审美经验与艺术规则都在参考之列,语言游戏规则也会限制想象话语的表达。艺术想象凭借文字构建了无数想象世界,审美判断下诞生的虚拟指称与起源故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内涵与可能性也会在那些被不断创造的可能世界中丰富起来。故事的发生与构造的本质成为了识别跨世界个体是否同一的关键,多种可能性的成立、存在与否都需要在起源处找到同一,在不断延申的历史中,想象话语的可能性在语言游戏规则不断重构的自然遵循过程中既得到了展现,又不断被丰富。
〔参 考 文 献〕
[1](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韩林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21.
[2](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M]. 徐大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5.
[3](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英)罗素.数理哲学导论[M]. 晏成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60.
[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 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6]Kripke S.Naming and Necessity[M].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7]Kripke S.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M].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8]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Grammar[M]. Oxford:Basil Blackwell,1974.
[9]SHUSTERMAN R.Analytic Aesthetics[M].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
[10]SCRUTON R.Art and imagination: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 South Bend,Indiana:St. Augustine's Press,1998.
[11]王峰.美学语法: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陈波.逻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3]周祯祥.必然、蕴涵、世界与关系 模态逻辑的历史和基本理论探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4]张力锋.模态与本质 一个逻辑哲学的研究进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5]高新民.迈农主义与本体论的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6]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7]龙小平.可能世界中的名称和同一性[D].西南大学,2007.
[18]郭喨.“可能世界”中的必然与同一[D].浙江大学,2012.
[19]徐晔翀.论可能世界语义学中的个体跨界的同一性问题[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0]鲍海敏.关于“非存在”问题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
[21]吴浩田.罗素摹状词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22.
[22]吴凤伟. 克里普克“规则遵循”问题探究[D].黑龙江大学,2010.
[23]王荣虎,潘天群.论跨世界个体关系之同一理论与相似理论的“殊途同困”[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03):57-63.
[24]方芳.论可能世界对文学虚构叙述研究的影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02):130-134.
[25]杨红玉.论蒯因对模态谓词逻辑的批评[J].中州学刊,2016(08):109-114.
[26]倪蓉.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内涵语境中失效的诠释[J].外语学刊,2007(04):12-16.
[27]陆剑杰.莱布尼茨“可能世界”学说的哲学解析[J].社会科学战线,1997(04):51-59.
[28]余多星.克里普克可能世界思想的哲学价值探析[J].青年与社会,2014(01):280-284.
[29]宋荣,杨雨.指称与心灵——当代西方心灵哲学视域中指称研究的最新进展[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37(06):7-12.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