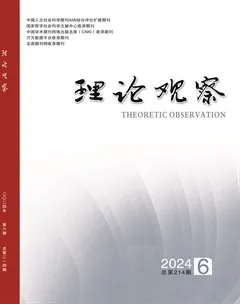世界范围内船葬习俗的文化意义探析
摘 要:目前学界对于古代巴蜀地区发现的船棺葬的文化意蕴和内涵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的船棺葬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船葬可以与古代巴蜀的船棺葬做对比。世界范围内的船葬主要可以分为船棺土葬、船棺火葬、船棺崖葬、船棺海葬和随葬船只等几种,在东南亚与大洋洲、拉丁美洲、古埃及和斯堪的纳维亚都能见到各种类型的船葬。各地的船葬与史前洪水事件和海洋灾害事件息息相关,可能隐含了古代先民对史前洪水与海洋灾害的记忆,是先民“惧水”与“畏水”的情感体现。在世界部分地区先民的信仰观念中,普遍有人死后会乘“魂船”渡过“冥河”的相关说法,这可能也与先民的“畏水”与“崇船”情结有关。
关键词:古代巴蜀;世界;船棺葬;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B93;K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6 — 0101 — 09
在巴蜀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流行的墓葬葬式经历了多次演变。在新石器时代,发源于四川盆地西缘、北缘的营盘山文化流行石棺葬;随后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西北侧河流台地区的宝墩文化,较为流行无葬具和少随葬品的竖穴土坑墓。进入青铜时代后,三星堆文化中流行统一规划的大墓地,可能是聚族而葬,但其主要的墓葬形式仍是之前宝墩文化时期的竖穴土坑墓。继三星堆文化而起的十二桥文化,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蜀文化中,开始流行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船棺葬”,即以木船作为死者的葬具的情况,并多伴有较丰富的随葬品。偏东的巴人也流行船棺葬。对于巴蜀地区“船棺葬”的来源及其象征意义,一部分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众说纷纭。笔者注意到,除了巴蜀地区外,在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中,也多见与船有关的丧葬方式。通过对其他地区“船葬”的研究,或许可为研究成都平原“船棺葬”的内涵及意义提供灵感。
需要说明的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本文所提到的“船葬”,指的不仅仅是以船形棺木作为葬具的“船棺葬”,还包括了随葬实用船或船模、将船作焚烧遗体之用、绘制有与船有关的图案等。只要是涉及船的墓葬或是丧葬方式,都属于本文所探讨的广义“船葬”的范围。
一、成都平原的“船棺葬”及学界研究
对于古代巴蜀地区这种以船为棺的现象,冯汉骥较早对此进行了讨论,通过对四川昭化宝轮院所发现的特殊墓葬情况,提出了“船棺葬”的叫法。[1]“船棺葬”在成都平原地区大致兴起于商周时期的十二桥文化时期,昌盛于晚期蜀文化时期(即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一直绵延到西汉初年,蜀地逐渐融入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为止。据陈云洪[2]、娄雪[3]等人的不完全统计,截止2017年,成都平原地区先后发现了160余座船棺葬,发表了相关的发掘报告20余篇。其中还包括已被发现但未见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船棺葬墓地。墓地的主要情况详见各发掘报告,陈云洪等人的研究中也对其做了较为完整的归纳,故本文暂不赘述。
这些船棺葬的葬式和葬俗各有千秋,比如其中有的是一次葬,有的是二次葬;有的有二层台,有的没有二层台;有的有棺盖,有的没有棺盖;有的是单人墓,也有的是一坑多棺的合葬墓;有的随葬品较丰厚,也有的少见随葬品;有的在船棺内还套有小棺,也有的没有;有的墓坑中填充青膏泥或白膏泥,也有的不填充;有的埋在土中,也有的放置在悬崖峭壁上。在这些“个性”中,也能够看出这些船棺葬拥有一些“共性”,那就是将棺木雕凿成船的形状,尤其注重对棺木头部和尾部的装饰,使其底部具有弧度、首尾两端上翘,呈现出船首和船尾的样态。典型的巴蜀地区船棺葬如图1所示。
图1 成都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船棺葬M917
(图片来源: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年,第137页)
关于成都平原先民“船棺葬”的用意及文化内涵,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车广锦认为,凡是行船棺葬的地区,在古代都盛行独木舟。因此国内各地的船棺均起源于独木舟。船棺葬是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先民“灵魂升天”观念的一种葬俗,并注意到了在世界范围内,墨西哥、南美洲等地也有类似的“驾舟升天”相关的葬俗与传说。[4]陈明芳认为,船是海洋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其目的是满足死者在另一世界中的生存需要,集中体现了海洋民族的信仰、追求和生活方式。[5]段塔丽认为,船棺葬体现出了先民具有强烈的“送魂”意识,将死者的亡魂送往其祖先的发源地。[6]刘芮伽认为,船棺葬是“习水民族的特殊葬俗”。古蜀人傍水而居并善于驾驶舟船,舟船也是先民日常的交通工具。根据“事死如事生”的古代丧葬传统,这或许是一种“以水为家”的信念。[7]陈锽注意到了墓葬图像中经常出现的舟、车与桥,认为墓葬中的这三类意象具有共同点。其中,船是“渡魂之舟”,是中国古代“浑天说”和灵魂不灭信仰的反映,并根据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和居民交通工具的不同,在墓葬中呈现出“南船北车”的特征。[8]
综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船棺葬的文化内涵大致有二:一是由于古人存在着“灵魂不灭”的信仰,认为死者在死后会去往他处。而舟船正是承载亡者灵魂去往他处的其中一种重要交通工具。二是为何会选择船作为亡者的交通工具,这是由于舟船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体现了先民的亲水习性。目前发现的所有“船棺葬”中,当地先民都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独木舟的习惯。
此外,梁钊韬[9]、唐昌朴[10]、黄尚明[11]、李子[12]、陈云洪[13]、雷雨[14]等学者分别从文献学、考古器物类型学等角度研究了成都平原的船棺葬。但他们更注重讨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和文化演进的方向及脉络问题,而不是其文化内涵。在这些讨论中,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域外也有类似的船棺葬的习俗,如拉丁美洲、东南亚与南亚、大洋洲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等。但少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船葬葬俗做进一步的介绍与研究,也少见有将其他地区的船葬与巴蜀的船棺葬在精神文化方面进行对比的研究。因此,笔者拟通过本文,对国内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船葬习俗进行一些阐述,从而找出世界史前文化中“船葬”在精神文明与思想内涵方面所具有的共性,以期对古蜀地区的船棺葬研究提供参考与启发。
二、国内其他地区与世界范围内的船葬
在国内其他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中,也发现了不少与船有关的葬俗。限于文章篇幅,我们在此挑取一些典型的做不完全统计与阐述。
(一)国内其他地区的船葬
除了成都平原外,国内的船棺葬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此外在东北、西北等一些地区也有见到。除成都平原之外,长江流域的船棺葬多以崖葬的方式进行,其葬式葬俗和文化内涵多有共通之处。下面以福建武夷山的船棺崖葬为例简要介绍。
在福建武夷山地区,也见到了与巴蜀地区类似的船棺葬。该地区的船棺皆是安放在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上,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有“数千”之多。但在1973—1975年福建省博物馆对该地区的船棺崖葬进行调查时,仅剩下了10处,且大多数墓葬中空无一物,多只见碎瓷片、碎陶片四处散落。以白岩崖洞墓为例,该处棺木呈船形,全长489厘米,宽55厘米,高73厘米。主要分为底和盖两部分,上下套合。棺底首尾两侧向外翘起,棺盖近半圆形如船篷状,整体由闽楠制成,制作水平较高。死者为中年男性,约55-60岁,仰身直肢葬。(见图2)棺内发现有龟状木盘、纺织品残片、尸垫、竹席、粽等。[15]
图2 福建武夷山的船棺葬
(图片来源: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县文化馆:《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第13页)
对于武夷山船棺崖葬的文化内涵,曾凡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闽越族的遗俗。闽越族崇拜鬼神,喜居山林,尤爱巫术。而“巫”是“神”的代表,“神”又是住在天上的。“巫”作为沟通人界与神界的使者,需要通过高耸的山峰来接近神居住的地方。[16]朱天顺也认为,高耸入云的山峰常被古代的人们看成通往天上的道路而受崇拜,山峰的雄伟与难以接近,则常被幻想为神灵的住所而受崇拜。[17]但在这些研究中,只解释了“崖葬”的文化内涵,认为崖葬将死者放置在高耸的山峰之上,是更接近神所在的天国的位置。但这些研究中并没有解释为何会选择船棺作为葬具。
其次是东北及西北地区的船棺葬。青海乐都柳湾的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使用独木舟形制的船棺。在柳湾墓地清理的366座齐家文化墓葬中,288座配有葬具,其中船棺葬184座,占总数的63.8%。由此也可以看出船棺葬在该地区的兴盛。该地区的船棺为独木棺,是将一整段圆木从中间掏空并做成船舱的样式,顶部和底部削平,两端也削成平头。一般长约1.5—2米,宽约0.5米。[18]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处墓葬中,呈现出成年男性位于船棺内,仰身直肢葬,而成年女性位于船棺外,面朝男性侧身屈肢葬的葬式(如图3),显现出了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并且女性极有可能是殉葬而死的。还有一部分船棺葬中,也发现了人殉的痕迹,如柳湾墓地M979,墓主人在船棺内仰身直肢葬,船棺外随葬有四个人头骨,显然是人殉的遗迹。[19]这些发现都说明了,配享船棺的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也更多,且绝大部分情况下为男性。
图3 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船棺葬M1061
(图片来源: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柳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辽宁翁牛特旗(现属内蒙古赤峰市)石棚山小河沿文化中也出现了用桦树皮作为葬具的习俗。在发掘现场中,发现了死者身下有桦树皮的痕迹,而死者身上则没有,说明是以桦树皮制作成了船棺。这种习俗应与当时该地使用桦皮舟有关。[4]除了上述这些地区的船棺葬之外,在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等地,也发现有船棺葬,且多为崖葬,与武夷山的船棺崖葬类似。因此不再赘述。
另外,除了以船作为棺椁之外,还有随葬船的现象。如河北平山的战国的中山王墓中,除传统的陪葬坑、车马坑之外,还发现了葬船坑。葬船坑平面呈“凸”字形,分南北两室,南室东西并列三条大船,南北各有一条小船,北室的船不存,但根据遗迹及残留物品显示,很可能是一条装饰有彩画、铜环的主船。根据大小来看,这些船都是实用船。在葬船坑北面,还有一条长109米的狭沟,可能是“象征性的河道”。[20]
综合上述发现来看,笔者认为,国内的船葬分布范围较广,各地的表现形式也不一致,既有船棺崖葬,也有船棺土葬,还有随葬船等。但其中有三个共同点:其一是国内出现了船葬的地方,也都发现了先民使用舟船的痕迹,说明舟船是当地先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交通工具。车广锦也提及了这一点。其二,以船棺作为葬具,或是随葬舟船的人,其生前的社会地位一般较高,财力也比较雄厚。不论是船棺土葬或是船棺崖葬,抑或是随葬舟船,筹备葬仪所需花费的人力物力也比普通墓葬更多。如中山王等身份、地位相当高的一国之君,亦在其墓葬中随葬舟船。充分说明了船葬者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其三,多出现在大江或大河的流域。
(二)东南亚与大洋洲的船葬
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及太平洋诸岛上,也发现有与中国类似的船棺葬的习俗。雷雨介绍了越南红河流域青铜器至铁器时代的冯元文化、桐豆文化、扪丘文化、东山文化等几种考古学文化,指出越南与古蜀地区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在其文中,对越南红河流域的船棺葬也有涉及。他指出,在越南的海防、朱芹、朱山、越溪、隆洛卯等地的东山文化遗存中,皆发现了与古蜀地区类似的船棺葬遗存,只不过在时间上略晚。棺中随葬有铜凿(斤)、环首铜削、铜拍等物(见图4)。[14]除越南外,在泰国、印度、婆罗洲、菲律宾等地,也发现了较为类似的船棺葬。以东山文化的越溪墓地为例,从船棺的制作方式来看,这些船棺普遍是由一段圆木中间凿空而成的独木舟,棺身两端有打磨平整的痕迹,整体形体较大;从船棺的放置方式来看,有的船棺是简单放置在竖穴土坑内的,如同巴蜀地区的船棺葬;也有的是被地面上的柱子支撑着的。[21]由此看来,东南亚地区的船棺葬在与巴蜀地区的船棺葬表现出相似性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巴蜀地区所没有的新葬式葬法。不少学者在此前认为,东南亚地区与巴蜀地区在汉代以前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22]从船棺葬习俗来看,便可印证这个判断。
图4 越南海防东山文化的船棺葬
(图片来源:雷雨:《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第18页)
在更远一些的菲律宾、婆罗洲及大洋洲地区,当地土著也盛行船棺葬,并且呈现出了和东亚地区船棺葬不一样的丧葬方式。在菲律宾,人们将死者安放在一根呈船形的挖空原木中;在一些地方,还会杀死奴隶并将其埋葬在主人身边,以便在死后继续为主人服务。在菲律宾的Bohol岛,当地的一位酋长被安葬在称为“barangay”的船棺内,周围殉葬有70多名携带武器、护身符和食物的奴隶,就像他在活着的时候经常驾船率人外出劫掠一样。[23]
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Sarawak)地区,人们用棕榈树制成的船来装载死者的尸体,并将死者的一些个人遗物和食物装载在船上漂流而去,这样他就可以乘坐这艘船在死后继续旅行。在当地的“亡灵节”上,也会派出一艘小船去象征性地接回亡者(即扔在屋子后面)。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地区也有这种船棺海葬的习俗,因为在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漂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波利尼西亚先民就是漂洋过海来到此地的。但在其祖先漂洋过海的漂流记忆逐渐淡化之后,该地的丧葬习俗逐渐改变,只在葬礼仪式中使用独木舟作为一种象征意义。在大洋洲的其他地区,如萨摩亚群岛、美拉尼西亚、斐济等地的土著中,也存在类似的丧葬习俗。[24]
在加里曼丹岛的尼亚河畔,也发现了与中国长江流域比较类似的船棺崖葬。船棺被放置在一个高达300英尺的悬崖上的洞穴内,一旁的岩壁上用鲜红的铁矿石描绘出了一批船和张开手脚舞蹈的人物形象,显得粗犷而又原始。这可能是表现“死者之舟”的一种宗教仪式。[5]
(三)古埃及的船葬
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沿岸,并沿着尼罗河两岸分布。由于尼罗河经常洪水泛滥,因此当地先民经常需要靠舟船出行。在古埃及文明中,舟船的形象经常被见到,包括各类船只的模型、刻画在陶片、纸草、石板等多种材料上的船只图案等。据报道,1954年,在胡夫金字塔南侧周围的墓室中,也发现了大量木材、绳索与燧石、锤子等造船材料,研究者认为是随葬大型船只的痕迹。该船被命名为“第一太阳船”,距今已有4600年的历史,是目前发现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型木造船。1987年,又在“第一太阳船”的西侧发现了“第二太阳船”。[25]
在埃及的Abydos地区,也发现了第12王朝时期皇家船葬的遗迹。一条长约20米的大型木船的残骸被放置在一座地下拱形建筑内。由于年代久远,且在当时有被拆除重复利用木材的迹象,因此保存得已经很不完好。在葬船室四周的墙壁上面,留下了大量与船有关的壁画(见图5)。船的图像大致由简单的线条勾勒,显现出扬起风帆、有多个船桨一起划动的样子。其中偶尔穿插着动物和其他人物、花卉的图像。[26]有研究者认为,在古埃及,船只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象征,并表达了一种“混乱中的秩序”的隐喻意义。[27]
图5 埃及Abydos地点葬船室中有关船的壁画
(图片来源:Julia Clare Francis Hamilton. (2022) Hedgehogs and Hedgehog-Head Boats in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in the Late 3rd Millennium BCE. Arts 11:1, pages)
(四)斯堪的纳维亚的船葬
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即今天的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维京人,成为不列颠岛上的撒克逊人和西欧大陆法国、荷兰等国挥之不去的梦魇。维京人尤善驾驶长船漂洋过海,对英、法等国进行劫掠。他们不仅在当地打家劫舍,有时还在不列颠岛或法国定居了下来,形成了不列颠岛上的“丹麦法区”与法国的“诺曼底公国”等多个维京人国家或定居区。此外,他们还驾船先后抵达了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定居点。最远抵达过位于今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文兰”地区,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和海洋探索精神的民族。
维京人主要信仰的宗教经历过一次转变。其原本信仰以“奥丁(Odin)”为首的北欧诸神。10世纪后,随着维京人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不断加深,基督教开始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传播,并逐渐取代了旧宗教,使得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经历了一次整体改宗。在改宗之前的异教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盛行船葬。
需要说明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地域概念,而“维京人”是一个民族概念。9-11世纪维京人主要兴起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却不仅仅只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随着维京民族的迁徙和扩张,其在不列颠岛、日德兰半岛、西欧大陆、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西西伯利亚地区皆有分布。在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处在与西方文明世界交界处的维京人,流传下来的记载更为详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维京人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因此接下来会用到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地区维京人的相关资料。
异教时代维京人的船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船作焚烧尸体之用。焚烧时可能是在岸上焚烧的,也可能是在水面上焚烧的。阿拉伯人伊本·法德兰曾经在伏尔加河畔的维京人聚居区参观过一场维京葬礼。他对此记载道:出殡之日,酋长的船被拉到岸上,人们围着它走动,口中念念有词。一位称作“渡灵师”的老妇人将停尸架置于船上,再将衣服、垫子铺于其上……与他放在一起的有酒精饮料、食物、香草和他所有的武器。随后,一条狗、两匹马、两头母牛、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会被杀掉并放入船中……死者最亲近的家属点燃船下的木柴,其他人将更多燃烧的木头扔进火中。只需一个小时,一切化为灰烬。[28]
由此可见,死者是一位居住在伏尔加河畔的维京人部落的酋长。在其死后,人们将死者遗体、死者身前所用的衣物、武器等,与一部分祭品一同放入船内,并将船点燃。葬礼需要有“渡灵师”之类的宗教人士在场主持,并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
另一种方法是将船作为棺椁下葬。这种例子发现得很多。以苏格兰西部Ardnamurchan半岛的Swordle湾地点为例,该处就发现了10世纪维京人的船棺葬遗存。该处船棺葬是在一个自然形成的土丘上加工而成的。土丘从中部被掘开,下面铺垫了若干大小石块,并将船棺放置在其中后关闭墓门。葬具是一艘长约5.1米的小型铆钉划艇,可能是一艘更大的船的“微缩版”,而不是实用船。该船棺为东西向,死者头在西方。随葬有装有食品的铁锅(头部旁)、号角(头部右侧)、别针与戒指(身体上)、一把制作精良的带鞘的剑,但没有剑尖且呈S形弯曲,可能是故意损坏后再下葬的(身体左侧)、宽刃斧头(靠近脚)、盾牌和长矛(距尸体有些距离,大致对应中下半身)等。[29]
除了船棺火葬和船棺土葬以外,还经常发现维京人的墓葬中有与船有关的石雕、画像等。对于维京人的船葬的精神内涵,有研究者认为,维京人在船葬方面的多样性,显示出幸存者在有选择地记住或遗忘死者。在船棺葬中,随葬品显示出了劳动和杀戮的行为。这几种行为与船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构建叙事,并通过神话叙事来纪念死者。除了神话联想之外,也有学者认为,绝大部分分布在不同地方的维京人都是用了船葬的方式(冰岛、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等地的维京人因缺少树木除外),是因为船葬是维京人一直以来的传统,有助于培养他们共同的归属感和忠诚感。[30]
此外,根据部分学者的介绍,在南亚、拉丁美洲、印度洋部分岛屿等地区,也存在着船棺葬或与船有关的葬俗。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详细介绍。
三、关于船葬的一些问题的探讨
通过上文,我们简要了解了国内其他地区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与船有关的墓葬习俗。笔者想对船棺葬的文化内涵方面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船葬是史前先民“畏水”的表现
对于船棺葬的文化内涵,陈明芳和刘芮伽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前者认为,船棺葬体现了“海洋民族的信仰、追求和生活方式”[5];后者认为船棺葬是熟悉水性的民族的特殊葬俗,体现了“以水为家”的信念。[7]言下之意都是主张船棺葬是先民“亲水”的体现。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一来说船葬是“海洋民族”所特有的有待商榷;二来船棺葬不仅不是先民“亲水”和“以水为家”的体现,正相反,船棺葬可能是先民“畏水”的体现。具体依据如下:
其一,若要说船棺葬是“海洋民族”特有的丧葬习俗,有些牵强。包括巴蜀地区在内的长江流域,在史前时期以及封建时代早期都盛行过各种形式的船棺葬,但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并不靠海,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舟船也仅仅是在江河和湖泊中划行,既谈不上是“海洋民族”,也说不上是“海洋文明”,但在这些地区依旧盛行船棺葬。古埃及的文明区域基本集中在尼罗河中上游的沿河地带,离地中海、红海都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也不太能说得上古埃及民族是一个“海洋民族”或是具有“海洋精神”的民族。笔者认为,说船葬是“海洋民族”所独有的,说法有些片面。如果说是“大河或者海洋沿岸民族特有的”,则比较全面。
其二,许多有船葬习俗的地区,都流传有史前洪水灾害的传说,或是发现了与洪水灾害有关的考古证据。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不少史前城址中也出现有防水的功能;出现了不少与治水有关的工具和水利设施的遗迹;流传下了大禹治水等与洪水有关的传说。这些洪水灾害可能与气候的变迁或者先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有关。[31]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有很大一部分盛行船葬的地区也经历过史前洪水,或留存下了与洪水有关的记忆。如古埃及在史前也经常遭受尼罗河洪水泛滥的侵袭。至于一些靠近海洋的地区,如东南亚、大洋洲等,由于海洋的变化无常,史前先民的生活安定与否常被海洋所左右。海洋在慷慨地给予他们食物的同时,也阻隔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更时常带来热带风暴、海啸等海洋灾害。因此,笔者认为,先民对于大河和海洋的态度是敬畏的,是惧怕的。在洪水来临之际,船是能够漂浮在水面上、拯救先民生命的重要工具,能够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带给人安心之感。因此,先民选择船棺葬,或是其他与船有关的葬俗的本意,不是因为“亲水”,相反,是“惧水”的体现。
弄清楚了这一点后,我们再站在“畏水”的视角下去看看长江流域的船棺崖葬,就能发现很多东西都说得通了。以往的学者认为“崖葬”是将亡者安置在离天空更近的地方,而天空是神明的居所。但这种说法对于为何要选择船棺则没有太强的说服力。笔者认为,如果从“畏水”的角度来看,崖葬的方式含有躲避洪水之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意味。当洪水灾害来临时,先民们往往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洪水的侵袭。这种记忆可能造成了后世的一种“尚高”思想。在排成队列时,以前为尊;在水平高度上,以高为尊。后世的宫殿与神庙建筑(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地点大型建筑基址)往往都是建造在较高的地方;封建君王与臣下相会时也总是喜欢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以充分显示自己的权威。长江流域的船棺崖葬可能正是这两方面的文化意蕴的结合:船棺是对史前洪水记忆的回顾和“崇船”观念的体现;而“崖葬”则体现了源自躲避洪水的“尚高”思想。这也就是为何要在崖葬中也选择船棺来作为葬具体原因。至于巴蜀、青海等地的船棺土葬,实际上也是对史前洪水的回顾和“畏水”情结的体现。
(二)船葬是先民“崇船”的观念的外化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来看,原始先民的交通工具其实有多种,除了靠水地区的舟船之外,还有骑马、驾车等多种出行方式,为何会选择船呢?笔者认为,先民对船的崇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洪水灾害来临时,船能够带领人们漂浮在水面上,躲避洪水灾害;二是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原始时代,船是不少地区先民们沟通外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三是舟船能够用来捕鱼、航运,乃至外出劫掠等,在不少地区起到了维持先民生计的作用。四是在不少地区的原始宗教中,都存在魂船与冥河的说法。这一点下文会详述。“畏水”和“崇船”同时存在于先民的观念之中,使得各地的先民不约而同地在丧葬仪式中使用了船作为棺椁、随葬品或象征物。
在东南亚及大洋洲一些地区,由于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岛屿之间被汪洋大海所阻隔,因此当地先民到达其他岛屿的旅程充满艰辛且极其危险。在他们往来迁徙的旅途中,舟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舟船的保护,使得他们在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上找到了一处栖身之所。所以当地先民对舟船充满了崇敬,进而认为舟船具有通灵和沟通生死两界的作用。
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的船葬方式是最为多样的,既包含了船棺火葬、船棺土葬,也包含了所葬舟船或者舟船的象征物。在维京墓葬的舟船刻画中,维京长船往往被描绘成满载人员与武器,全速前进,在巨浪上快速滑行的情景。[32]笔者认为,在维京人的精神信仰中,不仅仅是长船本身,船上所搭载的勇士与武器、乘风破浪的样态,都是他们所想要表现出来的重要部分。斯堪的纳维亚气候偏寒冷,农业生产无法满足民众的生活所需,因此乘长船航行至不列颠岛、西欧大陆等地打家劫舍或拓展殖民地,成为维京民族的重要生活来源。而船在维京人的航海活动中显然是不可替代的。舟船搭载勇士出海,满载战利品归来,是维京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因此,在墓葬中应用舟船,也显示了维京人对于船的崇拜,是舟船神圣性的体现。
(三)船葬是各地传说中“魂船”与“冥河”的反映
一部分学者提出,船棺葬是古代先民“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是要搭载亡者的灵魂前往某处。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具体是要搭载亡魂前往何处呢?学界对此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升天”[4],也有的说是“祖先的发源地”[6]等。在各地的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中,都出现了类似于“送魂之船”和分隔阴阳两界的“冥河”的意象的描绘。这可能是史前先民选择船葬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地的神话传说中皆有对死后世界的描绘。在这些描绘中,常出现冥河与舟船的身影。如中国古代认为人死后会踏上“黄泉路”,渡过“忘川”,也被称为“三途川”。两河流域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人死后将化作死灵携带供品(即随葬品)前往冥界。当死灵们前赴冥界时,必须横跨一条名为胡布尔(Hubur)的河流。若死灵未能满足特定的条件,将被这条河流所吞噬。在河上还有一位名叫Gilgames的驾驶魂船的船夫,负责摆渡死灵,并从他们那里取得报酬。[33]古埃及人也认为,太阳神每天日暮时分都会驾着太阳船,在赛特神的帮助下进入冥府,并穿过阴暗的冥界,与巨蟒进行搏斗,并在清晨从东方喷薄而出,日复一日。[34]北婆罗洲杜松族的原始萨满教信仰中,也将逝者死后的道路描绘为攀爬一座山峰和渡过一条河流。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的“逝者船”的丧葬习俗,认为这些船能将死者运送到天界。[35]
在世界各地的有关于死后世界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魂船”与“冥河”,这绝非偶然。在这些神话中,河流往往有两重作用:一是被视为生与死,即阳界与冥界的分界线,跨过了河流,就进入了冥界;二是冥河往往带有经历磨难与接受挑战的意味。亡者的魂魄或是需要花费一定力气,或是需要付出一定的财物代价,或是需要审判此世的善行与罪行,才能顺利通过这条冥河。
笔者认为,世界各地与“魂船”“冥河”相关的死后世界传说,也与史前先民经历的洪水灾害和“畏水”“崇船”的情结有关。因为洪水或海上风暴,使得先民在内心深处对大江大河和大海产生了畏惧之感,由此在神话传说中将跨过冥河视作了一种困难与挑战。此外,“崇船”的情结,使得先民在神话传说中构筑出了在冥河上的“魂船”形象。只有在“魂船”的帮助下,死者的亡魂才能够渡过冥河,前往最终的目的地。
四、从“畏水”与“崇船”的角度解释巴蜀地区的船棺葬
在对世界范围内船葬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初步研究后,我们得出了史前先民普遍存在“畏水”与“崇船”情结的结论。那么,如果把这条规律应用到巴蜀地区的船棺葬中去,或许可以对研究该地区船棺葬的精神文化内涵带来新的启示。
首先,巴蜀地区在盛行船棺葬的年代,也频发史前洪水。有气象学者的研究表明,因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逐渐恶化,成都平原地区在距今4.6-3.7ka BP之间以及3.2ka BP前后是成都平原的古洪水频发期,成都平原地区在这段时期内可能经常遭受洪水的侵袭。[36]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址,在宝墩文化二期至三期之间突然衰落,并伴随着文化面貌的改变,可能与史前洪水摧毁了宝墩文化二期的这些城址有关。此外,也能够见到许多古蜀先民修筑水利工程的遗迹和用于治水的工具。彭邦本认为,宝墩文化诸古城的城壕具有水利工程的性质;三星堆古城的高大城墙和城市布局显示出其水利技术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十二桥文化时期不仅发现了滨水的大型宫殿建筑群,而且还在指挥街遗址、方池街遗址等处发现了多条属于该时期的乱石埂,被认为是大型水利设施系统的一部分。[37]此外还出土了一批与治水相关的工具。其中有“杩槎”(用杆件扎制成支架,内压重物的河工构件,一般用来挡水,见于成都指挥街遗址[38])“竹编拦沙筐”(见于成都指挥街遗址,同上)等器物,并拥有“竹络笼石技术”(见于成都抚琴小区遗址[37])“砌筑卵石技术”(见于成都方池街遗址[39])等治水方法。[40]在文献记载上,也有古蜀君王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工程的记载,如汉扬雄《蜀王本纪》载“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41];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古蜀先王开明氏“决玉垒山以除水害”[42]等。由此可见,古气象学、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三者都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巴蜀地区在史前经历过大洪水的侵袭。因此,巴蜀先民自然而然地会有“畏水”的心态。
其次,巴蜀地区以船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特别是成都平原地区,自古以来河网密布,水草丰茂,适合渔猎经济的发展。船只在当地先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了三星堆-十二桥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的范围扩展到了渝东与鄂西地区,该地区的朝天嘴[43]、中堡岛[44]、路家河[45]、红花套[46]等遗址,皆带有三星堆文化的因素。而成都平原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通过驾驶舟船,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到达这些地区。因此,舟船不论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还是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古代巴蜀先民将舟船作为崇拜物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可见,古代的巴蜀地区,既存在史前洪水,又以船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和生计的依靠。笔者认为,在这些条件下,巴蜀先民可能产生了“畏水”与“崇船”的心态,并通过船棺葬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五、结语
通过对世界其他地区史前船葬的了解与研究,我们认为,在盛行船葬的地区中,很多都发生过史前洪水或者与水有关的自然灾害。而舟船在先民面对洪水灾害时为他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此外,使用舟船捕鱼、航运或劫掠,还是不少先民们的生计所在。因此,选择船作为葬具或随葬船,既是先民对于洪水记忆的残留,也是他们对陪伴着自己生产生活的船的致敬,体现了他们“畏水”与“崇船”的情结。此外,在世界各地有关逝者死后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多有“魂船”与“冥河”的相关情节,笔者认为这也源自先民“畏水”与“崇船”的情结。这些情结通过神话传说与史前宗教的方式,最终以船葬的方式被表现出来。世界船葬中的这些规律在巴蜀地区的船棺葬中同样适用。
〔参 考 文 献〕
[1]冯汉骥,杨有润,王家祐.四川古代的船棺葬[J].考古学报,1958(02):77-95+145-152.
[2]陈云洪.四川地区船棺葬的考古学观察[J].边疆考古研究,2015(01):241-268.
[3]娄雪.川渝地区早期舟船文化的考古学观察[J].中国港口,2017(S1):61-66.
[4]车广锦.论船棺的起源和船棺葬所反映的宗教意识[J].东南文化,1985(00):49-61.
[5]陈明芳.论船棺葬[J].东南文化,1991(01):23-31.
[6]段塔丽.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丧葬习俗——船棺葬及其民俗文化内涵[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01):119-124.
[7]刘芮伽.事死如事生——古蜀文化船棺葬的演变及文化内涵[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07):104-106.
[8]陈锽.魂舟·魂车·魂桥——图像中的灵魂信仰探讨之三[J].新美术,2018(09):4-27.
[9]梁钊韬.“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J].思想战线,1985(06):66-69.
[10]唐昌朴.从船棺葬俗考察巴蜀的族源[J].历史教学问题,1990(05):51-54.
[11]黄尚明.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J].江汉考古,2005(02):70-73.
[12]李子.船棺种族之属辩诬[J].武夷学院学报,2008(01):46-49.
[13]陈云洪.成都金沙遗址船棺葬的分析[J].南方民族考古,2014(00):45-59.
[14]雷雨.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J].四川文物,2006(06):17-23.
[15]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县文化馆.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0(06):12-20.
[16]曾凡,杨启成,傅尚节.关于武夷山船棺葬的调查和初步研究[J].文物,1980(06):21-31.
[17]朱天顺.原始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34.
[18]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柳湾[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88.
[19]苏瑞琪.从墓葬看甘青地区史前社会的等级分化[D].河南大学,2019:52.
[20]河北省文化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9(01):1-31.
[21]戴胜男.从东南亚与巴蜀地区的船棺葬窥探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J].财讯,2016(30):137.
[22]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2009(01):4-23.
[23] Tenazas, Rosa C. P. The Boat-coffin Burial Complex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ts Relation to Similar Practices Iin Southeast Asia[J].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973(01): 19-25.
[24] Moss, Rosalind Louisa Beaufort. The life after death in Ocean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 Milford, 1925:28-29.
[25] 王鲲.古埃及太阳船能否通往天国?[J]. 飞碟探索,2010(05):56.
[26] Julia Clare Francis Hamilton.Hedgehogs and Hedgehog-Head Boats in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in the Late 3rd Millennium BCE. Arts,2022(11):31.
[27] Dorian Vanhulle. Boat Symbolism in Pre- and Protodynastic Egypt (ca 4500-2600 B.C.): an Ethno-Archaeolog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Ancient Egyptian Interconnections, 2018:173-187.
[28] Else Roesdahl, Trans. Susan M. Margeson and Kirsten Williams.The Vikings[M]. London: Allen Lane and Penguin Press, 1991:165-166.
[29] Harris, O., Cobb, H., Batey, C., Montgomery, J., Beaumont, J., Gray, H.,Richardson, P. Assembling places and persons: A tenth-century Viking boat burial from Swordle Bay on the Ardnamurchan peninsula, western Scotland. Antiquity, 2017, 91(355):191-206.
[30] Andren, Anders.Doors to other worlds: Scandinavian death rituals in Gotlandic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Euro- pean archaeology, 1993(01): 33-56.
[31] 刘俊男.上古洪水来源及禹治洪水考[J].船山学刊,2001(01):63-66+20.
[32] Andreeff, Alexander 2012.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picture stone sites. In Herlin Karnell, Maria (Ed.) Got- land’s Picture Stones: Bearers of an Enigmatic Legacy[J]. Gotl?覿ndsktr Arkiv: 129-44.
[33]Annus, Amar. "Some otherworldly journeys in mesopotamian, jewish, mandaean and yezidi traditions"[J]. Studia Orientalia Electronica, 2009: 315-326.
[34]佚名.驶向“彼岸”的太阳船[J].大自然探索,2005(10):74-75.
[35]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段满福,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85.
[36]贾天骄.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以来地震与古洪水等事件环境考古研究[D].南京大学,2016:99-100.
[37]彭邦本.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87-96.
[38]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J].南方民族考古,1987:171-210+242-245.
[39]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方池街古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3(02):297-316+329-336.
[40]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74-276.
[41]全汉文.卷五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M].(清)严可均,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58:414.
[42]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18.
[43]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9(02):41-51.
[44]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7(01):45-97+132-139.
[45]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6]红花套考古发掘队.红花套遗址发掘报告[J].史前研究,1990-1991:309-317.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