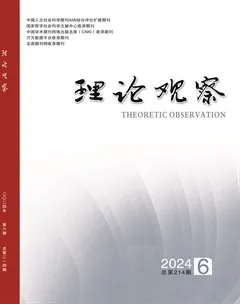安史战乱中的货币
摘 要:“乾元重宝”与“得壹元宝”分别是唐廷和燕政权在公元670年前后发行的两种货币。铸发“乾元重宝”是唐肃宗战时财政布局的货币表现,也是唐后期经济运行体制变革的发端。相较唐廷来讲,燕政权铸发“得壹元宝”似有模仿之嫌,但若是比物假事,燕政权更强调新生政权合法性的构建,而非经济层面的战略布局。
关键词:安史之乱;货币发行;战时货币;财政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K242.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6 — 0095 — 06
安史之乱自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范阳起兵,迄宝应二年史朝义林中自缢,前后持续七年有余。此战历来都被史学家痛诋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许多关于安史之乱的研究也由此判断展开。这种判断是站在唐廷这一正统王朝立场的先入之见,所得结论容易陷入旧式政治史范式的路子。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思路就是从特定事件的某个细节入手,或是战争态势,或是敌对双方人物构成等。析而论之,这种做法集中且深入,能够开启安史之乱研究的新视角,本文对战时政权货币发行的讨论就是这种新视角下的尝试。
一、乾元重宝的发行始末
(一)发行原因
在玄宗天宝九年(750),曾发生过一次“五星聚于尾、箕”[2]卷23·天文志三433的异常天象。安禄山起兵后,亦称应“四星聚尾”之相①。故此处安禄山所称的“四星聚尾”与玄宗年间的“五星聚集”应指同一天象。为起到号召作用,以“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11]270为谶言,大肆宣扬唐王朝气数已尽的舆论,以此来构建燕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反观唐廷,在战争的初期处于被动局面,唐军节节败退,唐玄宗出逃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即唐肃宗。肃宗从玄宗手中接过的是军事和舆论双重告急的唐王朝,故其所承担的就不止平定叛乱的军事使命,还有宣传李唐王朝天命未尽的政治使命。
安禄山政权在至德二年(757)出现了重大变化,正月,安庆绪杀死安禄山篡位称帝,但其难以服众,叛军凝聚力大大削弱。[1]卷150·列传3004九月,在回纥的帮助下,唐军攻克长安,收复潼关。[1]卷70·列传1921同年十月,收复洛阳。此时的唐肃宗终于能从危急存亡之秋的战争困境中走出来,分二分余力在国家建设方面了。
次年(758),唐肃宗对国家中枢体制、天文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3]65-67。肃宗连续密集的政治动作,是为更好地配合军事行动所部署的战时体制,也是为打碎“尾为燕分”的“谶言”,重塑李唐政权天命合法性所做的政治宣传。乾元重宝的发铸,便是这重大部署中的一环。乾元元年(758),第五锜升被唐肃宗提拔为“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2]卷149·列传第七十四1883。同年七月,肃宗便“铸当十大钱”[3]卷36·唐纪2774,并命名为“乾元重宝”[3]卷36·唐纪2774。
自南北朝以来,在朝代更替之时改制铸币就被赋予新生政权独有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普及民众对新政权高度认同的政治筹码。肃宗虽仍承李唐皇室的天命,但李唐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要想作出回击,夺回民心,肃宗必须展示出自己革故鼎新的形象。改元、改革、铸造新币,似有意将自己的统治与父亲玄宗的时代划开,塑造与玄宗朝不同的新气象。
肃宗发行乾元重宝,除了重塑李唐天命,是否还有别的考量?在乾元重宝发行之初,唐廷就明确指出铸造此币是为获得“十倍之利”[1]卷28·食货志上1194的收益,解决“三官之资”[1]卷28·食货志上1194告急的问题。那当时的肃宗究竟面临什么样的经济窘境?
第一,巨额战争消耗。
至德二年(757),燕政权仍旧占有七州六十余城,拥兵六万余众,彻底平定叛乱对于唐廷来说绝非朝夕之功。唐军虽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但肃宗为筹集兵力,一方面征调西北兵入援,一方面向回纥借兵,军资军费消耗巨大。肃宗外援回纥军平定叛乱,唐廷虽不负责回纥军的日常开销,但肃宗对待回纥的和亲政策和优厚接待规格尽显拉拢之意。为获得回纥的军事支持,肃宗将正在守寡的宁国公主转嫁给回纥可汗[3]卷36·唐纪2774,同时对回纥士兵的
赏赐也十分丰厚,如,唐军夺取洛阳后,肃宗“宣政
殿宴劳之”犒劳回纥军,赏赐其“锦绣缯彩金银器皿”[1]卷150·列传2905。
第二,财源枯竭。
安史之乱的交战区虽集中在中原地区,却因猝然生变,朝廷播迁,唐廷不得不停发或削减官员俸禄。这一举措直接导致很多地方政权停摆,当然行政系统内部的财政收支也随之紊乱。《资治通鉴》对这一现象有过生动的描述:在大历朝以前,各地方“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3]卷24·唐纪2851。地方政权没有了地方官吏的经营与维持,再加之战争的摧毁,肃宗时期在籍户数断崖式下跌。据杜佑对安史之乱前后课税人口的记录,由天宝十载(751)至乾元三年(760),唐廷所控制的在籍户数锐减,战争导致的伤亡、流亡使得政府损失近六百万在籍编户,课税人口耗减三百六十万[4]卷6·食货典200。如此看来,此时的唐廷正面临租庸调征收、调运困难的窘境。
面对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肃宗开始重用第五锜,布局战时经济政策。肃宗对第五锜的重用,引
得部分朝臣的不满。房琯上书弹劾第五锜为聚敛
之臣,认为第五锜同杨国忠一样都是“厚敛以怒天下”[6]卷10·厘革161,重用第五锜是“除一国忠用一国忠也。”[6]卷10·厘革161唐肃宗则反驳:如今天下危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6]卷10·厘革161,而你却“恶琦可也”,那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呢?[6]卷10·厘革161从肃宗“六军之命若倒悬然”的措辞,足可窥见唐廷筹措钱财之急迫。
(二)乾元重宝的生财之道
乾元重宝的铸发是否真正缓解了唐廷的经济压力?乾元元年(758)七月,第五锜奏请开铸乾元重宝,“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2]卷44·食货志四748。开元通宝每缗重六斤四两,在唐代每一缗为一千文,十文为一两,换算后每文重一钱(二铢四丝),折合现代的计量单位约4.25克①。此时乾元重宝每缗重10斤,10斤为160两、3840铢,折合每文约重3.84铢,折合质量约为6.8克,此处对单枚乾元重宝重量的推算与实际考古挖掘所得相近,证明铸造乾元重宝的原材料和工艺技术与开元通宝相近[18]91-93。按照天宝中“每贯钱用铜筑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4]卷9·食货志九223来计算,每文开元通宝的铸造成本为0.75文,每一克的铸造成本为0.1875文。若仅以克重差异来计铸造成本,每一文乾元重宝的铸造成本为1.2文(开元钱)。
杜佑在《通典》中曾详细记载了铸造开元钱的年度数值“约一岁计铸钱二十二万七千余贯文(当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引者)”,按照杜佑所载“百分之二十五”的耗损来算,开元钱的铸造成本为245025贯(326700×0.75=245025),获利为81675贯(326700×0.25=81675)。若丁匠效率和生产工艺不变,一年铸造乾元重宝同样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按照两者1:10的兑换比率,唐廷改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326700贯开元钱(326700×10=3267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1.2=392040)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年将增收2874960贯开元钱(3267000-392040=2874960),折每月增收239580贯开元钱(■=239580)。
乾元二年(759)三月“琦入为相”[1]卷28·食货志上1203,肃宗君臣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货币增值——“更铸重轮钱”[1]卷28·食货志上1203。第二次增发的货币继续沿用乾元的年号,另加“重轮”二字以示区分,二十斤为一贯,一贯即一千文,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为1:50。按照本文推算乾元钱铸造成本的思路,20斤为320两、6960铢,每文约重6.96铢,折合质量约为12.32克。此处所得的单枚乾元重宝重量的推算与实际考古挖掘所得相距甚远,现今出土的重轮钱平均克重在22g左右,这证明每一枚重轮钱的铜鑞锡比率要高于开元通宝,即重轮钱的实际铸造成本是远高开元和乾元的。如果在计算过程中,将丁匠成本忽略,仅以铜鑞锡比值差异来计铸造成本,实际铸造重轮钱的成本是推算铸造(或称铸造开元钱的铜鑞锡比值)的1.78(1+■=1.78)倍。由于重轮钱与开元钱克重相差过大,因此还应计算克重差异带来的成本差异,重轮钱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4.5(■=4.5)倍。综合两种差异成本,每一文重轮钱的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8.01倍(1.78×4.5=8.01)。
按推算乾元钱收益的思路来推算铸造重轮钱的收益,唐廷一年铸造开元钱“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成本为245025贯,能获利81675贯。若丁匠效率不变,一年铸造重轮钱同样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按照重轮与开元1:50的兑换比率,唐廷新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16335000贯开元钱(326700×50=16335000),除去392040贯开元
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
年将增收13718133贯开元钱(16335000-2616867=
13718133),平均每月约为1143178(■≈1143178)贯开元钱。
唐廷频繁的货币调整,人为导致市场中流通货币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多,在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多出来货币都作用在升腾物价上。在新币发行后,长安地区的“米斗至七千”[1]卷28·食货志上1203。反观安史之前的物价,天宝五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1]卷41·食货志一728。从天宝五年(746)至乾元二年(759),短短十多载,米价翻了近500余倍,故书中所载“饿死者相枕于道”便不足为奇了。
除了物价升腾外,乾元钱的发行还导致货币“私铸”盛行,时任京兆尹的郑叔清在几个月间逮捕的私铸钱之人高达八百多人[3]卷37·唐纪2786。沸腾的民怨、混乱的经济迫使肃宗做出让步。朝臣们将混乱的根源“归咎于琦”,第五锜事业受挫,“贬琦忠州长史”[3]卷37·唐纪2785。第五锜遭贬官,改革事业的主创者被放逐,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让当权者放弃从发行货币中获利。肃宗权衡了铸币与民生之间的利弊后做了些许让步,于上元元年(760)六月宣布将乾元重轮钱“减作三十文行用”[1]卷28·食货上1203,即将重轮钱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调为1:30,将开元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即是将乾元钱与开元钱平行流通。若上元年间发行的重轮钱与乾元年间的品质相似①,在调动兑换比率后,唐廷铸重轮钱的币值相当于9801000贯开元钱(326700×30=9801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此时唐廷铸造重轮钱一年仍能获益13718133贯开元钱(9801000-2616867=7184133),平均每月约为598677(■≈598677)贯开元钱。
肃宗的退让并没有平息事态,加之战争已经进入平稳期,继任的代宗迫于民间舆论最终决意将战时货币废除,在宝应元年(762)四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1]卷28·食货志上1203,第二次发行的重棱大钱则直接废除,“不在行用之限”[1]卷28·食货志上1203。自乾元元年七月始唐廷为获铸发货币之利弥战争之需,几经调整货币政策,至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彻底废除乾元重轮钱,至此,肃代两朝的货币调整终于落下帷幕。
若是将肃、代时期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串联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上的表格。假设唐廷九十九座铸钱炉在每一次政策变动后,其生产全部用于铸发新货种,那肃代两朝货币调整政策可为唐廷带来总计22873611贯开元钱的纯收益。高达两千三百万贯的收益对于战时体制的唐廷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先来推算唐廷在安史期间军费的支出。据杜佑《通典》所载,天宝年间唐廷的边防兵力总计49000员,马匹总计50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安史初期,除去安禄山所领三节度使兵力,唐廷实际掌控的兵力为252500员,马匹34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按照此数据推算,安史期间唐廷所能掌控的边兵总数相当于天宝年间边兵总数的60%(■≈0.6)。又据杜佑记载,天宝年间唐边兵每年的经费为“千二百十万”[4]卷172·州郡二1954。那么,安史之乱初期,唐廷每年边兵经费支出为7200000贯(12000000×60%=7200000)。如此算来,货币调整所增收的两千三百万贯收益可供唐廷维持三年多的边兵支出。
再来看官俸的支出。据史籍记载,唐廷京官在开元末年的年的收入为“一十五万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4]卷35·职官典546。外官的收入传统史料未见记载,根据陈明光先生推算,唐外官年禄的支出总额约为米九十七万余石,合全国外官内外官年禄支出共计一百二十万石米,折一千二百万斗米[14]81。由于唐代是“钱帛兼行”的流通方式,实物与钱帛并行流通。若按照前文所提天宝五年长安地区“米斗十三钱”的巨额物价来计算的话,唐廷所得的两千三百万贯收益可买米1769230770斗(■≈1769230770),即可供唐廷支付147年(■≈147)的官员俸禄。若按照乾元三年“米斗钱千五百”[2]卷25·五行二453的高额物价来算的话,所获收益可买15333333(■≈15333333)斗米,依旧可供应唐廷支付15个月(■×12≈15)的官俸。
(三)小结
房琯将第五锜归为“聚敛之臣”之言不假。但在战时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极端的货币政策又变得情有可原。乱世君主持续不断调整的货币政策,除了暴露在数条政权建设诏令中的政治打算,还有维系战争支出的经济考量。但是这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战时货币只能是“干戈未息,努藏犹虚”时期的权宜之计,其注定不能同开元通宝一样长久流通。
二、得壹元宝的初铸时间考辨
(一)初铸时间的争议
目前,关于得壹元宝的初铸时间的争议主要源于两处史籍的不同记载。《新唐书·逆臣传》的记载是:“乾元二年正月朔,筑坛,僣称大圣周王……夏四月,更国号大燕……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壹’钱。”[2]卷150·逆臣传上2743据《逆臣传》的记载可知得壹元宝应始铸于乾元二年(759)。而《资治通鉴》则记载:“乾元三年闰四己卯,赦天下,改元(上元元年)……是日,史思明入东京。六月,……亦铸顺天、得壹钱,一当开元钱百。”[3]卷37·唐纪2786《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上元元年六月才应该是得壹元宝始铸时间。
目前,多数学者将得壹元宝初铸时间认定为乾元二年①。但霍宏伟和廖子中两位老师在《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综论》一文中认为得壹钱的初铸时间应为上元元年六月[15]146。为此,两位老师从史料的角度出发,将原因主要归纳为如下两点:其一,他们认为在乾元二年九月之后,史思明进入洛阳成以后,“城空,无所得”[3]卷37·唐纪2783,又害怕李光弼断其后路,所以“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13]卷37·唐纪2783。其二,他们认为《实录》之所以在上元元年重复记载史思明入城,是因为“当时城空,李光弼在洛阳,思明还屯白马寺”[11]卷221·唐纪音注16555。通过梳理上述的原因,两位学者将史思明是否进入洛阳城与史思明能否铸发新钱等同,即固化了史思明不进入洛阳城就不可能铸造得壹钱这一逻辑,以至于对史料来源考辨,铸钱之动机与虚实都未能考虑。
除了学界对得壹元宝初铸时间的争议,《新唐书》内对于得壹钱初铸时间的记载也有抵牾之处。《新唐书·食货志》有载:史思明带领军队进入洛阳后,“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2]卷44·食货志四748,后又因为被人说“‘得壹’非常祚之兆”[2]卷44·食货志四748,所以将“得壹元宝”改名为“顺天元宝”。此段与《资治通鉴》都将初铸得壹元宝的时间定为史思明真正占领洛阳城后。若对比几处史源的成书时间,《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资治通鉴》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再对比三处关于得壹元宝的记载,《资治通鉴》对得壹钱币值、形制以及铸造时间的记载和《食货志》的表述高度一致,故《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应是选取了《食货志》的内容。如此看来,并非《资治通鉴》与《逆臣传》的记载有出入,而是《新唐书》中前后两部分的记载有出入。《新唐书》作为一套成体系的书,前后部分出现如此之大的抵牾之处,不合逻辑。
(二)初铸时间之再考
“亦”字之差。若是逐字对比这几处史料,便可发现新的线索。关于铸造得壹钱,《逆臣传》所载的是“铸”,《食货志》所载的则是“亦铸”,虽一字之差,意思却是大相径庭。“亦”在《辞海》有也、又、特、助词、通“奕”[8]五种义项。在此处应取前两种,“亦”若取“也”之义,应是承接上文肃宗“铸乾元重宝”这一举动,强调史思明在据东都后也新铸货币这一事实。但原文又在“亦铸”之后写明是得壹元宝,说明作者想表达的是“重铸得壹元宝”这一举动,而不仅仅是重铸货币。故此处取亦的“又”之义更合逻辑,即史思明在占据东都后又铸造了得壹元宝,这也就意味着在上元元年六月之前,就已经铸造过得壹钱了。
若是在上元元年六月之前铸造过得壹钱的这个推论成立,那是否就意味着得壹钱的初步铸造时间一定是乾元二年呢?那《食货志》与《逆臣传》的抵牾之处又应该如何解释?再回归到史料,《逆臣传》“乾元二年正月朔,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壹钱”的记载只是单纯地记录了铸造得壹钱这一行为。反观《食货志》则有对钱的形制以及币值的详细记载,如,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那么《逆臣传》与《食货志》的抵牾之处很可能是名义铸造与实际铸造的差异导致的。史籍中所载的铸造之“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名义铸造,一种是实际铸造。《逆臣传》所载“夏四月····铸‘顺天得壹钱’”为名义铸造,《资治通鉴》和《食货志》所载“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为实际铸造。
为支撑上述推论,可先剔除铸得壹钱的时间点,重新梳理史思明杀安庆绪后的时间线。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四月在范阳(今河北涿州)称帝,改元顺天。九月,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但未入洛阳城,暂屯白马寺。上元元年三月,史思明携军队进入洛阳城。《逆臣传》所载铸得壹钱的时间为乾元二年四月,即史思明范阳称帝时期,《食货志》和《资治通鉴》所载的铸钱时间为史思明据东都后即上元元年三月。因此,初铸时间的争论点应在范阳称帝和据东都之间,而非史思明是否入驻洛阳城。
据《旧唐书》记载,安禄山攻下两京以后经常用骆驼把“两京御府珍宝”运到范阳,而史思明镇守范阳期间,趁职务之便将这些财物全部据为己有。史思明击退唐军,杀入邺城以后,用安庆绪府库的钱财犒赏士兵,除了侵占财物外,安庆绪“先所有州、县及兵”[3]卷37·唐纪2779都归于史思明麾下。由此观之,史思明在范阳在称帝前,就已经继承了安氏父子的大部分资产,兵力和财力都十分殷实。因此,范阳铸钱诏令的主要用意绝不是扩充兵力和财力。与肃宗迫于军资的窘境相反,史思明称帝后则是将大燕政权合法性构建摆在首位。《安禄山事迹》中有载:“〔思明〕乃立宗庙社稷,谥祖考为皇帝,以妻辛氏为皇后,次子朝兴〔清〕为皇太子……置侍中、尚书令等官,立台省”[7]卷下110。这套政策是史思明为快速获得自身合法性而铺设的政治筹码。除了对安禄山、安庆绪的追葬以及没有铸造得壹元宝的记载外,《安禄山事迹》关于史思明成套国家建设政策的记录与《逆臣传》的内容非常相近。
从上述罗列可以看出,史思明在范阳称帝时期所铺设的政策涵盖宗庙祭祀、百官僚属、货币赋税等各个方面。在史思明的规划中,范阳期间的史氏政权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军事战略部署,而是新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史思明虽是安禄山和安庆绪的继任者,但安禄山军队中义子番将云集,政权两次更迭都是闪电政变而非礼法传承,大权在手的史思明要面临更多的潜在挑战。史思明想要将安氏政权平稳过渡为史氏政权,并非易事。亲身经历安氏政权兴亡的史思明深知单靠武力控制安禄山旧部不是长久之计,汉族官僚建议的“皇帝制度”或许是条可行之路。所以,对于范阳称帝时的史思明来说,铸币能否顺利流通并不要紧,铸钱的象征意义大于流通意义,以铸币为内容所牵连出的一整套皇帝制度的建设才是史思明的真义。
史思明在入驻洛阳后,情况就发生了转变。南宋洪遵所著的《泉志》曾记载:五代时期钱币学家张台认为得壹、顺天钱是“思明并销洛阳铜佛所铸”[10]卷4·违品上192,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这种钱就不能用了,于是处于战区的人们又将这些钱用来铸造佛像,现今剩下的钱存留于“伊、洛间甚多”[10]卷4·违品上192。张台的说法可与《食货志》中“亦铸造得壹顺天钱”的记载以及得壹钱顺天钱的考古出土情况相互印证。也就是说,从乾元二年的范阳称帝到上元元年六月的入驻洛阳,将近一年半的密集军事行动使得史思明财情告急,不得不通过销毁铜像、铸发大钱来筹集军资。
(三)小结
综合以上论述,基本可以认为“得壹元宝”的名义铸造时间为乾元二年四月,实际初铸要等到次年的三月了。《逆臣传》中所载“乾元二年正月朔”“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壹钱”是史思明政权建设中的一环,《食货志》和《资治通鉴》所载“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则是对史思明实际铸发行为的记载,三处的记载时间及逻辑关系顺通,并非记载失实。同时,史籍中关于得壹钱记载的失真之处不是铸造时间的出入,而是《逆臣传》和《资治通鉴》将得壹钱与顺天钱不分先后,统一一处,一概而论①。
对得壹钱铸造时间的考辨并非无用之功,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国家、战争这三者的关系。在范阳称帝之时,史思明急切地推行其皇帝制度的建设政策,做铸造得壹元宝此类的“太平之事”,并非头脑发热的冲动行为,而是改革安史旧部、培植史氏势力的重要部署,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在入东都之后,国家建设层面的安排在范阳时期基本完成,造炉铸币供军资的紧迫性就得以凸显。
三、结语
本文第二部分从得壹元宝初铸时间的考辨中梳理出其发行脉络,结合第一部分对于乾元重宝的讨论,会发现这两种货币都是战时政权的继任者发行的战时货币。在当下国际交往中,运用货币手段去控制战争态势、维持战争支出早已成为常用伎俩。而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对立政权的继任者们在战争状态下打响的货币战争,就已经包含了类似的洞察。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战争时期的历史,一方面显示的是战因、战势、战果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暗含着战时政权运转的关键要素。若将目光只聚焦于货币与战争的层面,很容易忽视国家在战争时期的主角地位,若是将国家带入货币与战争这对常规概念中,则会引导我们更全面理解三者的互动关系。
首先,货币服务于国家存续的各个阶段,在战争时期的货币有普及国家认同和维持战争支出的双重要义。唐肃宗和史思明发行的乾元钱和得壹钱,都是战时货币的性质,也都承担过政治宣传和军资来源这两大的历史任务,但两者选择货币为政治、军事工具的时间点有差异。唐肃宗自灵武即位至乾元年间的改革,潜伏两年,待政权成熟后,短期内将货币作为帝王更迭的宣传符号,长期则将货币看作是军事供养的工具。而史思明却在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就急于运作,其深意在于迅速建立权力认同,却也是安史政权短期内非正常更迭隐埋的祸患。
其次,在帝制时代,皇权掌握一切。政府掌握绝对的铸币权,战争潜力的上限就取决于铸币炉铸钱的速度,直到完全摧毁了货币的价值。健全的货币反而会限制政府资助军事的能力。[21]210战时货币政策之于经济如同饮鸩止渴。战时政权持续不断调整的货币政策,体现的是货币发行收益率、战争形势、民生忍耐度之间的反复博弈与较量,三者在来回的试探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肃、代时期的货币调整政策虽收放有度,有力地支持了唐廷平定叛乱,却也产生了“虚实钱”“钱重物轻”等货币乱象。
最后,就肃宗时期的货币调整来看,以货币资助军事这一决策并非偶然使之,而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国家财政运行变革的发端。肃代时期,唐廷巨额的军费支出倒逼国家财政以货币化为导向,长期的货币导向也使得逐利化渗透在国家运作的各个环节,唐后期官僚考核的理财化、中枢斗争焦点的财权化都是“发展经济”这一命题在晚唐国家治理中重要性提升的隐晦表达。
〔参 考 文 献〕
[1]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姚汝能.安禄山事迹[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陆费逵,等.辞海[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老子.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21.
[10]洪遵.泉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13]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J].人文杂志,2013(02):65-76.
[14]陈光明.官员俸禄支出计划[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15]霍宏伟,廖子中.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16]吴光华.晚唐的社会与文化[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17]王永生.三千年来谁铸币[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18]张满胜.最早的重宝钱—漫话唐代乾元重宝[J].东方收藏,2015(04):91-93.
[19]赛费迪安·阿莫斯.货币未来:从金本位到区块链[M].李志阔,张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