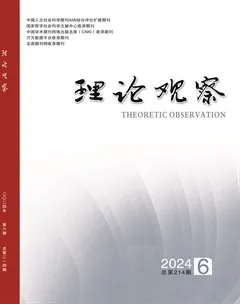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社会参与的渠道作用
摘 要:数字智能社会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可能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抑郁。本文以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数据为基础,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法、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抑郁的影响,并利用渠道分析法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抑郁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越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老年人简单交往型、健身锻炼型、组织团体型、助人奉献型社会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参与频率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间起着渠道作用;社会参与类型方面,简单交往型、健身锻炼型、组织团体型、助人奉献型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中均起着渠道作用。基于研究结论,从政府、上网设备制造行业以及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社会参与;抑郁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6 — 0076 — 11
一、引言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8.7%[1]。与上个十年相比,该年龄阶段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上升幅度则提高了2.51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24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1.1%,我国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可见,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战略。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指出“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增龄伴随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3],强调了我国老年人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隐含了提升老年人心理福利的指向。与之相呼应地,学界对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进行了重点探讨。受年龄增加带来的个人躯体功能下降、社会角色转变等冲击的影响,我国老年人群面临总体幸福体验低、睡眠问题突出、以及自尊水平总体不高等问题[4];且老年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地区及人群差异,经济不发达地区、女性、农村、学历低、无配偶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加不容乐观[5]。抑郁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衡量指标[6]。研究显示,抑郁在老年人群中高发[6],对老年人的身体、心理机能以及认知功能都将产生消极影响[6-7],抑郁情绪是老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重要预测因素[8]。由此可见,抑郁是老年人精神健康和生命质量的严重威胁,研究我国老年人抑郁问题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推动实现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人口老龄化态势日益严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坚持积极老龄化观念有助于牢牢掌握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先机和主动权。世卫组织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认为积极老龄化的目的是“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9-10]。从定义中不难发现,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包括健康、参与以及保障;此外,积极老龄化尤为强调老年人的主动参与意识和能动性,这提示研究者加强对社会参与的探究。既有研究从社会互动、角色归属、功能发挥等角度对社会参与的内涵进行了解读[11-13]。几个角度或聚焦老年人与他人保持联系、高度参与人际交往活动;或强调老年人在生产性及休闲活动中表现出有意义的社会角色;或突出老年人社会参与对他人及社会的贡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从相关学者对社会参与的界定中可以发现,社会参与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人社会资本、身份认同等起到关键作用。而就社会参与影响老年人抑郁这一议题,众多研究者作了讨论。大量的研究认为,社会参与与老年人抑郁间呈负相关关系,社会参与的频率、种类数量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抑郁[14],不同社会参与类型、模式对老年人抑郁会产生不同影响[15-16]。可见,社会参与与老年人抑郁有密切的关联,从社会参与视角切入探讨并缓解老年人抑郁问题必要且可行。
与此同时,伴随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更新,我国已经迈入数字、智能社会,互联网引发了巨大关注与热议,网民规模逐年攀升。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79亿,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比例达到13%[17],互联网愈发渗透进老年群体。与《报告》数据相呼应,诸多研究亦关注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影响。尽管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互联网使用给老年人健康、社交以及隐私带来的消极影响[18],但大多数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19]、降低老年群体的孤独感[20]、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21];同时,互联网使用还有助于老年人维系社交网络[22]、抑制社会隔离[22]、使老年人更加主动参与和融入社会[24]。综上,互联网使用或将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进而对老年人抑郁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本研究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智能化的双重背景下,以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为起始,以老年人抑郁为落脚,基于CHARLS2018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间的关系,并分析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抑郁之间发挥的渠道作用,为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参与与老年人抑郁
当前,国内围绕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开展的研究并不鲜见,但由于社会参与活动包罗万象,社会参与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学界就如何测量社会参与这一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因此不同研究者研究中的社会参与内涵不尽相同。总体来看,当前学界主要以是否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种类与频率、社会参与类型以及社会参与模式等形式对社会参与加以测量并讨论社会参与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社会参与测量方式的演变使得社会参与和老年人抑郁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参与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机制被愈发深入、细致地揭示出来。针对是否参与、参与的种类及频率等,相关研究发现社会活动参与越多、越频繁,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越低、抑郁情绪上升越慢[14][25]。而另外一些研究侧重探讨社会参与的类型、模式等对抑郁产生的影响。李月等(2020)指出,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因果效应[15]。另还有研究表明,相比低参与型和家庭中心型,个人中心型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相比低参与型的老年人,个人中心型显著降低了中龄老人的抑郁程度,家庭中心型和平衡型的低龄老人表现出了更高的抑郁概率[16]。这些研究结果都证明了在“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抑郁程度”[26-27]这一总体性、概括性、且受到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支持的结论的基础上,细化的社会参与类型起到了何种作用正愈加受到学者关注并获得了解。
由以上可知,社会参与是影响老年人抑郁的重要因素,是否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的种类多少、社会参与频率以及不同的社会参与类型、模式对老年人抑郁会产生不同影响。
(二)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参与
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的双重背景下,近年来学界对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参与之间关系的关注度逐渐上涨。关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学术界形成了两种观点。
扩大理论[28]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能够有效帮助老年人获得信息、增进社会资本、拓展社会网络、减轻社会隔离,进而促进老年人更好进行社会参与[23-24]。具体来看,上网频率越高,孤独感和孤立感越低。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与他人接触的数量越大、越容易,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增加老年人的社交联系[29]。互联网为老年人的日常交流、社会交往以及与外界的联系提供了在网络空间上的延伸,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更频繁多样的互动,减少了社交孤立,体验到强大的社会支持和紧密的社会联系[30]。还有学者探究了英国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电子邮件与社交孤立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发现与日常用户相比,每周或每月使用一次互联网/电子邮件的老年人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使用互联网/电子邮件少于每三个月一次的用户比每天使用的用户更容易被社会孤立[31]。
与“扩大理论”相对的“取代理论”则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获取信息、社交以及娱乐的路径,而鉴于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上网时间将会挤压原本投入到社区活动中去的时间,即使用互联网会降低与家人的沟通交流,社会交往规模会明显缩小,对互联网的使用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和由此产生的强关系,从而对个人的社会参与及心理健康产生负面效应[32]。另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降低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33],线上社交平台会削弱老年人的邻里交往,降低其社会参与水平[34]。
(三)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
当前学界针对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丰硕,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也获得了更高的关注。
互联网使用究竟是改善还是加剧了老年人抑郁症状?国内外研究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相关研究成果更强调互联网使用给老年人心理健康带来的显著福利效应,多数研究认为使用互联网能够降低应然层面老年人的抑郁患病风险和实然层面老年人的抑郁水平[35-36]。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更少抑郁,且使用频率越高、熟练程度越高、使用功能越多,其抑郁得分越低[37]。就具体内容来看,与在线正式生产活动(学习、工作)相比,在线非正式休闲活动(社交、娱乐)有助于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38]。还有些学者引入了中介、调节变量等,探究互联网使用会通过哪些变量影响老年人抑郁,进而得出相应作用机制。丁志宏等(2023)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社会网络支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在使用互联网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过程中,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是家庭网络[39]。
此外,也有少部分研究关注到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强度或频率的影响,认为过度的互联网使用及无意识、高频次、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的手机依赖、成瘾行为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40]。
结合文献回顾,对既有研究不足进行简要说明。第一,相关学者对互联网使用、社会参与及老年人抑郁三者中任意两者的关系讨论较为充分,但缺失将三者置于同一论题下讨论三者关系、尤其是将社会参与放置于中介或渠道变量位置的研究。第二,当前针对社会参与类型开展的研究仍然不足,在细分社会参与类型基础上探究不同社会参与类型对老年人抑郁会否产生不同影响以及不同社会参与类型在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和抑郁程度间是否都会起到中介或渠道作用的研究则更为有限。基于已有研究基础,同时为填补相关研究空白,本文以互联网使用为自变量、老年人抑郁为因变量、社会参与频率及类型为渠道变量,探究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抑郁的机制。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用的数据来自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8),其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首次开展,截至2018年共进行四次访问调查,其样本已覆盖总计1.24万户家庭中的1.9万名受访者。调查主要面向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家庭和个人展开,访问内容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收入消费等经济情况等。出于调查时序远近以及调查使用问卷内容与本文选取变量贴合程度两方面考虑,本研究选择CHARLS2018年数据,在剔除主要变量(社会参与、抑郁以及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和60岁以下的样本后,最终得到8167个满足要求的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取与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抑郁,CHARLS用于测量抑郁程度的工具是10条目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量表主要包含10个问题,受调查者需要回答过去一周内体验以下感受或具有以下症状的频率:(1)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2)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3)我感到情绪低落;(4)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5)我对未来充满希望;(6)我感到害怕;(7)我的睡眠不好;(8)我很愉快;(9)我感到孤独;(10)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上述问题的选项包括“1很少或根本没有”“2不太多”“3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4大多数的时间”。其中,问题5、8旨在测量老年人的正向感受,其余题目测量的是反向感受。在进行后续分析之前,先对两个正向感受问题进行反向赋值,再将所有题目得分加总,生成本研究因变量“老年人抑郁”。量表的总得分范围在10至40之间,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抑郁度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07,表明稳定性较高,可用于后续分析。
2.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互联网使用,以“互联网使用频率”作为衡量指标。CHARLS2018问卷中与互联网使用频率相关的题目有两道,分别是“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上网活动”以及“您过去一个月上网活动的频率”,其中前者的选项为“是”和“否”,后者的选项则包括“1差不多每天”“2差不多每周”“3不经常”。两道题目的作答逻辑为如果“过去一个月进行上网活动”即转入上网频率题目并作答;而如果“过去一个月未进行上网活动”,上网频率题目则会被记录为缺失值。本研究按照以上逻辑,将上网频率题目中缺失值替换为“0”,同时为更加便利地观察和分析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参与及抑郁的关系将上网频率题目得分进行反向赋值,由此结合两道问卷题目形成了“互联网使用频率”指标,指标得分越高代表互联网使用越频繁。
3.渠道变量
本研究的渠道变量是社会参与,具体构建了社会参与类型和社会参与频率两个分指标。
社会参与题项选取及类型划分方面,本研究参考李月等(2020)[15]及赵忻怡等(2022)[41]对社会参与变量的操作化,选取(1)串门及和朋友交往;(2)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3)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邻居提供帮助;(4)跳舞、健身、练气功等;(5)参加社团组织活动;(6)参加志愿者活动或慈善活动;(7)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8)上学或参加培训课程8项活动作为社会参与的测量题项,并参考李月等(2020)的研究将社会参与划分为简单交往型、健身锻炼型、组织团体型、智力参与型以及助人奉献型五个类型[15],其中活动(1)为简单交往型社会参与、(4)为健身锻炼型社会参与、(5)为组织团体型社会参与、(2)和(8)为智力参与型社会参与、(3)(6)和(7)为助人奉献型社会参与。受调查者过去一个月若进行相应活动则认为其具有该类型社会参与,五类社会参与均为二分类变量,参与为“1”,否则为“0”。
社会参与频率方面,在依据社会参与类型选取社会参与测量题项的基础上,计算生成社会参与频率指标,这一指标与学界普遍采用的社会参与操作化界定相一致,本研究构建这一指标是为了更好地同已有研究进行对比与对话。CHARLS2018问卷就社会参与频率题目设置了“1差不多每天”“2差不多每周”“3不经常”3个选项,结合是否参与活动和参与活动频率两道题目并出于便利后续分析的考虑,将每项活动得分处理为“0不参与”“1不经常”“2差不多每周”“3差不多每天”。参考赵忻怡等(2022)衡量社会参与程度的方式[41],本研究将社会参与的8项活动频率加总作为社会参与频率变量,8项活动总分在0-24范围内,得分越高表示社会参与越积极。值得说明的是,由于社会参与频率变量总分受到老年人参加的活动种类数量和参加每一类活动的频率决定,所以社会参与频率变量实际上也具有社会参与种类数量的意义。
4.控制变量
依据既往研究和本研究的需要,本文还设置了若干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点、婚姻状况、养老金获取情况、最高受教育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家庭月支出。具体来看,研究将受访者的性别(男= 0,女= 1)、婚姻状况(非在婚= 0,在婚= 1)、居住地点(农村= 0,城市= 1)、养老金获取情况(未获取= 0,获取= 1)处理为虚拟变量,年龄依据受访者的出生年份和调查年份计算得到,最高受教育水平设置为五分类变量(未受过教育=1,未读完小学= 2,小学文化= 3,初中文化= 4,高中及以上文化= 5)。为避免个别极端值影响、缩小数据间的绝对差异,将家庭月支出取对数处理,个人的健康自评包含从1至5的“很不好”到“很好”五个取值。
所有变量的定义、取值及分布特征可见于表1。
(三)分析工具及方法
本文全程分析均依托Stata17.0软件进行,渠道分析法是本文的核心方法。
相关研究将渠道变量定义为“受自变量影响或决定转而会影响因变量的变量”[42]。本研究参照相关研究做法[43][42][44],先对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影响因变量老年人抑郁的回归系数 (可见于方程1)进行计算,随后将渠道变量加入回归方程,重新计算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回归系数 (可见于方程2),最后对比两个回归系数并计算渠道变量在解释自变量影响因变量中所起到的渠道作用大小。本研究中如何使用该方法具体可见下:
首先构建方程1,用于检验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对因变量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Di=?琢0+?琢1Interneti+Xi?酌+?滋i(1)
在本方程中,Di代表个体i的抑郁程度,Interneti代表个体i的互联网使用情况,Xi是本研究选取的个体性别、年龄、居住地点、婚姻状况、养老金获取情况、最高受教育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及家庭月支出等控制变量,?滋i是随机扰动项。在对各控制变量加以控制后,?琢1可被看作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对因变量老年人抑郁的简化效应,其既包括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直接效应,也包括互联网使用通过各渠道变量对老年人抑郁的间接效应。
其次构建方程2,方程2在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渠道变量Ci,以探究互联网使用如何通过各渠道变量影响老年人抑郁。
Di=?茁0+?茁1Interneti+X1i?酌+Ci?浊+?滋i(2)
在方程2中,渠道变量Ci指的是受互联网使用影响从而影响老年人抑郁的变量,具体包括社会参与频率及社会参与各个类型。
在计算得出 和 后,1- / 即为渠道变量在解释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作用中所占的比重[43][42][4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表2展示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回归结果。模型1、2、3均以老年人抑郁为因变量。其中,模型1仅纳入自变量互联网使用,模型2仅纳入控制变量,模型3同时纳入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比模型1、2、3,发现模型3与模型1、2在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方面均无明显差异,仅回归系数数值有细微变化。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模型3。
首先,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老年人抑郁水平越低。模型3显示,互联网使用在1%水平上负向预测了老年人抑郁得分,互联网使用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老年人抑郁得分将下降0.302个单位,相应地,其抑郁水平也将下降0.302个单位。因此,可以认为互联网使用频率的上升将起到抑制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作用。此外,对比模型1和模型3,可以发现相比于模型1,模型3中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有明显下降,这说明研究设置的控制变量在解释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抑郁中同样发挥了作用。
其次,本研究中全部控制变量均显著影响老年人抑郁。性别方面,与男性相比,女性抑郁程度更高。年龄方面,如模型2、3所示,年龄对老年人抑郁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受调查老年人年龄与其抑郁程度显著负相关,老年人年龄越大抑郁水平越低。居住地点方面,相较于居住于城市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抑郁得分更高、程度更深,这与大量既有研究结论相同[45],表明居住地点是老年人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婚姻状态方面,与非在婚老人相比,在婚老人的抑郁程度更低,这表示配偶对老年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养老金获取方面,获取养老金与老年人抑郁水平间呈显著正相关。最高受教育水平方面,老年人最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抑郁度越低,这反映出教育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积极效应。自评健康方面,自评健康越好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越低,这表明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加剧老年人抑郁情绪。家庭月支出方面,家庭月支出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抑郁,即家庭每月支出越多,老年人抑郁程度越低。
(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在验证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抑郁间的渠道作用之前,还需先验证互联网使用对渠道变量社会参与具有影响,这样渠道作用才有意义。基于以上逻辑,本部分以渠道变量社会参与频率、社会参与类型为因变量,以互联网使用为自变量,控制好相关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老年人社会参与越频繁。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将上升0.372个单位。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支持了“扩大理论”,研究认为互联网作为老年人与外界沟通交流的窗口,起到了便利老年人社会参与、促进其社会融合的作用。
表3还展示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五个类型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智力参与型社会参与外,互联网使用对其他四个类型的社会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首先,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老年人简单交往型社会参与倾向越明显。本研究使用互联网的609名老人有553名利用手机上网,手机中微信app及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等双向互动工具有助于老年人建立并维系个人社会网络,产生社会资本[19][22],进而增进其简单交往型社会参与。
其次,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越有助于老年人参与健身锻炼型活动。这与李立清等(2022)研究结论相反[46],与王世强等(2021)研究结论相一致[47]。李立清等(2021)认为,互联网使用挤占了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从而对其体育锻炼时间、频率产生了抑制作用。王世强等(2021)则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够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多信息资讯,促进其学习,从而对其健身锻炼强度与频率产生正向影响。本研究认为,使用互联网可能使得老年人价值观念、对体育运动的看法发生一定变化,进而影响到其健身锻炼行为。
最后,随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老年人愈加倾向于参加组织团体型和助人奉献型活动。这或许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正如互联网使用正向影响老年人简单交往型社会参与的可能机制,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与他人沟通,这增加了其参加各类活动的可能。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类app的使用,老年人可能对组织团体活动相关信息(社团、社团所组织的活动以及本地有哪些社团等)和助人奉献活动相关信息(助人奉献活动的形式、对象;捐助人所需达到的标准和完成捐助活动后对个人的奖励;本地举办的助人奉献活动等)有了更加广泛深入的了解,这对其投身于相应活动有助推作用,使其相较从前在心理层面更愿意或在行为层面更多参与到相关活动中去。
综上可见,互联网使用无论是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频率还是几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均有积极作用,对老年人积极老龄化、释放自身内在潜能、实现“老有所为”大有帮助。同时,老年人群增加对互联网的使用一方面有助于老人自身更加充分地融入现代数字社会;另一方面,将更多老年人纳入互联网用户队伍对数字社会朝更加完善、包容方向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是可以尝试的缓解数字非正义、不平等的一条路径。
(三)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抑郁:社会参与的渠道作用
在前文对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及相关渠道变量的影响进行验证的基础上,本部分主要探讨渠道变量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之间的作用。表4呈现了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抑郁的渠道分析结果。
在对渠道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前,先对表4进行简要介绍。表4中模型4至模型9是在表2中模型3基础上依次加入单个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表4中最后一行为,其数学含义是加入渠道变量后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对因变量老年人抑郁回归系数的下降幅度,代表着渠道变量所起到的作用大小。
模型4展示了社会参与频率的渠道作用。在模型4中,社会参与频率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负向显著,这表示社会参与频率负向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社会参与越频繁,老年人抑郁水平越低。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回归系数同样为负,结合表3中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的回归系数(0.372,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示互联网使用通过正向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进而负向影响老年人抑郁,因此可以认为社会参与频率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间的渠道变量。此外,将模型4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0.235,在5%水平上显著)与表2中模型3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0.302,在1%水平上显著)作对比,可以发现系数的绝对值变小,显著性水平也有所降低,这表示渠道变量社会参与频率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间发挥了作用,其在解释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中约占22.2%的比重。
在对社会参与频率的渠道作用加以验证后,验证社会参与类型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之间是否发挥渠道作用。模型5至9展示了5个社会参与类型的渠道作用。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老年人参加简单交往型、健身锻炼型、组织团体型、智力参与型以及助人奉献型活动进而对老年人抑郁度产生影响。但由于表3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智力参与型社会参与”并无显著影响,因此“智力参与型社会参与”的渠道作用不存在,故其不是渠道变量。而模型5至9中除智力参与外的各类型社会参与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均显著,这代表4个社会参与类型均为有效的渠道变量。还需关注的是,4个社会参与类型对老年人抑郁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这表示它们都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抑郁,参与这4类活动越多,老年人的抑郁水平相应越低。
表4还展示了4个社会参与类型在解释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的负向影响中发挥的渠道作用大小。可以发现,简单交往型、健身锻炼型、组织团体型、助人奉献型社会参与依次分别能够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5.3%、11.3%、5.6%和6.0%,其中健身锻炼型社会参与解释力最强。
五、结论讨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CHARLS2018数据,对互联网使用、社会参与及老年人抑郁三者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具体来看,互联网使用的频率对老年人抑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既有的多项研究结论相符[35-36],也再次证明了互联网之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福利效应。
第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有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互联网使用频率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老年人上网越频繁,其参与社会活动的种类越多、参与频率越高。第二条路径是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几个类型具有积极作用。使用互联网对老人简单交往型、健身锻炼型、组织团体型、助人奉献型几类社会参与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表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实现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以及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后果有重要作用。
第三,社会参与是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抑郁的重要渠道,多种社会参与类型在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抑郁的传导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证分析部分显示,社会参与频率和4个社会参与类型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中均发挥着渠道作用。赋权理论认为,赋权的对象属于弱势群体,其与信息沟通和人际交流密不可分[48],这与本研究中互联网使用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结论具有相似的内涵。活动理论则认为,相较于没有活动力的老人,有活动力的老人更容易对社会感到满意[49],这一观点则为解释本研究中社会参与显著抑制了老年人抑郁水平的结论提供了依据。以上两个理论与本研究所探究的主题以及最终得出的结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托;反过来看,本研究的结论则验证了在探究互联网使用、社会参与与老年人抑郁关系议题时赋权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就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参与及老年人抑郁关系方面的发现还与前文文献回顾部分提及的多项研究有所呼应,本研究与这些研究共同佐证了互联网使用、社会参与对改善老年人抑郁状况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面向政府、上网设备制造行业以及家庭与个人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各级政府要及时、严格落实国家关于设施适老化改造的政策法规,加快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为老年人创造安全、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在适老化改造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还需加强对老年人的宣传和引导,帮助其树立起合理的网络观,让互联网成为其与家人、朋友沟通交往的有效工具、为其生活工作赋权增能,助力老年人更好融入社会。第二,上网设备制造业需要进一步提升设备的适老化程度。具体来说,可以在字体大小、界面、功能、操作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研发并推出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上网设备,增进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趣味性、易用性、感知有用性,降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门槛,使更多老年人借助互联网增加社会参与,缓解抑郁情绪。第三,老年人个人应利用好政府、设备制造行业及家庭成员营造的有利于其学习使用互联网的环境,有意识地转变自身态度,提升互联网使用能力和媒介素养水平。家庭成员也应利用网络与老年人积极交流,在老年人出现困惑或产生抗拒心理时为其讲解互联网如何使用、帮助其破除对网络的恐惧心态,做好“数字反哺”。要以老年人个人和家庭的合力助推老年人更加顺畅地使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参与更多社会活动,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首页-数据-普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EB/OL].[2024-01-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王萍萍:人口总量有所下降 人口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EB/OL].[2024-01-18].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401/t20240118_1946711.html.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通知[EB/OL].[2022-02
-07].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01/content_5676342.htm.
[4]何艳丽,张瑞星.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现状及服务模式分析与思考——以河南省调查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8,26(09):89-93.
[5]许金鹏,康正,王海鑫,等.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与社会,2022,35(12):85-92.
[6]唐丹.城乡因素在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模型中的调节效应[J].人口研究,2010,34(03):53-63.
[7]陈昕,赵鹤亮.中国社区中老年人抑郁情绪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
(04):971-973.
[8]成媛媛,王越,刘学,等.老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及相关因素研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5,24(11):1005-1007.
[9]世界卫生组织.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项目-老龄化与健康报告[EB/OL].[2002-04-29].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82323/ca5517a1.pdf sequence=1.
[10]世界卫生组织.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项目-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关于实施情况的报告[EB/OL].[2005-04-14].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58/A58_19-ch.pdf.
[11]Bassuk SS, Glass TA, and Berkman LF.Social Disengagement and Incident Cognitive Decline in Community dwelling Elderly Persons[J].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1999(03):165-173.
[12]Glass TA, De Leon CF, Bassuk SS, and Berkman LF.. Social Engagemen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Late Life: Longitudinal Findings[J].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006(04): 604-628.
[13]Jason LA. .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Genera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J].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 Practice, 2006(02): 132-139.
[14]苏镜安,李岩,张敏强,等.老年人抑郁情绪发展轨迹及社会参与的作用:空巢与非空巢老人的对比研究[J].心理科学,2022,45(03):740-746.
[15]李月,陆杰华,成前,等.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与抑郁的关系探究[J].人口与发展,2020,26(03):86-97.
[16]何文炯,张雪,刘来泽.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J].治理研究,2022,38(05):12-24+124-125.
[1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2023-08-28.
[18]武宜娟.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的网络参与[J].学术交流,2021,326(05):141-155.
[19]贺建平,黄肖肖.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以社会资本为中介[J].新闻界,2020(08):57-66.
[20]宋士杰,宋小康,赵宇翔,等.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人孤独感缓解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9,185(01):63-69.
[21]赵建国,刘子琼.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20, 200(05):14-26+126.
[22]黄荣贵,骆天珏,桂勇.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项基于上网活动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13, 283(01):227-233.
[23]倪晨旭,王震.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J].人口学刊,2022,44(03):59-72.
[24]靳永爱,赵梦晗.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9,41(06):44-55.
[25]杜希望.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与多层面视角[D].华中科技大学,2022.
[26]Chiao C, Weng L J, Botticello A L.. Social participation reduces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
er adults: an 18-year longitudinal analysis in Taiwan[J]. BMC Public Health, 2011,11(01): 1-9.
[27]Okura M, Ogita M, Yamamoto M, et al. More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less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in Japanese older adults irrespective of physical frailty[J]. European Geriatric Medicine, 2014(05): S114.
[28]和红,闫辰聿.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隔离”还是“融入”[J].人口学刊,2022,44(02):72-84.
[29]Cotten, S.R., Anderson, W.N., & Mccullough,
B.M. The impact of ICT use on loneliness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among older adults[J].Gerontechnology, 2012(11): 161.
[30]Heo, J., Chun, S., Lee, S., Lee, K. H., & Kim,
J. Internet Use and Well-Being in Older Adults[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5,18(05): 268-272.
[31]Stockwell, S., Stubbs, B., Jackson, S.E., Fisher, A., Yang, L., & Smith, L. Internet use,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in older adults[J].Ageing and Society, 2020,41: 2723 - 2746.
[32]Kraut R, Patterson M, Lundmark V, et al.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09): 1017-1031.
[33]Gilleard C,Hyde M,Higgs P.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Third Age:The Impact of Internet and Cell Phone Use on Attachment to Place in Later Life in England[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7(04): 276-283.
[34]Hage E, Wortmann H, Offenbeek M V, et al. The Dual Impact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on Older Adults’Social Conectivity[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 2016,29(01): 31-50.
[35]Guo, H., Feng, S., & Liu, Z. The temperature of internet: Internet use and depress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J].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2(10).
[36]翟亚,尹文强,李万鹏,等.中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现状及其对抑郁症状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2023,39(03):365-369.
[37]杜鹏,马琦峰,和瑾,等.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教育的调节作用分析[J].西北人口,2023,44(02):1-13.
[38]杨梦瑶,李知一,李黎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基于两级数字不平等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22,28(06):132-147.
[39]丁志宏,王妍.使用互联网会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吗?[J].兰州学刊,2023,353(02):148-160.
[40]段玉珍,吕欣.“银发族”手机依赖行为探因及应对[J].传媒,2020,326(09):91-93.
[41]赵忻怡,韩啸,梁兴堃.老年群体微信使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J].情报科学,2022,40(10):82-89.
[42]程令国,张晔,沈可.教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来自中国老年人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5,14(01):305-330.
[43]Cutler D M,Lleras -Muney A.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health behaviors by education[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0,29(01): 1-28.
[44]刘利鸽,刘红升.特色农业发展与农村老人抑郁:代际关系的渠道作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04):201-212.
[45]冉晓醒,胡宏伟.城乡差异、数字鸿沟与老年健康不平等[J].人口学刊,2022,44(03):46-58.
[46]李立清,丁海峰.互联网使用、闲暇时间与农村居民体育锻炼——基于2018年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兰州学刊,2022(04):108-122.
[47]王世强,郭凯林,吕万刚.互联网使用会促进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吗?——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1,35(05):62-70.
[48]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76-81.
[49]〔美〕N.R.霍曼, H.A.基亚克.社会老年学——多学科展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66-68.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