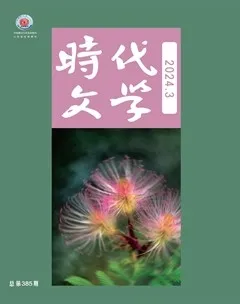我的年
我总以为,过年是因为一生太长了,长到看不见尽头,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就用年把日子截断。就像用镰刀割麦子,毒日头底下,弯腰埋头割了半晌,抬头看看还不见边际,浑身的劲立马就泄了,镰刀挥起来有千斤重。要是地块小,一弯腰一抬头,就要割完了,浑身的劲像风吹过来,立马膨胀了,轻快欢悦地割完一块又一块地。
过年又是因为人生太短了,从呱呱坠地到垂垂暮年,短到一眼就看见头,直白得没有一点风景。人们就用年把日子截断,像园林里的隔断,“有墙壁隔着,有廊子界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一年一年摞起来,人生仿佛就丰富了。
依了生命的长度,切割出数量不等的年。年年岁岁有相似,岁岁年年又不同,成其为每个人的一生。
我回望自己大半生被年切割过的日子。
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农村过的年,大都是物资匮乏的年代。
我父母的意思是孩子跟着他们一年到头没享什么福,苦倒是吃了不少,过年了,就竭尽所能让孩子们高兴。年三十上午,不论买几斤肉,母亲总是用十三印的大锅烧火煮肉,腾腾热气和肉香从做饭的小棚子里钻出来,氤氲着,弥漫着,把家里家外的空气熏成年三十才有的味道。父亲拿个大盆盛肉和肉骨头,把大盆装得满满当当,快步往屋里走去。早等得心急火燎的姊妹仨像鸡雏跟了老母鸡,颠颠地跟在后面跑了去。这顿肉不能放开吃,父亲看见哪个孩子还眼巴巴的,就又撕了肉往他嘴里塞去。
除了吃到肉,过年这两天,孩子都可以不用干活。吃罢肉的下午,无限满足地跑出去疯玩了。母亲和父亲就一直在忙年。父亲在天井里,把一年来攒下的木头用洋镐劈了,晚上熬五更,在屋里点起火盆取暖。燃烧完的木柴华丽转身,变成红红的木炭,父亲就把两根长铁筷子担在火盆上,烤出酥脆焦黄的馒头片,每个孩子都得吃,说是五更里吃了一年不生病。
我的父母,用他们的慈爱和温暖遮盖了贫穷,在我的年里留下浓浓的肉香,我的年里跳动着红彤彤的木炭火,温暖我一生。
有了女儿,渐渐习惯在婆家过年。在婆家过的年,更是热闹,盛腾。
年三十这天, 兄弟三个带了妻儿从城里的小家赶往山村的老家。婆婆特意用大锅烧柴火煮腿骨。这种伴着烟熏火燎之气煮的腿骨格外香。婆婆带着满身的柴草屑刚走出低矮的灶间,二哥就带了家什进去,一会儿,被热腾腾的肉香包绕着端了一大盆肉骨头出来。天井里早放好了桌子,二哥刚放下盆,好几只手已经伸了过去。站着的,蹲着的,嘴里咝咝哈着气,互相看看彼此不雅的吃相,笑声溢出天井。
只要不是冷得厉害,吃罢午饭,我们就在天井里摆开阵势。大哥带了孩子们打扫卫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孩子们干着干着就围着电视机边看边闹。二哥是主厨,边算计晚上的菜品,边做准备。三哥,我的爱人,自相识以来,我总是称呼他为“三哥”,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改变。三哥在家是老小,不论爹娘还是哥嫂眼里,他都是比孩子们大一点的孩子,他没有自己专职干的活。谁喊他他也应声,他就像个陀螺似的店小二,哪里需要就转到哪里。我们妯娌仨洗刷十一口人同时用的锅碗瓢盆,剁肉馅剁素馅,炸春芽炸带鱼,各有其职,忙而不乱。公公婆婆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看看这个笑笑,看看那个笑笑。
晚上吃年夜饭,觥筹交错猜拳行令,春晚往往成了下酒菜肴。
吃完团圆饭,我们六个齐下手,包完新年早晨的第一顿素馅饺子,点响炮仗,“爆竹声中一岁除”,仿佛生活的不如意真的连同旧岁一块去了。人们用这种形式表达着生命中一个个美好的愿望。
在婆家过年,祖孙三代,十一口子人,从年三十直闹腾到大年初二,每人都像卸完了车又加满了油,带着这股热闹劲儿各自回小家,奔向又一年的新生活。
可腾腾热火,说灭就灭了。公婆再也不长年轮,没有了爹娘的家,只是一所宅院,在空荡荡的年里破败下来。我曾渴望在一场盛大的烟花中过年,也曾向往在年里走向千里江山。那是我想要的不同凡响的年。年过半百,咀嚼起爹娘健在时家里那些令我厌烦的不变年事,却像父亲点在五更里的火盆。或许,正是这些看似一成不变的规矩里,延续着生命的律动。
老人变成了桌子上的牌位,让我看到自己的去处,也让我看到自己的来处。在乡村,因农事,据农时,创年立节,蕴蓄希望和祝福。也许我们的祖先明白,日子不是无限延长的,它随时随地会断掉。凡生命皆如此。三哥就突然和我毁约,把我的年变成了年关。
今晚又是年。
我在城里沿袭了乡村的年俗,我的家堂桌上摆了三哥的牌位。他刚过半百,我不能让他和公婆平坐在一起。我说服了所有的亲人,让我改一改规矩,我请三哥一个人回家过年。
我把三哥的遗像拿出来,立在桌上。我揣着三哥的照片去赶年集,看见往年我们在年集里拉着小车子挤来挤去,边说边笑。现在年集还是红火热闹。火红的热闹中,我感受着自己一点点被冻成一坨冰,寒冷向四周辐射开来,我咬紧牙,坚定地走向热闹的深处。
年三十中午,我也煮骨头。不忘给三哥放一小碟蒜泥。我想也许他能闻到我终于又把我们的家炸出了浓浓的年味。
我一点点擦拭他的遗像,像过年给他穿起我精心做的新衣。我对着三哥举杯,和三哥过他走后的第二个年。
吃罢年夜饭,我不看春晚,把琴对着三哥放下,低眉信手轻轻弹奏,我想让三哥从我的琴声里,看见我活着的样子。
我熬五更。我揽三哥照片在怀,坐在母亲给我缝制的蒲墩上,靠在暖气片上,细细碎碎地和他诉说我这一年琐琐屑屑的日子。
这是我和三哥的年。俗套的年事里,我要让三哥看着我一点点站起来。
我和三哥的年,已无关迎新除旧,已无关日月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