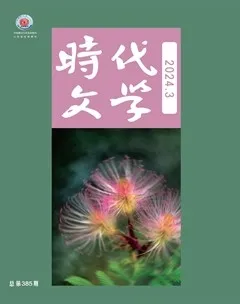新生
待产病房里,陪护家属们你一言我一语,低声闲聊着,一位眉眼俊秀的小护士急匆匆推开门说:“14床,去检查;16床,准备一下。”16床正是我。
我确实需要准备一下,因为这时的我像一只大熊猫,需要爱人扶起来才能下床,自己连只鞋子都穿不上。又一次慢慢挪进产检室,吃力地爬上冰冷的产床,医生检查的结果是:没开骨缝。这是我第三次上产床,第三次原样下来。见我又回来了,婆婆叹了口气,又用哄孩子似的口吻说:“快再吃点东西吧,生的时候有力气啊!”我接过姐姐买来的油饼,吃了两口,全部吐了出来。我大哭起来,不想生了,要回家。爱人不敢吱声,婆婆悄悄嘀咕着:“女人都要过这一关,哪有不生的道理!”眼看着病房里越来越暗,太阳照进病房的影子扁成了一条线,一天又要过去了。我的主治医生一阵风般地来到病房,嗓门提高了八度:“这么说吧,门小人大,能出去吗?”这是位身材高大的女医生,走路虎虎生风,说话的声音能瞬时填满整个病房。她快速走近我,从镜片后瞥了一眼我的肚子,做了一个往外挤的动作,说:“考虑考虑剖腹产吧!”说完,打开门,又一阵风般去别的病房了。
我妥协了,决定做剖宫手术。
天哪,在医生的“威逼”下,我脱下病号服,突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原来是位男麻醉医生正端坐在手术床前,我脑子里轰的一声,慌慌张张抓衣服遮身体,但所有衣服已递到室外。我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遭白晃晃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撕咬我的身子,皮肉像被刀片旋一样疼,我感到了巨大的羞辱,我痛彻地体会到人的弱小和无助。那一刻我好像晕过去了,等我稍稍清醒一点,本能地去捂自己赤裸的身体,唉,有用吗?掩耳盗铃。闯过了这次鬼门关,后来谈论起产房里有男医生这事时,朋友们的说法是,正常得很。医生眼里不分男病号女病号,他们只关心打针、动刀的具体部位。
无影灯的银粉纷纷飘落,无声无息,我安静下来,平躺到手术台上。“这位准妈妈,刚才还号啕大哭呢。”小护士悄悄地说,然后是偷笑声。几位年轻的医生指着我的肚子,问东问西,比比画画,主刀的正是刚才那位走路如风的王医生,在跟他们讲解着什么,都是我听不太懂的专业术语。我闭上眼,任满脑子白光流曳。
上半身和下半身被白围帘隔开,麻药注入了腰椎,很快,下半身似乎不存在了。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一会儿,听见主刀医生跟旁边的实习医生说:“你看她这个肚子特别大,肚皮也有些厚,切开的时候……”她一边解释着,一边动了手术刀,肚皮割开了,我没有感觉出一丝疼痛;紧接着是“哗啦哗啦”的水声,不知道是羊水还是血水。一阵“叮叮当当”手术刀、手术剪碰撞的声音过后,一名小护士喊:“出来了,出来了,怎么长这样啊!”我一听,心凉了半截,孩子什么样?不一会儿,只听“哇”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传进了耳朵,那位麻醉医生笑道:“听这声,这孩子劲儿不小!”
医生一边给我缝合伤口,一边还给实习医生讲解着如何下针。孩子呱呱落地,可我的心还悬着。
我动也动不了,被裹起来抬上担架车。终于回到病房,大家又一阵手忙脚乱,把我安置到病床上。爱人安顿好我,两只大手摸向襁褓:“儿子,睁开眼,叫爸爸!”他笑得乐开了花,婆婆的目光也不离婴儿左右,咯咯地笑个不住:“刚生下来咋会叫爸爸嘛!俺又添孙子喽!”
我在医院的两天一夜中,母亲没吃一口饭,坐立不安。孩子生了,父母也坐车到了。母亲心疼地念叨:“你说说,生个孩子差点要了闺女的命啊,好好的,挨了一刀!”父亲心疼地到床边给我掖被角,不小心碰着了输液的管线,我“哎哟”一声,母亲嗔怪道:“你快离远点儿,笨手笨脚的,别碰疼了闺女!”我的父母,他们只担心我的身体。
麻药的效力还在,我翻不了身,一直牵挂孩子是否健全,想看看孩子什么样。婆婆连忙抱过孩子,说:“好着呢,好着呢!刚才睁开眼了,看着随你,就是个小小红啊!”爱人帮我戴上眼镜,我吃力地侧头瞅了瞅,襁褓中是小小的他:脑袋身子很协调,肉嘟嘟的小脸,小嘴巴咕嘟着,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投降似的靠紧耳边,似乎睡着了。“怪不得小护士笑,原来这么难看啊……”我还没说完,母亲抢过话儿:“你们年轻人啥也不懂啊!老话说,月窝里的孩子丑过驴。这小家伙可不丑,眉眼这么清秀,这就是好看的孩子了!”
我和爱人结婚后,受下海风潮影响,他一展翅膀,从山东飞去深圳打拼。半年后,我也办好停薪留职手续,追赶他的脚步。本来我们打算在深圳闯一闯,创下一番事业,没承想,久别重逢的甜蜜过后,我就怀了宝宝。到底是创业还是要孩子呢?这是个大问题。在此之前,我曾经怀过一次孕,那时新婚晏尔,不懂如何避孕,我却不想那么早要小孩,没经爱人和家人同意,自己去医院把孩子拿掉了。过后婆婆埋怨,爱人不高兴,母亲怪我不懂事,我也懊悔不已,但为时已晚。这次我不敢再私自决定了,我们去问在深圳一家医院当儿科医生的舅妈,她说我这种情况必须得要孩子,否则容易滑胎。她举出表嫂的例子,表嫂就是因为流产伤了身体,迟迟未能再怀孕。
带着深深的遗憾,我由深圳飞回山东。腹中的宝宝,乖巧温和,妊娠反应也不剧烈,我胃口大开,能吃能喝,孕肚日渐明显。我孕前不足100斤,到孕后期猛增至140多斤,同事笑称我光有横,没有竖,越来越像个圆球。原来的衣服压进箱底,我穿上姐姐怀孕时穿的外套,要多夸张有多夸张,脸也越来越臃肿,真是丑极了。我不敢照镜子,不敢看自己一塌糊涂的样子。我曾是学校年轻女教师穿着的时尚标杆呀:春天粉色及腰夹克、藏青色阔腿裙裤,夏天一身紫色碎花连衣裙,秋天大八片收腰方格风衣,同事们都叫我时装模特儿。学生、同事羡慕的目光时时令我骄傲。
丑就丑吧,平安就好,可妊娠期到五个多月时,一件突发的事又让我处在了担惊受怕中:当时我住在单位分的婚房里——一种筒子式的平房,电线线路很老了。一次,在用电热器烧水时,不知哪里漏电,我的手猛地被电流震开,身子趔趄到一边,差点摔倒,头似乎要炸裂,回过神来,我想的是,坏了,会不会影响到胎儿?会不会生一个不健全的孩子?我从此有了心病,查阅了一些书籍资料,看到导致畸形的种种实例,虽没有关于这事的任何资料,可仍默默忧心。我没有跟父母及婆家人说这件事,怕他们大惊小怪,更怕他们也跟着担忧。我时时关注自己的肚子,时时与胎儿对话:宝贝,要好好的,老天保佑你。第六个月,我去做了彩超,虽然医生诊断胎儿发育正常,我心头压着的石头却还放不下,夜里常被噩梦吓醒。怀孕第七个月时,我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爱人只好辞掉了深圳的工作,飞回我身边。深圳到山东,几千里的距离,阻断了他创业的梦想。他是落寞的,因为外出的闯荡失败了。看到我逐渐笨重的身子,看到胎儿的胎动,他才逐渐快乐起来,常常趴在一边与它对话,给它听优美的胎教音乐。可我心底的秘密却不敢告诉他,我如履薄冰,害怕胎儿会有一点点、一丝丝不好的症状。现在终于确定孩子是个健全健康的婴儿,我一歪身子酣然睡去。
我醒来时已是下午。时值五月初,雨后的天空如一块蓝宝石,晶莹璀璨,阳光温柔地斜射进了病房,对面的院墙边,挺拔的梧桐树新绿盎然,蔷薇枝叶扶疏,正在开启一场盛大的花事。多么美的春光啊。我寻找着孩子的笑脸,忽然想到傅天琳的诗《我的孩子》中的诗句:我的盛开的花朵/我的蓓蕾/我的刚刚露脸的小叶子/你听见妈妈的呼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