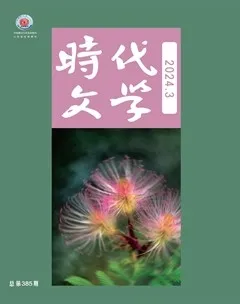张哲,你还在骑车吗
我跟张哲见面的次数不算多,有一次吃饭的时候闲聊,她说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婆媳关系,并在结束这话前跟进一句,真的。
“婆媳是天敌”的说法,似乎早已给这层关系下了定论,也就是说不管怎样,这种天生对立的关系,从古至今都是无解的。我即刻想到了近期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笑话,问她,你知道奶奶为什么一般都挺喜欢孙媳妇的吗?等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我才说出下半句话,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张哲意识到,这个玩笑其实是在质疑她刚刚说的那句话的真实性。但是她却认真地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崇拜我的婆婆,对她为这个家的付出表示由衷地欣赏。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张哲在生活中比我经历得多,我尚且还没有涉及,或者具备成立家庭所需的复杂与智慧。张哲却仿佛能在这些荆棘丛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来,并慢慢地游刃有余地走在上面。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我说起这个话题。这让我想起张哲的小说,母女关系之间的缠绕与盘根错节,是她小说中的叩问之一,而婆媳关系也是从这类主题中衍生而出。她发表在《十月》上的《观山海》,足以证明母女之间的纠葛与原谅。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张哲和我要去鲁院的高研班改稿。我们相约在一家螺蛳粉店一同吃了午饭后去教室,她很早就到了,我能感觉到她的准时不仅仅是出于对时间的把控和与我的约定,还出于对那碗螺蛳粉的兴趣。
我还在车上,她就发来截图问我要吃什么她先点上,我到了就可以直接吃了。果然,我到了以后,两碗热腾腾的螺蛳粉就端了上来。她像个小孩子一样拆开一次性筷子的塑料包装,两根筷子拿在手里互相搓了搓,把木屑清理干净后,便开始夹起上面的酸菜,然后说,我好久没来吃这家螺蛳粉了,每次过来我都一定要在这儿吃。她把一种原本熟悉的环境表达得好像很陌生,她看了看周围,补充说,所以,不知道这家还是不是原来的老板。
对我来说,一家喜欢的店铺从来就是想去就去说走就走。我问她,有孩子就不能出门了?不能就把他放在家里,然后你自己出来吃螺蛳粉吗?张哲摇摇头,好像原谅了我并不理解作为母亲的辛苦。
记得上次见她时,她说要开家长会,她还从没有去开过家长会,对第一次开家长会这件事感到紧张。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基本没去参加过我的家长会,去参加的总是姥姥,也幸好是姥姥,我只需要含着眼泪对她说一句,姥姥,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我妈妈?我下学期会努力的。所以分数以及在学校的各种调皮捣蛋,到姥姥那儿也就终止了。
隔辈参与到孩子的养育之中在国外并不常见,在国内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张哲家似乎也不例外,但她没有完全放手不管,她依旧在紧凑的时间里,竭尽所能地塞满她对儿子的关心和爱护。好像把她小时候所经历的一切缺失,都补充进了她与儿子的关系之中,对儿子的一切事情,也是尽力做到亲力亲为。
饭后,她和我从店里走出来,那是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冬天,北方很久没有连着下好几场这么大的雪了。我们俩牵着手,在冻雪上像企鹅般小心翼翼地行走。铲雪的义工在路上扫出了一条只够一人行走的小路,我让她先走,跟在后面问,你后悔生小孩吗?我感觉生完小孩,你的全部时间都被占用了,你每次说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好不自由。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
你后悔选择要孩子吗?
这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吗?我不知道。但似乎没有人会回答不,一个“不”字,意味着否定一个生命的存在,以及对“已经成为母亲”这个事实的挣扎与诋毁。
她似乎对我的问题并没有感到惊讶,也并没有回过头来看我。她说,如果能再选一次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要孩子。她停下来,站在雪道的尽头等我。然后她说,从一开始,我就被灌输了顺产、母乳喂养的观念。每天都有人给你讲这些事情,然后你就感到这是你必须选择的道路,你1211a084354381f5b0d015f6b60364787459aa2fccd3c5d7788dd5f4e451a4cf觉得应该这么做。她捋了捋背包的肩带,又挽着我的手继续说,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将来到底要不要孩子。
我笑了笑,告诉她我还没成家呢,暂时不用想这么多。她也笑了笑说,也对,你现在就好好玩,不然以后就没有时间玩了。
女性从青年步入中年的一大特征,或许就是将话题从学业和工作的重心,渐渐转向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生育、家庭、孩子、教育。张哲是我认识的写作者中为数不多的,持续创作同时又承担着养育幼童责任的母亲。
每次见到她,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聊起生活中的琐碎,写作、文学或者编辑工作反而寥寥。她为我打开了一个时间的窗口,让我好像看到了还未经历之事的艰辛与复杂,当然其中还掺杂着不少欣慰与惊喜。每次交谈的时间、空间里,仿佛都充盈着我们作为女性,在面对生活的种种经历时的尴尬与无所适从。我们的交谈从夏天转向冬天,又从冬天走向了春天,而我和她到今年已经认识了三年。
第一次相识,是在2021年5月,那时我们共同参加了老舍文学院与北大合办的第一届骨干作家研修班。她带着没有明显边框的眼镜,丰盈的中长发在北大初夏的风中微微拂动。她主动跟我打了招呼,我是《北京文学》的张哲。
或许是因为同行的缘故,我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即使话题从来不是工作相关的内容。她似乎热爱散步,喜爱放学后在北大的校园里探索。有时在阳光下,她会戴着一顶遮阳帽,还穿着白色的衬衣,然后你看着她的时候,她就会望着你,温柔地喊出你的名字。
我们这个班是老舍文学院第一次与北大文学院合办研修班,也是唯一一次。我们被安排在一家离北大并不算太远的宾馆入住。那个班里大多都是北京人,张哲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刚毕业回国参加工作三年,对这种上课的体验并未感到大惊小怪,甚至有时还会因为起不来床而错过几节课。当班上的同学每次说起上班后还能回到学校做学生的感觉真好的时候,我并不能够体会此话的含义。
每当这时候,张哲就会附和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摆脱孩子的生活了,出来上课让她有了合适的借口,暂时卸下带孩子、接孩子的任务。她感到放松、快乐,同时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这种自由的向往的一些自责和惭愧。
去年十二月见她,似乎因为孩子长大了,她松弛了一些。我问她,现在是你接孩子放学吗?你上班怎么接?她大笑说,我给他报了两个课外班,上完我正好下班接他放学。她仿佛在生活里找到了某种绝妙的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方法。
有一天下午,我们没有安排上课,与我同住的同学回家看望小孩去了。我一个人骑车去附近的理发店剪完头发,回来已是傍晚,正好碰见从外面回来的张哲。她问我要不要去她屋里坐坐,她一边从口袋里摸出房卡一边表示,听与我同住的同学说起过,我一个人住酒店有点害怕,她便说我可以晚上到她房间睡。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她小时候的事,很细碎,除了星座之外,我已不记得其他具体的细节。接着,她起身去启动热水壶的按钮烧水,并拔下正在充电的手机,开始听罗翔的讲座,那个晚上我们是在罗翔讲课的声音中入睡的。
从宾馆到教室步行大概要三十分钟,如果骑共享单车的话,只需要十五分钟。我们每天早上都去扫共享自行车,追逐前面的同学,然后从同学的身旁超过,回过头微微一笑揶揄地说,你怎么骑得这么慢?然后大笑着继续快速地蹬车,那应该是我在那段时间里最珍贵的瞬间。下了课,我们又成群结队乱哄哄地去食堂排队。
那天在张哲屋里睡了一晚之后,我感觉和她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们从同学变成了朋友。后来我发现,我从未在这些排列还算整齐的共享单车车队里发现过张哲的身影。某次下课后闲聊才知道,张哲竟然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每天她都会早早地起床洗漱,然后提前半小时就步行出发,中午也没办法回酒店午睡,因为中午除去吃饭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走过去再走回来时间刚刚够,所以她中午的时候都回教室休息。
走近了意味着产生了感情,产生了感情就不得不做出牺牲,我开始放弃骑自行车,每天和她一起走路往返。她对此感到十分不好意思,每次都对我们说,你们先骑车走吧,别管我了,我慢慢走过去。
后来我发现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我总因为没有午休导致下午的课经常昏昏欲睡,我便提出以后中午休息时教她骑自行车。她对这个提议似乎有点迟疑,但碍于我的热情,便答应下来。
那天中午,我给她弄了一辆共享自行车,基本上没有教她任何技巧,就告诉她车往哪边歪,车头就往相反的方向转。我告诉她最大的技巧就是,摔几次就学会了。
每个骑车的中午,我常常想起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的间奏曲,恍惚间,我总觉得她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年轻时光脚骑车的片段,她也在初夏的某个蝉鸣的中午,光脚在北大文学院在那个空旷寂静的院子里来回骑着自行车,独自享受着脚底与踏板之间的触感,那种从内心升起的由衷的像孩子般的快乐,那种不用想到自己还得回家做饭带孩子的轻松感,让我也沉浸在莫名的轻松与快乐之中。
我们之后再也没有练习过骑车。好像这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不想再尝试不想再提起的秘密。也不知道后来张哲有没有再想起学骑车的经历,或者她有没有再尝试去学习骑车,所以,有没有人能回答我,她现在到底学会骑车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