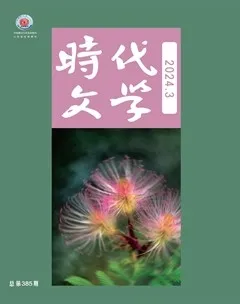万物生琉璃:厮杀、互悯背后的苍凉
读完张哲的十几篇小说,我感觉内心情绪满溢,无数女性形象在眼前飘荡,她们以其强悍丰饶,以其互相间的厮杀与怜悯,以其种种失败、不堪的命运,让读者既被她们的力量震动,为她们徒劳的挣扎叹息,又由她们于一切失败之后对世事苍凉的感悟而获启示。张哲写出了多样的女性形象,写出了人不断挣扎又不断失败的命运;继张爱玲之后,写出了强力女性在厮杀、互悯背后的苍凉,进一步走向了“万物生琉璃”的澄澈境界。
互相折磨又彼此慰藉的情感联系
在张哲的小说中,《山顶上的雪》是比较特别的一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我”父亲在离家很远的畜牧站因煤气中毒而死,并且,当晚,由县畜牧站来的肖师傅也宿在该畜牧站,两人一起死亡。之后,肖师傅的遗孀便不时长途跋涉,来“我”家所在的村庄拜访。她一次次来,并未开口问过其丈夫的死因,似也不带什么怨怼,仿佛只是过来转转,有时还帮“我”母亲洗几件家里人的衣服。她任由村里人对她的到来充满疑虑,这些疑虑最终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到“我”家人的头上。某一天,遗孀带来了独生子,小孩间将话说开,两个死去丈夫的女人终于开口回溯往事,并试图互相慰藉。此次交谈后,这个女人再未来过。
因为小说只需要呈现它必须呈现的那一部分就足够了。这呈现的一部分,是肖师傅的遗孀第一次登门,鞋子被泥水浸透了,去河边洗脚的细节;是在一次次沉默的拜访之后,“雪水湿润了山背,迎来了女人和她的儿子昆宝”。当外乡女人带来她的独子,读者便明白,她已经彻底原谅和放下,要带着自己存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家人与“我”的家庭相见了。这里,读者亦如“雪水湿润了山背”,感受到无须说出的暖意。
而外村女人一次一次地来,她后来提及,孩子在她回去时第一句话总是:“妈妈,问了吗?”从中读者明白,她并非是要将命运的不公抱怨在“我”一家身上,并非是用无声的方式来制裁,而是内心的伤痛让她胆怯地不敢开口来问,只敢于在静默中一次一次来此,寻求某种安慰。
这些幽微复杂的情绪,张哲处理得十分出色。不需要写的部分,哪怕也许是让事件因果更清晰的相关线索,她也果断地让其隐形,显现出张哲对于材料剪裁的高明。而需要写的部分,即两个女人间隐约的、既互相折磨又彼此慰藉的情感联系,她通过整个小说,处理得温润含蓄,令人难忘。
小说里有很多充满灵感的细节,譬如女人在被问到自家孩子有多大时,“瞧瞧不远处的二弟”,说“跟他差不多大”。只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跟他差不多大”,就让二弟“被点了名,颇得意,又不自在”,还像献宝一样向女人展示他捡到的铁片。这一细节,对小孩子的心理把握相当准确。
再如,“火舌跳动,二弟用冰块喂着火,火瞬间就灭下去,冰块化了,不多时火又蹿了出来,锅子周围愈来愈热,羊肉缩成了一块块,硬得跟燧石一样”,这里,“用冰块喂着火”的表达,新鲜特别。几个句子便在读者眼前勾画出煮羊肉的鲜活画面。
张哲还特别用心地使用了隐喻手法:“山顶上还有一层积雪,亮亮地闪着,如同凝固了的蜡油,被时间锁在了冬天。温度升了,雪一点一点地融化,露出土地的颜色,太阳照在上面,像锦缎上针脚的暗影。”
这一段景物描写在悄悄地点题。小说题目是“山顶上的雪”,“被时间锁在冬天”的雪象征着两家人各自沉溺在痛苦中,以及两家人之间如坚冰一样难以融化的隔膜。而“温度升了,雪一点一点地融化”暗示出,随着女人一次次到访,两家人的关系在松动,在渐渐升温。“锦缎上针脚的暗影”很好地隐喻了两家人在这一段交往中,那种既互相折磨又彼此温暖的关系,为抽象的情感关系找到了一个非常具体、妥帖的隐喻意象。
在后文,张哲写道:“终于出了太阳,雪停了,太阳把坚硬的山烤成了胶状的、絮状的、水状的,雪水湿润了山背,迎来了女人和她的儿子昆宝”从这一段,我们也感觉到化雪的温暖,再次感受到张哲使用隐喻、赋予抽象的情感以具体形象的魔力。
万物生琉璃:厮杀、互悯背后的苍凉
张哲的小说里塑造了多个富有意味的女性形象,她们彼此厮杀,又相互怜悯。这些厮杀与互悯的故事不仅生动细腻,背后还充溢着看透世事人情的苍凉,并进一步走向“万物生琉璃”的澄澈之境。
1.母女关系:激烈的开局
女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最亲密的可能便是母女关系了。张哲很多小说的核心是在处理母女关系。较早发表的《一个椭圆的,分离的元音》里的前三篇小说,即《清洁日》《热气球》《游乐场》中,母女冲突十分激烈。到了后来的小说《观山海》,母女关系在更加平和、日常的洪流中显现。
《清洁日》《热气球》《游乐场》中的女性人物,往往有一个特征鲜明的西式名字,如《清洁日》中的玛丽娜、格蕾丝,《热气球》中的“法兰绒母女”,《游乐场》中的桃瑞斯。也许正是因为西式的名字造成了某种距离感,便于张哲在小说虚构中,将关系的冲突推至某种极端状态。叙事者不带感情波动的叙述,凸显出人物关系的冷漠。几篇小说里,造成主人公冷漠的很大原因是,母亲在女儿年幼时,刻意树立了另一个孩子为“优秀的”“出类拔萃的”榜样,这不仅是为了激起女儿的嫉妒和焦虑,其深层的动机往往是某种权力意志的体现。在母亲可以掌控一切的年纪,女儿受到难以磨灭的伤害;那么,当女儿长大成人、开始具有力量的时候,母亲的衰老也难以激起女儿的任何同情。
《清洁日》里,已成年的女儿揭露出,母亲当年每每称道的格蕾丝其实有偷盗的习惯,并以自己的随同犯罪向母亲示威,力图推倒母亲当年树立的“优秀榜样”,更不惜以自己之罪昭示母亲的失败——判断力的失败,与教育女儿的失败。作者写道:“三十多年来她就是靠着这个秘密支撑到现在,她以为只要这个秘密脱口而出,母女之间的较量就能被颠覆。”这里提到的“秘密”,便是格蕾丝其实屡屡偷盗、品格有亏的事实。但时隔多年,也许因为过往已无法挽回,也许因为母亲不愿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玛丽娜的复仇遭遇了“无物之阵”,在母亲“你不要再说了”的直白拒绝面前,继续遭遇从小感受到的羞辱、委屈与失败。不过,小说情节继续行进,当一个陌生男人对玛丽娜造成威胁时,母亲拖着残疾之躯不顾一切冲来保护女儿。虽然最终与女儿有了“共同的秘密”,母女关系却依然疏离、客气。小说最后写到母亲离去,钢铁双拐敲击地面“一声又一声密得透不过气”,从声音的角度隐喻出,母女关系依然对峙。而双拐敲击的声音“清脆,洪亮,振聋发聩,甚至让人发狂嫉妒了”,这里突然出现的“甚至让人发狂嫉妒”意味深长,究竟女儿是在嫉妒母亲那种永远冷静的力量感,还是在嫉妒钢铁双拐反而与母亲更亲近?这都是在理解上可以延伸的方向。这便在母女对峙的关系中又融入了相互亲近、怜悯的因素,张哲对于亲密关系的极端状态的把握,独特而新颖。
《清洁日》的姊妹篇《游乐场》里,同样有一个漂亮、优秀的“另一个孩子”的形象,她名叫安。这个小说里,更冷酷的是,桃瑞斯的母亲以怂恿的方式,激起安的虚荣心,令她一次次挑战危险的游戏,最终酿成事故。而母女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了某种既对立又共谋的关系。对立之处在于,母亲借“另一个孩子”激起女儿的好胜心、竞争欲,同时掌控桃瑞斯和安的情绪;共谋在于,当女儿发现事态正滑向不可遏止的悲剧时,母女二人都默许了事态的发展,合力让一个美丽的“瓷器”摔得粉碎。
从这最初的几篇小说可以感觉到,张哲尽力写出人性幽微、不可臆测的暗面,撼动几乎是最不可动摇的母女关系的边界。从这些貌似冷酷的小说中,读者能感觉到,如此冷漠的表达与表现其实都只是表象,事实是,母女如紧密扭缠的两股绳索,彼此是对方最关切的所在,所以每一次受伤才会如此沉重、如此难以消化。小说文字的实验性也很强,多用短句;叙事者往往用感触、直觉来呈现一个场景或人物动作;句与句之间有较多的跳跃和留白……形式上的探索,同样指向张哲对于人物情感边界的探察。
到了《观山海》,母女关系在更为日常的情境中显现:母女一次同去寺庙的闲游,勾起二人多年相处的往事。母亲在工作上过于强势,“她的胜负欲和事业心,她的边缘化和被排挤”,令女儿不知不觉就在青少年时期吃了很多亏、女儿对此是有埋怨的;同时,在女儿的观察中,母亲确实也多次为她而牺牲了自己的出游、对生活的享受等,女儿因此也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母女俩同到寺院,问及寺中人起居、出家经历的谈话,无形中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松动、回暖。张哲以细致缜密的心理感受、精彩的情节和细节,让小说人物酝酿了几十年的甘苦酸辛汹涌澎湃而出,深深地触动读者。
2.强力女性的厮杀与互悯
张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极强有力的。像《快乐王子》中对孩子的学前教育极度上心的冯静果,《春海》中欲望翻腾的查玲,《二手玫瑰》中极力要在儿媳梁月前挣面子的白玉贞,《金花》里的主妇陈茉与月嫂冯金花,《鲣》中的李鸳和“我”,《四重奏》中隐隐较量的四个女人,《共生的骨头》中常与妹妹比较的何依依,《织火焰的手》中的妹妹……她们聪慧,尽力挣扎索取有限的资源,更时时存着与周围掐尖的人比较的心思。这种比较,与其说是一种想要超越对方的发愿,不如说是一种怕自己落队而不得不做的挣扎,即使胜利了,也依然充满焦灼,因为永远会有下一个强悍的对手出现。
小说《春海》里写到一群红鹦鹉鱼,可以看作对某种强悍的生命力的隐喻:
这批鱼的生命力异常顽强,战斗力也不差。从前这里还有几条清道夫……清道夫全军覆没,这些红鹦鹉是真凶,鱼尾如飞溅的雨点,在为胜利引吭高歌,疯狂舞蹈,引得查玲看入了神。战争还在继续,只是愈加的诡秘,其他物种都被吃光了,红鹦鹉开始同类间的弱肉强食,弱小者被强大者吞噬,查玲要是忘了投食,过几天一数准少几只,剩下的都是成了精的,不好惹的。
原来,仰一口水而活、家养的观赏鱼也可以是“不好惹”的,因为血肉厮杀过。这段明面上写鱼,同样是在隐喻小说中女性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战斗力。小说里,查玲原本想舍弃这些鱼,未必不是在财务自由后想过一种躺平的生活,但小说结尾,“鱼缸被洗刷一新,又养了两周的水。查玲要像迎接盛装而来的新娘一样,把那群虽然老迈但斗志昂扬的红鹦鹉迎接回来”,这里,这些“老迈但斗志昂扬的红鹦鹉”正是对于在情海沉浮、厮杀了一番而得胜的查玲的隐喻。
小说《四重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你说这混血小孩长得还真是好看。’广禄脱口而出,焕英没搭茬,把手机收了回去,举起眼前的铁观音咕嘟咕嘟喝了三大口。”这里说到的混血小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四个女人里,金力的孙女。因为杜焕英常常向人夸耀自己的孙子,所以听到对金力孙女的夸奖时,她不搭茬,“举起眼前的铁观音咕嘟咕嘟喝了三大口”,何尝不是将一肚子的不服气咽下去?再比如,梁广禄对抗别人嚼舌根的办法是:挣自己的奢侈品,“让身边的人恨得牙痒痒”。这些“心气比谁都高”“要活得精彩”的女人,是张哲小说里的核心女性形象。
小说《金花》,将女性之间的厮杀与互悯展开得十分充分。小说里,主妇陈茉生了宝宝,因为丈夫忙于工作,自己也缺乏护理孩子、将养身体的经验,不得已,请了一位“金牌月嫂”——冯金花来帮助打理。金花靠自己的勤勉、能干,渐渐得到陈茉的信任和好感,也帮陈茉把家里归置得像样起来。
然而,人性的复杂在于,明明陈茉已经信任了金花,却也在金花单独带孩子外出晒太阳的下午失魂落魄地下楼寻找;明明于了解逐渐加深后,陈茉在某一个瞬间吐出了“金花,我想让你一直留在我家,像家人一样”的温暖言词,却在婴儿照百日照时,因婴儿对待她俩亲疏有区别,陈茉感觉失了面子,对金花生出嫉妒和嫌隙。在这当口,金花遇到前夫来纠缠,陈茉一家选择了冷漠地回避;待金花离开后,不多时,被其辛劳照顾的孩子完全将她忘记了——这在陈茉心里再次激起波澜,因为,假以时日,她又如何保证自己不会遭到如金花般被遗忘的下场呢?《金花》这篇小说里,两个女人之间的厮杀,以及一次次互悯又再次厮杀的情节,被张哲写得曲折、丰富、生动。
3.哀悯何时来到
这便提出一个问题:厮杀之后,互相的怜悯、同情何时来到?阅读过小说的读者不难得出结论:哀悯在失败的时刻便会来到。哀悯会在对方失败时来到,也会在自己失败时来到。
像《四重奏》里四位同村、又一同搬到城南的女性,郭姐、广禄、焕英、金力,前三位一直羡慕远在澳大利亚带孙女的金力,多少有点暗暗较劲的意思,却在得知金力患有乳腺癌、时日无多的情况下,隔阂涣然冰释。在金力谈到自己带病为女儿、女婿、孙女做意大利面时,郭姐“第一次对金力所描绘的美好生活产生了共情”,能共情的原因是:金力马上要死了。否则,四个女人间的暗暗较劲会一直继续下去。如今,金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再也不具备与前三者一起比较的资格,这激起了同伴深深的同情。绝对的失败激起绝对的同情,是不是很有讽刺性?就这样,张哲将人性深处的嫉妒揭示得深刻。
《二手玫瑰》里,婆婆一次次想在儿媳妇面前撑场面,却仿佛遭遇命运的诅咒一般,不断陷入被轻蔑、忽视的境地,可笑又可怜。婆婆故意将“成功人士”的来电外放,想在媳妇面前炫耀,却因对方的辞令并不恭敬而急急关掉免提。婆婆一次次颜面扫地的尴尬,现出世情的真相。在人物的自我认知与事实真相“大裂”时,张哲以冷峻的笔触将人物厮杀背后苍凉的意味深切地揭示出来。一个个心高气傲的女子的尴尬、不体面被定型,张哲的文字称得上“稳、准、狠”,仿佛清晰度极高的照片,而其底色是苍凉。
当小说里的“我”失败时,张哲的文字充满自嘲。小说《鲣》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在金台夕照附近找了一间出租屋,木板和毛玻璃把我和另两对合租的小情侣分隔开……我反锁着门,一个人和衣躺在房间里,月光照进屋里,仿佛灌进半屋的水,我所有的家当,不外乎两麻袋的东西,此刻也裹上了银霜,此情此景不禁令我大恸,好一个万物生琉璃。
《鲣》里,“我”为带孩子而放弃了工作,做了多年全职主妇,又在丈夫张旋出轨后被迫离婚,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还被丈夫讥笑说:“你和李鸳都不是什么好鸟,难怪你俩是好姐妹,臭韭菜不打捆。”按说此时“我”应是万念俱灰、心神俱碎,而张哲却写“我”困处于狭小的出租屋里:“此情此景不禁令我大恸,好一个万物生琉璃。”当月光灌入出租屋,“不外乎两麻袋”的家当,在张哲笔下竟催生出了“万物生琉璃”的意境……好一个澄澈之境!诗句的原意与此处语境之间的差距让这个隐喻熠熠生辉,充满清澈又苍凉的悲哀。
这种澄澈,是意境的澄澈,也是神魂的澄澈。在“我”与李鸳完全的失败状态中,“我”洗去了比较的焦灼,毫无对李鸳可能经济犯罪的责怪,只留有对李鸳境况的担心。这是最高境界的互悯。也正因这互悯和自嘲,张哲的小说在厮杀的背后,写出了苍凉与悲壮。因为每个人都尽力拼搏,而拼搏的结果又注定失败,人总要由精力充沛的壮年走向老年,失败不可避免。挣扎越剧烈,无非是让结果更令人唏嘘、更惨烈而已。这就像《红楼梦》,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后,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也就是张哲的“万物生琉璃”。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琉璃”这个意象,既有易碎感,又是《法华经》所说的佛教七宝之一,代表清净和光明。用这个意象来概括张哲小说中有着强悍生命力的女性,在厮杀、互悯之后,达到透悟世情、放下执念的状态,是很合适的。当下,写女性的作品不少,而能写至“万物生琉璃”的境界,是张哲的小说引发众多关注的原因。
强悍生命力的表现之一:欲望
回到“强悍的生命力”,它可能的表现之一,是女性的欲望。张哲的小说《春海》显现出作者对女性欲望的集中思考。小说写一个丧夫的中年女性查玲,如何将丈夫遗下的钱财牢牢攥在手中,并于一次游泳中,对年轻的游泳教练谢淼动了心,以及这之后欲望翻涌的种种表现。
在小说《春海》里,新生的“婵阿姨”查玲的行动突破了人物心理层面的范围,一步步展开欲望的具体表现。查玲在与谢淼的情感交手中有试探、有观察,最终刹了车,遏制了欲望。
小说里,张哲摹写查玲欲望的方式很有趣,是用隐喻将查玲的欲望投射到一件件衣服上:
冬日里,春海拉着查玲去厂里的商店置办冬衣……查玲选的是一件苔绿色的羊皮大衣,领口织着一圈蓬松的芥子色毛领,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春海撺掇查玲穿上看看,套在身上衬得查玲柔枝嫩条,毛领子仿佛夏日里茂盛的合欢花。还是拤腰的呢,查玲嘴角兜着笑,手无处安放,在皮子上一阵摩挲。
读这段文字,可以深切体会到,此处查玲选中的衣服,与她本人达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此时,衣服即人,人即衣服。这苔绿色的羊皮大衣领口织着一圈蓬松的芥子色毛领,毛茸茸的,充满生机,很有触感。“套在身上衬得查玲柔枝嫩条”,这是关于年轻的查玲的隐喻,在衣服的隐喻上叠加一个关于植物的隐喻,“柔枝嫩条”,查玲的年轻以及欲望的欣欣向荣,都蕴含其中。“毛领子仿佛夏日里茂盛的合欢花”,继续叠加丰富的植物意象;“还是拤腰的呢”,衣服的新潮和苗条腰身,暗示出查玲的时尚感,以及身材的绰约……这同时也隐喻了查玲与丈夫春海生活的畅意。张哲善于使用隐喻,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春海死后,查玲在偶然中对谢淼动了心,并在一次看房过程中受到房屋中介小潘年轻的生命力的冲击,她忍不住翻检起自己当年的好看衣服:“一条白地水蓝条纹的连衣裙,小立领,扣子紧凑地铺到锁骨窝,没袖子,露出两条粉白的臂膀,裙裾飘摇,镶嵌着天青色的珠花绣片,转起圈来裙摆泛起一阵涟漪,那是春海从崇光百货给她买的,穿在身上宛如一个女学生。”读这段,这条连衣裙的式样,连带到相应身体部位的丰盈,装饰的繁复、色泽的清雅,令人应接不暇,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年轻、丰盛的美感。“穿在身上宛如一个女学生”,写出了查玲年轻时的美丽。而不出所料,经过岁月的腐蚀,“料子掺了丝,很娇气,受不住经年累月的重负,早被压得皱皱巴巴”,“裙子仿佛被抽去了魂魄,怎么看都不见当年的熠熠生辉”。这件连衣裙,与查玲同步感应,呈现出她此刻的状态,是已然年老、不复当年的青春了。“查玲仓促地剥开了纽扣”,这“仓促”两字,很好地写出了人物失望失落,害怕面对近于老境的自己的状态,传神又犀利。
接着,张哲直接写女性的身体触觉:
谢淼把双手递了过来,手很大,这和他的身高倒是协调,手指修长且白皙,每个指甲盖上还顶着一个月牙,指头的关节处很有骨感,衬得手指头愈发纤细而优雅,手掌铺开,淌下几滴水,仿佛绿意蓬蓬的睡莲。查玲爽利地把手伸了过去,手被攥得死死的,小小的拳头被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另一个男人的手掌中,这种感觉查玲第一次体会。一向高挑绰约的查玲居然可以玲珑小巧,她有点找不着北了。
“指头的关节处很有骨感,……手掌铺开,淌下几滴水,仿佛绿意蓬蓬的睡莲。”这里,张哲再次以植物来隐喻人物的姿态,“绿意蓬蓬的睡莲”,生机勃发又仿佛亟待被唤醒,再加上“淌下几滴水”的荡漾,仿佛是查玲贪婪吞食的眼睛,一寸寸地挪过谢淼的手,写活了查玲内心难以压抑的欲望。而小说最后,在对于彼此经济实力的考量中,男女主在情感中的优劣地位完全异位了。最终,查玲凭借经济上的绝对优势逃脱了被欲望吞噬的命运,她是胜利者。所以,她领回了那一缸弱肉强食的红鹦鹉鱼,隐喻着她将继续在经济和情感领域大杀四方。小说的逻辑是,稳固的经济实力护持了女性强悍的欲望(生命力)。
读到这里,我们也发现,张哲非常善于在小说中使用隐喻,譬如《虎头海雕和破冰船》中,简单的一句景物描写:“海被他们踩在脚下,乌绿色的海水不断翻滚,仿佛充沛的情欲和热望在眼皮子底下涌现。”好一片乌绿色的海水,又好一个“被他们踩在脚下”,女人的生命意志(欲望),借这一片海水传达得很到位。
苍凉中的幽默
正因为由厮杀、互悯,达到了“万物生琉璃”的高妙境界,所以,张哲不会在小说中困于人物的失败,而是由失败翻出光明,智慧的光得以通过,由此让叙事充满幽默感。在小说中,叙事者常常嘲人和自嘲,像《山顶上的雪》中这一段:
父亲熟悉牲口,又读过不少外面的书,他跟我说,生活在北极圈里的驯鹿人总是把鹿的耳朵豁开一块,叫打耳标。鹿的眼睛能记住给它打耳标的人的模样,从此那人就是它的主人了。我也照样子在羊的耳朵上豁口子,但那只羊用蹄子踢了我,它没有归顺我,反而对我多了份仇恨。
“我”照着父亲的教导行事,却易鹿为羊,结果“那只羊用蹄子踢了我,它没有归顺我,反而对我多了份仇恨”。我对于羊归顺我的痴心妄想,在它“反而对我多了份仇恨”的后果中,令人忍俊不禁。这里,“归顺”“仇恨”,一般情况下,都是特属于人的情感,张哲用于羊,便让羊充满了人情味。而且,有趣的是,“反而对我多了份仇恨”这句表达,如果直接写成“反而仇恨上了我”,幽默的意味就会大打折扣。“多了份仇恨”,意味着,这仇恨是多出来的、本不该有的,这反映出,直到叙述的时候,“我”还是很不甘心的,不甘心承受这“多出来”的仇恨,充满遗憾意味,这就更好笑了。短短九个字,不仅陈述了羊的感觉,还渗入了“我”遗憾又不甘心的感觉。同时,这一句如此自然,感觉应是张哲随手写出来的,并非经过刻意雕琢,这更显现出,幽默感是渗透在张哲小说骨子里的。
《观山海》中有一段对母亲的回忆:
终于到了她教我,上课回答问题她很少叫我,可想而知我学得不会太好,有一年期末,我数学考了64分,卷子的右上角多了三个字“大笨蛋”,字迹熟悉,我知道是她怒不可遏的冲动之作,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那个角撕了下来。
这个在卷子右上角批上“大笨蛋”的冲动之举,虽说怒不可遏,却也充满母女俩针锋相对的童趣,母亲的天真之气呼之欲出。
再如《金花》里写陈茉送初生的孩子去医院就医:
“国外都不给小孩输液。”陈茉知道自己的话挺招人烦,但她有点蓄意了,故意说些硌耳朵的话去挤压医生的忍耐力。“那你去国外治吧。”医生大梦初醒的样子,干脆撂下笔,看笑话似的瞅着陈茉怎么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医生大梦初醒的样子”是本段的笑点。可笑的地方在于,“大梦初醒”往往用来形容一个人懵懵懂懂的状态,却伴随着医生一句在语境中显得刻薄的“那你去国外治吧”,这就充满了讽刺意味。话语的内容,与说出这话的医生实际的心理状态,以及在叙事者口中医生仿佛表现出来的样子之间的歧异,体现出医生对病人不屑搭理、很嫌弃,而“大梦初醒”又仿佛憨态可掬,这就将医生与病人间的隔膜、不能苟同写得饶有趣味。
再如《四重奏》中引用的“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明代罗洪先《醒事诗》里的句子,在它的出处,它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是一致的,便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修行。而在新语境中,张哲赋予了这句诗以新意,重在表达“闲谈莫论人非”,是广禄希望知道她情感状态的人不要议论她“知三当三”。不仅如此,广禄还“反咬一口”,一本正经地让知情者“静坐常思己过”,由此获得了幽默效果:一种忌讳他人揭短,又故作正经、先发制人地教育起别人的口吻,令人觉得可笑有趣。
殊途同归、物极必反,由强力女性激烈的厮杀、纠结的互悯,最终走向“万物生琉璃”的彻悟,张哲的小说丰富生动,令人惊叹。正如《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琉璃世界”之生,可能需要经过万物的抵死纠磨、沸盈。张哲的小说,从万物中生出清净光明的琉璃世界,我相信,她之后的小说,必将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